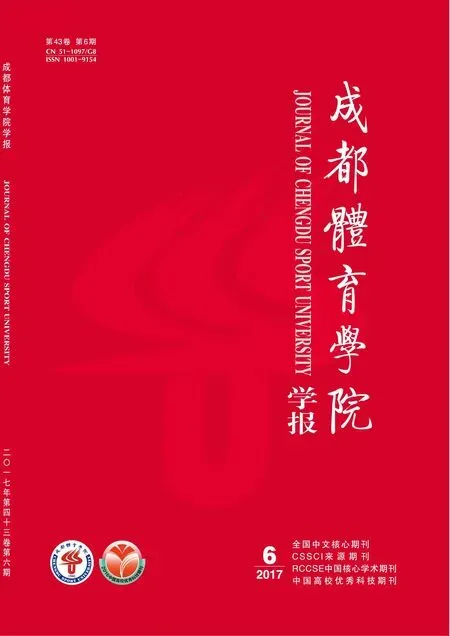仪式、记忆与认同:“三公下水操”中的身体运动研究
郭学松,王伯余,杨海晨,陈 萍,刘明云
仪式、记忆与认同:“三公下水操”中的身体运动研究
郭学松1,3,王伯余2,杨海晨3,陈 萍1,刘明云1
运用文本分析、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融合特纳仪式理论、族群理论等,基于福建珪塘“三公下水操”仪式中身体运动为研究样本,对历史记忆、身体运动及族群认同之间的相互逻辑进行探究。认为,乡土社会仪式中身体运动的展演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保持与传递功能;在身体运动呈现历史记忆的现实场域中,始发性历史记忆勾勒出民间乡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源起,建构性历史记忆强化了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的现实“结构与反结构”升华了身体运动象征内涵;在历史情景再现的场域中,论证了历史记忆、身体运动及族群认同三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逻辑。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乡土仪式;身体运动;仪式体育
马克思(Karl Marx)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随心所欲地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1]在中华民族的民间社会中,诸多民间体育是人们过去生活的社会现象而逐渐形成,正如郭学松研究指出,民间体育文化历经中国农耕文化的洗礼,已经成为这种农耕文化的重要记忆,这种文化记忆的主体是身体运动。[2]诸如此类的身体运动所形成的源头往往与相关历史事件以及所烘托的历史人物息息相关,在岁月不断更迭中逐渐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 or Memory for the Past)被认为是以历史事件为记忆对象,在不断循环的记忆中记忆本身也成为历史。[3]这种被记忆的历史更多的以回忆的途径及其身体展演的方式呈现与传承,它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表述。因为,人们对当下现实的体验,更多是来自他们对过去的继承与认知,这种沿袭和体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现在而存在,而这种对过去的集体记忆更多的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4]特别是乡土社会中的祭祀仪式。这些乡土社会的祭祀仪式又通过身体运动的展演为重要的展现手段,来反映人们对他们心目中“历史事件”的记忆,虽然某些身体运动所展现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都是历史本相,或者更多的是一种传说,或者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这种身体操演中的历史记忆展示了他们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心性,同时,这种历史心性背后仍有一种值得解构心境。这正是本研究选取福建珪塘村“三公下水操”乡土仪式体育个案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从身体运动的模仿中体感与反思埋藏在他们族群文化之中的历史心性,尝试了解留下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5]这种隐藏的“文本”及“历史心性”的深度挖掘也为体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多元化思考方向。
为了实现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深度考察,课题组主要采用在非活动期间及活动期间深入调查的形式进行了3次实地考察。第1次考察为2014年7月12-16日的非活动期间的实地考察。在为期5天的实地考察中,对村落社会环境、活动场所、生活习俗、族群文化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并对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其他村民等进行了深度访谈,期间还查阅了圭塘村叶氏族谱等文献材料。第2次考察为2015年3月6-10日的仪式活动期间。本次考察重点对整个活动的仪式进行观察和记录,在活动中对活动参与者、组织者、村落民众等相关人士进行访谈。第3次实地考察为2016年2月20-26日的仪式活动期间。本次考察主要为了解答调研报告中存在的一些疑惑,同时,课题组相关成员还亲自参与其中的火把巡游(举火把)等仪式活动,体感参与式观察的心性。在3次实地考察中,课题组收集了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文字材料,共拍摄照片1 000多张,录制录像4个多小时,整理访谈录音300多分钟,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保障。
1 田野简述:珪塘村与“三公下水操”
1.1珪塘村简介
福建长泰县珪塘村始建于宋朝年间,叶氏族群认同开基始祖为叶棻,然“棻公生于仙游,宋宝祐年间(公元1254年)任长泰县尉”。[6]自叶棻开垦珪塘以来,该村就以叶氏一脉相传(近代以来也有一些其它姓氏的移民搬迁居于此地,但仅为极少一部分),是中国较为普遍的移民族群村落。该村所保存的叶氏开基祖先的居所,明代的大夫井、清代的双面井以及具有族群象征的叶氏“追远堂”大宗祠皆是珪塘叶氏族群认同的重要遗迹。在村落的变迁过程中,珪塘村又分衍为珪前和珪后两村(珪塘村常住人口1万余人,其中珪前村5 238人,珪后村4 896人),虽“三公下水操”仪式的活动地点是在珪后村,而现在人们所提及的““三公下水操””活动始终以“珪塘”冠名。正是因为珪塘村以叶氏族群为构建主体,缘于祖先尊崇的历史心性及移民的族群特征,促生了族群体育““三公下水操””代代相传的主体原因。

图1 珪塘“三公下水操”“水中犁神”现场
Figure1Sceneofthe"godplowinginwater"inSanGongXiaShuiCaoinGuitangVillage
1.2乡土社会仪式中的“三公下水操”
“三公下水操”活动是珪塘村每年春节期间(该仪式主要在正月十七晚展演)所举行的具有闽南地域风格的乡土仪式体育事项之一。整个仪式过程又分为“水中犁神”(每年的参与“水中犁神”的队伍在6~8队之间,一般要求井兜的两队和下井兜的一队每年必须参与,像庵子脚、后西、东厝、西贡埔、后壁埔等各派一队)和火把巡游(锦鳞村选取百余名火炬手,参与水中展演的火把照明及寻找陆秀夫的巡游环节)两个主体部分。“三公下水操”的整个仪式历经4个小时左右,其中,在半亩荒唐中的“水中犁神”(即将所要参与展演的神灵塑像放置在辇轿中,并加以固定,人们抬着装有神像的辇轿在水中做左右、上下、前后的摇曳运动)环节最具象征寓意。每年参与“水中犁神”的表演者被分为6~8组中,每组固定6人,他们抬着三公爷(陆秀夫)的“金身”辇轿(前后各安排1人,左右各安排2人),在数千观众的围观中,奔跑冲过“半亩荒唐”水池的小铁门,开始水中的“梨神”展演。在环绕水池“水中犁神”的展演过程中,参与者充分发挥臂力、肩力、腰力等之间的相互协调作用,通过上下左右托举、牵拉、按压等摇曳的形式,沿着水池的四壁运动*参与“水中犁神”的队伍,最低要求是环绕池塘四周运动3圈,但是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例如2016年的展演中,第3组出场的队员在四周群众的鼓舞下,共完成6圈的身体运动展演。据笔者分阶段计时,每圈的活动时间在3~6分钟不等,与参与人员的体力、观众需求产生的影响等有关。。在“水中犁神”的身体运动过程中,参与者协调用力,辇轿沉浮轮转,波涛汹涌,水花四溅,重新勾勒了当年“三公爷”陆秀夫背着宋帝赵昺跳海时,在水中继续与元军搏斗的场域境况,[7]整个“水中犁神”历时两小时左右(图1)。
在身体运动模仿的现实展演场域中,我们不仅体感到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场景震撼,而且也诠释了身体运动的特殊象征寓意。正是这种象征性身体运动的模仿特质,赋予了“三公下水操”之“水中犁神”特殊的社会意义,同时也表征了该仪式活动中身体运动的共性与特性。在“水中犁神”环节结束后,珪塘村叶氏民众抬着“三公爷”的神像,在百余名火把手及数千参与者的簇拥之下,重演了当年沿岸寻找陆秀夫等尸身的历史场景。在身体运动的循环展演中,历史记忆被一代一代的保存,历史人物精神被颂扬,悲壮的历史场景一次次的映入眼帘,村落族群体的历史心性不断被诠释,族群的凝聚与认同不断被强化。
2 历史记忆:身体运动的场域
2.1身体运动中历史记忆的初始
“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自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开始在珪塘村始创并传承,是该村每年族群祭祀之“九龙三公*这里的“三公”是指被称为“宋末三杰”中的陆秀夫,其中“大公”是指文天祥,“二公”是指张世杰,““三公下水操””活动源自于这3位忠贞扶宋的民族英雄之英雄事迹,特别是“三公”陆秀夫保宋抗元历史。庙会”的主体部分,在闽南、香港一带颇具影响力,其历史记忆可追溯到宋元“崖山海战”事件。公元1279年,宋左丞相陆秀夫及大将张世杰所率领的宋军在广东冈州(今新会)崖山与蒙古军进行了中国少见的大规模海战(相传宋元双方投入军队人数多达30余万),史称“崖山海战”。南宋战败,“宋末三杰”也在该事件中或后逐一遇难。根据“宋末三杰”的年龄排序,陆秀夫位列第三,于是纪念陆秀夫的““三公下水操””活动中的“三公”便由此而来。那么,为什么叶氏族人要开展这项仪式活动纪念异姓的陆秀夫呢?
南宋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珪塘村叶氏开基祖叶棻时任长泰县尉的职务,主要统管长泰县内的差役、治安、财税等工作事宜。身为宋朝官员的叶棻,对“宋末三杰”的抗元斗非常支持,并在粮饷筹备等方面积极响应,其长子叶耆也在山东威海卫因抵抗元兵入侵为国壮烈牺牲。[6]缘于先辈们的浩然正气以及与宋王朝所形成的附属关系,并由此而塑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从而激发了叶氏后人们的英雄祖先崇拜历史心性,并将这种历史心性通过一件重大的历史战争事件而与相关重要历史名人互相关联,由此假借战争之历史本相演绎出族群仪式体育活动,通过身体运动的展演形式来映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动态,珪塘村“三公下水操”仪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心性下而被建构和传承的。

图2历史记忆中寻找陆秀夫及赵昺的火把巡游“现实场景”
Figure2The"realscene"oftorchparadeseekingforLUXiu-fuandZHAOBingasinhistoricalmemory
在珪塘“三公下水操”之“水中犁神”的身体展演中,更加直观的展现了陆秀夫与元军搏斗的历史场景,历史记忆被展现和还原,历史心性与族群心态被诠释,族群边界被勾勒以及由此而隐含的族群社会认同、资源共享与竞争的社会现实被呈现,身体运动的“小历史”映照了中国乡土的“大社会”。在民众手持火炬寻找“三公爷”尸身的历史场域中,历史场景再一次浮现在眼前。(图2)“崖山海战”后的海面上所浮现的十余万具军士的尸体,展示了历史战争的悲惨,也反衬了今之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人们书写了历史,历史造就了现在,现在更是一部历史的“续集”。千余名群众在一百多名火把手*参加“寻找陆秀夫”的百余名火把人员是沿溪镇锦鳞村的叶氏族人。很荣幸,在2016年的仪式中,笔者通过协调与沟通,全程参与举火把巡游及5公里奔跑“寻找陆秀夫”的“历史现场”,在振聋发聩的烟花炮竹声中,真正体会到这种历史记忆所演绎出的无限魅力。的引领下,以跑步的形式在村庄小巷中留下足迹,在小溪中印下了身影,在山脉中回荡着呐喊声,他们传递着先辈们的心愿,释怀着内心的情感。在火把巡游的现实场景中,似乎我们更容易联想到奥运圣火的传递境况,同时也使得我们深刻的感触到乡土仪式体育与竞技体育之仪式行为之间的蛛丝马迹与“情感纽带”。带着这种现实的情感,走进身体运动的“历史现场”,仿佛间又聆听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与豪迈。
2.2身体运动中历史记忆的建构
通过身体运动的展演来还原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形象或事迹,使一种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得到重新展示,勾勒了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作用。“三公下水操”仪式中的身体运动,通过一种水中搏斗场域情境的再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再现与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更是一种族群心境的宣泄。在沉湎于震撼的展演现场,我们也不免会提出如此疑问,历史上陆秀夫跳海后真的与元军搏斗过吗?如果没有,人们建构或假借这些记忆又是为了要说明什么呢?缘于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8]我们仍肩负着从历史沉钩的文本解读中探索未知的重任。
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缘于张世杰的指挥失当,宋军在崖山海战中,由军力占据优势而转为劣势。在元军的夹击之下,“自朝至日中,战未决。会日暮,雨暴作,昏雾四塞,宋师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妻子于水,继登昺船曰:“官家事危矣,奈何”!遂抱帝昺赴海,俱死于水。后宫及百官吏士从死者万数。[9]据《宋元战史》记载:“陆秀夫先将自己的妻子赶入海中以后,便登上帝昺的座船,向宋帝禀告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应当为国而死。陆秀夫又将金玺挂在宋帝昺的腰间;然后,陆秀夫便抱着这位9岁的宋朝最后一任皇帝,一起投入海中而死。”[10]从宋元的相关战争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其中并未发现关于陆秀夫与元军在海中搏斗的记述。于是,笔者又查阅了《宋史》和《新会县志》,得到如下材料: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公元1279年3月19日),元军大举进攻张世杰于厓山(今广东新会东南,当时是海岛),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末帝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也投海死,南宋亡。[11]康熙《新会县志》载:“秀夫走帝舟,舟大诸连结不可去。于是先驱妻子入海,朝服奏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遂抱帝赴海……等后死者不可胜计,……七日浮尸十余万。”[12]
从历史文本分析,元军与宋军在崖山海战时,最先进入战斗的是前方船只,而陆秀夫及宋帝昺所乘坐的船在船队的中后方,当陆秀夫背帝跳海时,元军并未进攻到他们的船只周围,他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和处理后事。从实际情况分析,如果他们只是求以死报国,跳海后很快就会溺死,更谈不上与元军搏斗。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呢?带着疑问,我们再次进入田野中与相关人员进行交谈,他们也没有提供相关更有说服力的证明,只是基于上一辈的记忆与口述而已,这种历史记忆更有可能是一种传说或历史的建构(但并不能就此盖棺定论)。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正史的一个重要补充部分,从历史记忆的层面上巡视,传说与正史文献所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3]钟敬文举了一个《搜神记》中宫人草的传说例子,说明宫人草的传说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它却反映了某一现实并不是一个捏造的事实。[13]这些民间的传说在一代代的传承过程中,往往又形成了一种记忆的“文本”,这种记忆“文本”并非仅被保存在大脑之中,也外显于身体展演的仪式中,或者说是不断重复的身体表演仪式让族群中的人获得了连续的传说记忆。[14]“三公下水操”中的“水中犁神”部分,更好的用身体运动诠释了这种传说,传递了这种“历史记忆”。由于这种“历史记忆”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所以,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中,人们获得、选择、强调、假借某些记忆,以强调一种族群认同。[15]
通过传说记忆中陆秀夫与元军在海中搏斗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升华了陆秀夫浩然正气的民族气节,凸显了这种民族精神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反响。在传说中不断构建起来的历史记忆与原始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一种相互的补充,它们皆服务于历史记忆的传递与表述,将两者更好的有机结合起来,往往可以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3]对于通过肢体展演来沿承的历史记忆,或者已经得到社会认可的集体记忆,在乡土社会中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能动反应,而是一个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生活资源,用以增强族群力量,在不同层面上实现“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理性”的综合表征。正因为这种历史记忆的保持与传递,激发了珪塘叶氏族群的保家卫国的激情,谱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日(公元1560年),倭寇集千人计剽掠小鸬鹚,以叶以遂为首领带领丁壮三百余枪头配合高安军练长林时新、林廷达率队出击,乘其不备,斩贼一百三十余人、贼首四人,贼寇四散逃遁。嘉靖四十年八月十四日(公元1561年),贼寇集千余人屯安溪刘仓,企图抢劫,被我发现,由叶以遂带丁壮与官军联合战杀,杀贼首四人,破其营斩获甚多。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寇又聚千人屯安溪刘仓,叶以遂率团防往救,把寇直追出侧岭,并且尽歼寇后队。到了近代,有叶文龙参加北伐的历史(1927年),有为了抗日珪塘家族会捐献飞机、大炮五万元的赤胆忠心(1938年)。[6]关于这些历史的部分内容已经过范文澜学者所考证,有据可证。从这些历史事件的时间分析,皆是发生在英雄祖先历史事件发生及“三公下水操”活动开创之后,这也是课题组调研“三公下水操”活动期间,叶老先生为何还要点出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族群延续的光辉历史,英雄祖先崇拜的历史心性正在叶氏族群中代代相传,通过这种身体运动展演历史记忆的现场而继往开来。
2.3身体运动中历史记忆的现实“结构与反结构”
珪塘村“三公下水操”活动是基于民间乡土社会中的庙会为载体的仪式体育活动,这种祭祀体育活动的展演形式即是以身体运动为本质特征,是一种纪念历史现象的现实展示。这种集体记忆在传承的过程中,往往由参与群体的当代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重新组合形成,通过文献、口述、行为仪式与形象化物体等媒介,将这些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15]任何信仰或者风俗都是既定社会思想的反映,它被许多社会现象所表达,又通过小区成员行为表达出来。[16]“三公下水操”仪式是村民们的一种自觉、自发和自愿的一种身体展演行为,而这种展演又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联中。[17]在“三公下水操”的仪式过程中,叶氏族人从现实日常生活结构中被释放出来,而又回到陆秀夫与元军搏斗的历史场域中,而他们所经历的交融,已经为此时的结构重新注入了活力。[18]这种身体运动所形成的交融是人类所特有的智能产物,涵盖了理性、意志及记忆,并随着社会中的生活经历的发展而发展。[18]因此,在“三公下水操”仪式体育行为中,身体运动的展演更多体现了与历史记忆、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等方面的交融,在交融中又不断被赋予新的现实意义,在特纳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翻转”现象而演绎的“结构与反结构”。
在“三公下水操”仪式身体运动中,能够直接参与观察到的是人神与历史场景的交融,在交融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两种形式的“翻转”或“结构与反结构”。每年参与“三公下水操”“水中犁神”的人员必须是叶氏族人,且通过两种形式确定参与对象。首先,采取选拔制。即通过每个村的活动筹备会,选拔一些年青体壮的男性参与。其次,采取准需参与制。即每年逢定亲、娶媳妇、生孩子、升入高等教育的人*参与者都是男性,这与活动的展演形式有关,要求净身不穿上衣,对体力也有要求,同时与地方男性主义权威性也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乡土社会中的隆重而又神圣的祭祀仪式中,女人所承担的角色更多是“后勤”的服务,闽南地域这种乡土风俗至今犹存,反应出在乡土社会仪式性体育活动中参与者的男女性别差异。,这部分对象具有优先准需参与的权利。在整个仪式中,这种准许参与的人员中最为特殊的群体是“新公”和“新婚”*“新公”就是当年从父亲角色转换爷爷角色的这些的男性,在短短的几天仪式“阈限”过程中,他们从仅仅是父亲的社会结构中解构出来,融入到爷爷这一社会结构中,实现一种身份的“翻转”。“新婚”是指当年结婚的男子,这部分男子通过仪式“阈限”过程中的身体展演,结束自己单身这个社会层,从而融入已婚的社会结构中,主要也是社会结构的“翻转”。。通过这种仪式的整个阈限过程,证实了她们身份的转换,从一种社会层次结构中解脱出来并融入到另一种社会结构中,实现特纳所谓的“结构与反结构”的“翻转”。
特别是“新婚”这一群体,他们通过“水中犁神”环节的身体展演,标志着他们新的身份被村落社会认同及认知。另外,“三公下水操”仪式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七傍晚举行,参与者裸露上身在水塘中做长时间的身体运动,也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一种公众展示。
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这种短暂的“阈限”(Threshold)阶段的身体运动,他们脱离了一种社会群体结构,从而进入到另外一种社会群体结构中,使自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在一种精神的激发下,在民众的见证下,在身体展演交融中,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位置发生了“翻转”。在“水中犁神”过程中,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神”,在整个仪式的阈限范畴中,在人们欢快的笑语中,在肢体运动展演中,在围观者的齐声呐喊中,似乎成为人们“把玩的工具”,然而,清洗净化后的“神”,重塑其在乡土民众中的社会地位。在整个阈限过程中,“神”的社会角色似乎形成了一种反差性的“翻转”,这种“翻转”的社会效应是重塑或强化其在民众思维、认知以及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认同,或者使其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性认同。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结构与反结构”中的交融而发生的“翻转”仅仅是一些表层的社会现象。在身体运动的背后,仍然试图积极呈现一种历史心性,以此诠释一个族群发展的延续以及族群心里建构。在整个仪式的身体运动的模仿过程中,为特纳所谓的“阈限”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同区域、特殊群体、极具象征的社会媒介体,在检验西方人类学理论在东方乡土仪式中的社会存在的同时,也使得体育人类学中身体运动所蕴含的哲理或理论基因被更好的诠释与呈现。
3 历史记忆、身体运动、族群认同之间的相互逻辑
认同(Identity)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由佛洛伊德所提出的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19]也是个体或群体对身份的追寻与确认。[20]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认同中的一个下属分系,通常指个体缘于客观的血缘连带关系或者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对特定的族群所产生的一体感。[21]在通常情况下,大杂居、小聚居的群体生活现状是作为社会人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因此也产生了诸多群体记忆或集体记忆。在人们从事的诸多现实社会活动中,更多是为了强化人们生活群体成员之间的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以延续族群的凝聚。[15]为了获得或者保持这种族群凝聚,生活在同一族群体中的人们又会假借族群“历史”的工具性,挖掘储存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 the Community)中的集体记忆。这种群体性的历史记忆造就了族群通过追忆过去来型塑族群认同成为可能。[22]在中国广袤的乡土社会中,运用这种历史记忆的力量形成族群凝聚事件也见怪不怪,这取决于中国乡土社会之“差序格局”的现实境况,即由一根根私人联系而构成的网络。[23]族群体在这样“差序格局”社会环境的沿承与发展的过程中,群体的认同危机往往伴随其中,假借或建构某种特殊的群体性的历史记忆,是族群体形成集体认同所需要面对的,也是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或资源竞争提供群体性服务,[23]作为乡土祭祀仪式体育的“三公下水操”活动便是在这种情境下被建构出来,而一直在族群体中瓜瓞绵绵。
“三公下水操”是叶氏族群的一种象征性群体活动,是以身体运动的象征性来保持与传递族群体的历史记忆,通过这种族群体的身体展演来表征历史记忆,使族群认同的延续或重新建构成为可能。在乡土社会中,村民们通过身体展演实现了对“历史记忆”及历史现场的追忆与重现,系统呈现了乡土社会中信仰的发生、衍分及整合的全部历程,使人们能够洞悉各族群又是如何运用各自的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的社会功能来协调与处理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24]借助族群传说或建构“历史”的形式,“历史”皆被理解成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是趋于虚构的社会记忆,[25]而正是这种被选择因素的存在,促生了珪塘村叶氏族群通过每年一次的“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来塑造或维持族群体的共同记忆的动机,并在实现族群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地作用。[26]在“三公下水操”的身体展演现场,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为了族群竞争、延续或生存而建构的“历史”,这些“历史”通过身体运动的形式被保留或固化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被不断的操演而代代相传。在建构这些历史记忆的同时,人们往往又会遗忘当年陆秀夫下决定背帝跳海的具体初衷和详实内容,为了树立英雄祖先的伟大形象,形成英雄祖先崇拜历史心性,这样选择性的建构及有意的遗忘更多的是为了族群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族群认同。
“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是叶氏族群的共同结晶,通过每年一次循环往复的身体运动,以“英雄祖先崇拜”的形式来保持或重构族群所共有的历史记忆,延续固有的或形成新的族群凝聚力,这也是一个移民族群为了实现资源竞争所需要假借的。
从叶氏宗谱记载可以看出,珪塘村叶氏族群的开基祖来自莆田仙游地区,是一个带有移民性质的群体,正是这种移民所形成的新族群环境,往往促生了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用以寻根来创造新的集体性历史记忆,以凝聚新族群认同。[15]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族群体为了更好的延承,需要借助历史记忆的型塑与建构形成族群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由珪塘村叶氏族群之“英雄祖先”所创造的光辉事迹往往成为族人型塑我族形象所需要假借的一种社会“资本”,而群体性行为的“三公下水操”仪式中身体运动的模仿往往承担着这种特殊的使命。在循环往复的代代相传中,这种历史记忆成为族群认同的逻辑起点,贯穿于整个族群发展的过程之中。在族群认同中,“三公下水操”仪式中这种象征性的身体运动通过身体模仿展演的形式来重现历史记忆中的场景,使得的身体运动更多的表征出原始的工具理性。
4 结语
仪式的存在与延续必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其所形成的民俗必然有其历史渊源,这其中必然会涉猎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典型的“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中。在中国广袤的乡土社会中,人们以身体作为媒介来重现或建构历史的场景,通过身体运动及其展演场域的重现来保存与传递一种群体固化的历史记忆。通过一些特殊事件的历史记忆的展演,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源竞争的潜在资本,同时也为族群向心力的产生与巩固创造条件,进而形成族群认同。“三公下水操”仪式中身体运动正是在这种“英雄祖先崇拜历史心性”下所凝集的叶氏族群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种原生性身体运动的展演场域中,通过历史记忆、身体运动及族群认同的相互逻辑思辨,推演出当前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以及乡土仪式体育之间的多元化关联与互动交融。
[1]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2.
[2] 郭学松,郑敬容,缪仕晖,等.原生态民俗体育“菜头灯”活动的农耕文化记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5):31.
[3]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3(3):184;184-185.
[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82.
[5]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北京:中华书局,2009:2.
[6] 叶松根.长泰县珪塘叶氏源流宗谱[M].2001:98;1043-1044;1047-1055.
[7] 郭学松,缪仕晖,陈萍,等.三公下水操的体育价值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5(2):178.
[8]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
[9] 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等.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360.
[10] 李天鸣.宋元战史·卷三[M].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1481.
[11] 陈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17.
[12] 薛起蛟,汤晋纂(余玉成修).(康熙)新会县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出版社,1991:36.
[13] 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4-196 .
[14] 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26(1):139-143.
[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81;418;49;58.
[16] B.Malinowski.“Baloma: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M].England And Wales:BiblioLife,2009:420.
[17] Alexander,Bobby C.Ritual and current studies of ritual:overview.In Stephen D.Glazier(ed.),Anthropology of Religion:a Handbook[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7:139.
[18]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3;129.
[19] 车博文.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20] 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3.
[21]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15.
[22] 赵琼.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对共有祖先的追述为视角[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41(3):87.
[2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21.
[24] 刘朝辉.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A].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2006:641.
[25] 黄应贵.时间、历史与记忆[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1999:285.
[26] 高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7,18(3):8-9.
(编辑 马杰华)
Ceremony,MemoryandIdentity:AStudyontheBodyMovementinSanGongXiaShuiCao
GUO Xuesong1,3,WANG Boyu2,YANG Haichen2,CHEN Ping1,LIU Mingyun1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body movements in the San Gong Xia Shui Cao in Guitang Village in Fujian,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d the logic among historical memory, body movement and ethnic identity by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grating Turner's theory of ceremony and theory of ethnic group. The study shows that performance of body movement in rural society ceremony ha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retaining and transferring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field of body movement displaying historical memory, original historical memory outlines the diversified origi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ve historical memory strengthens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reality sublimates the symbolic connotation of body movement; the logic connection among historical memory, body movement and ethnic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cene reproduction.
historicalmemory;ethnicidentity;localrituals;bodymovements;ritualsports
G80-054DocumentcodeAArticleID1001-9154(2017)06-0052-07
G80-054
A
1001-9154(2017)06-0052-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福建原生态村落体育研究”(14CTY022)。
郭学松,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史,E-mail:xs_guo1202@126.com。
王伯余,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E-mail:314865026@qq.com。
1.宁德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2.泉州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福建 泉州,362000;3.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ingde Normal University,Ningde Fujian 352100;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 Fujian 362000;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108
2017-03-11
2017-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