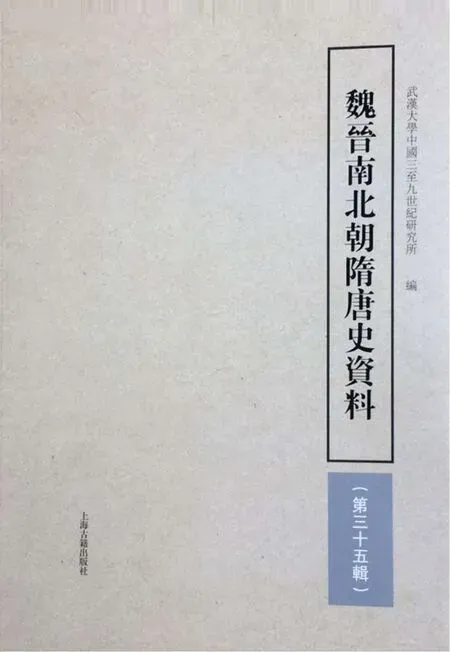北 魏 講 武 考
——草原傳統與華夏禮儀之間
劉 瑩
北魏講武考——草原傳統與華夏禮儀之間
劉 瑩
近年來,隨着對中古時期軍禮制度研究的逐漸深入,作爲軍禮重要組成部分的講武禮儀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北朝講武制度雖也有論及,但現有的研究大多立足於隋唐禮制,只簡單指出了北朝講武禮的某些特徵,對於北朝講武的發展變化及其承載的文化要素依然缺乏深入的討論,對北魏早期七月七日講武則關注更少。*近年來,中古時期國家禮儀的研究已經擴展到了五禮制度(吉、凶、賓、軍、嘉)的各個層面。軍禮方面的研究雖在不斷進行,但依然不够充分,北朝講武的研究成果更是有限。梁滿倉在《魏晉南北朝的軍禮》中專節討論了此一時期講武練兵的問題,指出北朝講武與南朝存在差异,在北魏早期爲部族傳統,到北朝後期逐漸納入《周禮》框架,標誌着五禮制度的逐漸成熟(梁滿倉: 《論講武練兵》,《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15—446頁)。陳儀、任重《魏晉南北朝的閲兵禮》則指出北朝講武多與馬射相關,而南朝則多有水兵訓練(陳儀、任重: 《魏晉南北朝的閲兵禮》,《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43—47頁)。王瑜在以唐代“講武禮”爲中心進行考察時,指出魏晉南北朝的講武並不正規,直到唐代纔成爲“成文的、正規的國家禮儀”(王瑜: 《關於中國古代“講武禮”的幾個問題——以唐代爲中心》,《求索》2009年第4期,第217—220頁)。陳志偉《北朝講武考論》則認爲北朝講武活動增多,且已成爲皇帝親自主持的禮儀活動,到北齊與北周時成爲一種國家制度。但講武上升爲“禮”,成爲國家軍禮的一部分則是在唐宋時期(陳志偉: 《北朝講武考論》,《蘭州學刊》2011年第8期,第156—160頁)。日本學者丸橋充拓則從魏晉南北朝正史志書的構成探討軍禮成立的過程,認爲從《魏書》開始“講武逐漸成爲軍禮的核心内容”(丸橋充拓: 《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における「軍礼」確立過程の概観》,《社会文化論集: 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紀要社会文化学科編》第七號,2011年3月,第53—61頁)。又,同氏《唐代射礼の源流》一文中也稍稍涉及北魏的講武,認爲北魏七月七日馬射,是射禮與講武的混合禮儀,但並未對其進行深入論證(丸橋充拓: 《唐代射礼の源流》,《中国古代軍事制度の総合的研究》,平成20—24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3年,第145—153頁)。作爲北魏國家禮儀之一種,*爲方便行文,此處“國家禮儀”一語泛指國家、朝廷經常性舉行的儀式活動,並不單指記載於禮典的禮儀制度。關於“講武禮”的最終形成與確立,是貫穿北朝與隋唐的重要問題,本文僅就北魏時期的講武活動進行探討,不涉及“講武禮”的確立問題。在《魏書》不多的講武相關記載中,也能窺探到北魏政治、社會文化的些許樣貌。
一、 拓跋七月七日講武之習俗
關於北魏講武的記載,最早見於《魏書·序紀》。史載平文帝鬱律五年,即東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僭晉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絶之。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魏書》卷一《序紀》,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0頁。此次講武活動時間不明,似乎只是爲戰争進行的動員活動,與後來較爲固定的講武活動不太相同。昭成帝什翼犍建國五年(342),拓跋七月七日講武活動確立。據《魏書·序紀》:
(建國)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爲常。*《魏書》卷一《序紀》,第12頁。
此次講武活動中,大致包含了北魏早期講武活動的幾個重要因素: ① 時間: 秋七月七日;② 參加者: 諸部落;③ 活動内容: 集會、馳射;④ 設施: 壇埒。此後關於七月七日講武活動的記載都過於簡略,或是一語帶過,或是記載其中某一種活動,這使得昭成帝時這一次講武活動的記載顯得尤爲重要。儘管如此,昭成帝以後關於講武的記載,也多少可以補充關於此一活動的認識。
此後的講武活動,首見於道武帝登國年間。據載:
(登國六年)秋七月壬申,講武於牛川,行還紐垤川。*《魏書》卷二《太祖紀》,第24頁。
(登國八年)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群臣,仍講武。*《魏書》卷二《太祖紀》,第25頁。
拓跋珪即代王位之前,拓跋部一直處於離亂的狀態,或許由於這一原因,七月七日講武在昭成帝建國五年後一直不見記載。道武帝於登國年間的兩次講武,分别在登國六年(391)七月二日(壬申)與登國八年(393)七月三日(庚寅),似乎並未遵守以“七月七日”爲常的傳統。但天興二年(399)七月七日於平城鹿苑舉行的大閲,似乎暗示着這一傳統的恢復。*《魏書》卷二《太祖紀》天興二年載:“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閲於鹿苑,饗賜各有差”,第35頁。明元帝時所見七月七日講武活動,便是對這一傳統的確認與延續。明元帝永興二年(410):
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秋七月丁巳(七日),立馬射臺於陂西,仍講武教戰。*《魏書》卷三《太宗明元帝紀》,第50頁。
此後,七月七日講武的活動似乎比較固定。見於史籍的,有太武帝始光四年(427),“秋七月己卯(七日),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射中者金錦繒絮各有差”;*《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第73頁。又,太延五年(439),“秋七月己巳(七日),車駕至上郡屬國城,大饗群臣,講武馬射”。*《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第89頁。這兩次活動均在七月七日舉行。始光四年的記載雖未明言講武,但從時間、“築壇”、“戲馬馳射”來看,確爲講武無疑。此外,此條記載還補充了講武活動的另一重要内容——賞賜。依照講武各要素,《魏書》中的其他一些記載似乎也與講武有關,羅列如下:
(明元帝永興三年)秋七月戊申(四日),賜衛士酺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七日),賜附國大人錦罽衣服各有差。*《魏書》卷三《太宗明元帝紀》,第51頁。
(永興五年)秋七月己巳(六日),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游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魏書》卷三《太宗明元帝紀》,第53頁。
(太武帝始光三年)秋七月,築馬射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第71頁。
(文成帝興安二年)秋七月辛亥(十一日),行幸陰山。……己巳,車駕還宫。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2頁。
以上史料,大大補充了北魏早期講武活動的記載。綜合所有相關史料,整理如下表:

表1 北魏早期所見的講武活動

續表
從上表可知,除了集會、馬射以外,北魏早期的講武還包含有宴饗、賞賜及校數軍實的内容,甚至還可能伴隨有祭祀活動(如明元帝永興五年薄山祭太祖)。如此,則七月七日講武並不單純是一種軍事訓練,而是包含了集會、祭祀、騎射、宴饗以及賞賜在内的大型活動,在北魏早期的部族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那麽,除以上所舉活動内容外,北魏早期的講武活動是否具有其他特點?
從地理分佈上來看,北魏早期講武的地點分佈並没有一定的規律。大致依照從東到西的順序,整理表1地點如下:
黑山: 黑山不見於《魏書·地形志》。神二年(429),太武帝“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第2293頁。北伐柔然,其後還於黑山,舉行了“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的活動。而此前始光二年(425)北伐柔然,太武帝曾遣長孫翰從東道經黑漠北至柔然王庭。*《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第2292頁。則黑山很可能是從長川東邊,經今張北附近或以東地區,北入黑漠後的某一座山。*參(日)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 《自平城赴漠北的交通路綫——長川、牛川、白道》,《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19頁。遼代夏捺鉢(行營)所經處有黑山,在上京道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西北)興安嶺山脉之中。*《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444頁。遼代帝王常於夏、秋駐蹕於此,並舉行祭祀、射獵的活動。*如遼穆宗應曆十年(960)七月,誅耶律壽遠等,“以酒脯祠天地于黑山”,見《遼史》卷六《穆宗紀上》,第76頁);又應曆十二年(962)秋“如黑山、赤山射鹿”,見《遼史》卷六《穆宗紀上》,第77頁。又,元代從寶昌州(今内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太僕寺旗寶昌鎮)至上都開平(内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多倫縣西北)的途中,經過一條叫做驢駒河的河流,“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王惲: 《秋澗集》卷一〇〇《紀行》,《四庫全書》第1201册《集部·别集類》,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94頁。元代寶昌州在今張家口北,據太武帝北伐之東道不遠,從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比遼代捺鉢之黑山更接近。北魏太武帝所經之黑山,雖不能確定具體地點,但是北伐途中之一據點,當無疑問。
參合陂: 關於參合陂的具體位置,或説在北魏參合縣梁城郡,即今内蒙古涼城縣,或説在漢參合故縣,即今山西省大同市陽高縣。前説早見於《水經注》、《通典》,*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三《河水注》,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3頁;杜佑: 《通典》卷一九六《邊防十二·北狄三》“拓跋氏”條,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5374頁;同書卷一七九《州郡典九·古冀州下》“馬邑郡”條,第4743頁。對後世影響甚遠。嚴耕望通過對北魏早期參合陂的記載進行梳理,認爲猗“代郡之參合陂”及慕容寶兵敗處,當在平城之東,即今陽高地區。*嚴耕望: 《北魏參合陂地望辨》,《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河東河北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97—1402頁。田餘慶則通過分析代國時期拓跋與鮮卑之共生關係,判定桓帝猗后祁氏當出自烏桓,而“代郡之參合陂”正是拓跋與烏桓“錯居之處”,亦即今陽高縣。*田餘慶: 《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魏書·序紀〉有關史實解析》,《拓跋史探》,北京: 三聯書店,2003年,第108—216頁。本文從嚴、田二先生之説,則明元帝永興二年講武之參合陂當在今陽高縣地區。
長川: 根據前田正名等學者的研究,長川應位於于延水(今東洋河)上游,是平城通向漠北中道的必經之地。*(日)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 《自平城赴漠北的交通路綫——長川、牛川、白道》,第119頁;毋有江: 《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28頁。
平城鹿苑與南郊: 今山西省大同市。
牛川: 牛川在北魏善無,即今内蒙古涼城縣附近,大概“是流經歸綏平原與大同盆地之間的山區的一條河流”,在芒干水(今黑河)上游,爲平城與盛樂之間的交通要道。*(日)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 《自平城赴漠北的交通路綫——長川、牛川、白道》,第115—133頁;毋有江: 《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第28頁。
薄山: 明元帝所祭刻石,指道武帝天興二年正月西討高車,“還次牛川及薄山,並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之處。*《魏書》卷一《太祖紀》,第34—35頁。永興五年(413)六月,明元帝“西幸五原”,之後於七月己巳(六日)“還幸薄山”,七月丙戌(二十三日),“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魏書》卷三《太宗紀》,第53頁。則薄山可能在五原之東,雲中大室附近。據《水經注》,雲中東北白道中溪水畔有魏行宫阿計頭殿,城西陰山下有講武臺,臺東立有《高祖講武碑》,爲高聰所寫。*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三《河水注》,第234—235頁。則雲中附近本就是講武之所,位於今内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
祚嶺: 祚嶺即柞嶺,據《通鑑》胡三省注,“柞嶺即柞山之嶺”,*《資治通鑑》卷一二〇《宋紀》“文帝元嘉四年七月”條,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第3796頁。“柞山在平城之西,大河之東”。*《資治通鑑》卷一二〇《宋紀》“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條,第3774頁。清人顧祖禹引李延壽之説,認爲祚山在河東,當不誤。*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條,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2006頁。其地在明元帝時已是北魏皇帝的巡狩場所。泰常六年(421)七月,明元帝“西巡,獵于柞山,親射虎,獲之,遂至于河”。*《魏書》卷三《太宗紀》,第61頁。始光元年(424),柔然入侵雲中,太武帝於祚山發兵,北擊柔然,則祚山應距雲中不遠。*《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第69—70頁。祚山具體位置雖不能確定,但既在平城西北,且地近雲中與黄河,則很可能在西出平城,經參合陘、牛川、雲中,渡過君子津以至河西的巡幸道路上,這是當時平城與河西之間的重要交通路綫。*(日)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 《平城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綫——長川、牛川、白道》,第156頁。祚嶺(祚山)既去雲中不遠,又在黄河東岸,或許即在君子津附近。
上郡屬國城: 上郡屬國城即漢代上郡龜兹縣,在今陝西省榆林市,爲北魏進攻涼州的必經之地。
新壇: 新壇之名只此一見,《魏書·地形志》與其他地志史料中均無記載。道武帝登國七年(392)到達河西鄂爾多斯沙漠南緣,登國八年(393)由此向南,到達羖羊原、白樓,西至苦水(即高平川),破侯吕鄰部,還白樓。六月,由白樓向北,七月至新壇,八月南征薛干部於三城(今陝西省延安市),九月,再次回到河南宫。*見《魏書》卷二《太祖紀》,第25頁。由此年的行軍路綫,講武處大概在三城之北,可能靠近鄂爾多斯沙漠南緣。所謂新壇,或許並非地名,而是道武帝在歸途中新築壇埒處。*此一意見受教於日本九州大學川本芳昭教授,特此致謝。
從上來看,北魏早期講武的地點並不固定,但其地點選擇是否有一定的標準?或者説,這些地點之間是否存在其他的相似性呢?
以上幾處講武地點,或是拓跋政治重地,或爲巡幸駐蹕之所,在拓跋部歷史發展中十分重要。如參合陂,昭帝禄官時,代國分爲三部,參合陂位於東部濡源、西部盛樂之間,地近烏桓部落,是拓跋部向東、向南發展之基地。即使到昭成帝什翼犍建都雲中後,參合陂依然是拓跋部落重要的集會之所。*嚴耕望: 《北魏參合陂地望辨》,《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河東河北區》,第1397—1402頁;(日) 岡崎文夫: 《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編)》,東京: 平凡社,1989年,第325頁;田餘慶: 《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魏書·序紀〉有關史實解析》,《拓跋史探》,第108—202頁。就自然環境來看,參合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有“蒹葭藂生”。*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一三《水注》,第1177—1178頁。或許由於參合陂獨特的政治地位,當地的榆木之林流傳着與桓帝猗及道武帝拓跋珪相關的神异傳説。據《魏書·序紀》:
是歲(桓帝十一年),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土無榆樹,故世人异之,至今傳記。*《魏書》卷一《序紀》,第7頁。
又,《魏書·太祖紀》曰:
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魏書》卷二《太祖紀》,第19頁。
榆樹本爲中國北方常見的樹種,既可種植以爲農用,又用於邊塞駐防,在古代城市中也常有榆柳成行的景觀。而塞外草原,樹木以樺樹與楊樹爲主。*Robert N. Taaffe, The Geographic Sett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4.雖有部分部族亦種植榆柳,如黠戛斯,但畢竟是少數。*《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附黠戛斯傳》曰:“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6147頁。在羌、胡中,也可見到一些樹木成林的神异傳説。居於金城的羌人中,曾流傳一位名叫梁暉的羌人首領的故事:
按耆舊言: 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山,榆木成林。*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二《河水注》,第181頁。
又,昭成帝死葬金陵,營梓宫,木柹盡生成林。*《魏書》卷二《太祖紀》,第19頁。《魏書·禮志》載北魏太平真君中,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祭祀位於烏洛侯國之石室:
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第2738—2739頁。
以上所見,樹木成林常與羌、胡神异傳説或祭祀相關。而實際上,林木確實是北方部族祭祀活動中的關鍵要素。關於北方諸族的祭祀問題,江上波夫曾對匈奴祭天的儀式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其中涉及了鮮卑、契丹等部族的祭祀活動。在這些北方部族的祭祀中,繞林而祭、豎木供牲在祭祀儀式中具有共通性。*(日) 江上波夫: 《匈奴的祭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 中華書局,1993年,第1—36頁。顔師古亦曰:“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張守節《史記正義》,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2893頁。可見林木在胡族信仰中本就具有神聖性,而以上所見樹木成林的神話傳説,正是這一信仰觀念的表現。
明白此點,再考察以上講武地點的自然環境。參合陂既是代、魏政治重地,又有與桓帝、道武帝神异傳説相關的榆樹林。黑山雖不能判明具體地點,但靠近興安嶺的遼代黑山自不乏樹木,元代驢駒河北的黑山雖皆蒼石,但驢駒河卻“夾岸多叢柳”。*王惲: 《秋澗集》卷一〇〇《紀行》,《四庫全書》第1201册《集部·别集類》,第394頁。長川位於于延水上游,“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爲藂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一三《水注》,第1179頁。上郡屬國城附近有榆溪,“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三《河水注》,第253頁。以上所見九個地點中,能判明自然環境者雖不足一半,但從其餘地點所處位置來看,也當在水草豐茂、林木繁盛之地。關於此點,還可參考遼代行營居址的選擇。
遼代帝王四時隨水草轉徙,“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中》,第373頁。據《遼史·營衛志》,春捺鉢爲鴨子河濼,其地“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夏捺鉢無定所,有吐兒山、子河、黑山之選,“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秋捺鉢在伏虎林,常“入山射鹿及虎”;冬捺钵稱爲廣平淀,“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居此地時常“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中》,第374—375頁。北魏早期講武地點雖不固定,但帝王巡幸與征伐、射獵本不分離,以上地點亦是皇帝巡幸駐蹕之所。
在明確了七月七日講武活動的參與者、内容、地點選擇等要素後,大概可以對七月七日講武的實態進行推測。淺見以爲,北魏早期的七月七日講武活動實爲拓跋鮮卑之秋祭。
前舉江上波夫的研究中,已經明確了草原遊牧民族一年有春、秋兩次祭祀。此説雖已爲學界共識,但對於拓跋部落秋祭的内容,學者亦有不同看法。江上氏以白登山祭祀昭成、獻明、太祖三廟當之。*(日) 江上波夫: 《匈奴的祭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第10頁。佐藤智水則認爲鮮卑拓跋秋祭在七月,卻未論及鮮卑秋祭與七月七日講武之關係。*(日) 佐藤智水: 《北魏皇帝の行幸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號,1984年,第39—53頁。康樂與佐川英治二氏均繼承江上之説,康樂認爲拓跋九、十月廟祭與小歲賀、五月五日饗、七月七日饗等都是源自北亞傳統的祭典;*康樂: 《國家祭典的改革》,《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 稻鄉出版社,1995年,第170頁。佐川氏則在探討平城鹿苑機能時,提出白登山廟祭與孟秋或季秋的馬射相當,爲鮮卑拓跋之秋祭。*(日) 佐川英治: 《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7號,2007年,第49—76頁。佐川氏的説法注意到馬射與祭祀之關係,點明了拓跋部落聯盟中與四月祭天相對應之秋季祭祀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非常具有啓發意義。但關於白登山廟祭與秋祭是否等同,以及拓跋孟秋馬射與季秋馬射之關係等問題,還需進一步探討。此節就前一問題進行探討,後一問題留待下節再論。
關於白登山廟祭,《魏書·禮志》曰:
明年(永興四年),(明元帝)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後二年(神瑞元年),於白登西,太祖舊游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别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爲逆,有保護功,故别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第2736—2737頁。
由此段史料可知,早在永興四年(412),明元帝即在白登山爲太祖立廟,並兼祭天神,只是祭祀無常時,並不固定在秋季,祭祀時奉以太牢,即牛、羊、豬。神瑞元年(414)所立三廟,可謂永興四年太祖廟祭的擴大。其以昭成、獻明、太祖三廟爲中心,於九月、十月之交,由皇帝親祭,祭品改爲馬、牛、羊,並行“貙劉”之禮。“貙劉”之禮見於《續漢志》,東漢立秋迎氣之後,行“貙劉”之禮。*《續漢志》第五《禮儀志中》記立秋郊禮畢,乘輿還宫,“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又曰:“貙劉之禮: 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見《後漢書》志第五,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3123頁。又第八《祭祀志中》曰:“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見《後漢書》志第八,第3182頁。關於這一禮儀,學界或説是祭祀中天子射牲這一環節,或以之爲漢代都試,又或認爲其與都試二者不同,但關係密切。衆説紛紜,並無定論。*前説參見王瑜: 《關於中國古代“講武禮”的幾個問題——以唐代爲中心》,《求索》2009年第4期,第217—220頁。第二種説法參見薛英群: 《居延漢簡中的“秋射”與“署”》,《史林》1988年第1期,第19—25頁;高二旺: 《略論漢代磚石畫像中的軍禮》,《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33—36頁;焦天然: 《兩漢都試考——簡論漢簡中的秋射》,《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71—75頁等。最後一種説法有劉麗琴: 《居延漢簡所見秋射制度》,《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106頁。明元帝白登山廟祭之時並無“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的相關記載,*《後漢書》志第五《禮儀志中》,第3123頁。所謂“貙劉”,很可能只是親自射牲或斬牲以祭祀祖先。
其次,從活動形式來看,作爲與春祭相對應的秋祭,應具有與春祭相近或相似的儀式程式。北魏四月西郊祭天之史料早已爲衆人所熟悉,爲方便比較,不避繁複,引述於下:
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黄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内近南壇西,内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宫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内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摇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内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第2736頁。
又,《南齊書·魏虜傳》:
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第985頁。
(太和)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範雲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第991頁。
結合以上材料,西郊祭天禮儀中的核心要素大概有: 築方壇、立木爲神主(由七木增至四十九木)、獻牲、繞壇、巫樂、宴會(内、外朝臣及賓國大人畢集)等,儀式舉行的時間也不止一天。從神瑞元年開始,白登山廟祭雖已是一種固定的祭祀,並由皇帝親行祭禮,但春四月的祭天的儀式要素均不見於白登山廟祭,因此也很難將白登山三廟祭祀看作與四月祭天相對的秋祭。*除白登山廟祭以外,還有一條史料不能不進行檢討。《魏書》卷一〇九《樂志》載:“又舊禮: 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内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第2827頁。據此段記載,北魏時期曾有孟秋西郊祭天的禮儀,似乎比七月七日講武更接近於秋祭。但關於孟秋西郊祭天的記載完全不見於記載,而此段所敍,又將孟秋祭天與孟夏祭東廟對舉。若將孟秋西郊祭天看作秋祭,那麽孟夏祭東廟是否應具有與其相當的地位呢?淺見以爲,依祭祀所用樂舞爲《八佾》之舞來看,所謂孟秋祭天與孟夏祭東廟可能是天興元年鄧淵“定律吕,協音樂”之後制定的四時祭祀的一部分。因其只是短暫的實行過一段時間,或者只是制定而未曾實行,因此稱爲“舊禮”,並不是拓跋部一直存在的祭祀活動,不能看作拓跋鮮卑的春、秋二祭。
反觀七月七日講武,設壇埒、薦饗、諸部畢集、宴會等要素幾乎完全對應。又依前顔師古言,鮮卑秋祭必有林木。七月講武地點正好滿足這一條件,而四月祭天中逐漸增多的木主,或許即是榆木成林神异傳説的某種象徵。再如馳射、宴饗、賞賜等,大概便與“奏伎爲樂”同時進行。以上内容在匈奴的祭祀中也可見到。*參見(日) 江上波夫: 《匈奴的祭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第1—36頁。其中有一點不同是,四月祭天在平城西郊,而七月講武則没有固定的場所。這一點看似區别甚大,但北方草原民族春、秋二祭很可能本來就没有固定的祭場。*相比於没有固定地點的七月七日講武,北魏四月四日的祭天禮儀雖固定在平城西郊,但在孝文帝延興四年(474)以前,祭壇的位置很可能不是固定的。據《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載,延興四年“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第2740頁。據此,延興四年以前西郊祭天禮儀有兩項習俗,一爲木主逐年遞增,一爲新帝繼位則更改祭壇的位置,即所謂“更兆”。獻文帝以此兩事“無益於神明”,因此“革前儀”,理當在“定置主七”之外,還“定置”了郊天壇的位置。《水經注·水注》曰:“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熊會貞以爲“建興四年”當作“延興四年”。酈道元於平城西郊所見的郊天壇與郊天碑很可能是延興四年“定置”以後的結果,熊説當不誤。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一三《水注》,第1142頁。參之匈奴,其大會祭祀的龍城亦可寫作“蘢城”或“籠城”,是“自然林木或豎樹枝之處,或樹木、柴薪堆積處”,*(日) 江上波夫: 《匈奴的祭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第9頁。可見,只要有自然林木或人工立木的神聖性場所,皆可成爲春、秋祭祀的祭場。又,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五月行幸陰山,七月壬午(九日)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群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宫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21頁。可見,北魏早期將春祭固定於西郊,文成帝和平四年以前的秋祭則便宜行事,並無定所,延續了草原民族長久以來的舊習。
論述至此,北魏早期講武活動的實態已基本明了。從昭成帝開始固定在七月七日舉行、稱爲“講武”的活動,實際上是拓跋部落聯盟春、秋二祭中的秋祭。在此之時,選取水草豐茂、樹木成林(或自豎木)之地爲祭場,修築壇埒,會集拓跋部落聯盟之衆部族,以繞林(或繞壇)、薦饗的方式祭祀神靈,並進行騎射、宴饗、伎樂、賞賜等活動。這並不僅僅是出於軍事訓練目的的一種例行禮儀,而是以拓跋部爲中心的部族聯盟的一次盛會,反映了一種長久流傳的草原民族文化傳統。通過在不同地點舉行集會祭祀,既是對部族聯盟關係的鞏固與加强,也是對拓跋部政治核心地位和北魏政權正當性的再確認與宣揚。
由於七月七日祭的重要性,這一部落集會活動在北魏前期一直存在,直到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纔“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74頁。但拓跋國家的這一重要活動,卻在《魏書》中記載寥寥,文成帝以後幾不見於史書。這是逐漸控制中國北方、逐漸適應華夏政治文化的拓跋國家的必然改變。
二、 從七月講武到九月閲武
北魏七月七日講武的記載,到文成帝興安二年(453)戛然而止。但前引和平四年七月九日所發詔書,仍稱“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群官講武平壤”,可見講武之事並未中斷。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了七月七日講武在史書記載中的消失呢?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表述差异所導致的記録缺失。如表1所見,道武帝曾於天興二年七月七日於平城鹿苑進行了“大閲”,就時間來看,當爲講武活動無疑。此處既有“大閲”的記載,那麽講武是否也可能以其他名稱出現在記載中呢?爲防疏漏,整理北魏時期軍事訓練相關記録如下(表2)。

表2 北魏時期軍事演練相關記載
①《魏書·高祖紀上》記作“庚子”,《資治通鑑》則作“庚午”。按,孝文帝太和五年九月並無庚子,《通鑑》“庚午”爲是。見《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51頁;《資治通鑑》卷一三五《齊紀一》“高帝建元三年九月庚午”條,第4246頁。
表2中所列的活動被稱爲“大閲”、“閲武”或“治兵”。由表2來看,除了天興二年的大閲在七月七日舉行以外,其餘大閲的舉行時間並無一定規律,所指内容似乎也有變化。明元、太武之時,大閲似爲戰時動員與檢視,如明元帝永興五年正月曾舉行兩次大閲,己巳日大閲集合“畿内男子十二以上”,庚寅日大閲則“部署將帥”,*《魏書》卷三《太宗紀》,第52頁。四月西巡,討越勤部;太武帝神三年(430)西討赫連定途中,“大閲于漠南,甲騎五十萬,旌旗二千餘里”;*《魏書》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第2402頁。太平真君四年(443)六月大閲於西郊,九月北討柔然。而孝文時所見大閲,卻不盡如此。延興四年(474)八月大閲於北郊,九月有征伐蜀漢的活動,但延興五年(475)十月大閲後卻並無戰事。翻檢史書記載:
(延興四年)八月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戊申,大閲於北郊。*《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40頁。
(延興五年)冬十月,蠕蠕國遣使朝獻。太上皇帝大閲於北郊。*《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42頁。
兩次大閲均在同月使節來訪之後。此時的大閲與其説是戰争動員,不如看作接待使節時炫耀國力之儀式更爲恰當。
相比於大閲,治兵的性質更易判斷。道武帝登國十年(395)八月治兵黄河南,九月進兵,與慕容寶對峙;太武帝始光元年九月治兵東郊,十二月發兵北討柔然;神三年治兵,西討赫連定;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八月治兵西郊,九月南伐。凡治兵者,均爲備戰,表2所見亦無例外,此不一一。*據曹永年,平文帝鬱律五年“治兵講武”之後,有南下攻打離石之舉,可見此次活動重在“治兵”。參見曹永年: 《關於拓跋地境等討論二題(摘録)》,收録於田餘慶: 《拓跋史探》附録,第203—209頁。此事未收録於表2,特備注於此。
閲武首見於太武帝太平真君十年(449),此次活動雖稱閲武,實爲治兵,據載:
九月,閲武磧上,遂北伐。事具《蠕蠕傳》。*《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第103頁。
九月,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鋭,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闈堅守,相持數日。*《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第2295頁。
太武帝時期的閲武只此一見,之後的記載雖僅有四例,但無一不在九月舉行,顯示出一定的規律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成帝時期的閲武見於興安二年,這也是七月築馬射臺的最後記載。
據《魏書·高宗紀》,興安二年七月“築馬射臺於南郊”。*《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2頁。前節已知,修築馬射臺是七月七日講武的重要活動,但此月並不見講武記載。至九月壬子,文成帝“閲武於南郊”。*《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3頁。兩事同見於南郊,是否説明興安二年七月所築馬射臺,實爲九月南郊閲武而準備呢?
前見文成帝和平四年詔書,因講武修築宫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而下旨當年講武沿用舊處,從下詔的時間在七月九日來看,此時的講武已不在七月七日舉行。獻文帝時,濟南太守鹿生有治稱,“特徵赴季秋馬射”。*《魏書》卷八八《良吏列傳·鹿生傳》,第1901頁。孝文帝延興二年(472)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37頁。可見,文成帝以來,拓跋部落聯盟於七月七日舉行的秋祭已不再被冠以“講武”之名,而講武一事改至九月,也被稱做“閲武”。從上引延興二年詔書來看,相比於七月七日的祭祀、騎射活動,至孝文帝時,九月講武的内容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下,便對九月講武内容進行梳理。
首先整理表2所見四次閲武情況如下:
(興安二年七月)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九月壬子,閲武於南郊。*《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2—113頁。
(太和五年)九月庚子,閲武於南郊,大饗群臣。*《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51頁。
(太和二十年)九月戊辰,車駕閲武於小平津。*《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80頁。
(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丁卯,詔使者吊殷比干墓。戊寅,閲武於鄴南。*《魏書》卷八《世宗紀》,第194—195頁。
九月閲武的記載,分見於文成、孝文、宣武時期,並非一時之事。就舉行閲武的地點來看,除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在洛陽北部的小平津外,其餘活動均在城南。關於小平津講武場,《水經注》曰:
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徒隸府户,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五《河水注》,第385—386頁。
北中郎府城建於太和二十年,*《太平寰宇記》卷五二《河北道一》“孟州”條引《洛陽記》云:“太和二十年造北中府城”,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1078頁。是洛陽北部護衛京師的鎮戍之地。孝文帝於此年在小平津講武,很可能與北中郎府置府有關。而北中郎府既爲羽林虎賁駐防之地,則此年講武必爲關係都城防衛之大事。從文成帝興安二年南郊閲武,和平四年下旨沿用舊處開始,講武很可能便被固定在都城南郊。或許從此時起,講武已逐漸與京師駐防産生關係。
作爲講武重要内容的馬射,在講武活動中的地位亦有起伏。從興安二年修築馬射臺來看,文成帝至孝文帝早期,築壇騎射、宴飲娱樂依然是講武的重要活動。而太和十六年(492)八月癸丑,孝文帝下詔:
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弃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强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别俟後敕。*《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70頁。
擅長騎射征戰的北方部族,本應以武事爲長,但在孝文帝的詔書中,卻是“教武闕然”的狀態。究其原因,則在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相比於武藝,重要的是習武教戰的方法,相比於馬射,重要的是講武時所進行的“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從孝文帝太和十六年開始,“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一直作爲講武重要内容的馬射退居其次。
此外,一些新的内容也出現在講武中。拓跋講武,本爲部族聯盟集會之事。而至少從獻文帝時起,皇帝徵召州郡吏員赴京師“親問風俗”,成爲講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謂州郡吏員,可能以州刺史及郡太守爲主。宣武帝時,“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魏書》卷七一《裴叔業傳附兄子粲傳》,第1573頁。恒農太守裴粲因此前往拜會司州牧元雍。除裴粲與前見濟南太守鹿生外,《魏書》所見徵赴講武者,還有前後擔任雍州刺史的元楨與元澄。可見,參與季秋講武的當爲畿内太守、州刺史及地方要員。
此時的講武也不限於“親問風俗”,更是皇帝問政訓誡、獎勵政績之時。孝文帝初,元楨出任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據記載:
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内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 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足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魏書》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列傳·南安王楨傳》,第493—494頁。
孝文帝對元楨的訓誡中,首先稱讚了元楨的孝行與治績,隨後强調長安鎮當以綏撫飢民爲要,再戒以遵禮、恤政、慎行三事,便完成了皇帝與地方官員之間的一次問對。元楨固爲朝臣,但作爲拓跋宗室,亦是孝文帝叔祖。孝文帝對元楨的訓誡可能並非接見地方官員時“親問風俗”的標準模式,但垂問地方情況,並加以指導,可能是講武時皇帝訓政的重要内容。此外,還需對政績顯著者加以表彰賞賜。濟南太守鹿生就曾被獻文帝“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魏書》卷八八《良吏列傳·鹿生傳》,第1901頁。此後,宴饗群臣、君臣同歡當是自然。
以上,對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後講武的變化進行了大概的梳理。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後,華北統一,柔然敗退,政權内部的叛亂亦被平息,*興安二年二月,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逆,伏誅,事引建甯王崇及子麗,亦賜死,事見《魏書》卷五《高宗紀》,第112頁。國家開始進入穩定發展、休養生息的時期。從這一時期開始,北魏皇帝北巡至陰山的時間與次數明顯減少,對於中原地區與農業發展則日益重視。*参見(日) 佐藤智水: 《北魏皇帝の行幸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號,1984年,第39—53頁;何德章: 《“阴山却霜”之俗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2輯,武漢大学出版社,第102—116頁;(日) 藤井律之: 《北朝皇帝の行幸》,(日) 前川和也、(日) 岡村秀典編: 《国家形成の比較研究》,東京: 學生社,2005年,第370—391頁。在此背景下,同稱爲講武的七月秋祭與九月閲武之間出現了諸多變化(見表3)。

表3 七月講武與九月講武之比較

續表
曾經以拓跋部落爲核心而舉行的七月七日講武秋祭,逐漸淪爲一種騎射、宴饗活動,直至太和十八年五月,孝文帝下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同年八月孝文帝巡幸陰山講武臺,高聰撰《高祖講武碑》,*《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74頁;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三《河水注》,第235頁。成爲對這一悠久傳統的最後緬懷。而這一時期出現的九月講武,則跨越了拓跋部落聯盟祭祀集會的範疇,成爲皇帝與朝臣共同參與的一種宫廷儀式。並通過增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演習戰陣、問訓吏政等儀式内容,使講武成爲皇帝統領胡、漢,施政布教的場合,成爲北魏政權用以溝通朝廷與地方、集中展現王朝政教功績的禮儀舞臺。
此後,關於七月七日活動的記載亦偶有一見。宣武帝時,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在功衰期間,欲於七月七日在北園會同文武進行馬射,其府録事參軍張普惠諫曰:
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閲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虚,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第1728頁。
元澄雖接受了張普惠的諫言,卻欲“託辭自罷”,便答曰: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雍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第1729頁。
元澄生於平城,其欲於七月七日舉行馬射,自然源於當年北都生活之經歷。但在中原文士張普惠的眼中,此舉卻不合國家制度。應依國家“令教”,於九月施行。對此,元澄辯解説,七月七日馬射雖非典制,但卻是雍州地方的舊有儀式。在不妨礙公務、勞民傷財的情況下,“任人私射”,又有何不可?
遥想昭成之時,燕鳳出訪前秦,曾向苻堅描述拓跋部落孟秋集會的盛況:“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魏書》卷二四《燕鳳傳》,第610頁。而到北魏後期,七月七日秋祭已完全退出國家儀典,成爲了一種地方習俗與個人記憶。相形之下,元澄的辯解,令人倍感落寞。
三、 北魏講武之典據
以上兩節,探討了北魏早期七月七日講武之實態與北魏後期九月講武之變遷,對於前後講武的内容與形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關於北魏講武的疑問並不止於此。鮮卑秋祭爲何稱作講武,九月閲武的轉變又以何爲據,便是此節將要探討的問題。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同爲北族政權,以秋祭爲講武是否是五胡十六國一直以來的傳統?關於十六國時期講武活動的記載,略見於下:
(東晉咸和三年)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虚。(張駿)大蒐講武,將襲秦雍。*《晉書》卷八六《張軌傳附孫俊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235頁。
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閲馬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矣。*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卷十《濁漳水注》,第942頁。
苻堅宴群臣于逍遥園,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年少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朱肜上《逍遥戲馬賦》一篇,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太平御覽》卷五八七《文部》“賦”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第2645頁。
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姚)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閲于城西,幹勇壯异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第2981頁。
(南燕建平四年)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慕容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晉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記》,第3171—3172頁。
根據以上史料,不難看出,前涼張駿大蒐講武,姚興、慕容德大閲城西,均是爲戰争而準備,其規模雖浩大,但重在簡練武卒、選拔壯异,與北魏七月秋祭並不相同。石虎於閲馬臺訓練親衛騎兵,以鳴鏑爲軍士出入之號令,據《鄴中記》:
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坎爲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騰黑矟,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閲馬於此臺。乃於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集於臺下。隊督已下皆班賚。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又齊走於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矟從事,故以黑矟爲號。*《太平御覽》卷三〇〇《兵部》“騎”條引《鄴中記》,第1383頁。
石虎於每個月的第一天與最後一天,於漳水南岸訓練宿衛騎兵,其以髇箭(鳴鏑)爲號令,使宿衛奔走於漳水南北。此訓練方法,不禁令人想起匈奴冒頓鳴鏑射馬之事。這種訓練方法或許亦是源於胡族騎射,但並非北魏七月七日講武之淵源。而苻堅逍遥園講武則更接近一場綜合詩文、騎射等娱樂活動的宴會,其具體細節不得而知,與北魏講武之關係亦不明確。
由於史料所限,在十六國時期,源於北族傳統的秋祭活動可能並未施行,或者曾有施行,卻不合華夏之禮法,因而未記録在册。不論如何,以秋祭爲講武的習慣,在此一時期似乎並未確立。
那麽,北魏“講武”之稱呼是否爲承襲魏晉禮儀而來?其與中原之禮典又有何關係?
兩漢時期,並没有專稱爲“講武”的禮儀。一般認爲,漢代都試即是漢代的講武禮儀。而都試舉行的時間有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之説,其是否有固定時間,尚無定論。*參見屈建軍: 《漢都試小考》,《青海師專學報》1993年第1期,第63—67頁;王瑜: 《關於中國古代“講武禮”的幾個問題——以唐代爲中心》,《求索》2009年第4期,第217—220頁;焦天然: 《兩漢都試考——簡論漢簡中的秋射》,《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71—75頁。曹魏時期,似以立秋閲兵爲制,但亦有十月治兵的記載。*《晉書》卷二一《禮志下》,第661—662頁;《宋書》卷一四《禮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8—369頁。西晉初期,大閲多在冬季舉行。*參見陳志偉: 《三國兩晉講武考》,《北方論壇》2014年第6期,第103—106頁。但晉祚不久,其南遷後雖有講武之舉,卻並没有形成長久、固定的禮儀習慣。如此,要從魏晉時期尋找北魏講武禮儀的淵源,實爲不易。
儘管如此,中原文物制度依舊爲北魏講武禮儀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禮》。關於《周禮》與北朝制度建設之關係,學界已多有探討。從北魏早期開始,《周禮》的影響便散見於郊祀禮儀、宫城設計、職官制度等方面。其或與胡俗相摻雜,或爲胡俗之依託,在北魏早期制度建設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更在孝文帝改革中發揮了全面的影響。*關於北魏時期《周禮》的應用與影響,參見(日) 川本芳昭: 《五胡十六国·北朝史における周禮の受容を巡って》,《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3篇《五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胡漢融合について》,東京: 汲古書院,1998年,第367—389頁;樓勁: 《〈周禮〉與北魏開國建制》,《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7—148頁。魏晉以來,《周禮》學説日益與國家政權建設及正統性問題緊密聯繫,其中“蒐”、“苗”、“獮”、“狩”四時田獵之禮也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講武禮儀的主要參照。那麽,北魏早期鮮卑秋祭是如何借助《周禮》而成爲“講武”之儀?其孟秋講武之禮的轉變是否也能在《周禮》中找到依據呢?
首先,關於《魏書》帝紀中四時田獵活動的記載問題。對此,樓勁認爲《魏書》帝紀中“或據實載爲‘校獵’、‘講武’、‘治兵’、‘大簡輿徒’之類,或依儒典而書‘蒐’、‘獮’、‘狩’等四時講武名稱,史法甚嚴,並不隨意”,*樓勁: 《〈周禮〉與北魏開國建制》,《唐研究》第十三卷,第91頁注20。此説甚是。需要補充的是,《魏書》中記作“蒐”、“獮”、“狩”者分别指稱春、秋、冬三季的田獵活動,符合《周禮》之説。而如前所見,稱作“講武”、“治兵”者,卻不全是田獵,甚至《周禮》記載爲冬季田獵的“大閲”,也有與田獵無關者。此外,《魏書》中也簡單稱呼田獵活動爲“田”、“獵”、“射”,可見,《魏書》雖采《周禮》之説,卻也不拘泥於《周禮》,而自有其筆法。北魏早期將鮮卑秋祭稱爲“講武”,也並非對《周禮》的簡單托附。
如前所述,北魏早期七月七日講武的實質是拓跋部落聯盟於孟秋時節進行的祭祀集會活動,是一種草原文化傳統。而中原禮儀文化中的講武,則與《周禮》四時田獵之禮聯繫緊密。《周禮》對於四時田獵禮儀雖都有記載,然“凡田之禮,唯狩最備”,*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卷一七《月令》,鄭玄注,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2993頁。最爲重要和詳備的依然是冬季大閲。此處便依據《周禮》大閲之記載,對鮮卑七月秋祭與中原仲冬大閲進行比較。
《周禮》四時田獵雖是以射獵爲名,但其目的卻在於“習射御之事”,*《漢書》卷七六《韓延壽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4年,第3211頁。以“不忘戰也”。*《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2954頁。從内容上看,仲冬大閲儀式流程大致如下:*參鄭玄注,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九《大司馬》,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第1805—1813頁。
1. 前期: 修戰法(頒講武之法、修檢旗、物)——萊於野——立表
從以上流程來看,《周禮》仲冬大閲包括前期與田獵當日兩個時期,田獵當天的儀式又包含了兩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以中原車戰與步兵爲主,以鼓鐸爲令,號令車徒三行三止,並制服仇敵的軍事演練;第二部分則是圍獵、獻祭的田獵内容。前一部分與其説是軍事訓練,不如説更側重於令行禁止的儀式感,表現的是居安思危、“不忘戰”的政治理念。而田獵部分,四季各有特點。據《周禮》,“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鄭玄注,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九《大司馬》鄭玄注,第1806頁。“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鄭玄注,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九《大司馬》鄭玄注,第1807頁。“秋田主用網,中殺者多也”;*鄭玄注,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九《大司馬》鄭玄注,第1808頁。“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鄭玄注,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九《大司馬》鄭玄注,第1811頁。其四時田獵,正模擬了四季農耕從除草、去蕪存菁,到收穫、分配的關鍵環節。由此可知,《周禮》所載講武是中原地區脱離漁獵生産、完全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産生的禮儀,體現的是中原王朝居安思危、注重農事的政治思想。從這點來看,北魏早期七月七日祭饗與《周禮》所見講武禮儀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
但若忽略二者不同的文化内涵,單從兩種儀式的形式上來看,鮮卑七月秋祭與中原四時田獵也有某些相似之處。例如,前期準備工作中,鮮卑秋祭需修築壇埒,而中原田獵則需萊野、建表;儀式當日,鮮卑諸部畢集,中原則彙集朝野之臣、鄉里之民;鮮卑借射獵考校馬射之術,中原借田獵演練戰陣之法;鮮卑有蹛林之祭,中原亦有郊廟之饗。中原國家還利用蒐獵之時,點閲民夫,*參杜正勝: 《編户齊民的出現》,《編户齊民》,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第23頁。北魏早期講武可能也涉及人口、牲畜數目的檢校。*《史記》與《漢書》記載匈奴五月龍城大會曰:“五月,大會蘢(《漢書》作‘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見《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892頁;《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3752頁。鮮卑春秋二祭與匈奴相近,可能亦有課校。結合以上諸點,若將集軍事演練、田獵、祭祀爲一體的中原國家集會活動看作講武禮儀的話,那麽,將符合以上要點的拓跋部落聯盟祭祀習俗稱作“講武”,也就不奇怪了。
鮮卑七月秋祭與中原田獵之間有不少暗合之處,但北魏季秋講武之典據,卻不那麽明確。
文成帝時,北魏開始於九月舉行講武儀式,這一時間與《周禮》四時田獵的時間均不相同。《禮記·月令》記載田獵的時間在季秋,記載講武的時間卻在孟冬。據《禮記·月令》:
是月(季秋)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卷一七《月令》,第2987—2988頁。
(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禦,角力。*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卷一七《月令》,第2993頁。
根據《禮記》,季秋田獵時,具五兵(弓矢、殳、矛、戈、戟),整齊馬色,備車駕,樹旗幟,並按照等級分授將帥,列陣於所田之處。司徒誓衆,天子服戎服,親執弓矢以射獵,並以所獲之物祭祀四方之神。《禮記》記載雖簡略,但就儀式内容來看,實與前見《周禮》仲冬大閲相去不遠。而孟冬“將帥講武”,則只是練習騎射、比較氣力。鄭玄注曰:“(季秋)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卷一七《月令》鄭玄注,第2987頁。而孟冬講武則是“爲仲冬將大閲,簡習之”。*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卷一七《月令》鄭玄注,第2993頁。就時間來看,北魏季秋講武,似以《禮記》季秋田獵爲依據。
而就講武的内容來看,北魏季秋講武在祭祀、騎射内容之外,不僅增加了符合中原禮典的戰陣之法,還多出了皇帝訓政、獎勵治績的部分。這多出的内容,不僅超出了禮儀經典的規定,也不見於南朝的講武儀式。
東晉偏居江左,禮儀多闕。繼東晉之後的劉宋,既有閲武,又行大蒐,二者均於春季舉行。*就《宋書》帝紀所見,劉宋閲武常在春季舉行,僅孝武帝孝建二年(455)於九月在宣武場舉行閲武,事見《宋書》卷六《孝武帝紀》,第117頁。其中,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二月舉行的大蒐之禮在《宋書·禮志》中留下了詳細的記載。其時正逢幕府山南崗宣武場完工,宋文帝於宣武場設“行宫殿便坐武帳”及“王公百官便坐幔省”,樹門建旗。大蒐之日,文帝從太極殿出發,東出雲龍門,再經北廣莫門至宣武場。其時百官從駕,太子入守。至宣武場後,部曲張圍,衆軍進圍,文帝親入旌門射禽。其後犒賞衆軍,還宫。*見《宋書》卷一四《禮志一》,第369—371頁。此次大蒐車服制度,一應俱全,不僅是劉宋大蒐之模版,更對南朝大蒐禮儀産生了長久的影響。*《隋書·禮儀志》曰:“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見《隋書》卷八《禮儀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63頁。但其内容只有《周禮》大閲田獵部分,軍事訓練則在閲武時舉行,内容當是訓練步兵與水軍。如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二月閲武,下詔曰:“朕以聽覽餘閑,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宋書》卷六《孝武帝紀》,第127頁。又大明七年(463)正月,欲“克日於玄武湖大閲水師”。*《宋書》卷六《孝武帝紀》,第130頁。則劉宋時期,大蒐與講武實爲兩種禮儀,此與《周禮》不同,而與《禮記》相似。但不論何者,均不見君臣問對、獎勵政績的内容。
南齊講武時間並不固定。《南齊書》帝紀所見講武雖多在九月,但亦有正月、八月及十月的記載。《南齊書·禮志上》曰:
九月九日馬射。或説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南齊書》卷九《禮志上》,第150頁。
乍看此一記載,似乎南齊的講武即是九月九日馬射,實則不然。據《南齊書》,此制出自宋武帝劉裕爲宋公時,九月九日彭城項羽戲馬臺馬射一事,然此一禮儀或習俗卻全不見於《宋書》。丸橋充拓認爲這一禮儀並非單純的講武,而是“射禮與講武的混合”。*參見(日) 丸橋充拓: 《唐代射礼の源流》,《中国古代軍事制度の総合的研究》,第145—153頁。而實際上這是“名人效應”下産生的一種娱樂活動,此前可能只是民間或軍中的遊戲,南齊時又在宫廷中舉行,因此記入《南齊書·禮志》,並非有經典依據的國家禮儀。由於記載簡略,南齊講武的具體流程不得而知。但就儀式内容來説,南齊的講武依然以水軍與步兵的訓練爲主,*如永明六年(488),“九月壬寅,車駕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見《南齊書》卷三《武帝紀》,第55頁。並未超出劉宋講武的範圍。
如此,在比較了劉宋、蕭齊講武之後,已不難看出北魏講武發展過程的獨特之處。本爲鮮卑秋日祭祀的七月七日集會活動,依託《周禮》,以“講武”的面貌進入了北魏早期國家政治生活中。而隨着華北的統一,隨着北魏皇帝巡幸傳統的逐漸消亡,伴隨戰事而轉移、以胡族部落爲核心的祭祀集會漸漸不符合國家統治的需要。固定於都城、以君臣關係爲紐帶、包容胡、漢朝臣的季秋講武就此出現,而來源於草原文化的馬射活動也得到保留。北魏講武在吸收中原禮典要素的同時,也發展出了超出禮典的部分。本以草原遊牧文化爲内核的七月七日祭,轉變爲北魏國家宣揚文治武功的國家儀典。這樣的講武雖有不倫不類之感,但卻真實地反映了北魏時期草原傳統與華夏禮儀之間調試、融合的政治文化進程。
四、 結 論
出身遊牧部族的北魏政權,在建國之初,在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延續着來自草原的傳統。就禮儀方面來説,除了特色顯著的西郊祭天外,北魏早期必然還存在着其他性質相似的禮儀與祭祀。但由於歷史記載的原因,這些富有异族色彩的儀式活動被有意、無意地從史書中抹去,在北魏的歷史中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儘管如此,通過歷史留下的蛛絲馬迹,我們依然能够捕捉到這些活動的存在。本文對北魏早期七月七日講武的探索,便是一次小小的嘗試。
就現有的記載來看,七月七日講武與四月祭天儀式類似,均來自北方草原傳統。但在史籍中,四月四日的西郊祭天被寫於《魏書·禮志》,獲得了與中原南郊祭天相匹敵的地位,而七月七日祭儀卻僅僅散見於各帝紀,喪失了作爲拓跋鮮卑秋祭的本來面目,成爲歷史記載中無足輕重的一筆。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忽視北魏早期七月七日祭饗所具有的重要性。高井康典行曾以遼代會同三年行朝移動中,遼代與各國外交展開的過程爲中心,探討了遼代皇帝行幸時,移動的政治空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指出遼代皇帝的巡幸及巡幸途中的外交禮儀,宣示了對新領地的支配,展現了遼代統治的權威。*(日) 高井康典行: 《遼代の遊幸と外交—もう一つの伝統“中国”—》,《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十集,東京: 汲古書院,2015年,第125—150頁。北魏早期七月七日的集會活動也恰好形成了一種類似的移動的政治空間。如果説,固定在平城西郊的四月四日祭天通過參與的人員、儀式的内容確認了拓跋部及北人的核心地位與權力,那伴隨皇帝巡幸及征伐活動而進行的七月七日秋祭則通過召集諸部、講武馬射、賞賜、宴饗等活動,宣揚了對其統治之下的各部族及領土的領有權力,展示了國威,加强了北魏皇權與政治中心之外諸部族之間的聯繫。對於部族勢力仍廣泛存在的北魏早期來説,其重要性可能並不亞於平城西郊祭天禮儀。
隨着華北的統一和北境戰事的消弭,北魏統治的重心逐漸向南轉移,巡幸的減少與講武固定於南郊是這一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在由部族活動轉向宫廷儀式的過程中,北魏講武不可避免的受到華夏禮儀文化的影響,在草原傳統的基礎上,依託於中原禮典,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有的講武禮儀。這一轉變過程發生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包含了胡、漢兩種因素,不能簡單的以“漢化”加以概括。它是北魏政治文化自然發展的結果,反映了北魏早期政治、社會發展的歷程。
另一方面,北魏七月七日講武衰亡的過程也反映了政治、政策改變與社會、文化變遷之間的差距。文成以後講武雖在九月實行,但胡族原有的七月七日儀式卻以宴饗的形式保留到了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使遷都洛陽,改胡服、禁胡語之後,七月七日馬射依然留存在地方與個人的記憶中。從這一點來説,政治上的斷絶與禁止並不等同於社會文化的改變。從《洛陽伽藍記》以及北魏後期出土墓誌的記載來看,北魏後期詩書文物,似乎一片“鬱鬱乎文哉”之景象,但孝文之後不到三十年,北魏即陷入混亂。相比於短暫的“後改革時代”的“文明榮光”,存續了將近一百年的“平城傳統”,是否依然影響着北魏後期宫城内外人們的生活呢?
在南北政權對立的背景下,講武禮儀經過北魏時期的發展,逐漸成爲重要的國家禮儀。南北使節往來時,講武活動則成爲雙方炫耀國威的政治舞臺。北魏太和五年(481),孝文帝因講武宴群臣,宋使殷靈誕與齊使車僧朗參與其間。*見《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第151頁;《魏書》卷九八《島夷蕭道成傳》,第2164頁;《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第988—989頁。兩年後,即南齊永明二年(483),齊武帝於玄武湖講武時,接見北魏使者李道固,“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第989頁。北齊於季秋講武於都外(後改爲季冬),又有四時田獵,北周則依《周禮》於四時田獵講武。*《隋書》卷八《禮儀志三》,第164—167頁。其時具體情況如何雖難以知曉,但從北周天和三年(568)十月,武帝“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的盛況來看,*《周書》卷五《武帝紀上》,第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76頁。北朝後期,以皇帝、大臣爲核心的講武活動,已轉變爲集合了京城居民、外國使者的大型展示活動。若將時代向下延伸,從唐代“公衆性”儀式文化形成的角度來看,*關於唐代的公衆性文化,參見(美)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 《唐朝的公衆性與文字的藝術》,《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2—191頁。唐代的政治與文化活動常常帶有公衆性的特點,而唐代的禮儀活動也常常帶有很强的展演性,參見(日) 妹尾達彦: 《唐長安城的禮儀空間——以皇帝禮儀的舞臺爲中心》,(日) 溝口雄三、(日) 小島毅主編,黄正建譯: 《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6—498頁;(日) 妹尾達彦著,劉瑩譯: 《唐代的科舉制度與長安的合格禮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9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北魏講武對於北朝後期及隋唐禮儀制度與文化的形成,亦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