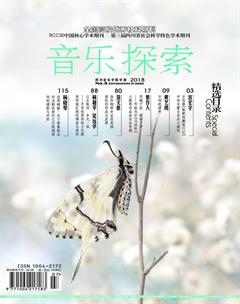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主曲调的比较分析
吕华珍
摘 要: 乱弹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取浙江区域流传广泛的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为研究对象,在查阅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两个剧种声腔的演变历史、声腔构成以及主要唱腔曲调展开对比分析,探索两个声腔剧种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差异性,总结它们的曲调特点,期许为学界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参考资料。
关键词: 处州乱弹;婺剧乱弹;主曲调;声腔剧种
中图分类号: J6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3 - 0050 - 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08
浙江乱弹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人们喜闻乐见、百听不厌,是极具地方特色、民间影响力大、群众热衷欣赏的戏曲声腔,堪称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乱弹的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艺术风格五彩缤纷,各剧种唱腔曲调和文武场音乐都各具特色、宏伟大气,伴奏形式别致多变,艺术手法协调和谐,演唱演奏技巧妙趣纵横,常让观众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语云:“戏曲、戏曲,一边是戏,一边是曲。”在浙江的乱弹声腔剧种中,流传区域面最广的要数婺剧乱弹。婺剧乱弹在金华、衢州两市及周边其它县市区均有所流传。除婺剧乱弹流传面最为广泛外,以处州乱弹为代表的剧种也颇具影响。处州乱弹和婺剧乱弹是浙江乱弹同声腔的两个不同称谓的地方剧种,长期以来深受地方群众的喜爱,成为一方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本文正是以在浙江地区流传广泛的两大乱弹声腔剧种的曲调特征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处州乱弹和婺剧乱弹之间主要唱腔曲调展开对比分析,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异同之处,为浙江乱弹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两个剧种声腔衍变的轨迹
自清代开始,浙江的乱弹声腔几乎遍布全省。其中,处州乱弹和婺剧乱弹是较有影响的两类。处州乱弹形成于清代初年,兴盛于清代中叶,因流传于处州(今丽水)、温州、金华等地区,并集中分布于丽水市莲都区、松阳县、缙云县、遂昌县、云和县、青田县等地而得名为“处州班”。处州乱弹班社繁多、剧目丰富,在流传的各县市区中,班社最多的区域要数现今莲都区(旧称丽水)碧湖镇、松阳县和缙云县。在声腔曲调方面,处州乱弹主要声腔曲调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三五七】与【二凡】为主的乱弹腔系;其二是以【皮簧】与【吹腔】为主的徽调腔系。由于处州乱弹与金华乱弹中徽调声腔、乱弹声腔的主要曲调渊源、形态相同,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婺剧。处州乱弹的腔系经历了由乱弹声腔的兴起、皮簧声腔的加入到高腔、昆曲及徽戏等声腔交融发展的过程。文献记载,清代光绪年间有处州乱弹到江西、福建等地演出,被当地人称为“浙调”“碧湖调”(或“湖调”)等,说明处州乱弹在光绪年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影响。
清乾隆年间,江西巡抚郝硕遵旨查办戏剧的复奏中记载:“石牌腔(吹拨)、楚腔(西皮)等,此时在浙江已经‘皆所盛行。” “兼唱吹拨和皮簧的班社,从三路纷纷流入浙江:一从江苏扬州沿运河至杭、嘉、湖一带;二从安徽歙县经新安江流入金华、衢州、严州;三从江西婺源(原属安徽徽州府)流入开化、常山一带。”由此可见,早期的处州乱弹是“双合班”,即两种声腔融合的演剧形态,主要由乱弹声腔和徽调组合而成,采用两种声腔同台演出的形式。徽调于清代光绪年间由安徽、江苏等地传至浙江丽水、金华和衢州等地。直至18世纪末期,处州乱弹在原来“双合班”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在缙云一带开始出现乱弹与高腔、昆曲、徽戏声腔合班演出的现象,被人们称为“三合班”(實为“四合班”,即四种声腔合成的剧班),为处州乱弹发展为多声腔戏曲剧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处州地区的乱弹班社数目繁多,且不同班社所唱的声腔也不尽相同,如青田县的“章旦班”“黄庄班”,松阳县的“吉昌班”,碧湖镇的“林月台班”等以演出处州乱弹声腔为主,其正本戏剧目多为处州乱弹腔;而流行于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和龙泉县等地的木偶戏班演出的大小剧目也以处州乱弹声腔为主,但有些剧目,如《耕历山》《拾义记》《夫人戏》等则以高腔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处州乱弹发展至今成为集乱弹、高腔和徽调等合流而成的多声腔戏曲剧种。处州乱弹的台词通俗易懂,念唱用处州官话,具有浓郁的地方韵味,音乐粗犷宏亮。演出时,班社后台五人,利用十余件乐器吹拉弹奏、曲调悠扬。丽水当地流传有这样一句俗话:“锣鼓响,脚底痒”,乱弹班社的鼓乐,总能使人精神兴奋,制造出热闹气氛。
婺剧乱弹,俗名“乱弹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被称为浙江乱弹,乱弹与明清时期开始流传在浙江的高腔、徽戏、昆腔、时调、滩簧调组成六大声腔统称为“婺剧”。婺剧乱弹包含着【三五七调】【芦花调】【二凡调】【拨子调】以及【紧皮】或【流水】五种不同类型的曲调。其中【三五七调】最早是明朝末期流行于皖南太平(今当涂)的“太平腔”遗音之一,因词格为三字、五字、七字,故俗名【三五七】;【芦花调】与昆曲、京剧中名【吹腔】或某些地方戏中称作【安庆调】的渊源相同,它既保留了原始曲牌连缀的特点,又运用了丰富的发展变化手法,是板式变化及曲牌连缀两者兼有的混合体;【二凡调】是婺剧乱弹的主要曲调,依据首句第一个句逗落音位置的不同将它分为“尺字二凡”“合字二凡”“上字二凡”和“五字二凡”四种类型。通过对其渊源的梳理和音乐形态的比较分析,【二凡调】并不是由邻近地方戏绍剧中的【二凡】传来,而是从【吹腔】【四平调】蜕化而来;【拨子调】在婺剧乱弹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源于徽戏的主要曲调,较少应用于皮黄腔剧种;【流水】源于徽戏中一种整板伴奏、散板演唱的曲调,在婺剧中被分为“夹板”和“滚板”,兼具固定音型伴奏与华彩性伴奏两种形式。
以上五种曲调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曲调之间不仅可以混合使用于同一出戏中,更可以根据剧情需要而灵活互转。一般来说,五种曲调在婺剧乱弹中“诸腔并蓄”,用于同一出戏,且必须遵循“同宫相依”的规律。所谓“同宫相依”即根据定调高低及曲调音区的不同,分成【芦花】—【拨子】和【三五七】—【二凡】两套,【紧皮】或【流水】则分作高低不同的两类,分别归属【芦花】和【三五七】。他们的组合结构相同,可以互为正反调。
二、两个剧种声腔渊源的异同
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是同声腔戏曲剧种在不同地域的称谓。既然他们属于同声腔剧种,所以两个剧种声腔渊源就有共性特征。在对比分析两个剧种之间主要唱腔曲调之前,对它们的源头进行探索研究,有助于充分认识两个剧种的主要唱腔曲调,从而为探索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唱腔的结构体系、唱腔在不同区域间的艺术衍变以及两个剧种间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形态提供相应依据,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两个乱弹声腔剧种的真实面貌。
关于乱弹渊源的问题,史籍中有不同的记载。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曰:“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乱而哀。”乾隆时期,李斗的《扬州画航录》写道:“雅部即昆山腔。花部即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前者说的“乱弹”指的是秦腔,后者指的“乱弹”则成了花部各声腔剧种的统称。这显然指的并不是处州乱弹或婺剧乱弹,而是将同时期产生不同的声腔都概括而谈了。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在浙江将各地流传的乱弹声腔班社剧团都冠名“乱弹”声腔班社剧团,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也给了浙江的声腔剧种与全国其它同时代产生的声腔及其剧种提供了艺术对比的历史依据和研究途径。
从历史记载来看,处州乱弹主要分布于丽水、温州、金华等地;婺剧乱弹主要分布在金华、衢州两市及周边区域。从流传分布的地域性看,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这两种剧种是带有一定的区域共性的。这或许是两个剧种同声腔的重要原因,它们的源起与发展必然有着一定的联系。经过笔者多年对两个剧种的采风调查,发现两个剧种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也存在一些异质现象。而造成两个剧种之间共性与差异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声腔渊源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声腔渊源相似是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两个剧种之间共性存在特征的主要因素,而声腔渊源的不同则是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两个剧种之间差异性表现的主要原因。
(一)两个剧种声腔渊源的相似性
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某些唱腔曲调的风格特征是比较接近的,这成为它们之间同戏曲声腔的基础。如处州乱弹唱腔的【反调】曲调与婺剧乱弹唱腔的【芦花】曲调,处州乱弹唱调【二汉】与婺剧乱弹唱调【二凡】都存在相近似的关系。作为同声腔的戏曲剧种,在某些唱腔曲调上出现这种关系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一个剧种是另一个剧种之源,或许是同出另一剧种之源。
依据调查、采访、分析、探索,笔者发现处州乱弹的唱腔曲调【反调】(谱例1)与婺剧乱弹的唱腔曲调【芦花】(谱例2)同源,都与安徽“石牌腔”系中的唱腔曲调【吹腔】(谱例3)息息相关。据乱弹声腔老艺人的说法:浙江乱弹声腔剧种的【反调】或【芦花】曲调是从安徽【吹腔】衍化过来的,而【吹腔】又称【芦花】或【芦花拨子】。因此,在乱弹声腔剧种中,婺剧乱弹【芦花】与處州乱弹【反调】属于同声腔的曲调,而乱弹中的【三五七】等曲调是【芦花】曲调经转调并衍化后的产物,它们之间是同根同源的“兄弟”曲调。
从上面处州乱弹【反调】、婺剧乱弹【芦花】与安徽“石牌腔”系【吹腔】唱腔曲调的谱例中可以看出,处州乱弹的【反调】与婺剧乱弹的【芦花】曲调,无论在旋法,还是调式、调性,以及结构的表现形式等都是比较接近或相似的。他们与安徽“石牌腔”系中的【吹腔】在旋律骨架上,在调式和调性方面也都有着血缘联系。这一切都说明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在声腔方面的相同点,而这相同点是建立在同源唱腔曲调【吹腔】基础上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充分说明声腔艺术之源相同的必然产生剧种之间某些艺术的共性特征。
(二)两个剧种声腔渊源的差异性
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两个剧种声腔在音乐表现形态方面也存在有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艺术要素的某些方面由于渊源不同则产生艺术上的异质表现,它不仅在唱腔方面有所反映,在文武场伴奏音乐方面也是如此;其二是作为地方剧种,他们吸收民间音乐作为戏曲声腔剧种源源不断的养料并融化为剧种的基本要素,这是包括戏曲在内的各门类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客观而理性的自然选择。也正因为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在生存流传的区域上有差异,从而吸收融化的民间音乐也有差别,故产生不同艺术之源环境条件下的艺术差异与某些不同特性的现象;其三是戏曲声腔剧种语音上的差别,并由此产生地方戏曲剧种“声”与“腔”的分化,同声腔的不同剧种在这方面出现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的艺术反映。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说明不同区域产生并流行的地方戏曲剧种,虽然是同声腔,但在剧种声腔渊源元素上有着鲜明的差异,从而出现某些不同艺术之源下不尽相似的表现形态。
三、两个剧种声腔主曲调的比较
处州乱弹的声腔音乐,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浙江诸乱弹声腔剧种,尤其是婺剧乱弹有相近之处,但在二三百年的艺术辗转实践中,形成了自身剧种的音乐特色,与婺剧乱弹等乱弹剧种在音乐上构成一定的差异。前面已对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声腔渊源及其异同的成因展开了对比探讨,下面,我们通过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声腔主要曲调的比较分析来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关系。
处州乱弹声腔主曲调由【平板】【乱弹尖】【二汉】【反调】【罗卜子】【慢板心】等板式构成。其中,【平板】(见谱例4)的演唱程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合方式,即先以散板头起唱,再接【平板】的原板,最后接唱【尾声】。处州乱弹几乎每出戏都要唱【平板】曲调,它是该剧种的核心唱腔曲调,音乐优美抒情,流利婉转,各种角色均可演唱。
婺剧乱弹声腔主曲调由【三五七】【芦花】【二凡】【拨子】等组成。在婺剧乱弹声腔的剧目中,【三五七】(谱例5)是剧中演唱的主曲调,是该声腔各出戏中必唱的曲调。它也有一套完整的组合程式,即从散板的“三五七叫头”起调,到进入原板【三五七】或进入“游板”接【煞板】结束句。曲调整体跳跃、奔放而热烈、协调并统一,塑造出非常雅致且交响融洽的艺术形象和色彩斑澜的音乐效果。
从上述谱例可看,处州乱弹的【平板】与婺剧乱弹的【三五七】两支曲调的旋律骨架、曲式结构、调式运用等基本相似。而且,他们的上下句结构和作为反复变化体形式的“副腔”,即第三与第四乐句形成的整体旋法和结束形式上都很接近。与此同时,【平板】与【三五七】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过门的旋律上:【平板】以 或 为主,而【三五七】则以 贯穿其中。并且,处州乱弹【平板】调高1=D,婺剧乱弹【三五七】调高1=C。还有,二者的伴奏也有着不同的地方,作为主奏乐器之一的笛在【平板】曲调中采用筒音作sol吹奏,而【三五七】曲调则以筒音作la吹奏。当然,其曲调各自取的名称【平板】与【三五七】也不同。
另外,从处州乱弹主曲调【二汉】与婺剧乱弹主曲调【二凡】,处州乱弹的【罗卜子】与婺剧乱弹的【拨子】,处州乱弹的【反调】与婺剧乱弹的【芦花】等主曲调,以及两剧种均同名称的【叠板】曲调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在旋律和句式的结构形式,调式调性表现状态和节奏及板式运用上都很接近,仅在某些音符的组成和调高以及曲名上有所区别。由此可见,两个剧种声腔主曲调有着相似或相近的表现形态,也有着明显区别的呈现方式。并且,两个剧种声腔曲调的各方面表现形式及结构也构成了剧种自身不同的色彩及特性,如同处在唱腔主曲调结束时具有【尾声】(谱例6)或【煞板】(谱例7)效果的唱句。
通过对二者谱例的分析比对,它们之间同名称的唱腔曲调如【哭板】【流水】等,也都有某些差别。
结 语
从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的声腔演变、声腔渊源和主曲调的梳理与比对研究中发现,尽管处州乱弹与婺剧乱弹是同声腔的两个剧种,在声腔渊源和主曲调方面有共同的艺术特征与表现形式,但也存在异质的表现形态,表现出地方特色和独特的风格特征。相似性有,两者都是以乱弹腔为基础,融合徽调、皮黄腔、高腔和昆腔发展起来的多声腔戏曲剧种;声腔渊源都与安徽的“石牌腔”系中的唱腔曲调【吹腔】有一定的关联;此外,二者主要曲调的结构安排方面也存在共性特征。在相异性的视角看,处州乱弹、婺剧乱弹是乱弹声腔流入处州、金华等地,结合民间音乐音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受其它声腔音乐及当地民众审美習惯的影响,都具有各自地域风格特色,呈现出相异的表现形式。这些正是两个剧种具有各自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两个剧种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本篇责任编辑 何莲子
参考文献:
[1] 杨和平.处州乱弹活态现状研究[J].中国音乐,2013(4):74-77,98.
[2] 杨松权.处州乱弹与浦江乱弹音乐比较研究[J].音乐探索,2017(2):111-114.
[3] 程郁.处州乱弹及其唱腔音调研究[J].中国音乐,2015(4):224-227.
[4] 周云杰.丽水乱弹提线木偶戏的戏曲音乐特征分析[J].艺术百家,2016(5):228-230,233.
[5] 周雅慧.怎样传承与保护古老的戏曲——处州乱弹[J].大众文艺,2012(17):136-137.
[6] 张祎.“婺剧乱弹唱腔【三五七】源自【望江南】”驳议[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7(1):73-76.
[7] 于善英.浙江地方戏曲唱法特性研究——以婺剧、甬剧、台州乱弹为例[J].艺术教育,2015(10):68-69.
[8] 叶晨俐.浦江乱弹 婺剧的基石与先声[J].今日浙江,2015(3):52-53.
[9] 章军杰.多元文化格局下婺剧传承与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10] 张祎,康瑞军.从婺剧乱弹【三五七】看戏曲曲体的发展轨迹[J].音乐探索,2011(2):19-22,27.
[11] 袁波.金华婺剧高腔、昆腔、乱弹、徽调的声腔特点[J].大众文艺,2011(5):71-72.
[12] 施维.婺剧乱弹声腔主干唱调“二凡”析[J].中国音乐,2007(2):102-106,146.
[13] 周大风.婺剧乱弹音乐初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4):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