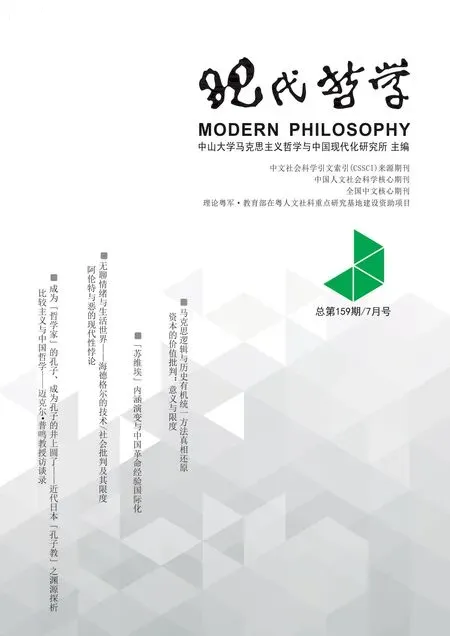亨利生命现象学中的生命言说问题
刘 宏
米歇尔·亨利在他的作品中讨论了很多议题,既有解释感觉、情绪、意志等传统问题,也有阐发他自己所提出的生命自我感触、生命言说、艺术的本质等新问题。其中,亨利对生命言说的思考占据着他不同作品的关键位置。亨利所做的就是要揭示生命言说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一种言说生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的这些尝试都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重新反思他的努力。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即亨利如何描述生命、亨利在其不同文本中阐发生命言说方式的尝试、这些尝试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不同著作之间的张力,试图探寻生命言说的模式以及言说生命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笔者重点探讨了亨利的这些尝试蕴涵的问题、在他不同的文本中存在的张力以及构成言说生命困局的原因,进而提供一条走出困境的可能性道路。
一、亨利对生命的描述
亨利指出,现象学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界定:一是作为方法的界定,一是通过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他指出,应该排除关于现象学的作为方法的界定,即一种实践着的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声称自己达到了确定结果的意向性解释方法。然而,“由于意向性是现象性的原则和唯一标准,它完全控制了显现,并且把显现还原为它的观看,因此意向性不能在它自身之中确立:作为一种使-观看,意向性不得不朝向被观看者,由于它的观看实际上不是其它东西,恰恰是被观看者的被看到,所以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对象被它的对象性条件所限定,并且在这个条件中被取消:在注视的对面被如此设定”*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 Paris : PUF, 2003, p.110.。亨利之所以排除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判定进路,是因为他看到了历史现象学方法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并没有回答纯粹现象性的现象化的方式,即现象之成为现象的原本过程,因此,现象学就停留在不确定性和总体的模糊性中。“还原让胡塞尔同时朝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它引导他到新康德和笛卡尔的方向上,视先验自我为所有自我经验的形式结构;一是,它引导他到另一个方向上,意识在此一直被意向相关物缠绕着,完全被卷入世界中。”*Dermot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 Routledge, 2000, p.12.
马里翁总结出现象学还原的“发展历程”:1.胡塞尔进行的“先验还原”,回到先验自我的意向结构,以先验自我构成思维对象;2.海德格尔进行的“存在还原”,通过此在回到存在的意义,现象学还原意味着我们的目光“从被朴素把握的存在者向存在的引回”*Martin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ränomenologie, Satz und Druck: Limburger Vereinsdruckerei GmbH, 1975, p.28.(中译本参见[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页。),换言之,“按照现象学的最内在的倾向,现象学的追问把自己引向了意向式之存在问题,而首先是把自己引向了存在本身之意义的问题”*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p.184.(中译本参见[德]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5页。);3.马里翁进行的“第三种还原”,回到存有召唤的纯粹形式*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momenology, trans. Thomas A. Carlson,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3.。较之于马里翁的“饱和现象”概念,亨利聚焦于现象学的对象,即生命的自我显现。因为“生命分裂了现象学对象和进入其中的方法之间的同一性”*Michael O’Sullivan, Michel Henry : Incarnation, Barbarism and Belief, New York : Peter Lang AG, 2006, p. 68.,在生命自我显现的中,显现自身得以显现。生命的自我显现是为其他现象奠基的源初显现。揭示这个源初显现的模式就是生命言说的过程。
亨利试图在其作品中探寻生命言说的方式。但是,他从未给出生命的严格定义,只是在他不同的作品给予生命概念以不同的说明。其中,最主要的表述是:1.生命是在其存在的任何方面都拥有感受自身和经验自身的功能和力量。它是本质的力量和感受,在自身的永久的痛苦与快乐的激荡中与自身同一,是绝对的自我感触,因此在根本上它是不可见者。2.生命在其不可见的内在性和本质的内在中感受和经验自身,在自身的感触经验中经验自身,拥抱自身,在其自身中经验自身,直接与自身同一。“生命显示自身,也就是说它向自身显现自身,正如哲学上所说的,它是自我显示(自我显现)。这一生命的的本质特性可以在它的任一形式中发现。”*Michel Henry, Words of Christ, trans. Christina M. Gschwandtner, Cambridge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p. 38.概言之,亨利哲学意义上的“生命”蕴涵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非意向性。生命的显现方式不依赖意向性意识。根本而言,生命是非意向性的自我感触。作为生命自我显现行为的自我感触优先于意向性意识。显现的本质是显现行为的自我显现。它必须是自发的,因此,它是生命的自发感触。
第二,绝对的内在性。生命的本质是生命和它自身的同一,它只能在其自身中感触自身,因此,生命是纯粹的绝对内在。内在性是原初显现的根本形式,是显现的自发形式。在亨利眼中,现象有两种显现模式,即内在性的模式和超越性的模式。后者指事物在意向性表象中的呈现。然而,超越性并不能产生属于自身的现象实在性,因为超越性不能确定地解决超越性自身是如何显现的问题。故此,超越性并非显现的自主性形式。但是,内在性和超越性并不是对立关系。“内在性是超越性的本质,因为前者揭示了后者,准确地说,内在性在其本质中给予了超越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前者揭示了后者。”*Michel Henry,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trans. Girard Etzkorn, The Hague, Netherlands : Martinus Nijhoff, 1973, p. 312.简言之,生命的绝对内在性是超越性的可能性条件。
第三,感触性。正因为生命的显现就是生命本身,因此它不是对象化的产物,也从不在世界中显现自身,而是一种绝对内在性的自我感受。“在一种生命哲学中,用我的基本术语说,生命是一种自我感触(une auto-affection),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自身而非世界的感触”*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 Paris : PUF, 2003, p. 287.,因此,它发生在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情绪中。在生命的自我显现中,在情绪中,生命在其自身中感发并揭露自身;它在自身的痛苦和快乐中,在充沛的内在性和活生生的生命中经验自身并与自身同一。它自身的痛苦和快乐是非意向性的,它们也不是关于某物的痛苦或快乐。
第四,不可见性。内在性的生命具有神秘的不可见性,因为“内在性并不以外在显现的方式显现,它是不可见的,这意味着它不在世界中绽出”*Michel Henry, Seeing the Invisible : On Kandinsky, trans. Scott Davidson, New York : Continuum, 2009, p. 7.。准确地说,“要观看就必须有一段空间的距离。但是,那里并没有距离,启示仅仅在感触性的肉体中没有间距地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根本的意义上,生命的这一维度是不可见的”*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 p. 289.。作为绝对内在性的生命,它始终是不可见的,以不同于可见的方式显现自身,即它不在超越性的世界视域中绽出,而是在自身中通过自身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
因为生命是绝对内在性的自我显现,它不会在外在化世界中绽出,所以任何文本语言和逻辑都外在于生命的自我显现;而任何文本都运用了语言和逻辑,因此,文本并不能通向生命。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文本的形式言说生命自身?该如何言说生命?如何可能回归到真正的内在生命呢?
二、亨利探索生命言说的尝试
艺术在马里翁的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他认为美学经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链接可见者和不可见者的桥梁。马里翁更为关注艺术史,重点讨论了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的作品。他对艺术的分析侧重于考察可见者和不可见者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可见者如何通过绘画这种艺术形式转变成可见者。他认为,不可见者在圣像中在双重意义上横穿可见者,一方面可见者因为不可见者而被打开,另一方面不可见者是可见者得以可能的原因。在他看来,绘画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现象——毫无不可见者位置的可见者——偶像(idol)。“换句话说,不可见者在其自身中揭示可见者。”*Jean-Luc Marion, The Crossing of the Visible, trans. James K . A . Smith,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因为不可见者的作用,我们当作可见者来知觉的东西才不是混杂而狂想的景观。可见者的成形是得益于不可见者的恩惠。艺术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见者,与此同时,世界的现象性因为新的可见者而变得更为丰富。伟大的作品实现了一种现象学的还原,使我们的目光朝向纯粹可见性。
而亨利认为,艺术试图揭示的是一种超越事物的隐匿显现,它启示了一个原初的领域,带我们回到生命的原初显现。他聚焦于抽象绘画,特别是康定斯基的作品和理论。亨利试图通过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展现生命言说的模式。他指出,康定斯基在西方艺术领域开启了一场革命,这次革命打破了绘画是模仿世界的陈规。对某个物象的表象并非绘画,那只是某个物象的摹本。抽象绘画开创了一种新的绘画显现模式,绘画是色彩和形式而非对某个物象的表象,绘画的自我显现必然是色彩和形式的自我显现。康定斯基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表达了言说生命自身内在感受的真实性。“一旦艺术家的情感力量压过了所谓‘如何表现’的物化追求,并为艺术感受释放空间,那么,艺术就开始步入正轨,并且重新追求那曾经遗失的‘表现什么’的答案,这正是艺术生命所赖以呼吸的精神实质。这个‘什么’的追求,不再是艺术停滞期的那种物质化、客体化的追求,而是对艺术本质和灵魂的追求。”*Wassily Kandinsky,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trans. Micheal T. H. Sadler, Auckland : The Floating Press, 2008, p. 35.亨利强调,艺术不该陷入客观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深渊,而应回归到自身的真精神之中,回到内在的真纯的感受性之中。因此,亨利指出,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并非是绘画领域的单一精神运动,它表明了所有艺术的内在真理。康定斯基在其作品中系统地分析了作为绘画基本要素的色、点、线、面。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绘画理论代表了所有艺术理论,抽象绘画定义了所有艺术的本质,即所有的艺术都是对生命的言说。艺术要脱离外在世界的束缚,回到内在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无疑是单调的,也是抽象的,因为它脱离于对外在化可见世界的任何依赖。康定斯基开创的革命揭示了言说生命的话语。不可见的生命是在我们自身中成就自己并且它是优先于可见世界而被给予我们的。
那么,绘画艺术如何言说生命?通过聆听寄居在各种对象内部的内在性回音,康定斯基发现了抽象。“每一种现象都可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体验,这两种方式不是随意的,而是与现象相关的——它们取自现象的本质,取自同一现象的两种特征:外在性的——内在性的。”*Michel Henry, Seeing the Invisible : On Kandinsky, p. 5.这一发现是对不可见的生命的发现,不可见的生命散布于各种要素之中并支持着它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断地从两个方面体验着现象,即康定斯基所谓的“内在的”模式和“外在的”模式。
外在的显现模式是对象在视域中的绽出,也就是说,它成为客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现象外在的显现意味着它在世界的绽出并成为可见者。“世界是可见者的世界,因为世界意味着外在性,外在性构成可见性。”*Ibid., p.6.外在性的现象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在性而被我们认识。在世界之中意味着外在性,现象外在性地显现自身,外在性等于显现,在外在性显现中,现象成为显象和可见者。
与外在的模式相对的是现象的内在性模式。“内在性是更古老的和更根本的给予模式。”*Ibid., p.6.现象的内在性显现揭示了现象本身不可见的情感力量。就内在性而言,绘画的元素不是色和形的物质形式,而是它们在自身之中展现的内在情感力量。例如,蓝色展现了一种安宁的情感力量,反映的是生命宁静的话语;白色意味着绝对的静谧,反映了生命降临前的虚空;点和蓝色类似,表达冷静;之型线体现了生命的不安和躁动。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艺术转变了我们对绘画和艺术的认知,它寻求表达色彩和形式的原初显现,即现象的内在性。色彩和形式的内在性是生命悲婉语言的体验,它们共同描绘着不可见的生命。色彩的运用并非来自对世界的临摹,而是源自它们的内在情感力量,形式的选择则源自它们对生命主体力量的凸显。对色彩的挑选并非源自它们与外在化世界的相似性,而是基于它们的内在情感力量。点、线、面的运用表达的正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力量模式。对作为不可见的形式和色彩本身的强调,康定斯基使得构图的法则脱离于外在化的客观世界,并将它们安置在主体性经验的情感中。所以,抽象绘画可以言说生命自我感触中的所有悲婉。
外在的显现模式和内在的显现模式对应着抽象绘画的物质要素和色彩、形式本身。我们必须从两个视点观察绘画,即它的外在物质要素和内在情感力量。前者是绘画的意义,后者是它的内容。“在画布或者纸张上的色彩和形是外在的,然而,任何形都是一种力量,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这种力量就是生命的悸动,是生命的欲望、不可见的力。”*Michael O’Sullivan, Michel Henry : Incarnation, Barbarism and Belief, New York : Peter Lang AG, 2006, p. 174.在抽象绘画中,“绘画的内容经历了一种本体论的转移,它从一种存在形式转移到了另一种存在形式,从外在转移到内在;意义则依然在可见的光照世界中展现它的存在,在色彩和形式中,在它们的可感显现中展现和被感知”*Michel Henry, Seeing the Invisible : On Kandinsky, p. 9.。这意味着抽象绘画最终实现了内容的本体论转换,成为内在化的内容。绘画的内容成了内在的,意味着不可见的生命不再是不可见。例如,“世界上并不存在红色。红色是一种感觉,它是绝对地主观的,最初并不可见。原始的颜色是不可见者,但是它们通过一种投射的程序在各种事物上得以延展”*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 p. 290.。它是一种展现,展现了生命的不可见性,描绘的是抽象;它是一种表达,它的目的是言说不可见的生命。这也就是说,“生命=悲婉=不可见者=内在=本性=抽象”*Michel Henry, Seeing the Invisible : On Kandinsky, p. 11.。
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通过“看”绘画而言说生命。我们只能在欣赏绘画而产生的自我感触中言说着生命自身,在我们倾听色彩和形式变化的音调中言说着生命的本质。绘画的主题是属于纯粹的色彩和形式所显现的生命的悲婉。简言之,绘画艺术是言说生命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通向生命本质的道。
基于康定斯基的美学理论,亨利从中发现了言说生命的可能性,他试图通过康定斯基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一种言说生命的合理化模式。康定斯基的色彩和形式理论详细地描述了各种色彩和形式的色调、力量。作为绘画要素的色彩和形式向我们展现的是它们的音调。它们的音调是统一的,都表达了生命的情感,生命的主体性和感受性在这些要素中显现自身。同时,生命的自我同一性并不与色彩和形式的变化性、多样性冲突。因为现实中,我们的生命不断地从一种感触过渡到另一种感触,生命这种不断地感触自身的运动即是色彩和形式变化性与多样性的原因。色彩和形式在抽象绘画中的变化就是对自身色调和力量的表达,就是在表达不断地自我感触的生命。
三、言说生命的困境
抽象绘画要素的运用、变化、组合、分解言说着生命的自我显现。“抽象绘画是在其绝对主体性的黑夜中拥抱自己的生命”*Ibid.,p.16.,抽象艺术诞生于生命的不断自我感触,“艺术是永恒生命的重生”*Ibid., p. 142.。然而,亨利在《野蛮》中又明确表示艺术只是对生命的表象,即在艺术中看到的只是“生命的表象,生命本质本体的表象”*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Scott Davidson, New York : Continuum, 2012, p. 36.。相对于其他哲学,他认为自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对他而言“难以找到一些概念方式去表达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学”*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 Paris : PUF, 2003, p. 289.。他认为显现不仅指世界的显现,而且包含悲婉的给予和启示。它是感触性,在纯粹的内在性经验自身。“显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一种异质感触中给予;另一方面,则是悲婉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我们从未看到的。”*Ibid., p. 289.只有生命能够通向生命,它即是终点又是道路,“在生命的本质和最内在存在的意志中,生命是永远不会在现象性的绽出维度中显现自身,即生命永远不会在世界中显现”*Michel Henry, Barbarism, p. 36.,所以对生命的表达只能是对生命进行表象。艺术将生命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它只是生命的表象,并不能等于生命。这意味着艺术对生命的言说始终只是对生命的表象。这样,亨利试图言说生命的尝试就陷入困境。
亨利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为此,他力图严格、准确地区分两种言说,即世界的言说(word of world)和生命的言说(word of life)。世界的言说是绽出的过程,是“‘外域’的到来,在外域之中,我们看见之物和我们述说之物被给予我们。言说意味着显现:使—被看见、使—显现”*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or, pathos and language), trans.Leonard Lawlor,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32, 1999, p. 346.。亨利举例说,我们通过听觉器官听到话语,然而听觉只能听到在我们之外、在世界上的共鸣,即声音、这个世界的噪音或者人类交流的词语。它们是世界上感觉到的声音复合体的一部分。“和视觉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在世界之中的可见者。”*Michel Henry, Words of Christ, p. 106.我们的感觉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力量,它们迫使我们接受世界,并在我们之外展示世界。“听是世界言说的模式,这种言说模式在我们之外,在世界之中述说着它自己。”*Ibid., p. 106.在这个意义上,聆听意味着声音在世界之中的传播。
生命言说基于生命的显现模式。“先于世界言说而且完全不依靠世界的言说的神秘现实性存在,生命的言说不仅能让生命在场,而且能够生成它言说的现实。”*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or, pathos and language), p. 353.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给予的生命,又是被给予的生命。“生命显现自身的方式就是生命言说自身的方式。因为生命在自身展现中显现,而不是在世界之中,在超越自身的差异之中显现自身,所以它与其他言说截然不同,世界的言说常常和自身之外的指向物关联,然而生命的言说道出了不同的特性:只是自说自己。”*Ibid., p. 353.总体而言,亨利在其著作中不断地迂回,试图严格、准确地说明生命言说方式的基本内涵,进而说明我们聆听生命言说的方式。
两种言说分别对应着两种聆听模式,一是意向性的和范畴的聆听模式,一是感受性的和内在的聆听模式。然而,“生命的言说是不可听的”*Michel Henry, Words of Christ, p. 107.,也就是说,意向性的逻辑不能表达生命的言说,我们只能在生命自身倾听生命的言说。这样的言说方式并由此所传递的言说是否意味着,生命的言说只能在个体的自我感触中显现?任何在世界视域中显现都不能揭示生命的自我显现,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生命言说的意义?两种模式之间如何转换?
相对于其他哲学,亨利认为自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对他而言,“难以找到一些概念方式去表达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学”*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 p. 289.。因为哲学或者艺术所表达的不是生命的内在的自我显现……表达生命的思想也不是生命本身,思想仅仅是对生命本身的表象。即使哲学和艺术都源自生命,也不能保证它们必然可以准确地言说生命。那么,对不可见者的给予方式的描述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难道纯粹地从“内在性”出发的哲学最终只能诉诸于“信仰”吗?
笔者认为,亨利的生命现象学试图兼顾两方面的内容:1.“看”并不依赖于“所见”;2.这样的现象如何可能。他强调生命的悲婉不依赖于“看”,它是自发感触,又强调我们并不能准确地感受到这种感触。如果我们能准确地感受到这种感触,那么它就不是生命的纯粹悲婉,而仅仅是一种意向对象。
现在问题聚焦于“看”和“所见”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看”有三个构成要素:看的能力、看的对象、光照。看的能力首先是和光照相遇,进而发生同类相感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看的行为把它触及到的物体的运动传播到全身,直抵灵魂,引起我们称之为看的感受。由此可见,构成“看”的三个要素是实现“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为清楚明白地分析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借助三段论的形式。首先,分析看的能力和看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三段论一:
1.看的感受总是与看的行为相关,
2.看的行为总是与看的对象相关,
3.结论:看的感受与看的对象相关。
进一步明确“看”其实就是“意向”的同义表达,那么可以用“意向”代替“看”在三段论一的表达。由此,三段论一可转换为三段论二:
1.意向的感受总是与意向行为相关,
2.意向行为总是与意向对象相关,
3.结论:意向的感受总是与意向对象相关。
可见,意向的感受总是与意向对象相关,生命悲婉也总是与意向对象相关,生命的欢愉也总是对美好事物的欢喜。在这个意义上,“欢愉的感受之所以是一种异质感触性(hetero-affectivity)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对象而非不可对象化的纯粹自我感触”*Brian Harding, “Auto-affectivity and Michel Henry’s Material Phenomenology”, in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2012, p. 98.。这意味着非客体化的行为奠基在客体化的行为之上。根据以上两个三段论的推理,生命悲婉是超越生命自身的,它总是与对某物的感触相关。
如果加入第三个要素“光”,那么三段论二是否会发生改变?“看”和对象的关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光”。这里,“光”是一个条件、功能。如果将亨利哲学中的悲婉概念等同于“光”,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悲婉是意向性和意向对象关系可能性的条件。进一步推理,作为不可见的生命是可见者可能性的条件。基于这样的替换,三段论二的第一个前提将会发生改变。“相关”表明了主项和谓项之间的超越论的联系。可见,意向的感受是意向性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三段论二的大前提会发生转变则得出:
1.意向的感受是意向性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
2.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关系是意向性的,意向的感受是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关系的超越论条件,意向的感受即是生命的悲婉,
3.因此,生命是非意向性的。
由此,“看”与“所见”分离了,生命不依赖于意向性,成功地论证了生命的言说方式不同于意向性的逻辑述说方式,进而表明对生命的言说可以脱离于世界的语言。
但笔者认为,亨利未必会赞同这种解读模式。因为生命才是逻各斯的原初形式,它是一切思想和推理的基础。为了说明这点,亨利以疼痛为例。我们直接感受到我们的疼痛。我们一般将疼痛理解为物理疼痛。然而,如果我们将疼痛还原为身体-疼痛本身,还原为疼痛本身的纯粹感受要素,那么,在生命的自我感触中,活生生的疼痛“告诉”我们疼痛。这样一种“告诉”形式就是逻各斯的原初本质。生命的自我显现是生命的言说,它是逻各斯的原初形式,是超越性的显现模式的基础,超越性的显现模式是意向性逻辑得以可能的条件。这意味着意向性的逻辑最终奠基在生命之上。因此,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地运用三段论言说生命。进而,意向性的语言不能阐明生命的自我显现,那么就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意向性的现象学能够准确地描述生命。
笔者认为,言说生命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思本身的局限性,一是生命本身的不可见性。言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困局。言说-思总是超越性的显现,某物的存在被言说、被思意味着某物呈现在意识之中。但是,显现本身的显现是某物在意识中得以某种方式被给予的基础。“关于某物的意识”在言说某物的过程中实施了一种暴力、一种遮蔽,它遮蔽了显现的自身存在,因为它用存在者的显现代替了显现本身,因为显现全都指向异于自身的他者,朝向外在,于是显现不再是显现本身的显现,而是被显现者的显现。然而,生命作为自我体验自身的自我感触,必然独立于意向性意识,独立于所有可见的超越性视域。“感触性是生命的现象学本质,在这个印象性的肉身之中,意向性的看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纯粹的非意向性。”*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 Paris : PUF, 2003, p. 117.言说-思与生命是完全异质的,对于言说-思而言,生命的悲婉是一种先验感触性(affectivité transcendantale)。
因此,我们试图用“言说”去传达生命本身就已经是对生命的破坏,但如果去除“言说”的方式,就无疑将生命神秘化。“面对”生命,如果我们最终只能是诉诸于信仰,那么无疑又将生命狭隘化。由此,它依旧是个“迷”。
四、结 语
我们应该如何解开生命言说模式这个“哥丹结”?笔者认为,可以在亨利使用的疼痛例子中发现一条阿里阿德涅金线。这就是身体。
亨利将“自发感触”和“身体”联系在一起,说明生命与身体的同一关系,进而提出三种身体的区分,即主体身体(subjective body)、客体身体(objective body)、有机身体(organic body)。一方面,我是这个身体,我在内在中感触我自己。换句话说,我是身体,我与它各种力量的运用和谐统一,比如我看、我听、我移动我的手、我感触。在这些过程中,我等同于正在进行的看、听、运动的感触。这个主体性的身体是不可见的,它只能自发感触自我。亨利认为,身体的内在感触性涉及的是显现的本质,这种模式是自发感触、自我显现。进而,它直接与生命的自发感触相关。一方面,我是这个身体意味着我与它是外在性的关系。因为我能看到它、触摸到它、将它视为客体。它作为一种对象存在于世界、空间中。另一方面,我的身体又是有机身体,它意味着我作为动物而具有的身体,是我身体各种器官、功能的集合体,它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完成我作为动物身体的基本需求。
然而,三种身体不是说我具有三个不同的身体,而只意味着我-身体的不同显现模式。一方面,我-身体在绝对的内在中自发感触自身,自我显现为主体性的身体。另一方面,我-身体是自我显现的感触主体,我感受到了我思故我在*Michel Henry, The Genealogy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Douglas Brick,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换句话说,外在化的身体存在、对它的思想-言说都是奠基于主体性的身体。我是我的身体,我是我的自发感触,身体在同一性中实现了不同显现模式的共现,生命就是在身体同一性的共现中言说自身。简言之,我完全是纯粹的主体性感受自身,生命和身体是天然的统一体,身体是言说生命和生命言说自己的天然舞台,它自显生命的言语和悲婉。
总体而言,米歇尔·亨利对生命言说模式的探讨为当代提供了一种言说生命、言说身体、言说艺术本质的可能性道路。他所开创的新视角不但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生命言说的大门,而且推动了现代哲学对身体、逻辑语言、艺术思考的进程。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