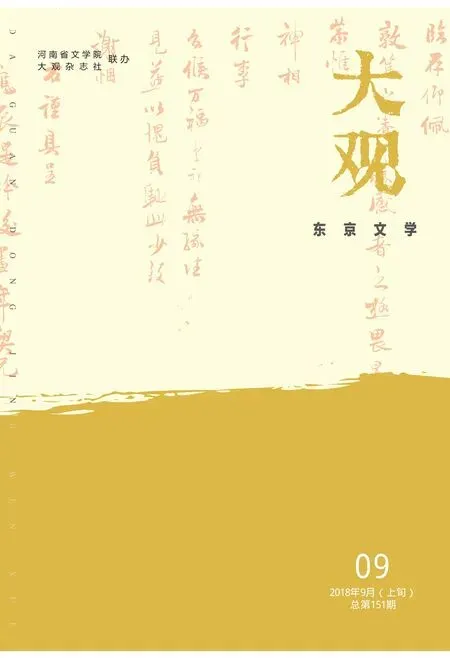不老的风景
杨厚均
这一回,聂鑫森先生向我们展示的仍然是他的短篇,他的三个文字极其节俭的小短篇。三个小说,加起来不过六千余字。
《下午茶》。《别墅院的菜园子》。《比邻》。正如三篇的总题“凡人俗事”所示,三个小说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人事:《下午茶》写机电厂厂长劳乐和他的同学茶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言默两人之间的一次茶聚,名叫“放下”的茶具是小说的“心眼”所在,揭示的是“闲可生静,静可生凉”的人生态度;《别墅院的菜园子》把身处城乡两地一家三代和睦相处的故事,引入到对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与忧虑之中;《比邻》讲述的是一对老邻居间友善诚信的往来。
说实在话,仅就小说主题本身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多可说的。尽管,三个小说,作者还是动了一些心机:通过三种不同生活空间——城市、城市准乡村(公园式别墅)、原生乡村——的琐事来演绎传统文化永恒的命题。这的确让我心生感动。但我不得不说,小说让我保持持久兴奋还是它的文体,它的节俭的文字。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今天的小说是越写越长了,而聂鑫森却是少数专注于短篇的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辈作家孙犁、汪曾祺等炉火纯青的写作,成为文坛美丽的风景,一些中篇长篇作家,也非常重视短篇写作,优秀作品迭出,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一开始写短篇就非同凡响,只可惜后来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并不擅长但却能带来诸多好处的长篇中去了。那个时期每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含金量非常之高,影响也是非常之大。聂鑫森就是那个时候冒出来的短篇高手,我甚至曾经预言,他的短篇小说极有可能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当然很不幸,这预言没有成真,这应该不是我的不是,更不是聂鑫森小说的不是,是文学的整体氛围发生了大的变化的缘故,那个奖不知从哪一年起就没有了。
可贵的是,在短篇这块园地,聂鑫森一直坚持了下来,不高产,但从不断线,细水长流,更其清醇。我曾冒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他就能乐此不疲呢?
我们的确感到了他对于这样一种节俭文体的偏爱,我们甚至感到,这种节俭文体的背后,是作者一片深切的文化情怀,一种顽强的文化心理,一股巨大的文化力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谈论孙犁、汪曾祺时,常常会言及古代笔记体小说,言及刘义庆,言及传统文人,我们今天谈聂鑫森是否还是可以沿着这样一条线索?
还是来看这三个小说吧。
小小的篇幅自然是无法容纳太多的人物的,《下午茶》只有两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好友,《别墅院的菜园子》虽是一家五口,母亲、孙女基本上没有怎么出场,母亲只有一句话,孙女也只有被动答话的两句话,实际在场的也只有父亲秋满仓和儿子秋声赋儿媳宦静静三人,《比邻》虽然涉及到的人物有两家两代同样五人,但真正的主角则是常惠生一人,全文基本上就只是写常惠生一人的行为和心理。
人物的多寡,同时也决定了场景转换的频率与场景规模的大小,三个小说的空间场景也是极为简单的,中心场景基本上就是每篇一个:一个茶室,一片菜园,一条通往邻居家的山路。极简的人物和极简的场景,到底是文体本身的规约,还是文体选择者的内在的文化审美取向?在一个人口高度集中的现代社会,在生活空间因我们对速度的征服和我们不断扩张的欲望的推动而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转换,同时被越来越多的物质景观所充满的时代,作者的这种选择是否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悲壮?
与此相应的是故事的波澜不惊。只有微澜,不见风浪。一次茶聚,就足以平息劳乐满身心的焦躁;秋家两代观念的错位,因相互的体谅而避免了尖锐的冲突;常惠生与尹德山的善良与诚信轻而易举就化解了旁人的议论与家人的不满。在这里,没有巧合,更没有博弈,一切就这样简单自然,这样流水般逶迤而安静。
小说的节俭之处还在于结构布局上的直接与朴实。开局没有景深,不作铺垫,直接进入现场;中局不生枝蔓,不弄玄虚,不设枢纽,多以对话、心理活动直接推动演绎“故事”;结局水到渠成,戛然而止,没有卒章显志、悬念大白的快意情节设置。如果用摄影术语来形容的话,三篇小说,既不是远点聚焦,也不是近点聚焦,而是中点聚焦。如果说远点聚焦与高远飘逸的审美心理相联系的话,近点聚焦则更多一份深入现实追寻刺激的精神诉求,而与中点聚焦相伴随的却是一份朴实无华的人生趣味。
人物、故事、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奠定了语言的走向。小说的语言同样是节俭的。首先表现在心无旁骛的语言流向。如果我们把一个文本的语言形容为一条河流,那聂鑫森小说的语言便是一条平缓的没有弯道和洄涡的河流,不会在任何一个局部做过多的停留,而以此来宣泄自己的语言快感,行其所行,止其所止,朝既定的目标缓缓而去。其次是简单明白的陈述句式。小说并不在意句式摇曳多姿的变化,大量的陈述句式运用,虽显单调,却也淳朴自然。《下午茶》的开头:“在这个三伏天酷热的下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到处生烟。焦躁的劳乐开车来到湘楚茶文化研究所,然后从车里蹿出来,直奔这栋小楼的三楼,敲开了言默工作室的门……”,寥寥数语,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以及劳乐焦躁的性情尽交代完毕,这样一种在当下创作中并不讨巧的言语方式,在聂鑫森这里依然运用得如此得体、娴熟。蜻蜓点水式的传统白描手法的运用,是聂鑫森小说语言的另一特色。与白描相对应的是各种各样的修辞,烘托、对比、比喻、拟人、排比、反问、顶真等等不一而足,聂鑫森的小说在这些方面似乎显得异乎寻常的麻木,整个就是一个实心眼,修辞的缺席,导致语言的经济、实在,内在的是主体情感的深藏不露,因为在我看来,修辞的出现,原是言说者主体强势介入的结果。
说到情感,这的确是我们理解聂鑫森小说的关键。很明显,三个小说,简单朴实的背后是一种浪漫情怀,一种对传统的钟情与守望。作者曾在他的某个小说的创作谈中说自己“还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尤对国学方面的书情有独钟”,说他的小说“不着意于故事的编排、营造,都是日常生活的碎片,似乎很散,但笼罩其间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氛围”。奇怪的是,我们在小说中明明感到这些,却并不知道作者的这种浪漫到底从哪里流溢出来。我们甚至看不到作者对他笔下某个人物的特别细致的描写,他似乎是默默地看他们,看他们不紧不慢,看他们独来独往。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聂鑫森的作品中,很少见有年轻美丽的女性主人公的在场。一般来说,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总会把自己的理想符号化为一个女性主人公,这样更方便他隐晦而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前面提到的孙犁、汪曾祺,他们都曾表示要除尽火气,要把文章写得散淡,但他们的作品里都有标志性的女性符号,在这样的符号里,作者尽情地投射自己的情怀。作为聂鑫森同乡的湖南作家,如沈从文、周立波等同样以短篇小说著称的浪漫作家均是如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聂鑫森这里,美丽女性符号的缺席,是他人生态度更为沉潜所致?这样的一份淡定,莫不正是传统文化的真谛?
几个散淡的人物,相对封闭的空间,波澜不惊的故事,朴素的布局,平淡的语言与深藏的情感,这几乎就是聂鑫森短小说的全部文体特质。
聂鑫森最近说,上年纪了,总喜欢写短些。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把小说写得很短。他的短小说的文体特质,三十多年就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越写越老到以外。大凡一般作家,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是要另辟蹊径,寻求自我突破。然而,这种自我突破的意识,在聂鑫森这里似乎并不强烈,几十年来,他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子,不紧不慢,不温不火。这需要多大的定力,多强的内心?和他作品中所讲述的传统文化相比,我觉得,聂鑫森的这样一种文体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彩而顽强的演绎,他这样的文体在后现代文体纷乱的时代,将是一道不会褪色的风景。
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某个夏天和我的表兄胡厚春(株洲作家)去拜访聂鑫森的场景:瘦高的他穿着宽松的白布大褂,因高大而微曲的身子,显出几分天生的低调,摇一把蒲扇,招呼我们坐下,然后津津乐道在北京学习时某老先生讲古典诗文意象的故事。那时的他也不过三十多岁吧,而神情却更像一位纯朴的老者。三十多年以后,读他新近的作品,我得到的还是这个印象。一个老成的作家,也是一个不老的作家。他和他的文体,是老到的,却是不会老去的。
他是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