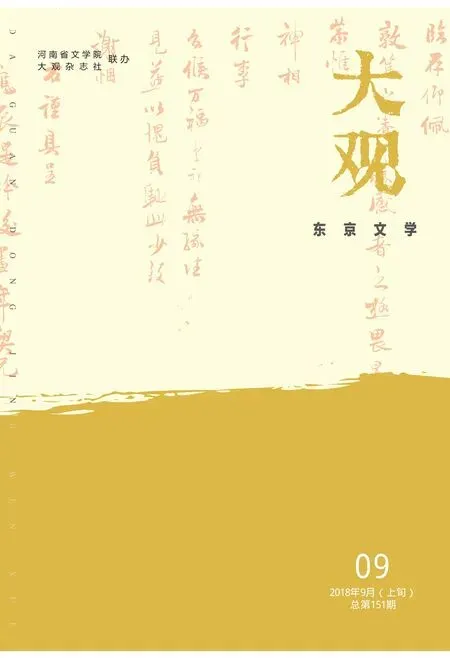肇事者(短篇小说)
1
何子舟坐在窗前,手里把玩着一只匕首。匕首寒光闪闪,橘黄色的手柄十分光滑。面前的旧三斗桌上有很多小孔,那是匕首刺过的痕迹,看上去像村里刘麻子的脸。何子舟的眼神并不在刀上,这把匕首他已经玩得相当圆熟,就像一件普通的玩具。他的目光在窗外。何老海正蹲在院子里补
渔网,那张渔网似乎经常被鱼撕破,或者被老鼠啃噬。所以何老海除了下河打鱼,其他时间多半都在补渔网。何子舟看着他手里的梭子颠来倒去,就像缝补这个老渔民紧巴巴的日子。
后来,何子舟把匕首戳在桌子上,走出屋门。他在何老海身边站定了,叉着腰,看他的脸膛、脖子、胳膊、腿和拖鞋里的脚。这些裸露在外的部分,除了花白的头发,清一色——黑,就像一个非洲难民。他知道何老海的背心下面,还包裹着两排尖凸的肋骨,就像一个黑色的骷髅。他对这身黑皮非常憎恶,就算没有日晒雨淋,他也白不到哪里去。可何子舟是白的,从头到脚白得彻底。所以,他对黑不仅憎恶,而且仇恨。
“舟子,回屋去。”何老海看着他的影子说。他从来不叫他“子舟”,而叫“舟子”,这样听上去亲一些。
何子舟没动。
这次何老海抬起头,停下了手里的梭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看到何子舟脸色很难看,眼神里像是撒了砒霜,毒毒的。
“你看你,站得跟个火钳子似的。”何老海说,“这是干啥?”
何子舟磨了磨牙,没说话。
何老海的梭子接着摇头摆尾起来,银色的丝线在阳光下看上去像一条闪亮的蜘蛛丝。何子舟想,这个瘦骨嶙峋的老渔民,活脱脱就是一只黑蜘蛛。
“回屋回屋,”何老海说,“老日头下火咧。”
何子舟又磨了磨牙,朝日光中吹了几口气,说:“有话问你。”
“说嘛。”
“我爹是谁?”
何老海的手僵住了,一脸皱纹盛着何子舟的眼神:“你、你说啥?”
“我爹是谁?”何子舟又问。
何老海确定自己听清了,他坐在地上,看着高高在上的何子舟。何子舟的脑袋上是老日头,所以何老海有些睁不开眼睛。他翕动着嘴唇,半天说:
“舟子,你傻了?”
“我没傻!”
“那……是中暑了吗?”
“我没中暑!”
“好端端的,咋说胡话?”
“我没说胡话!”
何老海似乎很渴,他使劲咽口唾沫,嗓子眼要冒烟了。他哑了一刻,目光落在何子舟的小腿上。那两段小腿藕一样白,火都烤不黑。
“听爹的,回屋去。”何老海说。
“你答我话!”何子舟用右手指指他,又放回腰上。
“我是你爹,”何老海说,“你是我儿!”
“你不是!”何子舟的声音里,升起了愤怒。
“我不是,那谁是!”何老海挥了挥梭子,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你自己清楚。”何子舟说,“说吧,我亲爹是谁?”
“不知道。”何老海呆呆地看着渔网。
“我家在哪儿?”
“不知道。”
“从谁手里买的我?”
“不知道。”
何子舟朝渔网狠狠地踹一脚,渔网上旋即多了一个破洞。他用手继续撕那个洞,好让脚拔出来。然后,他俯下身,朝何老海咆哮了一声:
“告诉我!”
何老海哆嗦了一下,电击似的,片刻后两手撑地,抬起了尖削的屁股。何子舟以为他要站起来,说不定还会扇他一个嘴巴子。但是何老海腿一弯,双膝着地,抱着他的腿,声泪俱下:
“舟子,我是你亲爹,我是你亲爹呀,舟子!”
2
河像个老病秧子,没精打采地趴在阳光下,连那几条波纹都翻得有气无力。几棵树在岸边傻站着,白痴一样。破渔船像变形的棺材,散落的鱼鳞发出腥臭味,引来了成群的苍蝇。何子舟坐在船舷上,跟匕首说话。
何子舟说:“我真想把何老海掐死!”
何老海给他下跪的时候,他真有这个想法。当然,他没这样做。他只是挣开何老海的手,或许太用力了,何老海仰倒在地。那一刻,阳光照亮了何老海脸上乱七八糟的泪珠。
匕首舞动着,像是摇头。何子舟也摇摇头,说:“可我不能,这个人养了我28年,我给他叫了28年爹。你说,我该恨他,还是该可怜他?”
匕首沉默,闪着锐利的锋芒。
何子舟说:“刘麻子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信。他和何老海打鱼时吵过架,所以我怀疑他是报复。可刘麻子向我赌咒了,他说如果扯谎,他就掉河里淹死。这么毒的咒,我没法不信,是不是?他还说何老海买我的时候,我脖子上挂着一个银锁。我把家里翻遍了,桌子柜子,床上床下,连墙缝和老鼠洞都掏过了,哪儿都没找到。”
匕首不知为何,脱手了,险些扎了脚。
“你干什么?”何子舟说,“你不愿听我说了吗?”他把匕首捡起来,在裤子上抹了抹,“你是我兄弟,亲兄弟,你可不能嫌我。你要是嫌我,我就把你砸碎了。”何子舟回头,往远处的渔村瞟了两眼,“你知道的,何老海要瞒我一辈子,到死也不会告诉我!”
匕首舞得有点张牙舞爪,何子舟说:“我只想知道我是谁,爹娘是谁,他们在哪儿?当然了,我也想知道是谁拐了我,我若找到他,兄弟,我就把你戳到他心窝里,把他的心戳成马蜂窝,你信不信?”
匕首连连点头,刀背上的日光,把眼球灼痛。
何子舟离开破船,上了那辆快散架的面包车。这辆二手车是他唯一的活路。他发动汽车,引擎干咳了一阵,嗡嗡叫着往前驶去。何子舟从倒车镜里,看到了灰蓝色的尾烟。
他在县城一棵大树的阴凉里等客,那里还有一些车,面包、轿车、摩托都有。他的车很容易从中区分出来,因为他的车最破。
那些司机盘腿坐在地上打扑克,李大娥向他招手,他没理。这女人的丈夫是个瘫子,靠她养活。李大娥的嘴很臭,爱说脏字,有辱她的性别。这女人比他小两岁,看他的眼神总有点邪。有一次她说车坏了,让他帮忙。他坐在驾驶室,检查仪表盘、离合和油门。李大娥坐在副驾上,手不老实,悄悄在他腿上爬。爬着爬着,就爬到了那里。他还是个童男子,羞怒难当,一把将那只粗短的爪子拨拉开。李大娥红着脸说:“习惯了,我还以为摸档把咧。”他跳下车,打开引擎盖,一眼看到电瓶线脱落了。他笃定,这是李大娥做的手脚。
何子舟打开车门,一条腿伸到车外,继续和匕首说话。何子舟说:“这些年,我做梦都想成为有钱人。有了钱,我就全天下悬赏,谁帮我找到爹娘,就给他一百万。就算找不到,哪怕给我个线索,哪怕扯谎骗我,我都给他钱。可我没这个命,我只能跑跑黑出租,老鼠一样讨口饭吃。”
匕首蔫头耷脑,好像瞌睡了似的。
“嗨,给我精神点!”何子舟说,“你告诉我,我该咋办?”
这时,李大娥领着两个人走过来,冲他挤挤眼,充满挑逗的味道。李大娥说:“来客了,我一车拉不完,你帮忙捎两个。”
何子舟把匕首放进手套箱,对那两个人说:“上车。”
3
李大娥用自己的车把他堵了,这是客人下车后的事。何子舟鸣鸣车喇叭,李大娥的车还是没挪窝。他正狐疑,李大娥的大象腿落了地,扭着屁股朝他走来,嘴角牵出两朵浮浪的笑。他把车窗摇下,问:“咋不走了?”
李大娥说:“你下车。”
“干啥?”
“饿了。”
何子舟说:“我不饿,你把车挪开。”
李大娥娇嗔地撇撇嘴:“人家帮你揽生意,就这么对我?”
何子舟犹豫一下,下了车。
旁边就是一家小餐馆,小餐馆的上边是一个小旅馆。两人在一个角落坐下,餐桌油漆剥落,黏渍渍的,看上去伤胃口。何子舟把简易菜单递过去,说:“吃啥,你点。”
李大娥捧着下巴,娇滴滴的,问他:“真请我客呀?”
“真请,随便点!”
何子舟说得很慷慨,不过他知道,那张菜单就算点齐了,也值不了几个钱。
老板是个少妇,比李大娥大不了几岁,人中旁边有颗痣,看上去很性感。她在这个小餐馆里,还扮演着厨师和服务员的角色。老板左手捧着小本子,右手捏着铅笔,严阵以待。李大娥在菜单上看来看去,拿不定主意。老板鼓励她:“爷儿们请客,下手狠点。”可李大娥只点了两碗面。老板很泄气,表情古怪地走了。在等待的过程中,李大娥一直看他,眼睛都不眨一下。何子舟不时看窗外,李大娥的眼神让他心里发毛。
“你老看我干啥?”何子舟躲不开,没好气地说。
“你好看。”李大娥说。
“我有啥好看?”
“你白,越看越好看。”李大娥伸出舌尖,舔了舔嘴唇。
何子舟瞪了她一眼:“妖精!”
李大娥“扑哧”笑了,几滴口水喷到了他的胳膊上。
面上来了,李大娥吸溜得声势浩大,额头上很快有了汗。何子舟没一点胃口,筷子在碗里瞎划拉。他很想喝瓶啤酒,可没办法。李大娥劝他吃,他索性把碗推到一边。李大娥吃完了她那碗,又看着他这碗,问:“你真不吃?”何子舟说:“真不吃。”刚想走人,李大娥已经把碗捧到脸前:“不吃多可惜,我再吃一碗!”何子舟看她把第二碗面席卷而下,连汤都没留,很佩服这个女人的饭量。
付过钱,何子舟走在前面。刚出门口,李大娥拉住了他一只胳膊。何子舟困惑地说:“猪老妹,你都吃了两碗,还有啥事?”
李大娥两条眉毛挑了挑,问:“你叫我啥?”
“猪老妹。”何子舟重复道,“猪八戒是你哥,对吧?”
还没等李大娥反应,老板大笑起来。何子舟回头,看到老板下巴上趴着一根面条,那是喷出来的。这娘儿们一定是幸灾乐祸,何子舟想,刚才李大娥点单的时候,她心里一准骂她蠢猪。一般来说,不知道宰男人的女人,都是缺心眼。
李大娥拿拳头捶他:“好啊,你骂我丑。”
“不是丑,”何子舟纠正她,“是夸你牙口好,胃口好,吃嘛嘛香。”
李大娥说:“不跟你贫,不就是嫌我吃得多吗?不吃老娘哪有力气干活!”
何子舟又往外走,李大娥还是拉住他。“干啥?”何子舟想把胳膊甩开,可李大娥用了手劲,他没得逞。
李大娥迷离了眼,朝上面的小旅馆努努下巴:“上去坐坐。”
“干啥?”何子舟提高警惕。
“说说话,”李大娥说,“就是说说话。”
“在这儿说。”何子舟很坚决。
李大娥认真起来:“在这儿不方便。”她盯着他,拿手指指自己的心口,那里是两个硕大的肉球。李大娥从头到脚,就数这里算个景点。她的手扎在了自己的景点上,说:“你这里一准有事。”
何子舟怔了一下:“我有啥事?”
“你瞒不了我,”李大娥说,“妹子我眼毒。”
“扯淡!”何子舟哼了一声。
李大娥不为所动,接着说:“有事说出来,有屁放出来,老憋在心里,早晚出毛病。”
何子舟没吱声。
“老妹也想给你倒倒苦水,”李大娥摇着他的胳膊,有点撒娇的意思,声音也嗲了,“好吧舟哥?”
何子舟似乎一下子爆胎了,心里那团浊气,呼呼地泄出来。
他们进了小旅馆,李大娥买单,钟点房,四个小时50元。走进房间,扑面一股霉味。床单上有星星点点的黄斑,让人产生某种联想。李大娥把屁股放上去,示意何子舟坐。何子舟顾自坐在破沙发上,看着她。
李大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说吧。”
“说啥?”何子舟问。
“就当我是你亲妹。”李大娥说。
何子舟一震。
“谁惹你了,老妹给你出气。”李大娥的口气,听上去像一个女匪。
何子舟习惯性地磨牙,磨了一阵,说:“倒你的苦水吧。”
李大娥立即换了副苦脸,好像从那张粗糙的面皮下,能拧出黄连汁来。“老妹苦,不是一般苦。”李大娥说,“家里那个活死人,躺了六年了。擦屎刮尿,洗洗涮涮,这都不说了。可我是个女人,女人你懂吗?”
何子舟沉默。
李大娥眼里有了泪光,狠狠说:“老天爷欺负人!”见何子舟木头人一样,她叹了口气,身子斜躺下来,曲起右臂,托着半个腮帮,直勾勾看他。何子舟随手拿起一只茶杯,在茶几上蹾了一下,那只茶杯竟然裂开,敞着褐黄色的茶垢。
李大娥说:“有气就撒,别憋着。”
何子舟又把另一只茶杯蹾了一下,蹾出了很大动静。还好,这只杯子抗击打,完好无损。
李大娥说:“别老拿杯子撒气,这儿还有比杯子好的呢。”
何子舟碰了碰李大娥的眼神,那眼神像条舌头,舔得他六神无主。
李大娥的苦脸开出了妖冶的花,又说:“舟哥,你真好看,你咋比女人还白呢?我想吃你。”
何子舟站起来,身上似乎有许多只手,挥着刀子,要杀这个妖精。他靠近了床,迟疑着。李大娥一把拉倒他,下巴正好放在了她的胸脯上。那地方软得邪乎,让他一直陷进去。李大娥翻过身,三两下就把他扒光了,然后,她把自己也扒光了。何子舟看到了两团白肉,白肉上各镶着一个红点,就像过年蒸的枣馍。他闭上眼,有些恍惚。李大娥拨弄着他,很快骑上来,嗓子里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个疯子……
他们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何子舟的汗把床单都溻湿了。他咬着牙,嘴里骂着什么。李大娥变成了很多影子,他想杀了她们。最后,他瘫在床上,像一条死鱼。
4
夜黑得像何老海的皮肤。何子舟把车停在院子外,看了看天上的星星。那些星星像流浪的孩子,眨巴着眼睛,似乎在寻找月亮。月亮去哪儿了?何子舟不知道。
进了院门,大黄狗嗖地蹿出来,围着他转圈,舌头在他身上一阵乱舔。他在狗头上摸了几下,让它休息。大黄狗听话地走回去,蛰伏在某个暗影里,打了个哈欠,把头贴在前爪上,不知真假地睡过去。
“回来了,舟子?”何老海从屋里迎出来,弓着腰,有点低声下气。
何子舟没理他。
“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
何子舟走进屋,扒下衣服,换上条大裤头,坐在三斗桌前,把一条腿跷到桌面上,无所事事地玩手机。
李大娥给他发微信,说死瘫子拉了一床,她刚把铺的盖的拾掇完,累得要死。何子舟心里有点不落忍,这女人命不好,跟他一样。他安慰她两句,李大娥感动了,发了个眼泪哗哗的表情,接着又说,以后可以在死瘫子身边想舟哥,她好幸福。何子舟咧咧嘴,想起了一个成语:同床异梦。
过了一会儿,李大娥又发来一条语音,何子舟听了,眼睛竟涩起来。李大娥说:“亲爱的,以后我帮你找亲人。”何子舟忽然觉得,他在这世上有了个亲人,她就是李大娥。何子舟本来不想让李大娥知道,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可李大娥把他“吃”了,他就再也憋不住,一肚子话全撂出来,还伏在她乳沟里哭了一通。李大娥搂着他,拍他的后背,就像他的娘。
何老海把饭端上来,竟有一条红烧鱼,看样子烧得挺讲究。平素何老海没亮过这个手艺,无非把鱼丢进锅里,放了调料煮熟了事。何老海站在旁边,像个太监。“尝尝咋样,舟子。”何子舟乜他一眼,看到那张老脸上铺满了讨好的笑。他越是这样,何子舟越烦,老东西心里一定有鬼,何子舟想,若不心虚,哪会这么轻贱。他朝何老海摆摆手:“睡你觉去。”何老海走后,他才狼吞虎咽吃起来。今天破了童子身,他真的饿极了。
不过几分钟,何子舟就吃完了。他把鱼骨头撮在手里,走出门,唤狗。大黄狗果然假睡,鼻子早闻到了味。它摇着尾巴,嗓子哼着曲,有滋有味地嚼着鱼骨头。何子舟蹲下来,看着它的吃相,心下有了温情。现在,在这个家里,只有狗才让他感到亲切。如果没有刘麻子,他还会心疼何老海。老头子的确不容易,老伴没了,风里雨里熬过来,眼里就他一个儿。可如今,一切都变了,回不去了。
何子舟把大裤头也扔了,用脸盆盛着水,当头浇了几遍,这才回屋。何老海一声不响地拿了他的衣服,去院里洗涮。发了会儿呆,何子舟关了屋门,又开始翻箱倒柜。何老海听见动静,推门进来,战战兢兢地看着他。
“找啥,舟子?”
“少管!”何子舟“啪”地合上一个柜门。
“爹帮你找,好吧?”何老海恳求。
何子舟回过头,虎视眈眈:“把银锁给我!”
“啥……啥锁?”何老海黄着脸。
“银锁,听清了吗?”
何老海摇着头,身子向后退,嗫嚅着:“没有,咱家没有,啥锁都没有。”
5
夏雪莲打开电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的留言。那个人网名叫“漂流瓶”,他说,他要找爹娘,他要回家。
夏雪莲是一个孀妇,丈夫英年早逝,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丈夫走后,她成了一名公益志愿者,开了一个寻亲网站。因为丈夫是个孤儿,这是他的遗愿。
夏雪莲说,加我微信吧,咱们好好聊聊。
他们很快加了微信。夏雪莲问,你是孤儿?
漂流瓶说,我有养父。
那你是……
我是被拐的。
几岁被拐?
不知道。
在养父家生活了多久?
28年。
还有家乡的记忆吗?
漂流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有山,门前好像还有个塘子,塘子旁边好像有棵大槐树……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梦见的。
夏雪莲问,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吗?
不记得。
好吧,我会努力帮你寻找。夏雪莲说,你最好把你的生物检材和血样寄给我,我向民政部门申请为你做DNA比对。
6
这个网站是李大娥发现的。那次小旅馆缠绵后,李大娥改口叫何子舟老公。她想了很多办法,发动亲友,发布微信,还想贴告示,被何子舟拦了。“我丢不起那个人!”何子舟说。一段日子后,李大娥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李大娥不气馁:“我就不信了!”在他们又一次躺在小旅馆的床上时,李大娥把手机上的网页拿给他看。
“我给你找了个活菩萨。”李大娥说。
何子舟认真看了网页,心里跳起了一豆火苗。因为网上有介绍,他们已经为十几个人寻亲成功。何子舟舍了力气,让李大娥好好“吃”了一顿作为答谢。末了,何子舟问:“你怎么找到的?”李大娥狡黠地挤挤眼:“找度娘呗,老婆聪明吧?”何子舟在她屁股上拧一把,这女人倒是心细,知道用百度。
“舟哥,”离开时,李大娥抱着他,“等死瘫子走了,你就做我真老公,好不好?”
何子舟未置可否。
李大娥出事是在二十天之后,那天何子舟心情很坏,因为夏雪莲告诉他,DNA没有比对成功。“不过我会一直帮你找下去。”夏雪莲说。何子舟苦笑了,他生就这个命,连菩萨也救不了他。
李大娥是下午三点钟出车的,当时来了两个小青年,一高一矮,高的像电线杆子,长发乱成了老鸹窝;矮的像树桩子,粗粗壮壮,光头可以当镜子。两人直奔李大娥,二话没说拍下一张百元大钞。李大娥喜滋滋地上了车,临走抛给他一句话:“晚上一起吃饭,我请客。”可是直到晚上十点钟,李大娥也没现身。何子舟给她打电话,竟然关机。正疑惑着,手机响了,想不到是警察打来的。
“你是李大娥的老公吧?”
何子舟刚想否定,对方说是从李大娥手机上找到的,他的号码被标注为“老公”。这么一说,何子舟只好默认。
“李大娥怎么了?”何子舟问。
“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对方说,“很不幸,你的妻子遇难了。”
何子舟赶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拉走了。他看到了李大娥的车,车里还有凌乱的血迹。在方向盘的下沿,粘着一簇搅成一团的头发。那是李大娥的,因为李大娥喜欢把头发染成葡萄红。他晕了一下,靠在车门上。警察说:“节哀。”他的视线模糊了。警察把他带回刑警队,询问了一些线索。何子舟摁了手印,开着面包车来到河边。起风了,河骚动起来,像是李大娥在仰着头骂人。
何子舟坐在河滩上,手里拿着匕首。匕首上月光游移,凄冷地钻进瞳孔。何子舟说:“兄弟,你告诉我,那两个混蛋在哪儿?”
匕首不说话。
何子舟说:“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大卸八块,我要把他们剁碎了喂狗!”
匕首抬起头,刺破了月光。
何子舟说:“大娥死了,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他的泪水滑下来,滚进嘴角,“怪我,那两个混蛋那么大方,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头。天上掉馅饼,有这种好事吗?我真应该给大娥做个伴,如果我在,那两个混蛋也许就断了念想,就算死了,也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不寂寞,你说是不是?”
匕首低下头,难过地淌下两滴清辉。
何子舟说:“大娥,我答应了,我要做你亲老公,听见没有?”
河水咆哮起来,像是李大娥在放声大笑。
何子舟没话了,握着匕首,一下一下戳着河滩。河滩不会流血,不会疼,连伤疤也不会留下。可人会,人除了流血、疼痛、结疤,还会死,就像李大娥。李大娥再也活不过来了。何子舟想,我也死了,死心了,心死了,像我这样的,活和死没啥两样。
月亮看着他,听他把一个字说了无数遍:
“杀!”
7
夏雪莲来了消息,说有几个人可以见一见。那几个人有老头子,也有老太太,他们生活的地方,都有山、塘子和大槐树。
“你来找我吧,我陪你一起去。”夏雪莲说。
何子舟没抱多大希望,可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毕竟,这是他的梦。如果从进入养父家算起,这个梦已经做了28年。28年前,他像一只动物,被人盗走,被何老海买去。他们一准还讨价还价,想到这些,何子舟就会磨牙。
何子舟原打算坐高铁,可要倒几次车,最近的车票也已售罄。他不能等,于是决定开着那辆破面包去。一千多里,何子舟也担心面包车会半道上罢工,给他难看。可他没别的办法,坐在车上,他拍了拍方向盘:“你他娘的给我争口气!”
何子舟从下午出发,如果一路顺利,预计第二天早晨可到。也许是受了鼓励,面包车还真没尥蹶子,一路干号,尾烟喷得气势汹汹。何子舟一直没下高速,饿了就在服务区泡块方便面,让发动机和轮胎也降降温。子夜时分,困劲开始上来,恰好前方修路,指示牌让绕行国道,到下一个高速口进入。这时,已经进入夏雪莲所在的省域了。
何子舟下了高速,把车停在路边,抽了支烟。李大娥死后,他总提不起精神,爱犯困。抽过烟后,他走到一棵白杨树下,撒了泡尿。夜风干热,裹着说不清的味道,熏得人头昏。何子舟拿出匕首,在树干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刺着,说:“大娥,我来找爹娘了。你说那些老头、老太太里面,有没有我亲爹、亲娘?他们多大岁数,会不会老得没牙了?”
匕首在风里默不作声,好像死去的李大娥,再也不会说话。
何子舟说:“要是这次找不到,我就不找了,彻底死心。大娥你保佑我,你到了那边,肯定啥都知道,你要是没忘我,就给我托梦。”
杨树叶唰唰响,好像李大娥答应了。
何子舟又朝树干上猛刺一下,这次刺深了,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何子舟磨着牙,说:“不行,我还得找。我要找拐走我的人,我要杀了这个狗日的!大娥你等着我,我若杀了人,不会等着被枪毙,我自己结果自己。”想了一下,何子舟又摇摇头,“不行,我还是不能死。我还要接着找那两个害你的混蛋,我把他们也杀了,为你报仇,你高兴不?”
风息了一下,死静。
何子舟上了车,继续赶路。走了一会儿,导航忽然失去了信号。他减慢速度,把导航重启一下,居然还是那样。何子舟无奈,想不到会在这里节外生枝。他估摸着方位,接着加速。在一个岔路口,他拐上了一条稍窄些的水泥路。黑暗中空无一人,刚才国道上还有偶尔交汇的车辆,现在他干脆成了独行侠。他把速度开得更快些,由于再无值得注意的东西,眼皮开始不知不觉打架。
何子舟不知导航是何时恢复信号的,他好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导航里的女人就说话了:“你已偏离航线,前方500米右转。”他骂了女人一声,转道行驶。女人又说:“路径重新规划中。”他不知道偏了多远,那条漆黑的水泥路,就像通向地狱的长廊。女人算好路径,接着说:“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之前,请按当前道路行驶。”何子舟疯狂地踩下油门,扑向黑暗的深处,身上的困意,竟然全都消失了。
黎明时分,他把车开到了郊外的一家汽修厂。这里离夏雪莲的城市,还有好几百里。直到八点多,修车师傅才到,在车前瞄了一眼,说:“撞得不轻啊。”何子舟说:“疲劳驾驶,撞树了。”修车师傅说:“前杠、大灯,还有挡风玻璃,最快也得到明天。”何子舟点点头,到附近买了条芙蓉王香烟,塞给修车师傅:“越快越好,我有急事。”
他在200米外的小旅馆里,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把兜里的钱拿出大半,开走了面包车。由于前边包装一新,面包车看上去有点滑稽,就像一个丑老太太,脸上搽了厚厚的脂粉。
午后,何子舟来到了目的地。估计夏雪莲正在午休,他没有立即联系她,而是进入一个餐馆,吃了一大盘水饺,然后看着窗外发呆。即便这里是省城,在这个城乡交接地带,还是有很多穷人。蹬三轮的、挎篮子的、卖菜的、打工的,来来往往,神情木讷而胆怯,似乎有城管要来赶他们。何子舟看到好多人身上都不怎么干净,领子上黑黄色的汗渍,屁股上的灰尘,就像标签一样,标明他们的身份。有几个中年汉子,挽着裤腿,敞着胸,嘻嘻哈哈说笑着,身上满是斑斑点点的白色涂料,大约是建筑工地的粉刷工。
下午三点半钟,他在一座奢华的住宅里,终于见到了夏雪莲。夏雪莲五十来岁,微胖,保养得极好,看上去雍容而有气质,脸上的笑似乎是天生的,给人温暖的感觉。何子舟坐在沙发上,双目呆滞,神色疲惫而忧郁。
夏雪莲给他沏了杯茶,说:“累了吧?喝水。”
何子舟喝了一口,感到咽部微痛。夏雪莲看着他,不说话,那抹温暖的笑里,似乎藏着心事。
“多谢夏姐帮忙,”何子舟说,“我可以去见他们了吗?”
“不忙。”夏雪莲说。
“我想见,”何子舟无意识地握紧拳头,“现在就见。”
“不着急。”夏雪莲依然婉拒。
何子舟不明白夏雪莲的意思,这个活菩萨,把他千里迢迢叫来,眼下却磨磨蹭蹭,到底为个啥?
“咋的了,夏姐?”何子舟问。
“那几个人……不用见了。”夏雪莲话里有话。
“为啥?”
夏雪莲的笑还在,却有了寒意。她从电脑旁拿过一张纸,递给他:“你看一看。”
他懵懂地接过那张纸。那是一份网上下载的“悬赏通告”,在某市城郊结合部,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个拾荒老人(警方称他为无名氏),当场身亡,肇事者逃逸。何子舟看到了现场图片,他只瞟了一眼,就把纸反扣在沙发上。
“这与我有关系吗?”何子舟脸色苍白。
夏雪莲点点头。
“啥意思?”何子舟的脸冷下来,有几分凶相。也许他不知道,这些天他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表情,样子蛮吓人的。
“你现在可以去找他了。”夏雪莲说。
“为啥?”何子舟的脸色由白转青,“我为啥要找他?找一个死人?”
夏雪莲拭了下眼镜,看定他:“因为,警方已经联系了我,你们的DNA比对成功。”
何子舟耳边“轰”的一声,眼前飞舞着数不清的星星。起身的时候,夏雪莲用双手握着他。那双手,柔软而温暖。
现在,何子舟跪在那个僵硬的尸体前,呼吸急促,双唇战栗。他不知道这个老人为何会流浪,也许他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的儿子,拾荒、乞讨……他就这么跪着,一言不发。后来,他把一瓶矿泉水猛灌下去。他的脸部开始扭曲,视线开始游移。他看到那个蓬头垢面的拾荒老人,像一个夜游的鬼,背着一个鱼皮袋子,倏忽出现在面包车前,然后,“砰”的一声,老人飞了出去,袋子里的纸片飞向天空。他下了车,车灯下闪着猩红的血迹。他没有把他抱上车,没有报警,没有拨打120。他叉着腰,表情有些狰狞,那摊血甚至让他感到了一丝快意。在无边的夜暗里,他阴狠地笑了一下,驾车扬长而去……
“爸爸!”何子舟虚弱地伏在了老人冰冷的尸体上。
当人们觉出异样时,何子舟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医生从那个矿泉水瓶的残液里,检测出了剧毒成分。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肤色黝黑的老渔民走出殡仪馆。他的头发全白了,与他的身体对比鲜明。他佝偻着腰,背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包,包里装着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里面有一只发暗的银锁。他在阳光下一边流泪,一边自言自语:
“舟子,我送你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