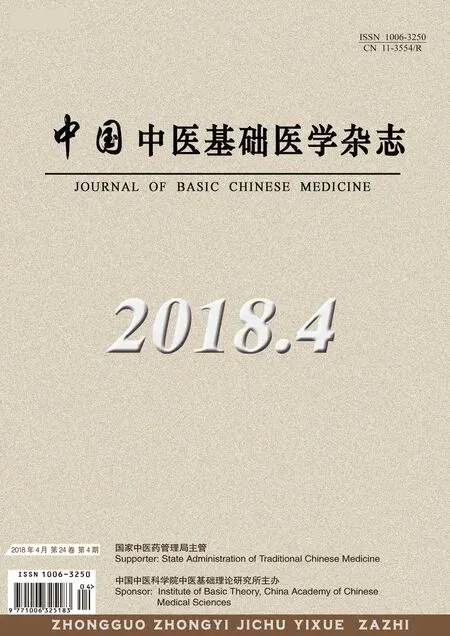明清时期中医外科对乳岩的认识探析
刘 静,陆德铭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医医院, 上海 200041;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乳岩属于中医外科四大绝症之一,中医对该病的认识可上溯《灵枢》,葛洪《肘后备急方》将之命名为“石痈”,并描述其局部症状[1]。明清之际中医外科发展到全盛时期,名家辈出[2],这一时期中医外科已广泛采用“乳岩”这一病名。尤其是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总结前说、发挥己见,对乳岩发生、过程、病因病机、治则、内外治法、方药和预后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基本奠定了中医外科对该病认识的框架。现代中医治疗乳腺癌基本参考治疗乳岩的理论,现就明清时期中医外科对乳岩的认识作一浅析。
1 对症状的认识
明代中医外科医家认为,乳岩初起为乳内结核,经年不消,不痒不痛或按之微痛,可伴有发热、胃纳不佳等症状,病久则坚硬如石,时常作痛,溃后深者如岩。汪机《外科理例》、薛己的《外科发挥》《外科心法》《外科枢要》及其校注的由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中皆有类似描述。其后王肯堂、申斗垣、陈实功诸医家皆承汪机、薛己。如申斗垣《外科启玄》中列有乳症十款,其中“乳结坚硬如石,数月不溃,时常作痛,名曰乳岩”。陈实功作了系统总结,认为乳岩“初如豆大,渐若围棋子,半年一年,二载三载,不疼不痒,渐渐而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凸者若泛莲,疼痛如心,出血则臭,其时五脏俱衰,四大不救”,这些描述甚合疾病的自然史。
至清代对乳岩症状的认识无更多发挥。《外科大成》《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与《外科正宗》一脉相承[3],《疡科心得集》《疡医大全》与薛己、陈实功的认识并无不同,《洞天奥旨》继承了《外科启玄》的乳症十款。值得一提的是《疡科心得集》将乳癖、乳痰、乳岩进行类证鉴别,补前人所未逮。
2 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2.1 情志内伤是乳岩的主要病因
妇女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故常罹患情志疾病。情志内伤首见气机失调,常表现为肝气郁积,进则引起脏腑内伤而成积。如《灵枢·百病始生》所言:“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明清医家继承前说,非常明确地提出乳岩与情志密切相关,认为乳岩由情志不畅、气血虚弱所致。如《外科理例》认为,乳岩“乃七情所伤,肝经气血枯槁之证”。《外科正宗》认为:“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有心,所愿不得志,致经络疲惫,聚结成核。”《证治准绳·疡医》采纳朱丹溪、薛己等医家的观点,《疡医大全》汇集陈实功、冯鲁瞻、胡公弼等多家言论,其论点皆不离肝脾。
2.2 乳岩病机为女损肝脾,男损肝肾
明清外科医家认为男女皆可患乳岩,将男性乳岩命名为“乳癤”,并认为男性的病机有别于女性。《外科枢要》提出“男子房劳恚怒,伤于肝肾。妇人胎产忧郁损于肝脾。”陈实功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女损肝胃、男损肝肾,男性多由怒火房欲过度以致肝虚血燥,肾虚精怯,血脉不得上行,肝经无以荣养,遂结肿痛。
2.3 对乳岩阴阳属性的认识
陈士铎和王维德均崇尚以阴阳辨证外科疾病的思想[4],《洞天奥旨》认为乳症“大抵皆阳症也”,而《外科证治全生集》将乳岩归于阴证门,认为乳岩是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阴寒结痰”而成。王维德的观点并未得到大部分医家的认同,如马培之评论《外科证治全生集》时就认为乳岩为心肝二经气火郁结,非阴寒结痰所致。
3 对治则治法的认识
3.1 乳岩内治以疏肝扶正为主流
基于对乳岩病机的认识,明清外科医家在治疗上主张疏肝扶正。陈实功传承“补(养)气血、解郁结”的思想,治疗乳岩以清肝解郁、扶养气血为主。女子乳岩从肝脾论治,早期以清肝解郁汤或益气养荣汤再加清心静养;男子乳癤从脾肾论治,以八珍汤加山栀、丹皮,口干作渴以加减八味丸,肾气虚以肾气丸,已溃作脓以十全大补汤。《外科大成》《外科心法要诀》皆宗其法,初期以神效栝楼散、清肝解郁汤;疮势已成时重视保护胃气,强调不可过用攻伐,以香贝养荣汤、归脾汤、逍遥散等。《疡科心得集》用加味逍遥散、归脾汤、益气养营汤等疏肝健脾,亦未出《外科正宗》窠臼。《洞天奥旨》则以补益气血扶正为首务,不用疏肝解郁之法,列化岩汤治疗乳岩。
王维德治疗乳岩初起用犀黄丸,肿块日渐肿大、皮色变异则难以挽回,勉以阳和汤、犀黄丸等内服,其实质也是扶正与散结相结合,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张贞庵《外科医镜》均承王氏之说。但王维德使用阳和汤治疗乳岩也遭到不少医家的反对,如马培之认为阳和汤断不可用,服之“速其溃”。
3.2 乳岩内治反对任用攻伐
汪机、薛己、陈实功等明代医家均明确反对单用十宣散、流气饮等行气破血之剂。薛己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提到:“如用行气破血之剂,则速其亡。”《外科理例》中记载了两个医案均服用行气之剂,1例“势愈甚”,另1例“疮反甚”均溃脓而殁。《外科正宗》中记载了一男子乳癤,经小柴胡汤、八珍汤、益气养荣汤等治疗“庶保收敛”,后其他医生接治以降火流气宽中等剂,而致邪火内淫、脾土受伤、阴血内竭、不治而亡。明清诸医家大都提到“解郁结”的治则,亦常用疏肝药物,可见其强调的是治疗乳岩应以扶正为主或攻补兼施,反对单纯应用行气破血药,任用攻伐。
3.3 乳岩内治甚少使用清热解毒法
明清医家治疗乳岩甚少使用清热解毒药物,此与反对“清凉行气破血”有关。《疡医大全》引陈士铎言:“治法必大补气血,以生其精,不必泄毒,以其无毒可泄耳”,更是将这种观点发挥到极致。惟有《外科启玄》提到乳岩“宜急散郁消肿祛毒,不然难疗”,惜未列方药。《疡医大全》引钱青抡的消乳岩丸方(夏枯草、蒲公英、金银花、漏芦、山慈菇、雄鼠粪、川贝母、连翘、金橘叶、白芷、甘菊花、没药、栝楼仁、乳香、茜草根、甘草、广陈皮、紫花地丁),此方颇合《外科启玄》的旨趣,而与疏肝健脾的主流思想相异。
3.4 乳岩外治法
自《刘涓子鬼遗方》至明代万历年间,中医外科治疗奉行内服外用并行[3],乳岩治疗亦是如此。明清时期乳岩外治手段有限,如“木香饼灸之”(《外科理例》),“外用蒜灸”(《外科枢要》),“降霜点之”(《外科启玄》),溃烂脓水不干用致和散为末掺之(《外科大成》)。陈实功擅长外治,《外科正宗》描述乳岩外治法为初起用艾灸核顶,起泡后挑破,披针插入四分,冰蛳散条插入核内盖封,核落后以玉红膏生肌收口。而王维德认为乳岩肿块日渐肿大,皮色变异,可以大蟾蜍破腹连杂外敷,尤其强调“大忌开刀,开刀则翻花,万无一活,男女皆然”,这在当时的医疗情况下此说是颇有见地的。
3.5 日常调摄
乳岩根于情志内伤,薛己提出“戒七情,远厚味”,陈实功认为患者应“清心静养,无挂无碍”,方能安定心神,寂忘诸念,毋使仓惶,保得神气不致变乱。这些观点也颇合临床实际。
4 对预后的认识
明清外科医家普遍认为乳岩预后不佳,如陈实功认为肿块木痛不红,有发热呕吐等全身症状,坚硬如石、溃后无脓、溃后肉色紫暗、痛苦连心、形体日削等症状均为逆证或死证。其在《外科正宗》中所载4个乳岩医案,结果都是“辞不治、俱死”。《疡科心得集》称“乳疡之不可治者,则有乳岩”,并认为“此证溃烂体虚,亦有疮口放血如注,即时毙命者,与失营证同”。
总之,明清中医外科学家对于乳腺癌的症状、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预后都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认为情志因素是乳腺癌的重要发病因素,病机上女子与肝脾有关,男子与肝肾有关,治疗多以疏肝解郁、健脾益肾为主,反对妄用清凉行气破血之法,并积累了一定的外治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现代中医外科治疗乳腺癌有深远的影响。如以顾伯华、陆德铭为代表的顾氏外科在治疗乳腺癌健脾扶正的基础上强调调摄冲任,在疏肝解郁的基础上重用解毒散结消肿,亦是对明清学术思想和经验传承[5]。
参考文献:
[1] 李桃花. 浅谈乳腺癌的中医学术源流[J]. 吉林中医药,2009,29(12):1099-1101.
[2] 艾儒棣,陶春蓉,刘邦民,等. 明清时期中医外科的特点[J]. 四川中医,2008,26(6):124-126.
[3] 和中浚.中医外科“正宗派”学术源流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2):124-126.
[4] 和中浚,周兴兰.《外科证治全生集》与《洞天奥旨》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3):459-461.
[5] 刘静. 陆德铭教授运用扶正祛邪大法治疗乳腺癌的学术思想初步总结[J].中医学报,2016,31(4):470-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