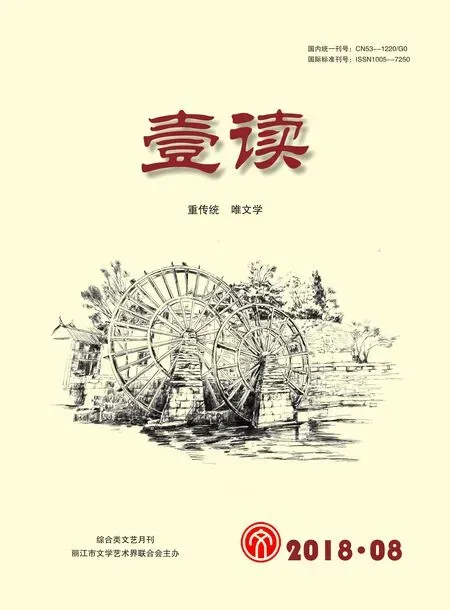事实的诗意
李艳新
诗歌《母亲的忧伤》仅是短短140字,以“母亲、大哥、大姐”简短的动作来表现1958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意味深长,充分地表现了口语诗歌特有的张力。
母亲放下跃进二渠工地上的泥筐
就向家奔去,推开门
看到五岁的大哥
正抓起地上的鸡屎,往嘴里送
三岁的大姐正要挣扎着站起来
又倒了下去,大姐本来会走了
吃食堂饭后,又饿得不会走了
母亲从怀里掏出省下的菜团
大姐以为是菜叶裹着的馒头
靠在墙根认真地剥着
菜叶终于剥完了
手里什么也没有了
一、精确而凝练的语言
杜思尚的这首诗语言朴素而精炼,很好的表现了口语诗坚守诗意的特点。《母亲的忧伤》属现实型的文学作品,讲述现实,剖析现实,带领大众直面现实,它立足于客观现实的再现,正视于现实,忠实于现实。因为这首诗并不是绕开或是躲避1958年那个“国人之伤”的现实,依据我们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则会认为少有作家敢于触及“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躲避或是粉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在《母亲的忧伤》中,诗人竟不避讳地表现了中国历史走过的一段弯路,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不少人会有意避之,而作者,敢于执笔写下那个骇人听闻的是1958年,敢于言说那时的饥荒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可见这首诗很好的诠释了口语诗拥有的“事实的诗意”的特性。
诗人用平常的语言构造出一幅充满意蕴的图画,以简练的语言蕴含富有深意的内容,即使是口语诗也被诗人表现得极其形象和意蕴,中国历史上的1958事件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诗人的这一首《母亲的忧伤》,无疑是为了提醒人们永记历史的存在,结合战国时期文论家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可得知诗人一家在1958年遭遇的经历给作者造成了极大的伤痕,这一创作方法与经历了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流派的创作缘由如出一辙。
二、自由的诗体
作为采用口语进行诗作,继承了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观念,用自由之文破除了古时永明体或现代新月诗派所设置的种种清规戒律对诗歌感情抒发的束缚,是诗体的又一次大解放,这样的创作无疑是打破了读者的阅读的期待视野,使人们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这种以口语入诗的言语形式致使作品拥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它不仅使作者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也使文学创作对象内蕴的“情”和“理”与外在显现的合适的文学达到了和谐统一。
当然,读者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作家的气质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自身携带的相关个性信息。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司马迁提出“发愤而著书”,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而宋代的欧阳修则认为“诗穷而后工”,其实,杜思尚的这首诗《母亲的忧伤》与这些古代文学家的文论思想是一致的,诗人将自己曾经的生活境遇和现今的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是一首从这个时代描绘那个时代的诗歌。火候不够就容易平淡,火候过大,容易显得浮夸,而本诗恰到好处,无一字写“悲”无一句说“愤”,但让读者触目惊心,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处。诗人因为在1958年中见了“从工地上回来的母亲还揣着菜团回来给快要饿死的家人”,建立起自己与外界的纯粹审美体验,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铭记历史的伤痛。
三、反传统的创作观念
杜思尚作为新生代诗人具有新生代诗人共有的特点,笔者根据多方资料稍作整理,那便是“在所值观念和理想意趣上,表现‘非英雄’、‘非崇高’的理念,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人常说的表现来告别传统的精英意识所散发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己。”这首诗所叙述的对象并不是某个著名文化人物或是某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而是以自己身边的家庭成员“母亲,大哥,大姐”作为诗的主人公,无疑,诗人的创作是“为市民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占有的语言和西化的语言,以及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和富有意味的调整。在艺术观念上,《母亲的忧伤》继承和发展了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的风格,也继承了“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这首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有力的强度,张力十足,画面的掠过,一帧帧浮现在眼前,读者被拉扯入事件本身,从而产生共鸣,犹如你就是诗歌中的本身,诗歌本身的情感就是读者自己的情感。《母亲的忧伤》就像叙家常一样向读者叙说他在1958年大饥荒年代经历的生活情景,不假雕饰,诗人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生活尤其是平民生活之路上迈出富有意义的一步。然而,即使在最大限度的逼近生活口语的同时也没有将艺术风格带入粗俗和平庸的藩篱。
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价值追求
鲁迅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身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当具有担当的真诚和勇气来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杜思尚作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诗人很好诠释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家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读这首诗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暴露批判社会主义制度下假恶丑的东西,正是为了保护、歌颂、肯定和召唤真善美的东西,我们读者应当具有博大而宽容的心胸,要用长远的眼光去体会作者在《母亲的忧伤》时所带着苦闷和纠结的良苦用心,明白他也在为了让中国变得更美好而尽心尽力呐喊的悲壮。曹操吟诵“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写出他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也体现他作为杰出政治家欲救百姓于水火的胸怀和抱负。
巴金的《家》描写中国年轻一代在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如何被残酷吞噬,或者艰难挣扎到斗争的不同命运的生活历程,他揭露、呼号,通过一幅幅生活的写实画面,不留情面地控诉封建专制势力的罪恶与残忍,揭示了封建专制必然走向灭亡的道路。新世纪诗歌可以说是90年代诗歌的延续,它面对的是日益汹涌澎拜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浪潮,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占着民众精神领地,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诗歌依然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而且更加边缘化。“在困境中生存”是《新世纪诗典》的诗歌首先应当直面的现实。让人欣慰的是,以伊沙、杜思尚、韩东等为代表的新世纪诗人依然在寂寞中坚守着精神的高地,如同“以文学为匕首”的鲁迅,孤独地在黑暗的现实中探索国民性的弱点。新世纪诗人们在反思90年代诗歌的经验的同时,也在努力重建诗歌与现实的最大机制。这些诗人中他们将自己的独特目光聚焦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用诗歌表达他们的生命体验。
五、口语诗的写作技巧
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那里包含着某些“空”,只有读者才能填这些“空白”。《母亲的忧伤》整个行文无疑就是这样的召唤结构,正因为作者这样巧妙地处理,诗文才能充分地引起读者填空、对话的兴味,从而联系1958年那个闹饥荒的年代,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共鸣,心痛神痴,潸然泪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学接受阶段——领悟。读者在阅读《母亲的忧伤》后潜思默想,体悟人生,提升精神境界。阅读《母亲的忧伤》,在阅读进行高潮阶段后读者会留下《母亲的忧伤》所呈现给读者的心理延续和留存余温,让我们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