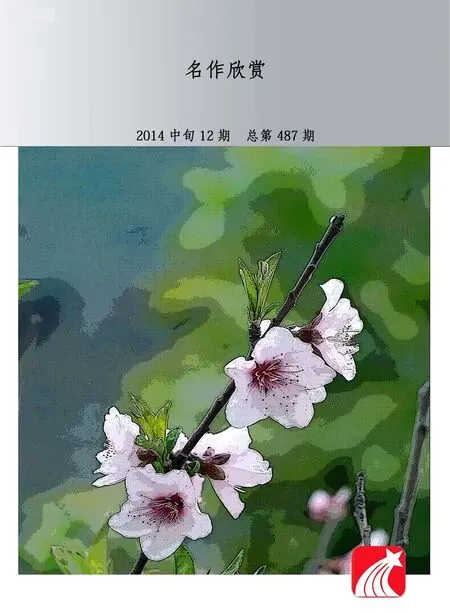古代动物变形神话的观念起源
——中国广义神话兽类“跨界流动”研究(一)
⊙赵 希 田梦源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333]
一、思维基础:从“活物论”到“万物有灵”
19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著名的“万物有灵论”对宗教和神话的起源做出了解释。泰勒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人从影子、回声、梦魇等现象中得到启示,猜想人类在躯体之外还存在灵魂。进一步的,他们推己及物,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具有灵魂,这也被称为“泛灵信仰”。“万物有灵论”对神话和宗教信仰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反对。据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的调查发现,世界上尚有一些民族在形成灵魂的概念之前,就已经有了巫术,也相信自然物具有人类的某些品格,正如柯斯文所言:“在宗教发展的开头阶段,人们还没有特殊的关于灵魂的概念;早期宗教意识实质上不过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自然具有活力这样一个一般的且颇不明晰的概念。”①基于此,泰勒的继承者马雷特又提出了“前万物有灵论”来补充泰勒的观点。中国神话学研究者袁珂先生认为这一学说“完全有其必要,并且合乎实际”②,将其应用于中国神话的研究之中,并把马雷特所定义的“前万物有灵论”重新命名为“活物论”:
刚从动物脱离出来的原始人类,开始制造并学会使用简单粗陋的工具,从事集体劳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使分节语言发展完善起来,借以交流经验,表达思想感情,并借此从事简单幼稚的原始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非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③
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被列维·布留尔称为“原始思维”。在他看来,最初的原始人思维中并没有灵魂的观念,但遵循一种集体表象之间的“互渗律”,“感到自己与其社会集体的神秘统一、与作为其图腾的那个动物或植物种的神秘统一”。④由于原始人对世界的感知是混沌一片的,因此他们把自己作为尺度去探测周围的自然物,也就是把它们拟人化,由此首批神话故事产生。这类故事在汉族神话中基本已无法复原,而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史诗中却还保留着最原始的记载。如纳西族的神话史诗《崇搬图》、白族史诗《创世纪》中都记载了“会走路的树木”“会说话的石头”等活物。⑤对于处在狩猎时期的原始人来说,动物是他们接触最多的对象。因此在这最早的一批神话中,表现禽兽和人类打交道的动物神话是神话的主要部分。据袁珂先生研究,《山海经》中的两个零片及“伯益和禽兽”等传说中记载的能做人言的动物与精通兽语的人,正是活物论时期动物神话的重要体现。⑥
二、静态变形神话:人兽一体
活物论时期的神话中描述的动物只经过了初步的拟人化,部分动物仅仅掌握了人类的语言,并不具有人类的精神品格,也尚未体现出形体的变化特征。直到人类产生了灵魂观念,并将之赋予自然物,他们眼中的万事万物才开始具有精神灵魂,并呈现出变化莫测的神秘特征,这也就是所谓的“万物有灵”。在这种条件下,动物就不仅仅是有生命的活物,而是被作为人格化的神灵对待,它们的形体在神话中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原貌,而是出现人兽形象、异种动物形象混合的现象。《山海经》中所记的神灵和精怪大多都是半人半兽的外形,他们是原始人自然崇拜的对象,如:
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稰用稌。⑦(《南山经》)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无水。⑧(《西山经》)
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⑨(《海内东经》)
这种人兽同体共生的现象被台湾研究者乐蘅军视为变形神话的一种表现方式,即“静态变形”⑩。乐蘅军把变形神话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力动变形”,即两种物体或两个形象之间的完全变化;另一种则是“静态变形”,指的就是多见于《山海经》中的这种人兽共体现象。对于“静态变形”的发生机制,乐蘅军将其解释为“正在表现着变形的过程”,他从达芙妮变身月桂树的雕像中得到启示,提出静态变形是动态变形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变化余味最酣饱的中途,突然因为某种原因(这些原因是永不可知的),而凝固了停顿了。于是它就以异类互体的形象被永恒地保留下来”⑪。然而,达芙妮变身月桂树的雕像毕竟是艺术家人为创作的产物,而神话,如马克思所言,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二者在发生机制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故事所承载的功能也是不可同类相推的;用一个静止的瞬间表现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更加符合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理性总结出的艺术创作规律,而并不适用于原始人的思考方式。
那么这种人兽一体的变形神话在原始思维的模式中,是如何被建构,又有着怎样的特殊功能呢?首先,神话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对原始时期的化石分析和相关语言学、文字学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对形体及功用作用的认识始终离不开对象的感性形式,始终寓于具体形象中”⑫。原始先民需要借助一些具体、直观的形象符号来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即使是对抽象事物的想象也必须经过具体形象的中介。比如,神话中“龙”的形象就来自多种动物本领和功能的叠合。同时,在原始思维中,事物的局部和整体是等价的。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为“分有律”:“整体连同其所有神话—实体本质进入部分,它在感受和实质方面就在部分之内,从这种意义上说,整体就是部分。”⑬因此,人兽一体的神灵形象,如人面、蛇尾、羊角一体的形象,虽然在视觉上看是不同物种的部分拼合,然而在原始人看来,这个部分拼合而成的整体形象,实质上同时拥有了人、蛇、羊三者的性状和功能,甚至还在叠加后产生了原本三者都不具有的神力。如《北山经》中犬身人面的山獐,就兼具人的表情和犬的行动敏捷,并且对天气变化还有一定的预兆作用: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山獐,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⑭(《北山经》)
在生存环境恶劣的远古时代,先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威胁,不得不在想象中借助动物的能力,来克服自然的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等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⑮原始人通过变形神话构造出这些人兽一体的神灵精怪,在想象之中完成了人与动物的性状与能力的叠加,这是建立在利用想象产生现实动力的观念之上的。在原始人看来,想象与客体是不存在对立的,“想象不能代表事物,想象本身就是事物;想象不仅仅是为对象产生的,它还具有相同的现实性,因此想象代替事物的直接存在”⑯。通过这种静态的形象叠合,原始人在想象之中突破了形体的限制,获得了动物的能力,从而实现了生命对于生存空间的超越。
乐蘅军在《中国原始变形神话试探》中指出,人们对于静态变形神话的看法往往是“这些怪物绝不给人时间的感觉,它们不是时间的存在,而是没有时间分割、没有意义呈诉的一种混沌的永恒存在”⑰,而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没有触及本质问题的一般看法。事实上,这种看法虽然模糊,却并非完全错误。静态变形神话中“混沌的永恒存在”的形象正符合混同的原始思维;另外,这些人兽一体的精怪确实也不是时间的存在,因为它们是空间的存在,是通过异类形象的叠合对于有限生命形式的空间上的超越。
三、力动变形神话:人对动物的化归
如果说异类共体的静态变形神话是一种生命对空间的突破,那么由一物转化为另一物的力动变形神话,则是生命对时间的超越。伴随着灵魂观念的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也在原始人心中萌芽,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观念。”⑱在“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原本随着肉体死亡而终结的生命,可以通过变形将灵魂转移到新的形体之中,从而实现生命的延续。因此,神话中的力动变形,实质上是一个生命在形体转化中不断绵延的过程。
原始神话中的力动变形多以人死后化为动物的方式发生,如: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⑲(《左传》)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⑳(《北山经》)
通过向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转化,鲧、女娃都逃脱了死亡的对生命的终结,从而使得灵魂在另一个形体内得以延续。那么,它们为什么总是化作动物呢?这与中国原始图腾信仰有关。“图腾”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思是“他的亲族”,印第安人将某种动物视为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图腾信仰。经过发展,图腾形成了一种文化,在亲属观念之上产生了祖先观念,进而也就有了关于氏族起源的图腾神话。在图腾文化中,存在着人与图腾相互转化的信仰图腾:一个人的降生来自于他所属的图腾物,那么他死后也应该回归图腾物。例如,在精卫填海的神话中,女娃死后化成了鸟,这并不是一个偶然随机的行为。据吕思勉先生研究,女娃之父炎帝与少昊是同一人㉑,而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的图腾正是鸟。因此女娃化作精卫,正是对其氏族图腾的回归。与之相似,鲧化作黄龙也是变形为其氏族的图腾动物。通过对动物图腾的化归,神话中的人物跨越了死亡对于生命的中断,在时间的意义上实现了生命的绵延。
四、生命一体意识
综观早期的动物变形神话,无论是静态形象拼合还是动态形变,无论是人到动物的转变还是不同动物之间的互化,都贯穿着原始人类强烈的生命一体意识。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原始人的这种生命浑融的意识,正是神话中变形的思想来源:
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各不同领域间的界线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形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性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㉒
这种生命一体的原始观念,在变形神话中具体表现为生命的平等、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秩序。无论是静态变形神话中的人兽一体、还是力动变形神话中的人兽互化,这都是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秉持着生命一体、万物平等的观念,甚至动物拥有人类不具有的能力而值得被崇敬。 这反映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差异又相互融合的关系,也就是一种辩证一体化的关系。一方面,原始人承认人类与动物存在形态、功能等多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可以通过人兽叠合的神话形象加以克服。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可以从动物身上获得上天、入海等原本不具有的能力,从而实现对生命空间局限性的跨越。另一方面,神话中人与动物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这从本质上体现了原始社会中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正如卡西尔所言:“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㉓
正如乐蘅军所指出:“透过变形神话的想象和创造,这一个变形再生,被赋予了永恒性:它超乎先前那受命于现实的脆弱生命,而是更坚执的和绵绵不绝的生。事实是,他已从物质的存在,上升为非物质的存在,从有限的生到达无限。他的生已成了一个永不灭绝意象。”㉔这说明,神话中的变形,正是生命一体化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
变形本身就意味着生命的秩序。中国先秦哲学认为万物的秩序表现为形态的变化。因为宇宙涌动不息、变化无常,所以宇宙中的动物和人也是不断转化的。变形不仅是动物的自然行为,还被视为产生新物种的方法。《庄子》中的许多神话材料就可以说明: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㉕(《庄子》)
有学者认为,鲲鹏寓言说明“物种变化被人看成宇宙生成过程的一项要素”㉖。通过动物的变化,宇宙生命的秩序才确立起来,这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变形意义的思考。
① 〔苏联〕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彤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0—171页。
②③ 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页,第11页。
④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3页。
⑤ 李缵绪:《白族文学史略》,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⑥ 袁珂:《原始思维与活物论神话》,见《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⑦⑧⑨⑳ 王红旗、孙晓琴撰绘:《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第35页,第284页,第64页。
⑩⑪⑰㉔ 乐蘅军:《中国原始变形神话试探》,见温儒敏编: 《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第283页,第283页,第300页。
⑫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⑬⑭㉒㉓〔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第52页,第138页,第141页。
⑮⑯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第44—45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⑲〔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54页。
㉑ 吕思勉:《古史辨·三皇五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371页。
㉕ 〔东周〕庄周:《庄子》,陈鼓应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㉖ 〔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