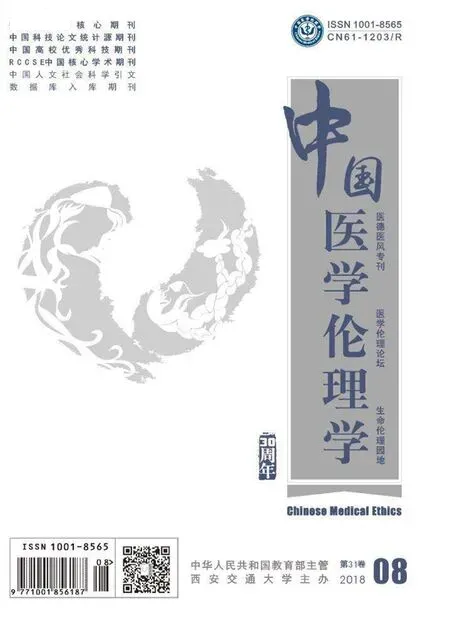头颅移植的技术、伦理争议及其展望
徐天启,张晓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上海 200127,timothy_93@sjtu.edu.cn)
早在19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头颅移植的设想,然而在当时就算是肝移植、肾移植等手术都面临许多技术瓶颈[1]。百余年来,头颅移植术的方案设计及动物实验从未停止[2-4],然而至今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13年,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Sergio Canavero提出人类头颅移植方案,并计划开展相关手术[5],这将头颅移植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国外科医师任晓平同样长期致力于头颅移植手术方案的研究[6],他们及其团队于2017年在人类尸体上完成了模拟手术。但原计划于2017年进行的世界首例活体人头颅移植手术并未按计划进行。一方面,头颅移植术在技术上存在限制,如脊髓切断后的神经修复、神经功能康复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人类也无法解决头颅移植术所带来的伦理上的冲突。本文就头颅移植的历史、手术技术及伦理问题进行综述。
1 头颅移植发展历史
1900年法国外科医生Dr. Alexis Carrel提出使用精细的针头和缝线,牵拉在离断血管上留置的3根缝线扩大血管断面从而完成血管吻合。该技术使得许多器官移植手术(主要是甲状腺和肾脏移植)取得了成功[7]。1908年法国外科医生Dr. Alexis Carrel和美国生理学家Dr. Charles Gunthrie使用该技术进行了第一例犬头颅移植,自此拉开了头颅移植研究的序幕。
1.1 血管吻合
在头颅移植技术发展过程中,有效的血管吻合是移植医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1908年,Carrel和Gunthrie首次尝试头颅移植手术,在未损伤供体犬头颅的前提下,将其连接到受体犬的身上,血流首先流经供体头颅,然后流入受体头颅。移植手术后前期受体犬的头颅存在视觉、听觉、运动反射,但数小时后其头颅状况发生恶化,可能是由于供体犬头颅存在约20分钟的无血流灌注状态引起。1950年苏联外科医生Dr. Vladmir Demikhov对该手术方式进行改良,然而,大多数实验犬多在几日内死去,存活最长的供体头颅存活了29天[2]。
1965年,美国的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White进行了新的尝试。他发明了“自灌注”血管环用于将颈内动脉和颌内动脉吻合,使得移植过程中供体大脑即使自躯体断离,仍能获得自颈内动脉的血液供应[1]。1970年,White首次在灵长类动物中进行头颅移植术。供体猴头颅在术后3小时可咀嚼、吞咽食物,眼球能跟随运动,EEG检测提示大脑处于清醒状态[1]。2015年,中国外科医生任晓平进一步完善了头颅移植过程中的血管吻合策略,提出只需切断一侧的颈内动脉及对侧的颈静脉,剩余的动静脉能持续为头颅供应血液[8]。通过该方法在鼠类中进行头颅移植,可使头部血流灌注维持在100/60mmHg以上,超过半数的实验鼠存活时间超过24小时,最长的存活时间超过6个月[2]。
1.2 免疫抑制
在头颅移植探索早期,由于免疫抑制剂尚未问世,器官移植因排异反应无法在临床展开。20世纪50年代起,得益于硫唑嘌呤、6-巯基嘌呤和皮质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的问世,肾脏、心脏移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开展。White首次在猴头颅移植实验中使用免疫抑制剂,证明了免疫抑制剂能够抑制头颅移植过程中的超敏反应,但高剂量的免疫抑制剂也导致了实验对象在9天后的后果[1]。
此外,现有器官移植手术的围术期免疫抑制方案并不具有普适性。例如,用于心、肝、肾等内脏器官移植术后的免疫方案在推广至面部、手部等富有大面积皮肤组织的移植手术时免疫抑制作用不佳[1]。这一现象直到1999年,新型免疫抑制剂诸如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的问世才得以改变。然而由于尚无人类头颅移植的案例,其可能面临的免疫抑制问题仍属未知[9]。
1.3 脊髓吻合
过去White等人进行头颅移植实验时,于脊髓C3-C4层面离断头颅与躯干,导致接受移植后的动物必须时刻给予人工呼吸支持[8]。2014年,任晓平提出游离头颅可自脑干切断,使供体的延髓仍能支配呼吸运动[8]。Canavero提出了脊髓融合GEMINI方案,希望利用缺乏重视的皮质-躯干网状-脊髓固有通路维持术后躯体的基本功能。相比于脊髓平面以上的神经元及锥体系通路,脊髓固有通路神经纤维更易再生。当锥体束受损时,借助于神经系统可塑性通过脊髓固有中间神经元发挥作用[5, 10-11],但其也承认,在人类中这种神经系统“重编程”的具体机制还有待完善[11]。
1.4 脊髓融合剂
脊髓融合剂大多为聚合物,如聚乙二醇、Poloxamer和Polxamine等[1]。2004年,美国Purdue大学Richard Borgens博士团队对受伤至脊髓截瘫72小时内的犬应用PEG材料,发现超过半数的犬在接受治疗后2周内自行行走[12]。2012年,Cho和Borgens在脊髓损伤豚鼠的脊髓周围植入PEG纳米颗粒,后通过测量躯体感觉激发电位(SSEP)来评估脊髓生理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提示PEG材料能特异性修复受伤脊髓中受损的细胞膜,减轻氧自由基的生成及脂质过氧化作用[12]。然而,Borgens的研究中选择的动物截瘫模型皆为脊髓压迫伤而并非横切伤,故PEG作为脊髓融合剂在头颅移植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讨论[11]。
1.5 血管再通、神经保护与脑缺血
任晓平认为,虽然在鼠类实验中实现了受体大脑的持续供血,但在人头颅移植手术中,由于存在手术台间的物理距离,无法像动物实验那样实现持续大脑供血[2]。目前主要有两种设想来减轻供血暂停可能造成的影响。第一种是低温疗法(White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灵长类动物的头颅移植实验是采用了深低温来进行脑保护[1];在任晓平之前进行的鼠类实验中,采用了亚低温进行脑保护[2,8]),第二种是使用Perftoran、硫化氢等具有神经保护作用的药剂[1]。
1.6 疼痛控制
头颅移植术后可能产生中枢性神经病变疼痛(CCP),Canavero表示可以通过选择性捣毁传导慢性疼痛的下额叶白质来解决此问题[13]。然而,此项手术尚处于理论及早期实验,无临床资料证明有效。
2 头颅移植方案
在HEAVEN手术的关键步骤GEMINI脊髓融合过程中,术者将使用特制的纳米级别手术刀进行脊髓切割以使损伤最小化;在C5、C6层面应用PEG,使皮质-躯干网状-脊髓固有通路(Cortico-truncoreticulo-propriospinal pathway)神经元轴突及部分锥体系通路神经元轴突融合;使用电刺激加速神经出芽,使脊髓固有神经元网络再次激活;使用特制的负压的连接器使脊髓两个断端维持在一起直到融合完成;在手术过程中,对供体的脊髓和受体的头颅进行低温处理,降低神经损伤的同时,保护供体的其他器官不因低温的运用而产生损伤。[3, 5, 10, 14]
3 头颅移植的伦理问题
头颅移植由于打破了公众对自然环境解释和分类的常规认知,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厌恶、不自然的情绪,由此激起公众对器官移植的反感[15-16]。1954年,Joseph Murray成功进行第一例肾脏移植,不少人认为这一手术违反自然规则。在此之后的50余年中,相继成功进行了心脏移植、面部移植和手移植,公众同样有类似的负面认知[18],头颅移植同样具有相似的社会动力学效应。面部、手移植的反对者认为,为进行一项以改善功能而非挽救生命的手术,而承受后续抗排异治疗的免疫抑制状态不符合不伤害的伦理原则。而头颅移植若应用于如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目前尚无其他疗法的患者,将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手术。之前饱受争议的肾脏移植、心脏移植等挽救患者生命的器官移植手术随着近年来的广泛开展,反对声逐渐平息[17]。
HEAVEN和GEMINI SCF手术的疗效尚不确切,有学者认为,HEAVEN手术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性的手术,更像延长生命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即使脊髓连接成功,患者仍需要服用大量的免疫抑制药物,而药物的效果无法保证[16]。
头颅移植概念及手术方案的提出,是建立在作为意识载体的神经系统与躯干新二元论观点的基础上。这种观点认为意识是由低级的神经生物学过程介导而产生,意识之于大脑的神经活动就像消化之于胃的蠕动。意识是完全由脑内活动介导的,几乎和躯干没有任何关系[18],因此头颅移植成功实施后,患者的意识能够得到完整保留。然而,以António Damásio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由于躯干与大脑有互相作用的生化和神经环路连接,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意识依附于整个大脑-躯干有机体,头颅手术成功进行后大脑和躯干是否能够相互“兼容”有待进一步检验[18]。
头颅移植还可能引起自我认知的混乱。现代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是嵌入式的,这意味着身体是人类本体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即使神经重连可行,患者仍会面临如何将新的躯体融入已形成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和身体意象(body image)等难题[16],涉及个体认知过程中对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及对自己身体相貌、体格、体能等方面的认知。在既往异体脸部及手移植的案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患者接受移植后,在精神状态上产生疑惑,最终引起精神问题[16]。
供体配子和基因的延续也是难以绕过的伦理问题。这点Canavaro医生也曾提到,但他认为,供体躯体上带有配子不但不是实施头颅移植的伦理阻碍,而是头颅移植的好处之一:一旦移植成功,且受体开始考虑生殖时,供体及其父母能够预期有他们基因背景的后代的出生[16]。虽然Canavaro医生在面对头颅移植伦理的质疑而给出的回答[17]中认为这是从死亡中衍生出生命的奇迹,但由此而产生的抚养权归属、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远未得到解答[17]。
头颅移植后诱导产生的器官排异反应可能对供体内脏器官产生伤害[9]。若不是用于头颅移植,这些器官本可以被安排给其他移植等候名单上的候选者,从而挽救生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器官仍是稀缺的医疗资源,需要进行肝脏、肾脏、心脏移植的患者往往需要等待数月乃至数年才能获取供体器官,有的甚至在等到供体前就因疾病恶化而死亡。而头颅移植中使用的每具供体本可以供给10至15个等待单独供体器官的患者[17]。
除此之外,进一步进行围绕头颅移植相关的前期动物实验在伦理审批上尚存在挑战。根据Robert White和Demikhov的前期实验,此类实验对实验动物的伤害是致命的,而其所能得到的结果也通常是试验性质的[1]。在一些国家,此类实验甚至无法通过动物福利及伦理研究委员会的审查[16]。
4 新闻报道与评价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Arthur Caplan在《福布斯》(Forbes)杂志撰文称“该研究不仅在科学上行不通,在伦理上也说不过去。”[19]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临床头颅移植违反了中国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希望有关单位伦理委员会起到应尽的责任。在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中国绝对不允许这种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20]同时指出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刚走出一个低迷的阶段,现在已经被世界移植界赞誉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我国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成为唯一合法来源,肝、肾脏、心、肺与小肠移植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急需培养一大批德艺双馨的移植医生,推进公民捐献大爱精神,要靠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走近世界移植事业舞台的中心。每一个移植医生都应该爱护国家的声誉[20]。
2017年10月23日,世界神经外科协会神经理事会和荣誉主席关于头颅移植问题发表声明:“目前施行头颅移植的技术有其可能,但这只是在人体头颅必需的脑血管吻合基础上建立脑血液循环,由于脊髓离断后,头与脊髓不能建立神经联系,人们仍没有能力做到脊髓离断后的神经再生。因此头颅移植在伦理学上不但不可接受,科学方面也毫无意义,从伦理观点上,我们的医务人员和手术操作必须考虑对患者有益,而不是引起媒体的关注,为此,任何个人和组织必须拒绝。”[21]
5 展望
头颅移植自概念提出、动物实验至今百年有余。虽然目前动物实验取得了一定进展,人类头颅移植的手术及围术期治疗方案也已提出,但不可否认在人类中进行头颅移植手术尚缺乏可靠的动物实验论证。同时,头颅移植亦牵涉意识、自我认知等认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在伦理上,接受移植后患者的身份、法律、社会地位、供体配子及可能繁衍出的后代的法律社会问题,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公众对头颅移植的接受程度等一系列伦理问题亦有待进一步讨论。相信随着对头颅移植相关的手术方式、免疫抑制问题、脊髓融合、神经修复、神经康复等问题研究的深入,人类头颅移植在技术上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但在此过程中,对头颅移植相关伦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也亟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