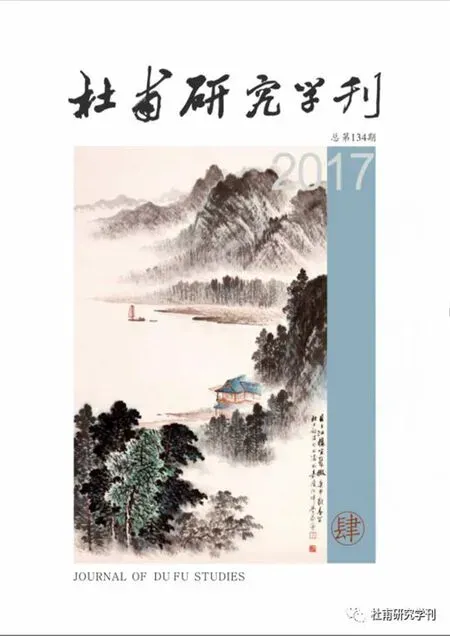杜甫“陷贼”辨
薛天纬
自北宋迄今,千年来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形成了认同度很高的共识,似乎不存在值得关注的疑点或争议。但关于某些节点的叙事,事实上仍有不小的悬疑。欲解决这些悬疑,很难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这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然而,仅仅凭借诗歌文本及基本史料(比如《资治通鉴》)的细读,仍可能有所收获,有可能对相关事件打破传统说法而作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新叙事。“陷贼”之说,即为一例,试辨之如下:
一,“陷贼”说之发端及传延
记述杜甫生平事迹最早的文献,在唐代,先后出于樊晃及元稹。樊晃是杜甫同时代人,大历年间任润州刺史,曾编《杜甫小集》六卷,所撰《杜工部小集序》有“至德初,拜左拾遗”之句。元稹应杜甫孙杜嗣业之请撰《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其中也有“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的记事。二者记述杜甫在安史乱中此一时段事迹较简略,着眼点均在“拜左拾遗”。五代后晋时,署名刘昫的官修《旧唐书》成,其《杜甫传》记曰:“(天宝)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叙事稍详,间有错误,但没有“陷贼”的记述。
到了北宋,编集杜甫集的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对诗人生平事迹作了概述,“陷贼”说首次出现:“天宝末,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至德二载,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诏许至鄜迎家。”与此同时,王洙对《旧唐书》关于杜甫的记事有所驳正,曰:“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纬按,指《旧唐书》)列传,彼为踳驳”,“《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集有《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王洙在这里以杜诗为据对《旧唐书》进行的驳正,无疑是可取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洙在提出“陷贼”说之际,自道其研判杜甫事迹的方法,是“观甫诗与唐实录”。“唐实录”是帝王的实录,只能提供杜甫相关事迹发生的大背景,而不可能直接言及杜甫事迹,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王洙正是“观甫诗”而提出“陷贼”之说。
正如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在《前言》中指出的,王洙所编《杜工部集》“是后来所有杜集之祖本。尔后,一切编年、分体、分类、分韵本皆以此为据”。也就是说,王洙所见到的杜诗以及诗的编年,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杜诗以及诗的编年相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就“观甫诗”这一话题,在千年之下与王洙展开“对话”。王洙是怎样通过“观甫诗”而得出杜甫“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的论断呢?通览杜甫自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756)携家北上避乱至至德二载(757)“窜归凤翔”这一时期的诗作,其中并未出现“陷贼”一语。我们可以推知,王洙的想法,乃是因为长安沦陷时杜甫本不在长安,但杜甫于至德元载九、十月间至二载春又在长安写有《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春望》等诗,因而断定杜甫这一时期人在长安;然而此期长安已被叛军占领,杜甫之在长安非“陷贼”而何?同时,杜甫诗中又有“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等句,“没贼中”“堕胡尘”这样的自道之语会提示王洙形成“陷贼”的判断。以上应该就是王洙的思维逻辑。王洙所说“独转陷贼中”一语,“独”是强调杜甫独自一人而非与家人一起,“转”的意思则强调杜甫是经过一番辗转而“陷贼中”(训参杨树达《词诠》),或释为“却陷贼中”(训参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再仔细推究“陷贼”二字,除了指明杜甫身在贼中之客观事实外,似还包含了杜甫其实是陷于叛军之手这层意思。
继王洙之后,宋祁在所撰《新唐书·杜甫传》中对杜甫这一时段的经历有了更详细的记述:“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赴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新唐书》“为贼所得”的说法,较王洙之“陷贼”说语意基本相同而表述更为明确,而且明言这是发生在杜甫自鄜州“欲赴行在”的途中。

“陷贼”(或“为贼所得”)说自宋代形成之后,一直传延至今,未见异议。兹列举最具代表性的若干说法如下: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之《杜工部年谱》:“(肃宗至德元载)闻肃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自鄜羸服奔行在”一语基本照抄《新唐书》,“陷贼中”则用王洙《杜工部集记》语。
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中华书局1962年12月出版)“附录”之《杜工部年谱》,与上引仇注文字全同。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附录”之《杜甫年谱简编》:“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获,押赴长安”。
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之《杜甫年谱简编》:“欲……投灵武。中途被掳至长安。”
萧、谢两种杜集最新注本谓“押赴长安”“掳至长安”,乃是“陷贼”之后叙事的合理延伸。
二,杜甫“陷贼”辨

以下即依托《杜甫全集校注·杜甫年谱简编》这段文字作“笺注”式的详细考察:
(天宝十五载)五月,奉先县受到叛军威胁,杜甫从长安奔往奉先,携家向北转移,至白水县(今属陕西)依时任白水县尉的舅父崔顼,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属京兆府。白水县(今陕西白水)属冯翊郡(同州)。冯翊郡的范围与今陕西渭南地区相当,即关中平原的东部,白水县位于该郡最西北端,北依黄龙山,是关中平原与陕北山区的过渡地带,所以较奉先安全。诗人在白水所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写道:“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诗写了对战争形势的关切,“相公军”指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官左仆射、同平章事,因称“相公”)所率官军,“铁马云雾积”谓兵力强盛。“东郊何时开”是盼望早日击败进攻潼关的叛军,解除长安东面的威胁。由此可知,此诗必写于六月上旬,潼关尚未失守时。
六月,叛军攻破潼关,白水受敌,杜甫又携家北逃……七月中,抵三川县,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题下原注:‘天宝十五载七月中,避寇时作。’……最后安家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

《彭衙行》作于翌年秋,已经任官左拾遗的杜甫在回鄜州省亲之际,回忆上年北上避乱的往事,诗曰:


《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长不录),注家谓作于这年七月中避寇时,良是。三川县属鄜州,今富县有三川驿,在县城之南,唐时三川县应即其地。诗以“观水涨”为题,实写途中遇到的一场山洪,并从眼前路途的艰难生发出“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一类人生感慨。诗中唯写山洪的凶猛险恶,而未言及叛军对人的威胁。《彭衙行》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告诉我们,杜甫携家自白水向北经坊州至鄜州这一路,自六月中旬至七月间并未与叛军遭遇,他所经行的地区虽然因地方官附贼而名义上已经沦陷,但并非被叛军直接占领。当杜甫一家在羌村住下来时,这个小山村也一定是安全的。
八月,闻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即从羌村出发北上,取道延州(今陕西延安),经石门,过徐寨,上万花山,到达延安七里铺,欲出芦子关转道灵武,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获,押赴长安。
《资治通鉴》载,七月甲子(十二日)肃宗于灵武即位。杜甫从羌村出发奔赴行在的准确日期无从得知,“八月”只是比较合理的推想。甚至杜甫奔赴行在的行动本身也是后世杜诗编集者及研究者推想出来的。其根据,只能是《彭衙行》中“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二句。鄜州的北面是延州,州治所肤施(今陕西延安)。芦子关在唐代属延州,位于延州西北部(今属靖边县天赐湾乡),出芦子关继续西北行,经夏州、盐州,可达灵武。杜甫如果不是以奔赴灵武为目的,其“欲出芦子关”的行动就无法解释了。至于《新唐书》谓杜甫“自鄜州羸服欲赴行在”一语中“羸服”的细节描述,以意度之,应是出于杜甫翌年所作《述怀一首》中“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二句,盖彼时自长安赴凤翔行在“羸服”情状如此,此时自鄜州赴灵武行在亦当同此“羸服”。


三,杜甫其实是潜回长安
北赴灵武未果,杜甫当返回羌村。然而,上文已述及,至德元载九、十月间至次年春,杜甫又写了《月夜》《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诗,这些诗篇明显作于长安。那么,杜甫如何又到了长安?如若跳出传统的“为贼所得”说,转换为另一种思路,我以为杜甫是自己潜回长安,姑称“潜回”说。
“潜回”说依据为何?我想至少有两点。首先,杜甫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使他不会在小小山村安住下来避乱。杜甫携家避乱,其实全是为家人的安危着想,他自己则时时怀有另一种打算。杜甫此前已有北赴灵武投奔行在之举,次年四月又有奔赴凤翔行在之举,在这两次行动之间,杜甫立足现实情势应该还有一次行动,即“潜回”长安。他的行动具有连续性,而且,每次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向朝廷靠拢。长安虽然陷于叛军之手,但如前引《资治通鉴》所记述,长安民间的抗敌活动很活跃,这些消息会在心向朝廷的百姓中不胫而走。杜甫“潜回”长安,应受到这种形势的鼓励。当时,官军与叛军的战事除河北、河南主战场及潼关一带之外,都发生在长安西部。我们来看看长安以西的形势:对于占领着长安的叛军来说,“西门之外率为敌垒”(前引《资治通鉴》),官军距离长安并不遥远。杜甫《悲陈陶》诗所写的陈陶之战,战场即在咸阳之东(详后),咸阳紧邻长安,咸阳之东实即长安的西郊。至于咸阳之西,前引《资治通鉴》已说到,“贼兵力所及者,……西不过武功”,武功再向西,出了京畿道的边界,进入岐州凤翔郡,《塞芦子》诗云“岐有薛大夫”,那里就完全是扶风太守兼防御使薛景仙控制的地区,而且即将成为肃宗进军长安的行在所。因此,在观察了平叛战争的总体形势后,在奔赴灵武行在不果的情势下,杜甫选择“潜回”长安,实即迎着官军进攻的方向、亦即向朝廷靠拢。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杜甫“潜回”长安,亦有长期形成的“长安情结”的驱动作用,并不排除他要亲眼看看长安失陷后的真实境况,这些都出自他无比深厚的家国情怀,我们实在不可低估了杜甫这种情怀的热切程度及其左右人之行动的力量。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闺中”之人知道杜甫此时人在长安,才谈得上“忆长安”。假如杜甫“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获,押赴长安”,对“闺中”来说,他就是出门一去无消息,失踪了,该向何处忆他?“只独看”之“独”,不仅写了因为自己离家在外,妻子只能独自望月怀人,又写了因为“小儿女”不解事,不能与母亲同“看”同“忆”,因而倍增了母亲的孤独和凄凉。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杜甫“潜回”长安,毕竟有一定隐秘性,所以他只给妻子做了交代,夫妻俩还将此事瞒着孩子,“小儿女”并不知道父亲去了长安,自然也就“未解忆长安”了。诗用所谓“对面写法”,所写“闺中”情事全出自诗人自己的想象。此种细微入里的心理描写,表明诗人与妻子各自将对方处境及心境了然于心。再回过来细味开首二句,诗人似感慨于前不久还与妻子并坐在鄜州的月下,而今夜自己离开家人来到长安,妻子就只能“独看”鄜州月了!
《哀王孙》(诗略)宜作于九月。诗人路遇的这位王孙,实为死里逃生。可知叛军在长安杀戮皇室亦有疏漏。
此期在长安,杜甫写有三首密切关注战局的诗篇《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以“诗史”价值而言,此三诗实不亚于“三吏”“三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杜甫在长安获知了战事的准确消息,“四万”之数与史书记载相合。“群胡”二句所写叛军气焰嚣张的场景,是杜甫在长安亲见亲闻。接着,又写了《悲青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

至德二载正月,杜甫在长安作《塞芦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南空荆棘。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二载三月,杜甫在长安作有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连三月”,诸家解说多有纷争,兹不论列。其实,“连”即连绵,犹“兵连祸结”之“连”,“烽火连三月”即“战火连绵的三月”。“家书抵万金”,表明诗人与家人曾有书信相通,只是战乱年月音信稀缺罢了。他在长安的住处家人是知道的,否则,“家书”寄往何处?
二载春,杜甫在长安的重要诗作还有《哀江头》。开首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潜行”二字,实可启发人们对杜甫“潜回”长安的想象。诗的结尾曰:“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诗人在曲江留连终日,至晚方归。他栖身城南,所以“欲往城南”;但却眼巴巴地“望城北”,因为他心向着城北。城北是肃宗行在的方向,前引《资治通鉴》“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数语,即是杜甫诗句的注脚。《悲陈陶》结句“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亦可互参。



积年读杜,疑惑在胸,难于释怀。今详参杜诗,略有心得,不避固陋,发为新说,愿与研杜诸君共为切磋。
注释
:①杨军撰:《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6页。元稹文又见《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6580页及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中卷)(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第15页,无“属”字。

③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58页;《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第61页。王洙《杜工部集记》亦载于《杜诗详注》“附录”,无“独”字。

⑤(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58页。《艺文志》载:“《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与此《唐书》相较,刘昫撰《旧唐书》晚出,故称《旧唐书》为“新书”。
⑦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⑧(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737页。
⑨(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杜甫传》研究杜甫事迹的方法,与王洙之“观甫诗”基本相同,其对杜甫事迹的记述除了杜甫与严武“睚眦”的不经之说采自《云溪友议》(详参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载《文史哲》2004年第1期)的“小说家言”之外,其余均可在杜甫诗文中得到印证。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宋祁提出“为贼所得”说的思维逻辑与王洙提出“陷贼”说也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