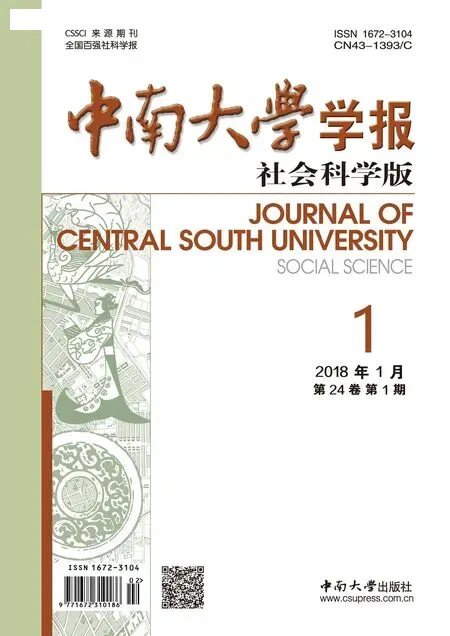资本显著不足不应适用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张素华,吴亦伟
资本显著不足不应适用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张素华,吴亦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并非对团体人格本身的否认,而是对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否认,因而确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事由的唯一依据只能是“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被滥用”。但资本显著不足并不构成滥用。在一个社会信用体系逐渐健全的时代,在一个投资风险预见义务已能够由债权人负担的时代,在一个注册资本信用逐渐削弱的时代,公司责任的独立性事实上取决于资产的独立性而非资本的多寡,再以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既不合时宜,又违背法理。因此,实务界理应摒弃资本显著不足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规则,转以资产的独立性作为替代标准。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独立人格;独立责任;资本显著不足;资产独立
一、引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称“揭开公司面纱”)是美国法院于19世纪末首创的一项制度,旨在“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被滥用之时,否认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公司人格,直索公司背后股东的责任”[1]。其中,资本显著不足便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常用事由之一,美国法院以此为由成功揭开公司面纱的比例高达73.3%[1](138)。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第20条第3款首次对该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2013年修正时保留)①。司法适用中,由于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给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类型化标准,法院通常会借鉴学理上的概括,并采用“具体情形+解释说明”的方式形成判决的主要理由②。而资本显著不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之一③。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公司人格否认”为检索词共获得235份裁判文书,以“资本显著不足”为检索词可获得其中的63份,剔除不相关的案例,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裁判文书合计39份,占比16.6%④。其中,有31份裁判文书是在承认“资本显著不足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这一大前提下作出的,比例为79.5%(见表1)。而从这些文书的正文来看,较之于论证资本显著不足何以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事由,实务工作者似乎更热衷于小前提的判断,即究竟何为资本显著不足,大前提几乎成了无需证明的定理。虽然也有少量判决拒绝承认大前提为真(见表1),但其理由还不足以颠覆实务界的既有认知(见表2)。不仅如此,学界也逐渐将问题的研究重心放至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标准和判断方法上,似乎“因为资本显著不足,所以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被滥用”的逻辑已变得理所当然。
二、资本显著不足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原因探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项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内容虽不断丰富,但其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理念却始终未变,即法律虽然鼓励社会公众踊跃投资,允许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降低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但绝不容忍他们滥用这种优势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学理上将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无疑是认为其已经突破了合理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底线,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常见的理由有:第一,资本规模与责任不一致,“如果一个公司缺乏与其责任相适应的资本,致使其没有足够的资产来清偿债务,那么允许股东们利用这种毫无价值的公司来逃避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⑤;第二,资本规模与股东的经营诚意及其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不一致,“资本显著不足,表明股东缺乏利用公司经营事业的诚意,意欲以小搏大,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降低投资风险,并将其转嫁给债权人”[1](144)。二者均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支持[2,3]。于是,资本显著不足被贴上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标签。当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其有权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当没有任何资本投入公司时,这个公司仅仅是一个壳,一个透明的壳,其不会为其所有者提供任何保护;没有投入,没有产出,就没有保护”⑥。接下来,学界只需对资本显著不足进行解释,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也只需认定小前提——何为资本显著不足,而无须考虑大前提即“资本显著不足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的真伪。

表1 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裁判

表2 承认或拒绝承认“资本显著不足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的理由
然而,大前提却未必为真。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事由最初来源于美国的司法判例,但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法院很少单独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揭开公司面纱[1](141)。73.3%的数据只能说明在成功揭开公司面纱的案件中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比例很高罢了,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决定性因素。正如Consumer’s Co-op of Ealworth County v. Olsen案法官所言,“资本显著不足虽然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揭开公司面纱的充分理由。为了揭开公司面纱,除了资本显著不足外,还需要有未能遵循公司形式的证据或者其他能够充分表明控制的证据”⑦。可见在美国,单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尚不足以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英国虽与美国同属判例法体系国家,但其却以成文法的形式限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情形,而根据1948年英国公司法的规定,资本显著不足也不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当然事由⑧。另外在大陆法系,无论是采“直索理论”的德国,还是采“透视理论”的日本,资本显著不足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观点从未成立,也鲜有相关的司法判决[1](146)[4]。这样看来,在我国,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事由,更像是对美国法院在司法判例中归纳出来的或然结论的直接继受,而这与我国司法裁判中演绎推理的思维模式不相协调:资本显著不足若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其又何以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当然事由?事实上,学界的理由并非无懈可击,资本规模与责任不一致、与股东的经营诚意及其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不一致,就能够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如果任何看似不合理的行为都被纳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调整范围,那么该制度本身又何尝不会被滥用?判断资本显著不足是否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当然事由,须先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本质,以及其究竟意欲规制何种不法行为,而后才能进一步论证资本显著不足是否构成这种不法行为。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本质探寻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意在否认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公司人格,从而直索股东的责任,其规制的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行为[5]。《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则明文禁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但从本质上讲,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仅在于限制股东有限责任或公司独立责任的滥用。
(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并非对团体人格本身的否认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逻辑前提自然是承认公司有人格,若公司无人格,则无否认之必要。人格的概念最初源于古罗马法,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天赋人权”理念的洗礼和德国法上“团体人格实在说”的产生和发展[6],“人格”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基本与民事主体资格等同,即生物人或非生物人能成为“法律人”的资格⑨。也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曾一度被认为是对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否 认[7,8],“如果股东要对公司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那么首先就要否定公司的法律人格,否则股东根本没有必要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9]。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显著不足意味着公司不具备人格独立之物质基础,自然也就丧失了民事主体资格。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绝非旨在否认团体人格本身。
首先,否认公司人格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有限责任是最基本的原则,即便公司因为种种原因走向“死亡”,股东还是只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如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旨在否认公司人格本身,则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无限责任;如果不能追究股东的无限责任,那么否认或不否认公司的人格于债权人而言有何区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没有意义。
其次,否认公司人格完全不需要新设一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众所周知,在我国,生物人是基于死亡(包括推定死亡)这一事实而丧失法律上之人格的。相应地,团体人格的丧失同样是基于“死亡”,要么是“自杀”(决议解散),要么是“他杀”(企业并购),要么是“被宣判死刑”(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自杀”或“他杀”是市场行为,自不必法律调整;但即便是“被宣判死刑”,在现有的公司法理论体系下,也有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清算程序(如破产程序)予以规制,何须单独新设一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因此,否认团体人格本身并没有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其并非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并非旨在规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百年发展史中的双子星,前者将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相分离,使公司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为意思表示,并维护该团体而非股东个人的利益;后者则以出资为限将股东责任有限化,从而令公司责任走向独立[10]。虽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与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均为不法行为,但只有当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与滥用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出现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二)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是对公司独立责任的否认
团体人格的产生可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的大学、教会和自治城市等,这些团体能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财产、为诉讼行为,故而具备独立之人格且被法律和社会所接受;但此时它们尚不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资不抵债之时仍得向其成员进行征税或费用的摊派。到了14—19世纪,商人为了垄断海外贸易的需求而联合经营并成立特许公司,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并拥有一定的财产及诉与被诉的能力。此时它们也具备了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同样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它们不仅要依靠会员之会费,而且要通过费用摊派的手段补充开销甚至亏损[10]。可见,人格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责任的独立,当时的公司只须具备独立的名称、必要的财产以及诉讼能力等基本要件,其人格即与成员人格相分离了。根据德国法“团体人格实在说”的理论,社会团体具有法律上之人格并非法律拟制,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法律只是确认了这一客观存在并赋予其法律上之人格[11]。至于团体之责任是否独立,实则与人格的独立性无关。而自欧洲中世纪到近代以来,拥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其责任本就不独立,这类公司也被称为无限责任公司。只是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公司规模的逐渐扩大,经营风险与日俱增,无限公司的无限责任形式令投资者望而生畏,于是他们对有限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在经历了两合公司的过度之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也正式标志着有限责任原则的形成: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相应地,公司则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无限责任[12]。公司独立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产物,而不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当然结果。在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出现之前,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虽然也被法律所禁止,但其还不足以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为不论公司人格被滥用与否,股东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在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出现后,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同时还能依傍有限责任原则全身而退,债权人风险骤增。为了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目的就是否认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直索公司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
事实上,“只有先否认公司的人格,才能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的理论来源于采狭义法人概念的传统德国民法。在传统德国法上,只有法人才具有团体之人格,而法人获得团体人格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此时,法人的人格、法人的独立责任与股东的有限责任达成了统一,若要追究股东的无限责任,则必然意味着法人已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法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则其就丧失了法律之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商法典》已经肯定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权利能力,赋予其主体资 格[13,14],团体人格与团体的独立责任等同的立法例已经成为历史。而在采广义法人概念的英美法系和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皆为法人,法人是否具有人格与其是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完全无关。“揭开公司面纱”或“刺破公司面纱”一词,最能准确地描绘出该制度的精髓,要知道“lifting”或“piercing”都没有“否认”或“剥夺”的意思[15]。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采狭义的法人概念,只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才具有团体之人格(《民法通则》第36、37条),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都只是自然人的特定组合而不具有团体人格⑩。但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显然改变了这一观点,不仅新增了非法人组织一章并赋予它们团体人格(《民法总则》第102条),且相应地删除了以责任独立作为法人取得团体人格的必要条件的规定(《民法总则》第58条)。可见,立法已然承认法人的独立人格与独立责任之间并无关联关系。“只有先否认公司的人格,才能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综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只是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或公司的独立责任;同时,也只有适用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公司才有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可能,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相应地,确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事由的唯一依据也只能是“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被滥用”。
四、资本显著不足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辨
既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责任独立性的否认,那么若资本显著不足能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则意味着资本显著不足构成了对公司独立责任的滥用。然而,公司责任独立与否与资本的多寡并无关系。
(一) 公司独立责任的关键并不在于资本的多寡
公司的注册资本长期担负着债权人最低担保的使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错觉:公司能否独立承担责任取决于资本的多寡。“资本与责任不一致说”“资本与股东经营诚意、投资风险不一致说”均持这种观点,它们认为股东低额出资的行为滥用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虽将自己的投资风险降低,却使债权人风险加大,而这些低额资本显然不足以令公司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这一观点的认知下,学界对资本显著不足进行了解释,通说认为其不应局限于注册资本的法定最低限额,而应着眼于“资本的规模相较于预期的经营规模和潜在责任而言是否合理”[16]。虽然2013年《公司法》取消了注册资本法定最低限额的限制,但有学者认为改革反而给资本显著不足的扩大解释提供了契机,“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的取消,不仅没能缩小股东的出资义务,反而令其承受出资义务被追加和扩大的风险。没有了最低资本的限制,资本显著不足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作用反而陡然上升”[17]。可见,资本多寡影响公司责任独立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这一观点赋予了注册资本过多的使命。
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初期,将公司注册资本的多寡与公司独立责任挂钩,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当时我国公司立法尚不健全,有关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会计制度、市场的披露机制、商业保险机制等的构建都不完善,整个资本市场缺乏公正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和分散债权人风险的金融体系,这个时候债权人的利益就如同刀俎之鱼肉,时刻有被吞噬的风险。此时,注册资本的担保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充足,则债权人风险较小,表明公司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资本不足,则债权人风险较大,公司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民法通则》第37条的规定就是当时情况的客观反映,没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不仅影响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甚至阻却其取得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时代背景下,采用这种方式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属无奈。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一个没有担保和责任保险机制、欠缺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完善的会计制度、欠缺披露机制、没有公正信用机构、欠缺‘珍视信用’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立法者以‘注册资本’为信,则只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临时的举措。”[18]
在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今天,再强调资本多寡之于公司责任独立的信用价值,无疑是画地为牢,与公司发展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首先,少出资是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赋予股东的一项权利,如果为了债权人的利益而剥夺股东的这种权利,那么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股东投资而降低风险。其次,公司独立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逻辑必然。由于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将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分离,一旦股东出资完成并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公司即承担独立责任。不能说“股东出资少,则公司资本不足,公司就不承担独立责任”。2013年《公司法》取消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理论上股东出资1元即可成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一旦成立就是有限责任公司,不可能因为股东出资少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转变成无限责任公司。最后,投资风险的预见义务理应由债权人自己承担。注册资本只有1元的公司,其承担独立责任的最低资产也是1元,如果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也就意味着债权人愿意承担这个“欠缺诚意”的交易所带来的风险,法律又何必忧他人之忧?在投资领域,高风险未必不会有高收益,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本应就风险作全盘评估,因此股东规避经营风险的行为合法合理,这不应成为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市场的理由[19]。事实上,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在资本市场早已屡见不鲜。于债权人而言,相较于公司资本、还款能力、担保和经营环境条件等传统指标,经营者的能力和信誉更能刺激其投资欲望[20]。兰世立出狱后凭什么再获百万资产,凭的就是与时俱进的互联网经营理念和长期积累的信誉和人脉[21]。在现代市场,经营者的信誉和能力就是一项无形资产,其有多少信誉、能力,市场就能够回馈其多少信心。如果债权人看中经营者的能力而予以投资,即使公司用以承担独立责任的最低财 产——注册资本显著不足,恐怕也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债权人也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不能让经营者为自己的投资眼光买单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可见,公司独立责任的关键并不在于资本的多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一旦股东出资完成,它就已经开始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了。
(二) 公司独立责任的核心在于资产的独立
股东出资完成后,公司的责任即告独立,此后公司将以自己的全部资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资产不同于资本,资本仅指注册资本,是股东已经转移或承诺转移给公司的财产;资产则是公司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其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它是能被公司实际控制和支配的所有财产,范围大于资本并包括资本。当公司发生经营危机时,所有的资产都要纳入责任财产的范围。因此,公司独立责任的核心就在于独立的资产,二者紧密相连[22]。一旦资产的独立性被破坏,公司的责任财产就有不当减少的危险;当公司责任财产被人为地减少,而侵权人却能够逃避债权人的追索时,公司独立责任即被滥用了。可见,滥用公司独立责任的实质就是滥用了公司资产的独立性。
首先,公司资产独立要求公司的财产不能与股东的财产混同。财产的混同将直接导致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无法确定,债权人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其责任财产不当减少。此外,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和组织机构也不能混同。人员、业务混同易使公司丧失经营自主权,组织机构混同会导致公司不能形成独立的意思表示,而这些混同又极易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公司承担独立责任的范围无法确定,债权人当然有权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否认公司责任的独立性。如果人员、业务、组织机构混同并不损害各自财产的独立性,则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将不予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人格混同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财产混同才是滥用公司独立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其次,资产独立要求公司能以独立的意思表示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财产。意思表示不独立,资产再多也可能会被蚕食;相反,即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元,只要这1元是由公司自主支配,其资产就是独立的。如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不当控制,通常表现为母公司完全操控了子公司的决策过程,使被操纵的子公司成为了母公司的工具[23]。而一旦不当控制形成,公司将不能自主支配自己的资产,公司责任财产就有不当减少的风险。再比如股东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合同债务或法律义务的情形,股东的不法行为要由公司责任财产来买单,这无疑也是对公司资产独立性的滥用。因此,意思表示独立也是资产独立的必要条件。
综上,资产的独立而非资本的多寡才是公司责任独立性的关键。资本多寡能反映投资风险的大小、原始责任财产的多少,但在投资风险义务已能够由债权人负担的时代,其已经不能作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绝对理由;反之,侵害公司资产的独立性则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减少公司责任财产以侵害债权人利益而债权人又难以预见的不法行为,当然应该直索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这也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所在。
五、资本显著不足的各种表现形式均非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事由
根据筛选出的这31份相关法律文书,除了“低于注册资本的法定最低限额”外,法院认定资本显著不足的表现形式至少还有3种(详见表3):其一,公司股东(或发起人)未能依照公司章程充分履行出资义务;其二,公司资本规模不合理,包括“股东投入公司的股权资本与公司从债权人筹措的债权资本之间明显不成比例”以及“股东出资显著低于该公司从事的行业性质、经营规模、雇工规模和负债规模所要求的股权资本的情况”;其三,股东抽逃出资。然而,“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与“资本规模不合理”实质上均不构成对公司责任独立性的否认,而“抽逃出资”甚至与资本显著不足没有必然关系。
(一) 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司股东(或发起人)未能依照公司章程充分履行出资义务是资本显著不足的表现形式之一,法院以此为由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比例约为26.5%。但实际上,未履行出资义务并不会损害公司责任的独立性。目前,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这两类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起始时间点并非股东充分履行出资义务之时,而是公司完成设立登记之时。一旦公司满足法定要件,并由工商行政机构予以注册登记,公司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且承担独立责任。而在这些法定要件中,充分履行出资义务的要求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在公司资本制改革之后,股东只需要认缴出资即可成立公司,这种做法将有效防止资本的闲置,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符合资本市场的运转规律。此时,公司章程上所记载的认缴注册资本的总额,对债权人而言,是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之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对股东而言,则是转移物的所有权之契约中须完全履行的交付义务。股东是否充分履行出资义务,不会导致公司原始责任财产的变更,自然也就不影响公司责任的独立性。事实上,从资产负债表的科目就可以看出,股东未转移的出资是作为应收账款置于资产项目下的,而公司的所有资产均是对外承担独立责任的物质基础,股东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不代表其可以逃避其已经承诺的出资义务,因此不属于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得以要求股东履行未完成之出资义务的请求权基础并非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请求权,而是民法基础理论中债权人的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也限于其认缴的出资。实际上,《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若因股东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而否认公司责任的独立性,股东可就不是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了,而应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来否认公司独立责任的误区在于没有意识到公司承担独立责任的原始责任财产在于股东认缴而非实缴的出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不会导致公司的责任财产人为的减少,因此完全不需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规制。

表3 资本显著不足的表现形式及相关案例
(二) 资本规模不合理
目前,资本的规模相较于预期的经营规模和潜在责任而言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认定资本是否显著不足的主要依据。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资本规模不合理的认定也参照了上述观点,主要表现为:①股东投入公司的股权资本与公司从债权人筹措的债权资本之间明显不成比例(法院以此为由否认或拒绝否认公司人格的比例约为5.9%);②股东出资显著低于该公司从事的行业性质、经营规模、雇工规模和负债规模所要求的股权资本的情况(法院以此为由否认或拒绝否认公司人格的比例约为41.2%)。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把资本规模是否合理的预见义务强加给了股东,本质上还是在探讨股东是否有经营事业的诚意的问题。前已陈述,在新公司法逐渐弱化注册资本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作用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还以所谓的股东诚意来保护债权人,已经脱离立法旨意。事实上,除了在特定行业国家仍需要以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来降低债权人的风险外,资本规模是否合理的预见义务本就应由债权人承担。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虽然债权人投资的对象资本规模可能不尽合理,失败的风险很大,但谁能保证其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如果公司以小搏大的经营模式一旦失败就让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那这是不是过于侧重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扼杀投资者的积极性呢?一个理性的债权人在出借债务时,就应当借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充分考虑对方的偿债能力,如果认为公司资本规模不尽合理会影响债务的偿还,债权人又何须出借?因此,资本规模不合理不是公司责任不独立的理由。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如果在债权人投资之后,公司扩大经营范围或从事高风险活动,使得其资本与经营规模或经营风险不一致,那么债权人是否有权基于资本规模不合理而请求否认公司责任的独立性呢?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曾引进“熟练的金融分析师”标准来判断资本规模是否合理。实际上,这里混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公司在投资的时候,需要与经营规模或风险相一致的是公司的资产,而不是原始资本。如果公司资产已不足以支撑其作出高风险投资的行为而股东仍恶意为之,那么公司已经沦为了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公司意思表示的独立性被滥用,当然可以否认其财产和责任的独立性。
(三) 股东抽逃出资
理论及实务界将股东抽逃出资作为资本显著不足的表现形式之一(法院以此为由否认或拒绝否认公司人格的比例约为17.6%),显然是认为“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时点不仅是在公司设立之前,还包括公司设立之后,也即公司设立后其资本同样有可能因股东转移或撤回资本而显著不足[1](143)[24]。然而,以这种方式判断资本显著不足没有任何意义。首先,股东抽逃出资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注册资本显著不足。所谓抽逃出资是指在公司所有的责任财产中抽走与自己出资额相当的一部分资产,而不是在注册资本的登记簿上抽走一串仅具象征意义的数字。如果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利润,资产大于资本,则即便单个股东抽逃其自己的部分出资也不会导致资本显著不足。因此,抽逃出资与资本显著不足没有必然联系。其次,股东抽逃出资的本质是对公司财产权的侵害,损害的是公司的独立资产。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一旦股东将出资转移给公司法人,其出资就已经转化成了公司的财产,此后股东抽逃出资损害的就是公司的私有财产。最后,股东抽逃出资的目的在于人为地减少公司的责任资产,其结果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当然可以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与未履行出资义务不同,股东抽逃出资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转移公司责任财产的非法目的,在资产负债表中直接表现为资产数目的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公司用以承担独立责任之独立财产的数量。纵使股东抽逃资金后公司资产仍旧充足(与经营规模一致),也难逃责任独立性被否认的命运。
六、结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并非对团体人格本身的否认,而是对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否认,因而确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事由的唯一依据只能是“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被滥用”。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是为滥用;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不当控制,是为滥用;股东利用公司规避合同债务或法律义务,亦为滥用;但资本显著不足却不构成滥用。在一个社会信用体系逐渐健全的时代,在一个投资风险预见义务已能够归还给债权人负担的时代,在一个注册资本信用逐渐削弱的时代,公司责任的独立性最终取决于资产的独立性而非资本的多寡,再以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当然事由,既不合时宜,又违背法理。因此,实务界理应摒弃资本显著不足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规则,转以资产的独立性作为替代标准。事实上,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见表2)也有拒绝将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事由的观点,只是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舶来品,虽然其已经在我国的法制土壤上生存下来,但却并非没有任何排斥反应,在演绎推理的逻辑思维下,既然资本显著不足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司法实务又何须坚守这种适用规则,造成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② 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主要适用于以下4种情形:(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2)利用公司人格回避合同和侵权债务;(3)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律义务;(4)公司法人格形骸化。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本文不对“资本”概念的争议作过多的探讨,关于“资本”的定义,本文遵循公司法语境以及学界通说,仅指“注册资本”。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孙晓洁:《公司法基本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
④ 不相关的案例是指,裁判文书中虽有“资本显著不足”的字样,但资本显著不足与裁判结果或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或仅宣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包括资本显著不足”而已。据统计,这类裁判文书共有24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4份裁判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承认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包括资本显著不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因为公司的资本显著不足,所以其独立人格被滥用”的逻辑思维的普遍性。
⑤ H. W. Ballantine, on Corporations (Rev.Ed.1946) §129, pp. 302−303.
⑥ Kinney Shoe Corp. v. Polan, 939 F.2d 209, C.A.4 (W.Va.), 1991.
⑦ Consumer’s Co-op of Ealworth County v. Olsen, 142 Wis. 2d 465, 419 N. W. 2d 211, 215 (1988).
⑧ 根据1948年英国公司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1)股东故意混淆公司财产和其个人财产;(2)公司的高级职员非以公司名义从事活动,或者以公司财产进行用于个人目的的活动的;(3)公司股东人数降至法定限制以下,公司继续经营满6个月的;(4)贸易部在依法调查公司状况时提出申请的。参见董安生主编:《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7页。
⑨ 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包括我国《民法通则》)引进了“权利能力”的概念,这使得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内涵等同,但本质上还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4页。
⑩ 根据《民法通则》的编排体系,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都置于自然人一章之下,可见当时的立法是不承认它们的团体人格的。
[1] 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2] 孙晓洁. 公司法基本原理[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3] 陈本寒. 商法新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4] 刘惠明. 日本公司法上的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及其应用[J]. 环球法律评论, 2004(1): 106−111.
[5] 范健. 商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6] 马俊驹. 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7] 王凤民, 程红梅. 揭开公司面纱——对公司法律人格的否定[J]. 中外企业文化, 2007(1): 28−30.
[8] 田田, 程兆齐. 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及其对一人公司的适用[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7): 69−74.
[9] 高旭军. 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之“法人人格否认”[J]. 比较法研究, 2012(6): 34−42.
[10] 虞政平. 法人独立责任质疑[J]. 中国法学, 2001(1): 126−139.
[11] 何勤华. 德国法律发达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12] 大冢久雄. 股份公司发展史论[M]. 胡企林,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3] 托马斯•莱塞尔. 企业与法人[C]//易继明.私法 (1). 赵亮,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09.
[14] 托马斯•莱塞尔. 德国民法上的法人制度[J]. 张双根, 译. 中外法学, 2001(1): 33.
[15] 哈密尔顿(Robert W.Hamilton). 公司法 (英文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16] 苗壮. 美国公司法制度与判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7] 赵旭东. 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J]. 法学研究, 2014(5): 18−31.
[18] 傅穹.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5): 96−99.
[19]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M]. 萧琛主,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20] 侯昊鹏. 国内外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研究的新关注[J]. 经济学家, 2012(5): 88−97.
[21] 彭俊勇. “前首富”出狱凭啥再创百万资产[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1119/151323801689.shtml, 2015−11−19.
[22] 马俊驹, 余延满. 民法原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23] 王利明. 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下)[J]. 政法论坛, 1994(3): 87−93.
[24] 胡改蓉. “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J]. 法学评论, 2015(3): 163−172.
Undercapitalization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ZHANG Suhua, WU Yiwei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The essence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lies not in denying the corporation’s personality, but in denying the corporation’s independent liability or stockholder’s limited liability principle, so the only reason for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is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ion’s independent liability or stockholder’s limited liability being abused. But undercapitalization does not mean “being abused.” In an age when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becomes gradually healthier, when the obligation of investment risk prediction can be given back to creditor, and when the capital credit is not as important as before, the independence of corporation’s liability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its assets rather than the amount of its capital.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by reason of undercapitalization is not only out of date, but violating the basic law principle as well. Therefore, the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give up that kind of customary rule and take the independence of corporation’s assets as a new standard instead.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independent liability; undercapitalization; the independence of corporation’s assets
[编辑: 苏慧]
2017−04−25;
2017−07−28
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留金发[2017]3109号)
张素华(1976—),女,湖北宜昌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吴亦伟(1989—),男,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10.11817/j.issn.1672-3104.2018.01.006
D913.99
A
1672-3104(2018)01−00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