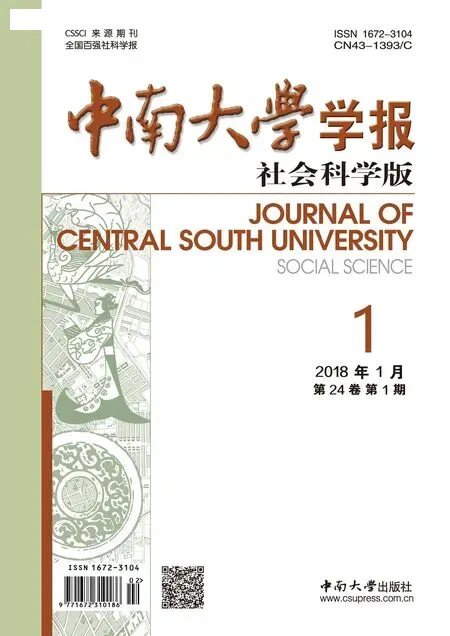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法律构造
潘俊
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法律构造
潘俊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重庆,401120)
基于信息不对称要求,经营者对处于信息弱势方的消费者负有法定告知义务。该种告知义务应与消费者知情权保持一致,限于“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并因不同交易模式表现出不同的告知范围。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可能构成欺诈,适用民法欺诈理论进行判断,并划分部分欺诈和整体欺诈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准。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构成欺诈时,可能出现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应允许消费者自由选择,且均可适用惩罚性赔偿;不构成欺诈的,可能承担不作为的侵权责任。
消费者合同;告知义务;欺诈;惩罚性赔偿
理论上,任何合同都是不完全合同,都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为典型的弱势群体,即使个别消费者的私人财富足以与经营者抗衡,但因信息占有的不对称,仍难以摆脱弱者地位。信息不对称常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解决该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传递给信息弱势方或诱使信息优势方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信息均衡的重要途径。告知义务也常称为信息披露义务,在消费者合同中是指具有信息优势一方的经营者将有关信息以口头、书面等形式告诉消费者,便于其合理判断,理性缔约。目前,有关消费者合同的研究,或基于产品责任角度分析经营者责任,或集中于惩罚性赔偿。即使论及经营者义务,也多从其对立面——消费者知情权进行分析,鲜有对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及其法律责任的系统性研究,而与此直接关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和其他民法规则也有体系整合之必要。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范围的确定
因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特殊性,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有别于缔约过失中的告知义务以及有名合同中确定的告知义务。缔约告知义务主要强调与缔约有关的重要信息,属于典型的先合同义务;有名合同确定的告知义务常为合同中义务,是订立合同主要目的之所在;经营者告知义务是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主要集中于合同订立前,与缔约告知义务重合,也可能存在于合同履行后,如产品召回告知义务,性质上属于附随义务。
(一) 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现有偏差
权利与义务具有相对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原则上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范围可以通过消费者知情权的范畴予以确定①。然而,我国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并不完全对应。首先,规制两者的法律模式不同。《消法》第八条第一款直接肯定了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并在第二款列举说明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具体内容,“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与之相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列举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缺乏一般性规定,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②。由此导致《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明确规定经营者承担向消费者披露有关信息义务的单行法难以与《消法》衔接,原本应互相联动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被割断,难以发挥体系化的作用[1]。其次,确定两者的法律规范效力层次不一,具体内容也有差异。消费者知情权常通过法律予以规定,而经营者告知义务则散落于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范围往往比消费者知情权要窄。在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纠纷案中③,原告以化妆品外包装上没有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和使用方法,致使自己难以正确使用该化妆品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现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都没有强制规定化妆品要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且被告已在产品底部明确标注了限用期限,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持相反观点,认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被上诉人乐金公司只按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了“限用合格日期”,没有按《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标注产品的安全使用期,侵害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在杨鸿诉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健”牌的美国·布朗威廉森烟草公司一案中④,对于原告提出的香烟生产厂家未在香烟的外包装上注明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厂址、执行标准(国产烟)等标识,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等法律规定、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主张,法院以外包装所作的标注符合国家标准驳回⑤。可见,分别通过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告知义务进行判断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那些直接通过消费者知情权得出要求经营者应当告知的信息,并不必然是通过经营者告知义务能够推出的内容。最后,两者实现的模式也有差异。《消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请求了解相关信息,是以推定消费者有能力认知或者有意识获取相关消费信息为前提的,而消费者事实上对商品或服务的不了解使得主动询问、获知的权利形同虚设,反而置消费者于不利。如我国香烟GB/T5606 2—1996《卷烟包装、标志贮运》仅规定在箱包装体上必须标注生产日期,但普通消费者通常不会整箱购买,而销售者也不会主动向消费者出示箱包装上的标注,导致消费者难以知晓香烟的生产日期[2]。
(二) 确定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应有模式
1. 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概括性条款
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建立在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这种不对称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恒定的。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可能逐渐趋于对称,原来信息对称的也可能发展为不对称,因此经营者告诉消费者的信息范围也应随情势的变迁而不断作出变化和调整[3]。即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范围应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推向极端。告知义务范围若不加以限制,经营者或为周全事无巨细地将产品、服务的信息进行披露,反而不利于消费者获取有用信息,最终可能出现类似于“过度或防御性医疗”的弊端。以买卖合同为例,通常卖方占有标的物,掌握标的物更多信息,但在对一些结构简单、其品质凭肉眼就可以查知的标的物进行买卖时,法律不应当强制卖方负担这种一般性的公开信息的义务[4]。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应当限于“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以实现缔约双方信息的均衡。这些信息或影响消费者决定是否缔结合同,或影响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效用的最大化实现,或产品、服务使用危险的避免。原则上,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都必须告知消费者⑥,涉及商业秘密、他人人身权内容的则可以不告知。同样,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范围的确定必须考虑披露该种信息对经营者本身、经营者所处行业发展、政府监管以及消费者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为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消法》不可能也不应对经营者告知的范围作出详细规定,而倾向于告知义务的一般化,即与消费者知情权相对应,采用概括性条款,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信息。概括性条款也被称为一般条款,是指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不同于具体规定的条文,法官可以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5]。它能够保持法律规范本身的稳定,其提供的法律理念与法律逻辑可以直接适用或援引,特别是在面对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时,一般条款表现出足够的适用张力。这种原则性规定,既能指导相关行业具体标准、规范的制定,也能在具体规范空缺或具体规则与基本法冲突时提供裁判依据,最终实现消费者知情权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统一。对此,可以将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规定为: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告知义务,负责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使用方法等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基本信息。
2. 不同交易模式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差别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上门推销、网络、电话、邮件购物等新型交易方式不断出现。与传统交易方式不同,这些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大多缺乏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或者接受商品、服务为一次性交易,不具有多次性、稳定性,经营者的信息更难掌握。尤其是在远程交易中,消费者对经营者的真实性、确定性以及商品的质量都难以确定[6]。由此导致除传统交易模式下经营者应当提供的信息外,消费者需要更多信息进行缔约判断。我国《消法》第二十八条增加了该类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并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对订立格式条款的信息披露作出规定。在欧洲,早在2011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颁布《2011/83号消费者权益保护指令》(2011/83/EU指令),其中第五条和第六条区分普通消费合同和远程合同以及无店铺销售合同,详细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提供的信息,如普通经营者都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主要特点、经营者的身份、经营者的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商品或服务的总价等;在远程合同及无店铺销售合同中,经营者还应向消费者提供撤销合同标准表格及与撤销权行使的相关信息。同时,在通过互联网、电视等方式的交易中,经营者不仅应直接向消费者披露相关信息,还需同时提交相关信息给第三方平台,保证消费者获取经营者的有关信息。
需注意的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经营者应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并非应消费者请求才履行。应消费者询问而告知的内容与经营者主动告知的内容可能发生重合,但经营者不能以消费者没有请求而作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抗辩。同时,该种告知义务属于法定的告知义务,不因消费者知情而免除[7]。即使消费者通过其他途径可能已经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经营者也不得以此作为自己无需再告知的抗辩。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违反与欺诈
在《消法》第十一条一般性地规定了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基础上,第四十八条和第五十五条进一步细化,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欺诈时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被视为最重要的责任形式。
(一) 欺诈的认定
《消法》并未规定欺诈的判断标准,是否直接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学说理论一直存有争 议⑦。肯定者无不认为,《消法》对欺诈没有作出特别的界定,自然应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的欺诈概念作相同解释,采取同样的文义、同样的构成要件。否定者则认为,《消法》不能简单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消法》中的欺诈应跳出传统合同法的研究框架,纳入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考察[8]。具体而言,两者认定欺诈的差别在于是否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以及相对人是否因为欺诈方的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其中相对人陷于欺诈的认识,其实就是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问题的讨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不论相对人是否因此被欺诈,都构成欺诈,适用惩罚性赔偿。“仅作虚假陈述或者故意隐瞒真相而未使消费者陷入错误,构成行政法上的欺诈,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对此有特别规定。”[9]这些常被援引作为“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论点的支撑。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原则上不应当支持尚未陷入欺诈的消费者请求惩罚性赔偿。首先,《消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是经营者的行政责任,并不意味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免除。其次,现有体系下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反映出《消法》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除《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都确立了惩罚性赔偿。与《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表述有所不同,这些条文均未使用“欺诈”这一术语表达,而一致使用了“明知……仍然”的语言表达结构,并未考虑相对方的状态,似乎有意区分。《最高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生产者、销售者不得以购买者明知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惩罚性赔偿抗辩适用于食品、药品领域,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认识。即使是因为立法过程中“知假打假”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意见难以统一,甚至较多数意见也未形成而有意避开,上述规定至少表明在所有产品或服务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迟疑态度。最后,相对人意识到欺诈仍然购买,其意思自由并未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法理上没有保护的必要。如果一律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支持这类惩罚性赔偿,实际是将本应由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行政机关负有的打假职责转移于消费者。特别是在法院不支持此类惩罚性赔偿时,消费者不仅不能获得赔偿,还将负担时间、精力等诉讼成本。仅从鼓励、支持消费者打假的角度考虑,完全可以采取消费者举报、行政机关对经营者进行罚款并奖励消费者的方式。然而,如果经营者应当告知而未告知的内容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畴,即使消费者知晓,也不能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至于是否要求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实际是对欺诈行为民事责任性质的认识。否定者认为,《消法》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无过错责任,不考虑行为人主观有无过错[10]。这一观点本质是建立在违约责任基础之上的。然而,将欺诈视为一种违约行为,便得出只要经营者未尽到告知义务就承担惩罚性赔偿的结论,将不适当地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否定者们其实是在担心,若肯定欺诈故意,消费者承担这一要件的举证责任,负担未免过重。但这完全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或证明程度问题予以解决,如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实行过错的客观化判断标准,只要存在欺诈行为就推定经营者过错;或加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要求信息优势方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降低消费者的举证负担[11]。国家工商局《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四条规定,凡销售该条所列举的假冒伪劣商品的,且不能证明自己确非故意欺诈、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的,应当承担欺诈消费者行为的法律责任。尽管第三条列举的欺诈行为不尽相同,但和第四条都立足于确定“欺诈消费者行为”,在欺诈故意认定时可以参照该条,采用故意推定的方法证明经营者欺诈故意。因此,经营者未承担告知义务,可能构成却并不必然构成违约,经营者欺诈故意这一要件不应摒弃。
如此一来,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构成欺诈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求经营者具有欺诈的故意以及消费者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认定为欺诈。但在食品、药品消费等特殊领域中,对消费者是否被欺诈不作要求,即使消费者明知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仍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
(二) 部分欺诈与全部欺诈的区分
随着对《消法》惩罚性赔偿认识的加深,汽车、商品房等价格较高的物品逐渐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出现了经营者隐瞒或虚构部分信息,消费者请求购买商品全价款的惩罚性赔偿争议。四川省首例汽车消费双倍赔偿案中⑧,对于因被告交付修复过的轿车车门以及隐瞒交付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而要求购车全款双倍赔偿的原告诉讼请求,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法院均予以了支持。案件审理过程中,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经营者仅是对产品某一部分存在欺诈,却承担整个产品价格的惩罚性赔偿,有违公平。部分欺诈通常是指经营者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整体上没有欺诈,只是局部存在欺诈行为,商品或服务整体的功能并未受到破坏。无论“局部”的范围大小,局部欺诈根本上也是欺诈,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只是欺诈惩罚性赔偿额的计算标准是否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价格,确实值得商榷。
在标的额较大的商品房买卖领域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肯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在第十四条确定了部分欺诈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换言之,如果商品房销售时存在面积欺诈的,则以欺诈 部分的面积计算加倍赔偿款,而非整套商品房的价款。”[12]如果经营者欺诈行为指向的产品或服务整体并无实质影响,却以整体价格的三倍赔偿,对经营者未免过苛,有失公平。部分欺诈在对产品或服务的整体产生实质影响时,以商品或服务整体的价格作为计算标准方为妥当,若这部分欺诈不影响整体使用,只减损其价值时,则应当以欺诈部分的价格为标准计算惩罚性赔偿。因此,确定部分欺诈的惩罚性赔偿价格时,不能停留于欺诈部分的价格,而应考虑该部分对产品或服务整体的价值影响予以确定。如果局部赔偿和整体赔偿都有依据时,则应当考虑两者适用产生的社会效果[13]。
三、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 欺诈的未履行告知义务责任
《消法》第五十五条惩罚性赔偿、《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缔约过失责任、第五十四条违约责任均涉及实施欺诈行为一方可能承担的责任。其中,缔约过失责任是订立合同时一方主体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合同是否成立或是否有效没有必然联系[14],不撤销合同同样可以请求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5]。因此,在构成欺诈的前提下,不论经营者未告知的内容是否属于订立合同的重要信息,也不论消费者是否撤销合同,消费者都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请求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撤销合同时,消费者还可能同时请求经营者承担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违约责任。“合同订立时经营者未履行必要的告知内容不能纳入合同约定内容,合同履行过程中经营者的限制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瑕疵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16]这意味着,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欺诈时,可能出现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承担的竞合。
而对经营者故意隐瞒或未告知消费者商品或服务的必要信息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作出购买决定构成欺诈,承担《消法》第五十五条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认识,各有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部分学者以该种惩罚性赔偿计算基准为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出发,认为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是违约损害,而非侵权损失[16]。另有学者置于消费者保护法整体考量,主张该种惩罚性赔偿突破《民法通则》或《合同法》常规,惩罚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同时使消费者获得更多赔偿,在规范体系上是《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或《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例外规定。被欺诈一方可以撤销合同而请求损害赔偿,性质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10]。可见,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决定了消费者选择违约或缔约过失救济的途径。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并不必然与缔约过失或违约责任相对应。首先,惩罚性赔偿根本上是惩罚欺诈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与因欺诈而缔结的合同发生联系。其适用建立在欺诈基础之上,只要满足欺诈的构成要件,消费者都可以请求支付三倍赔偿。“其他因债之关系或法律规定所应负的一切义务和责任, 均不因之而受影响。”[17]至于《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计算标准是“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则视为执行之便利。其次,单纯地将惩罚性赔偿划到违约或缔约过失中,可能存在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或实践运用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该条确定的惩罚性赔偿建立在合同被撤销基础之上,显然不属于违约责任。最后,若认定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消费者必须返还原物或退货,在部分欺诈情形之下不具有可操作性,如前述汽车消费双倍赔偿案中要求消费者返还曾被修复过的车门或整部车辆显然都违背合同成立初衷。因此,《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确定的欺诈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并不与缔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相对应。而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缔约过失和违约责任竞合时,自然应当允许消费者自由选择,并可请求惩罚性赔偿,将合同解除作为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基础不具有正当理由⑨。
(二) 非欺诈的未履行告知义务责任
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并非都构成欺诈,如经营者不具有欺诈故意的情形,此时可能承担单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侵权责任。在我国首例因服用药丸窒息死亡事件中⑩,药品“桂枝茯苓丸”本身不存在质量瑕疵问题,但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缺乏警示标语,导致购买者未能正确使用,违反了《消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要求经营者在产品警示说明或使用标志上清楚告知使用人应当注意的使用方法和应警惕注意事项的义务。消费者服用药丸造成的损害与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产品缺陷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此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最终也认定被告药品生产商生产的“桂枝茯苓丸”存在警示缺陷,是导致受害人窒息死亡的诱因之一,应当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不具有主观欺诈故意往往是否定经营者未尽到告知义务的欺诈赔偿责任的关键,实际判断时尚需结合经营者未尽到的告知义务的内容、方式等,最终确定经营者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如乘客起诉航空公司超售要求三倍赔偿的一系列案件中,法院认为,一方面,机票超售对合同履行具有重大影响,航空公司应向旅客予以特别提示,直接通过民航总局官网和航空公司官网对超售进行公示不具有有效性,根本上未尽到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另一方面,法律未对超售明确禁止,超售也符合国际航空业的售票惯例,航空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出现超售主观上更多是未充分掌握航班的机票预订情况,属于过分自信导致,并非对所有购票人进行虚假宣传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与经营者欺诈的主观恶意性存在区别。因此,航空公司只承担乘客相应的交通费用、住宿等损失。类似地,在酒店工作人员未提示消费者酒店客房洗发液、抽纸等用品不在住宿费范围导致消费者不知情另行付费、风景名胜区未告知停车单独收费而引起纠纷等案件中,经营者未向消费者告知有关信息通常也不构成欺诈,只承担返还已收价款等侵权责任。
四、结语
我国《消法》没有对经营者告知义务范围和违反的法律责任作出统一规定,有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难以找到联结点。与一般的告知义务相比,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负担着内容、规范程度都更为严格的告知义务,但《消法》确定的消费者知情权不能通过这些散见于各类行业规范中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予以实现,由此出现了消费者知情权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结构性偏差;同时,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承担的责任除了第五十五条的惩罚性赔偿之外,与一般告知义务并无差异。对于前一问题,文章通过告知义务范围的抽象化和类型化,建立了以消费者知情权为中心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对于后一问题,文章探讨了欺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如欺诈的认定,部分欺诈与整体欺诈区分的必要,并对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欺诈惩罚性赔偿是经营者告知义务违反的特殊责任形式,但并非唯一的责任形式,而与违反一般告知义务的责任共同构成经营者告知义务违反的责任承担。
注释:
① 消费者知情权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消费者知情权包括有关行政部门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抽查检验结果信息的披露,指向的是公权力机关,狭义的消费者知情权仅是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文章讨论限于狭义的消费者知情权,是在民法视野下讨论经营者应当承担的告知义务。
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一规定主要是强调后半段,经营者不得作出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是对告知信息质的规定,而非量的指引。
③ 原告刘雪娟在被告苏宁中心处购买了由被告乐金公司生产的海皙蓝O2时光嫩肤液,外包装上没有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原告认为,没有标识的化妆品,消费者难以正确使用,而苏宁中心对此进行销售,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消费者知情权,遂将乐金公司和苏宁中心一并起诉至法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6期。
④ 原告杨鸿在南京新面商场分别购买了“中华”“玉溪”、美国“KENT”牌香烟各一盒,香烟外包装上均未标出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址及产品执行标准等。原告认为,三被告均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要求产品或其外包装上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址等的有关规定,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遂起诉至法院。参见“香烟无保质期标注惹官司”http://news.sohu.com/26/20/news203632026.shtml,最后访问于2017年10月25日。
⑤ 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2002)白民初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宁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
⑥ 一般消费者都知晓的信息是否标识告知,应参考当时的行业规范、准则。这时的告知义务基础已脱离信息不对称要求,而转为某种文化或行业健康发展诉求。以白酒行业是否在包装上标示“过量饮酒有害健康”为例。早在1998年“王英、张驰前与河南舞阳富平春酒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审理法院认为,饮酒过度危害身体健康是公知的常识,饮者自诫。因每个人对酒的适应程度不同,因此《饮料酒标签标准》未要求在酒产品标签上必须作出饮酒危及人身安全的警示说明等。国家无规范性要求,故不能认定富平春酒标签无警示标志即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在2013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中,则要求应标示“过量饮酒有害健康”。
⑦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虽然规定了欺诈行为,但因为列举性规定,对这些情形之外的行为是否为欺诈的认定仍不能提供判断标准。
⑧ 原告朱某与四川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A市分公司签订订购一台广州2.0黑色本田雅阁轿车的合同,A市分公司将修复好的雅阁车交予朱某。事后,朱某获悉所购车辆曾发生过交通事故,遂以A市分公司有欺诈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市分公司退还购车款并双倍赔偿损失及承担其他相应损失。参见“3-15维权名案法官手记”http://news.sina.com.cn/c/2007-04-20/113612827050.shtml,最后访问于2017年10月25日。
⑨ 经营者未尽告知义务涉及产品或服务质量可能构成履行瑕疵,进而考虑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参见许德风:《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法学》2006年第1期,第 87-94页。
⑩ 原告冷之妻李秋华服用被告杨文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坤舒”牌“桂枝茯苓丸”一颗后,出现呼吸困难,随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原告认为,被告生产的药丸其药品说明书和标签上无任何警示语,存在缺陷,直接造成李秋华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参见《我国首例因服用药物致人窒息死亡案》,http://news.sina.com.cn/c/ 2007-12-07/043713036181s.shtml,最后访问于2017年10月25日。
[1] 杨铁军. 论消费者合同中信息均衡的实现[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252−257.
[2] 王启迪.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告知义务对应性偏差问题 ——基于司法案例的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学院学报, 2013(1): 62−68.
[3] 应飞虎. 经营者信息披露制度研究[J]. 经济法论坛, 2003(1): 240−260.
[4] 许德风. 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J]. 法学, 2006(1): 87−94.
[5] 朱芸阳. 论民法上的一般条款的理念和功能[J]. 湖北社会科学, 2013(4): 157−160.
[6] G. Borges, B. Ilrenbusch. Fairness crowded out by law: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withdrawal rights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7(163): 84−101.
[7] 万方.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告知义务之法律适用. 政治与法律, 2017(5): 151−160.
[8] 陆青. 论消费者保护法上的告知义务——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性案例[J]. 清华法学, 2014(4): 150−168.
[9] 谢晓尧. 欺诈: 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J]. 现代法学, 2003(2): 164−169.
[10] 朱广新.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3): 104−124.
[11] 刘俊海, 徐海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升华与制度创新 ——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为中心[J]. 法学杂志, 2013(5): 27−38.
[12] 李友根. 论汽车销售的消费者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案例评析[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4(2): 83−89.
[13] 张蜀俊. 隐瞒新车被撞局部受损赔偿全额车款还‘送’汽车[EB/OL].http://www.scjt.gov.cn/10000/10586/11298/11301/10014754.shtml, 2014−08−20.
[14] 冉克平. 缔约过失责任性质新论——以德国学说与判例的变迁为视角[J]. 河北法学, 2010(2): 115−120.
[15] 胡振玲. 受欺诈合同未被撤销时缔约过失责任之适用[N]. 人民法院报, 2008−10−05(6).
[16] 杨立新. 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民事责任之解读[J]. 法律适用, 2013(12): 29−37.
[17] 韩世远. 消费者合同与惩罚性赔偿[N]. 人民法院报, 2006−01−16(2).
Legal structure of the trader’s duty ofdisclosure in consumer contract
PAN Ju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Based 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trader has the legal duty to inform the consumer who is in the inferior position of information. Such duty of disclosure, in line with the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is restricted to the information on important matters related to goods or service, and is manifested by different informing ranges caus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ng patterns and levels. If violating the duty, the trader may bear liability for fraud, which can be judged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civil fraud where punitive damages can be cited and the specific computation is on whole or part necessarily. Whether tort liability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contract, the consumer can ask for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when violation forms fraud. And if there is only violation rather than fraud, the trader may assume tort liability.
consumer contract; duty of disclosure; fraud; punitive damage
[编辑: 苏慧]
2017−05−11;
2017−08−0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法调整对象的重新确定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15CFX039);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侵权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2016BS010);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项目“‘三权分置’下农林土地经营权抵押机制研究”(KJ1701002)
潘俊(1987—),女,四川泸州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法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07
D913
A
1672-3104(2018)01−00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