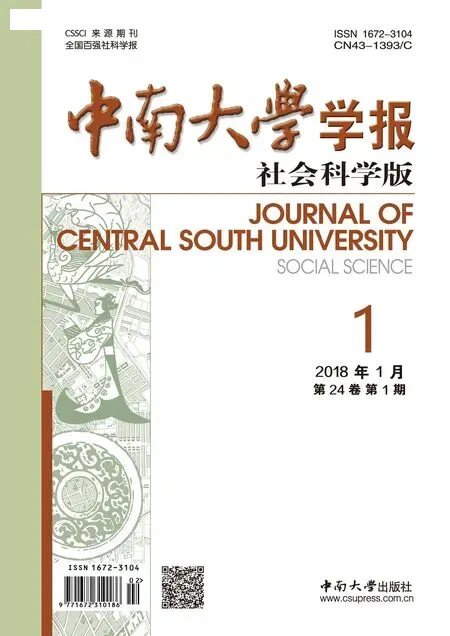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郭远远,陈世香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郭远远1,2,陈世香1
(1.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管理系,河北保定,071000)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转变成为国家政策执行领域的优先任务。通过对国务院历年公开政策文本的分析可知,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定位经历了多维度的转换: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文化建设的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就政策目标的视角看,文化建设经历了从组织结构调整到全面文化建设的转变;从文化功能的定位分析,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转变;在中央政策主导者的心理层面,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谨慎”到“自信”的转变。从这些转变趋势可以预见,未来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将进一步强化,有可能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先任务;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将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网络文化管理也将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方向。
文化建设定位;五年计划;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政策文本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后文简称“十九大报告”)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未来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进一步确立了文化建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但从历史演进视角看,国家对文化建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定位与认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并体现出国家意志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变化轨迹。厘清国家意志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明晰未来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国家定位,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文化建设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战略意义,进而更好地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与政策建议,并最终有助于推动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化建设虽然已经逐渐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但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政府财力、现代化建设发展布局规划、政策制定者思想认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相较于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直处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边缘。直到“十五”时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文化建设的边缘地位才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边缘走向中心。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涉及了文化建设的部分内容,体现了执政党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与文化主张,具有“元政策”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央政策落实和执行之始端的国务院政策文本,为我们“管窥”文化政策在落实和执行领域的“实然”状态与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而且,国务院制定或转发的相关政策文件是连接文化建设价值理念与文化建设实践的中间环节,最能体现国家文化管理思想的指向,能够反映文化建设在政策执行领域中的真实地位。尤其是历次“五年规划建议”,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研究制定形成,其形成过程被认为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是统一全党认识、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①。“五年规划建议”是国务院制定政策文本和发起政策执行的指导性文件。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次“五年”规划,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务院文化建设领域政策关注焦点的转变,以便清晰地认识国家文化建设定位转变的轨迹,并为未来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已有相关研究的文献评述
厘清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是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界对此已有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公共文化政策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或国家中央机关发布的文化政策等规范性文件,试图揭示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趋势。典型代表如李少惠和张红娟、周正兵、王铁钢、谢秋山和陈世香等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化政策的发展演变趋势,并对促成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1−4];韩美群专门探讨了2001—2010年10年间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趋势[5]。另一类是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入手,直接探讨文化建设的国家定位主题。典型代表如杨凤城、李志峰和乐爱国等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观念与思想转型情况进行探讨[6−7]。此外,还有诸多研究者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文化建设思想的角度,间接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的历史定位与未来发展趋势。以杨凤城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专门探讨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文化建设思想[8−9];平章起、郭威依据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思想就未来国家文化建设宏观方向做了分析[10]。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也存在些许不足。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文献聚焦于较短时期内文化政策变迁,如10年或某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任时期,未能系统地总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趋势;另一方面,即使是研究文化政策的长期演变的文献,也仅是关注文化建设某一特定方面的变化趋势,而未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国家文化建设战略定位的转换。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国务院文化政策文本,全面系统地分析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定位的演变轨迹,以便更清晰地辨识国家文化建设发展的思路,并就未来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做出科学分析和判断。
三、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文化建设的历史演变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定位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而发生转变的主要起点在“十五计划”时期,尤其是2003年以后。2003年6月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中央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发,系统地谋划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11],此后,国家文化建设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务院文化政策文本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文化建设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趋势。
(一) 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中的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在我国“自上而下”逐级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模式下,国务院政策文件的关注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项任务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的地位。根据对1981年以来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国务院有关文化建设政策文件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建设在我国政策执行领域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国务院政策文件关注主题内容的扩展。“六五”到“九五”时期的国务院政策文件主要关注组织结构调整,而“十五”时期及以后的国务院政策文件则涉及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规制、文化传承与保护、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管理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与调整(参见表1)。更为重要的是,从政策文件推动文化建设的效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政策文件聚焦的组织结构调整实际上并未进入文化建设的实质推进阶段,它关注的仅仅是文化管理部门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职能定位问题。此时,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符号,被束之高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而只有当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规制、文化传承与保护、意识形态教育等大文化范畴内容都进入国务院政策执行关注的视野,并上升到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层面时,才标志着文化建设真正进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的“核心区域”,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比如,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十五”期间,要以社区和乡镇为重点,全面加强文化阵地、文化队伍、文化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在基层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任务。

表1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务院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文件
注:相关文件资料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文化建设相关文件指“国发”与“国办发”印发或转发的文件,不包括“国(办)函”“国令”“国(办)发明电”等其他类型文件
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文件数量的增加。从“六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国务院批准或转发的与文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数量总体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具体来看,“十五”到“十三五”期间,文化建设相关文件稳定在平均每个“五年计划期”10个左右的较高水平上;而“六五”到“九五”时期这一均值则仅有1.5个(参见图1)。最近,也就是在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补齐文化发展短板”,吹响了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号角,再次明确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核心地位。

图1 历次“五年计划”时期国务院批准或转发文化建设相关文件数③
(二) 政策目标的视角:从聚焦组织结构调整到全面文化建设的转变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经把国家与文化关系视角下的文化政策区分为“常规”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 ‘proper’)与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 as display)两个部分。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主要与“公开炫耀”与“美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有关[12],它往往通过辉煌宏大的场面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常规”文化政策则是国家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包含艺术的公共资助(public patronage of the arts)、媒介规制(media regulation)④与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negotiate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等三个方面[13]。这种二维划分对于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不适用于解释我国文化政策目标的构成。面对“西方文化试图一统天下的野心”[14],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均处于“后发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必然包含更多的国家意志,文化建设的目标也会随国家意志变化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态性。总体来看,我国文化建设目标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关注组织结构调整到全面文化建设的转变过程。通过图2,我们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时期,国务院政策文件文化建设内容单纯地聚焦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调整;而“十五计划”时期及以后,国务院政策文件不再关注组织结构调整,而是进入实质文化建设阶段,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规制、意识形态教育、文化传承与保护、文化交流与贸易等文化建设内容几乎同步进入了国务院政策文件关注的视野。

图2 国务院政策文件的文化建设内容指向变化趋势
从政策目标的维度看,国务院政策文件聚焦的文化建设内容都是国家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目标的预想。而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预想的国家意志与人民个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相互矛盾。卡尔·马克思就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5]。但与一般民主国家执政党与政府单纯美化国家意志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不回避矛盾,而是积极地促进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以兼顾国家意志与人民个体利益。这一点在国务院文化政策文件中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具体来说,上述国务院政策文件内容大体上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国家目标:对内目标,立足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主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规制等措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文化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对外目标,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间竞争转向“软实力”竞争的事实,主要通过文化传承与保护、文化交流与贸易和意识形态教育,致力于构建民族文化身份,提升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本民族文化在文化多元化和文化霸权并立的激烈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比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就明确地把全面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概括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舆论引导、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制度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等八个方面。其中,前五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指向对内目标;后三个方面的内容则主要指向对外目标。这两类国家目标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体文化需要。
当然,文化政策构建的目标往往是混合的和多元的,以文化传承和保护为代表,既可以对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可以“表现为利诱的力量、说服的力量和吸引的力量”[16],通过文化吸引,有助于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文化建设的对内目标与对外目标之间是相融相通关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多元文化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是一种基于集体或国家层面的政治构建,但其基础也应该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体文化需要。因为只有能满足人民群众个体文化需要的文化才有吸引力,进而才能影响世界,增强民族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也正是基于此,2013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既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也要加大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正面宣传力度,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明确地把文化建设的对外目标与对内目标融为一体。
(三) 文化功能定位: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软实力核心的转变
从对文化功能定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文化功能的定位经历了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软实力核心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政策定位也经历了从单一/简单功能到全面功能转变的过程。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文化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注重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对文化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比如Stanley就把文化看作一种战略产品,它包括三重含义:一是作为意义符号工具的文化,即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文化,它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是用于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中交往与互动的信念、实践、含义和行为模式的总和;二是作为维护统治工具的文化,即传统文化的继承,它代表对人类优秀传统的继承,往往是增强与维护统治精英阶层权力的工具;三是作为环境适应工具的文化,即创造性文化,它代表着文化创造与创新,是确保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工具[17]。其中,作为传承的文化既可以通过社会化、教育和体验等方式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情境文化的构建,也可以通过启发创造性文化来间接影响日常生活情境文化。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的文化功能定位可以概括为“文化资本化”,即相较于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并将其功能理解为辅助性的社会资本,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提供支撑。在2005年11月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定位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8],强调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辅助作用。就国务院政策文件的焦点来看,“十五计划”以前,国务院文化政策主要聚焦于机构调整,尚未真正把文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只有到了“十五计划”期间,文化建设才真正进入国家关注的视野,尤其是文化规制、文化传承与保护和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供给成为了国务院政策关注的重点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政策执行领域,文化逐步“独立”出来——从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辅助性地位,分离转变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建设领域[19]。这与党中央领导的思路也是完全一致的。比如,2008年初,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能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 举[20]。这也进一步强调与肯定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即文化建设与经济和国防建设所代表的“硬实力”相似,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了多重目标,基于国际竞争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基于文明冲突背景下的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保护与宣传、基于公平和共享价值理念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都成为了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目标导向。
(四) 中央政策制定者心理层面:从“谨慎”到“自信”的转变
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最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根基”[21],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从中央政策制定者心理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策制定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谨慎”到“自信”的心理转变过程。可能受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民族传统文化激进批判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话语霸权的共同影响,从改革开放初到“十五计划”,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疑虑,认为其可能不利于现代化发展。随着国际与国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逐步崛起与西方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式微,以及国内“被骂”与“自虐”所形成的“文化自信的消弭”[22]之后,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重新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视。比如,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就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积极意义概括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旅游事业发展和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等六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高度自信。
谨慎往往与行动迟缓相伴,而自信则与行为坚定相随。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里,党的主要领导人虽惜墨如金,用词谨慎,但事实上都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比如,邓小平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23];江泽民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则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24]。但在国务院政策执行领域,文化建设相关行动却非常迟缓,具体表现为在“十五时期”以前没有与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国务院文件出台。而“十五时期”以后,伴随着中央政策制定者对民族传统文化自信心的增强,始终都有国务院文件专门强调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主题(参见图3),中央政策制定者对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凸显无疑,改革开放初期的质疑或疑虑消失殆尽。这与党中央对传统文化的定位也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在2016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就明确地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同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3 国务院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政策文件数量趋势
四、国家文化建设定位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国务院政策文本关于文化建设内容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中的定位已经变得清晰明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布局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对文化建设定位演变趋势特征的分析仅是依据国务院文件展开,故只能“窥见一斑”,尚难以窥其全貌。正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沃尔多(Dwight Waldo)所言,“理论建构往往是对事实的反映(theorizing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facts),并或多或少地背离了事实,因为摆在哲学家们和理论倡导者们面前的总是有限的事实和明确的目标”[25]。本文的研究也是如此,当我们基于特定的目标或方向去试图理解或剖析公共文化政策文本中所隐含的国家政策意图时不免“挂一漏万”,甚至背离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本意。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些许误读并不妨碍我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这些政策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政策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真实政策意图,发现政策走势,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建立了新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追求科学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建设则是实现这个伟大“中国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重要途径。因此,就文化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通过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建设,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通过组织结构和政策工具创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然是国家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政策议程的主要方向。
具体而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文化建设最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第一,文化建设有可能超越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先任务。对于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经济建设的领头羊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的必然选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而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城乡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这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明确地将“文化更加繁荣”也列为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强调的那样,人类个体需要是按层次逐级递升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以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期望与需要将更为迫切,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要也会日益强烈,而能否满足这些新需要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建设,而不是经济建设。如此,与文化建设经历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趋势相一致,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甚至有可能超越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先任务。
第二,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将成为未来20年国家文化建设核心内容。与文化建设功能定位经历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软实力核心的转变趋势相一致,国家未来会继续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来加强国家文化建设,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必须要加以强化。同时,伴随着文化管理体制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日趋加剧,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建设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将成为文化建设新焦点,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传承与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共同形成文化建设核心内容的“四足鼎立”局面。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6]。
从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可以窥其端倪。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之前的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均未明确涉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关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提及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的主张,但党的十七大报告与十八大报告均未对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进行专门与系统的论述;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首次把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区分,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加以系统专门的阐述,并把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认知提升到“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战略高度。
第三,网络文化管理将成为未来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方向。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从政策目标维度,国家文化建设经历了从组织结构调整到全面文化建设的转变。这里的“全面”不仅代表着受益人群的全覆盖,还意味着文化建设目标的多元化与涉及领域的全面化。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繁荣和“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传承与保护文化、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场域。规范网络社区文化传播秩序,也就成为实现提升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传承与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等多元化文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自然也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领域,全面文化建设也必须要兼顾网络文化管理的新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注释:
① 参见《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
② 因未查询到1978—1980年文化建设相关国务院文件,故省略。
③ 注:其中,“十三五”时期文件数量仅为截至2017年11月1日文件数,实际文件数量预计将超过“十二五”时期。
④ 媒介规制主要是基于大众流行文化对主流文化,尤其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挑战的考量,而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在此种意义上,传媒的调控、文化相关服务机构的审查与规范都具有媒介规制的性质。详细参见:Thompson, K. (1997),, in K. Thompson (ed.),and,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p. 1−68.
[1] 周正兵. 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J]. 中国出版, 2013(23): 11−16.
[2] 李少惠, 张红娟.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2): 110−114.
[3] 王铁钢. 论新中国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开创[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43(4): 47−53.
[4] 谢秋山, 陈世香.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97−202.
[5] 韩美群. 2001—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与发展状况检视[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3): 1−8.
[6] 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90年的文化观、文化建设方针与文化转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 25(3): 17−24.
[7] 李志峰, 乐爱国.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与政策演变思考[J]. 人民论坛, 2014, (32): 6−11.
[8] 杨凤城.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历史研究, 2013(6): 22−27.
[9] 杨凤城. 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论[J]. 中共党史研究, 2014(7): 27−34.
[10] 平章起, 郭威. 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三个面向”定 位[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5(5): 36−41.
[11] 祁述裕, 王列生, 傅才武. “十一五”文化政策回顾和“十二五”完善文化政策思路(代序)[C]//祁述裕,王列生, 傅才武.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3.
[12] Williams, R. State culture and beyond[C]//L. Apignanesi. Culture and the State.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4: 3−5.
[13] Mcguigan J.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M]. London: Open University, 2004: 63−64.
[14] 杨生平, 谢玉亮.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2): 60−63.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37.
[16] 李希光. 全球传播时代的议程设置与文化软实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 (B1): 5.
[17] Stanley D. The three faces of culture: Why culture is a strategic good requiring government policy attention[C]// Andrew C, Gattinger M., Jeannotte M. S., et al. In Accounting for Culture: Thinking Through Cultural Citizenship.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5: 21−31.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EB/OL]. (2005−11−7) [2017−09−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6/content_161057.html.
[19] 毛少莹. 中国文化政策30年[EB/OL]. (2008−11−11) [2017−09−10]. 文化发展论坛. http://www.ccmedu.com/ bbs35_ 75790.html.
[20] 赵宇. 国家文化软实力[J]. 党的文献, 2012(1): 111.
[21] 徐瑞仙. 从自卑到自信: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程与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 2016(2): 42−45.
[22] 罗嗣亮. 毛泽东关于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考及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 46−54.
[2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0.
[2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3.
[25] Waldo 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48: 124.
[26] 杜芳. 抗日根据地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领袖宣讲[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141−145.
The change of state cultural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An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 of the State Council
GUO Yuanyuan1,2, CHEN Shixiang1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2. School of Law, The National Police University for Criminal Justice, Baoding 071000, China)
Fo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 and become the prior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pen policy texts of the State Council, we can find that,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socialis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multi-aspects. On the significance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 has changed from “periphery” to ‘“core.” Regarding the policy objective, it has changed fro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o comprehensive cultural development. Pertaining to the cultural function, it has changed from supporting social capital to the core of national soft power As to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of policymakers in the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t has changed from discretion to self-confidence. We can predict that the statu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will be reinforced further and even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at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based on socialism ideology will become the cor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at network culture management will also become the major dir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cultural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five-year plan;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soft power; policy text
[编辑: 谭晓萍,游玉佩]
2017−10−08;
2017−12−27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15AH00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北省文化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HB14GL001)
郭远远(1982—),男,江西赣州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府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创新;陈世香(1973—),男,湖北鄂州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政策与服务、地方公共管理与政府体制机制创新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17
C939;D619;G03
A
1672-3104(2018)01−01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