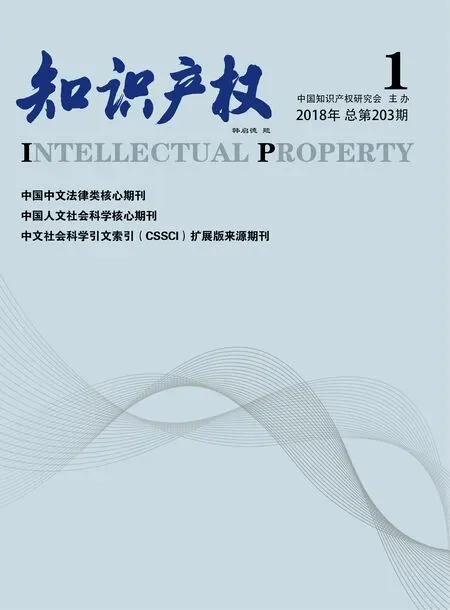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之检讨与展望
刘 平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两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案例1:华强方特(深圳)动漫公司与广州锦东市场经营管理公司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锦东公司作为市场的开办者、管理者,未履行其应负的经营管理及监督责任,对市场内存在的侵权行为的放任和管理上的不作为,实际为被控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帮助和便利,可以认定其与涉案侵权商铺构成共同侵权。二审法院推翻一审判决,认为因华强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涉案商铺存在直接侵权责任,根据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应当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没有直接侵权就没有间接侵权,且间接侵权应当是间接侵权人知道直接侵权事实的发生并仍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帮助,所以判决锦东公司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①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73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2:庄则栋等与上海隐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中,原告庄则栋、佐佐木墩子为《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一书作者,被告隐志公司为VeryCD网站经营者,该网站是基于P2P技术的互联网资源分享平台。原告以被告网站显示有《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一书的有声读物为由,主张被告未经授权在其经营网站上传播了该有声读物,侵犯了其著作权。一审法院以“安全港”规则为法律依据,主张用户上传侵权作品不能当然推断被告网站存在“明知”或“应知”的事实,且被告采取了屏蔽等技术措施,故判决不承担侵权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只有当提供P2P技术的网络服务商存在主观过错时,才会因为“间接侵权行为”而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因被告知晓网络用户多次涉嫌侵犯多名作家的著作权且在该网站发布了大量资源,作为专业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疏于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对网络用户侵害原告享有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
从以上二则案例判决文书的表述来看,“直接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应当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因间接侵权行为而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等法律用语纷呈,表明我国法院立足于法律续造的视角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类型予以了解构和重构,形成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二元模式,即“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区分,并将其与民法上共同侵权责任规则相勾连,导致我国著作权法与侵权责任法之间在保护著作权方面缺乏有效的理论协调与缝合机制。何为“间接侵权”?为何裁判认定当事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以间接侵权的成立为必要条件,而间接侵权的成立又必须以直接侵权的存在为前提?著作权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并列模式是否背离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从单独侵权到共同侵权的“递进式”认定规则?
(二)问题延伸:著作权“间接侵权”之迷惑
我国司法实务之所以采纳这样的表述,主要深受学界对域外版权理论移植的影响。比较法中,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存在三种范式:英国式“从属侵权”(Secondary Infringement)③Se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 26.;美国式辅助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④See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 S. 417, 435(1984).、引诱侵权(Inducement of Infringement)⑤See 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以及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⑥See Shapiro, Bernstein & Co. v. H. L. Green Co., 316 F.2d 304 (2d Cir. 1963).;日本场所机会提供型、工具提供型和系统提供型间接侵害著作权模式⑦参见李扬:《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的典型案例、学说及其评析》,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任张卫:《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理论的新发展》,载《网络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卷。。
事实上,早在200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便首次阐释了“间接侵权”的涵义:“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他人专利权,但却故意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发生直接的侵权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诱导或唆使别人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故意,客观上为别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这一判断方法被引入著作权领域则是在2005年的“金牌娱乐诉百度案”及2007年的“环球唱片诉阿里巴巴案”以后,一度成为学术研讨的热区。⑧其中影响较大的为王迁、王凌红著:《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理论上,著作权“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相伴而生,但二者在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上却迥然有别⑨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通说认为,“直接侵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直接实施侵害或妨碍著作权专有权利行使的行为,其判断标准关键在于这项行为是否受著作专有权的控制与法定免责事由(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存在与否。⑩王迁著:《网络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而“间接侵权”这一概念之界定尚无定论。我国著作权法对此虽无明文规定,但从反面推论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0条规定可知,“计算机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复制品是侵权复制品仍为持有、使用的行为”构成侵权,似有肯定“间接侵权”之嫌,由于并未直接从事软件复制行为,持有、为私人目的的使用行为本不构成侵权,但基于公共政策及预防侵权发生之考虑,《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将其拟制为间接侵犯软件复制权的行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5月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15条⑪该条规定:“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点对点)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侵权应当以他人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为前提条件,即第三人利用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点对点)等服务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侵犯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也似乎承认了“间接侵权”在我国著作权侵权中的应然法律地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立法缺乏相应规定情况下,司法裁判者能否以法官造法的方式创设新型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类型?“间接侵权”究竟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建构,还是对共同侵权行为的解读失误?我国《侵权责任法》之“侵权”是否有“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分?援引域外判例而形成的著作权侵权二元模式与传统民法共同侵权制度是否有共存的必要与空间?在侵害著作权行为认定上,作为特别法的《著作权法》与作为一般法的《侵权责任法》该如何适用?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理论阐述与案例引证来反思和检讨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之得失,以民法基本原理疏导著作权侵权责任之判定障碍,并试图构建著作权共同侵权规则来化解这一困境。
二、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之梳理与检讨
(一)观点梳理:我国著作权“间接侵权”起始由来
在我国,现有的著作权侵权规则体系是以《著作权法》第47条、第48条为根基,以《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为骨干,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为枝叶而建立起来的。
基于著作权法定原则及著作权的支配权性质,《著作权法》第10条采“限定列举+兜底条款”方式具体罗列了4项著作人身权与12项著作财产权附之与第(十七)项兜底性权利,从第30条至第46条明文规定了有关出版、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台方面的著作邻接权。除了第二章第四节对著作权进行合理使用的限制之外,《著作权法》第47条和第48条更是详细列举了18种侵害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的行为,以助益具体案件中判断是否构成侵害著作权的法律适用。
所以,著作权侵权的审判思路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属于法定的侵害行为类型,而这主要又通过著作权法定内容的解释来加以评价,先确定权利人主张的权利,再认定行为是否落入该权利的射程范围。这一评价体系对于侵权预备行为、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以及侵权损害后果扩大的不作为行为却存在立法空白问题。故而,学理和司法实务试图从解释论和立法论视角填补这一漏洞,以期克服直接侵权行为的封闭模式所带来的弊端。
有观点主张应对著作权及邻接权作适当扩大解释,扩大直接侵权行为的主体范围,将具备一定条件的间接行为人拟制为直接侵权人,此源自日本卡拉OK法理。⑫[日]田村善之著:《著作権の间接侵害》,载《著作権法の新论点》,商事法务2008年版,第266-267页。如“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将安装盗版软件的行为“推定”为侵犯复制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复制权”作扩大解释,将安装盗版软件的主体拟制为直接非法复制他人作品的主体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1期。
也有观点认为,在著作权领域,应采民法上法益保护论或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制。“设链网站的行为不构成公开传播行为,但仍然侵犯了著作权人依法应享有的利益,具体属于民法上侵犯他人法益的行为。”⑭陈绍玲:《论网络中设链行为的法律定性》,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第38页。如网络版权第一案“王蒙案”,当时我国著作权法尚未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且《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亦未施行,由于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侵犯原告王蒙的任何著作权专有权利,故而终审法院采纳的判决依据是当时《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兜底条款,认为世纪互联有限公司侵犯了王蒙的“兜底性权益”。⑮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海知初字第0005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而在“北京鸿宇吴天科技有限公司诉沈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加框链接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4)海民初字第19192号民事判决书。
由于“拟制说”是对既有法定著作权的扩展解释,而解释超过限度必将产生权利溢出效应,导致著作权法定流于形式,且附带有司法侵蚀立法之嫌;“法益保护说”或“不正当竞争行为说”对可保护“利益”范围的界定难以把握,容易造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泛化,以致法律适用出现“向民法一般条款逃逸”或“另起炉灶”的异化趋势。故而有学者建议司法工作者援引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则解决著作权侵权纠纷时应当秉持“谦抑性的司法政策”。⑰崔国斌:《得形忘意的服务器标准》,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8期。也正是因为这两种方法在解决著作权侵权纠纷方面捉襟见肘,主张借鉴英美、日本判例经验构建中国式著作权间接侵权制度的想法在我国大行其道。
总体来说,著作权间接侵权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直接侵害著作权专有权利的前置行为,二是为侵害著作权提供工具、设备或材料等辅助行为,三是扩大现有侵害著作权损害后果的行为。学者将实现著作权间接侵权法定化归因于加强著作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需要,而政策基础又在于著作权人利益在现实中受到了某种行为的损害。⑱王迁:《论版权“间接侵权”及其规则的法定化》,载《法学》2005年第12期。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单纯取向于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公共政策是否足以构成间接侵权法定化的事由?公共政策的需要是否应考虑立法成本和立法技术的可操作性?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本身是否存在难以克服的体系障碍?这就需要对著作权间接侵权进行透彻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
(二)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之检讨
1.“间接侵权论”混淆了侵权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
顾名思义,“间接侵权”的重点在于“侵权”,而“间接”作为形容词仅起修饰作用。本文以为,侵权就是侵权,无所谓“直接”与“间接”之分,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民法并无“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分类。这种划分乃是普通法的一套理论,但仅仅是经验之谈,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标准来进行判别。我国传统民法理论在讨论侵权责任法的调整对象时更注重侵权之“权利”内容之辨析,而基本不关注侵权行为的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都不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无论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其前提必须有权利被侵害,且这些权利必须为法定之权利。基于著作权法定原则,侵权乃是指侵害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16项具体著作权、第(十七)项兜底性权利以及第30条至第46条明文法定的著作邻接权。《著作权法》第47条和第48条更是详细列举了18种侵害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的行为,从条文表述来看,均是未经许可实施受他人著作权及邻接权控制的行为,故被学者称为“直接侵权行为”。
实际上著作权“间接侵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概念,既然侵权之“权”指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那么从性质上就应当属于对著作权的直接侵害,又何来“间接”之说?而将并未侵犯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行为称为“间接侵权”,名不副实,逻辑上难以自足。⑲李逸竹:《视频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对间接侵权理论之质疑》,载《网络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卷,第70页。这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概念,倘若不假思索地适用于司法实务,势必会造成法官思维上的纠结以及解释适用法律的困惑。究其实质,著作权“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分别对应侵权实行行为和非实行行为,无论是实行行为还是辅助行为,都是导致具体著作权受侵害的原因行为,“间接侵权论”实属混淆视听之说法。
就因果关系而言,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也没能解释直接侵权、间接侵权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如何,二者谁主谁次、谁起着决定性作用尚处于混沌之中。举例来说,设甲教唆乙上传某侵权视频,根据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乙的上传行为属“直接侵权”,直接侵害了视频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甲的教唆行为乃“间接侵权”,间接地作用于视频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然而,事实上甲的教唆行为与乙的实行行为相互结合造成了损害后果,与损害后果之间均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果多因”。只不过,甲是间接原因,乙是直接原因。根据损害原因力理论,责任的承担与侵害行为对损害后果原因力大小有关,这是按份责任内部划分的基本原理。然而甲乙谁是主要原因、谁是次要原因,谁对他人著作权受侵害具有更大的原因力,实务中恐怕很难区分。既然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不能将责任大小在直接侵害人与间接侵害人之间进行适当分配,那承认该理论于保障著作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英美版权法,无论是立法抑或是判例中,我们都只能找到“辅助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引诱侵权”(Inducement Infringement)以及“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这样的表述。美国人并未自行归纳出“间接侵权”的概念,“间接侵权”是我国学者独创性的“结晶”,是他们不辞辛劳从域外知识产权理论领域移植过来的一棵树,但最终并未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结出硕果累累。1990年“惠普公司案”(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中基于“共同侵权行为”认定被告责任的论据对著作权“间接侵权”作出了最好的反驳。⑳参见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2.“间接侵权责任论”与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的划分相抵牾
传统民法理论根据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具有同一性而将侵权责任分为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论将替代责任纳入其中,实则有悖于民法基本原理。
一方面,它混淆了“间接侵权”与“间接责任”在逻辑上的本质区别。“间接侵权”与“间接责任”并非同义语,前者谓之行为上的间接性,是一种与直接侵权行为相对应的侵权行为类型;后者属于责任形式之一种,谓之责任上的间接性,与自己责任相对,包括法律规定的基于某种特定关系应对直接侵害人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所有情形。换言之,“间接侵权”与“间接责任”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前者既非后者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前者只不过是导致后者的一种原因而已。㉑正如学者所论,传统侵权法中雇主责任就是“间接责任”或“替代责任”的典型形态,但由此并不能推导出雇主实施了“间接侵权”行为。参见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7页。譬如,美国判例法中的辅助侵权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就是一种自己责任,而不是间接责任。因为辅助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乃在于自己过错而帮助他人为侵权实行行为。㉒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39页。
另一方面,传统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在侵权行为类型的构建上并不存在“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在责任形态方面也没有“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区别。绝大多数学者在讨论责任承担的问题时,基本都采纳了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及补充责任的基本分析工具。所谓的“间接责任”只是少部分学者对替代责任的一种误解;所谓的“间接侵权的责任”应是一种自己责任,不应涵盖替代责任。正如日本判例根据卡拉OK法理将场所、机会、工具等提供者拟制成直接“利用”他人作品的主体,其行为直接作用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构成直接侵害行为,应该承担自己责任。但日本学界仍然将其称为“著作权间接侵害行为”,这在法理和逻辑上都是难以立足的。㉓李扬:《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的典型案例、学说及其评析》,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第65页。
3.“间接侵权论”下二元归责原则不符合法理逻辑与实践需要
在著作权领域,目前我国很多学者赞成二元归责标准,即“直接侵权”采无过错责任原则,“间接侵权”采过错责任原则。㉔有学者认为,“基于著作权专有权利的绝对权性质,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只要未经许可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主观过错并不是构成侵权的必要条件,只影响赔偿责任的承担。而构成‘间接侵权’的各种行为都不在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内,将其界定为对著作权的侵犯是出于适当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政策考量以及这些行为的可责备性,因此必须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参见王迁著:《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著作权“间接侵权”采过错责任原则,并无太大争议。㉕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4 页。尽管1995年“白皮书”㉖美国 1995 年《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工作组的报告》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系统或网络中的基于其改造中介服务所必需的自动、暂时性复制与传输,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复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负严格责任。参见刘德良著:《网络时代民法学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4 页。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采用了严格责任理论,但随后《美国在线版权侵权责任法案》与《美国数字版权和技术教育法案》将其回归为“过错责任”,1998年《美国新千年数字版权法》(DMCA)㉗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ct.28,1988.采取“通知后责任”(Notice-Based Liability),不外是对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达,同时法律又确立了“避风港”规则以限制权利滥用,保护技术中立规则。美国判例法形成的辅助侵权、引诱侵权均要求以过错作为责任承担的依据。英国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列举的三类“从属侵权”(Secondary Infringement)均采过错责任原则。此外,欧盟2000年《电子商务指令》、日本2001年《特定电气通信提供者损害赔偿责任之限制及发信者信息揭示法》亦采过错责任原则。㉘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42页。日本判例形成的著作权间接侵害理论则对此作了区分:在认定场所、机会提供者以及系统提供者责任时,适用卡拉OK法理,以管理支配事实与利益性为要件,通过“具有管理支配能力而不加以阻止并从中获利”推定场所、机会提供者以及系统提供者具有过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采推定过错的方式;而对工具提供者适用帮助侵权法理,亦采过错责任原则。
域内外在直接侵害著作权归责原则的认定上产生了极大分歧。美国版权法理论采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无过错不能免责而只能减轻法定赔偿数额。㉙17 U.S.C 504(c)(2).但英国版权法则坚持了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可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不知道”且“没有合理理由认为其知道”)为由主张免责。㉚“若有事实证明被告在侵权之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认为其行为所及之作品享有版权,则原告不能要求损害赔偿。”See (UK)Copyright Act, Sec 97(1).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和第48条详细列举了18种侵害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的行为,被学者称为“直接侵权行为”。该法对直接侵害著作权及邻接权责任的成立是否以过错为要件的态度比较暧昧,诸行为大多以“未经许可”作为前提条件,本文认为“未经许可”本身就是对侵权人过错的一种推定,利用他人作品,行为人本应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就发表他人作品、歪曲篡改作品、剽窃作品、使用作品应支付报酬而不支付等,是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具体表现。立法默认了著作权直接侵权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过采过错推定方式。况且,第48条第(六)项、第(七)项明显均采过错责任原则。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文件也有类似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20条明确规定出版者应当根据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过错与否取决于出版者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法发[2010]50号)第4段规定,无过错的网吧经营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坚持了过错责任原则。那种认为著作权“直接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同时又主张行为人可以举证证明自己“无主观过错或过错程度较轻”而“免除或减少赔偿责任”㉛王迁:《提供链接与帮助侵权——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一审判决》,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年第7期,第14页。的说法,本身就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内涵相抵牾。
在网络领域,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直接侵害著作权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然该款究竟是确立了何种归责原则,已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本文以为该款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无过错责任原则㉜在美国称为“严格责任”。参见徐爱国著:《英美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在德国谓之“危险责任”。参见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7页。的基本内涵是:法律特别规定以损害后果的发生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责任承担的根本依据,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无过错责任渊源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其真正作用不是解决责任的归属,而是解决损失分担和危险的分配。由于无过错责任要求行为人承担非常高的注意义务,适用时必须达到法律不得不特别强调这种行为的高度危险性程度。网络中侵害著作权的危害性似乎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侵权的频繁性主要是因为立法技术滞后和法律规则不完善,但这并不是说互联网本身严重危及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㉝张新宝著:《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第二,如果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势必会科以严格的审查义务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甄别。这种事先审查义务不仅与网络信息海量化的现实不符,而且也与促进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和繁荣的目的相悖。
第三,网络著作权直接侵权之“无过错责任”说的一个重要支撑依据是:既然《侵权责任法》将网络侵权责任放在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那么网络侵权行为就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该条理由过于牵强,因为条文所处的位置并不能决定条文内容的性质,立法者在体系编纂上将网络侵权置于特殊责任主体之下,旨在强调网络服务者有别于一般民事责任主体的特殊地位,不代表网络侵权行为就属于特殊侵权行为,也不意味着网络侵权责任应如监护责任、雇佣责任那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站在立法论的角度,该条应有“错置”之嫌。
因此,相对于《侵权责任法》而言,尽管著作权及邻接权由著作权法规定,但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仍然是一般侵权行为。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人为地将侵权行为区分为两类,由此衍生出归责原则的二元化,不仅有悖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设立宗旨及适用前提,而且在司法实务中也不具备分别归责的可操作性。承继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著作权侵权制度,不应不假思索地引入美国版权法中的二元归责原则,而应以一元化的过错责任原则来统摄所有侵权行为,只不过对某些行为须采过错推定的方式,以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保护与促进科技繁荣之间的关系。
4.“间接侵权论”未阐明直接行为人与间接行为人之间的责任性质和责任划分
侵权民事责任,有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之分,亦有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与补充责任之别。前已论述,著作权间接侵害人是基于自己过错而承担的自己责任、直接责任,非替代责任。至于其与直接侵害人之间究竟是各自单独承担责任,还是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抑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这与坚持“独立说”还是“从属说”有着莫大的关系。“独立说”下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特殊侵权行为,其存续不以直接侵害为要件,故而间接侵害人基于自己的过错行为而独自承担责任。而根据“从属说”,间接侵害人与直接侵害人之间必有某种关联,或为教唆、诱导关系,或为帮助促成关系,又或为扩大损害后果的关系。这种行为的客观关联性以及损害结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间接侵害人与直接侵害人之间不可能各自承担按份责任或由某一人独自承担最终责任,也不可能有补充责任适用的空间,而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间接侵害人与直接侵害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㉞王迁:《提供链接与帮助侵权——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一审判决》,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年第7期,第14页。进言之,这种责任的连带性缘于何处?所谓连带责任,大陆法系民法称为连带之债,在英美法系谓之“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德国民法典》第421条有明确定义。㉟参见张定军著:《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概括地说,连带责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责任主体的复数性。(2)给付内容的同一性,且每个责任人都负有全部给付义务。(3)债权人拥有任意选择权。(4)连带责任人内部仍然是按份责任,根据各自过错或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内部责任份额的限定主要通过追偿权来实现。关于连带债务成立的基础,德国民法理论中存在“债务原因同一性理论”“目的共同说”“相互清偿共同和相互履行共同说”和“义务的同一层次性理论”,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义务的同一层次性理论”,基本观点为:连带债务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债权人同一利益性与义务的同一层次性;债务人之中不应有终局责任人,否则不成立连带债务。㊱“连带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同一给付义务,每个债务人均对该给付承担完全的义务,而债权人仅有权在总量上得到一次给付。”参见张定军著:《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34页。据此,著作权间接侵害人实施了教唆、引诱、实质性帮助行为,直接侵权人实施了受著作权专有权控制的行为,两者相互结合导致了同一损害后果,任何一方行为的欠缺都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法律效果,间接侵害人与直接侵害人之间负担的义务处于同一层次,追求共同的目的,因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有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连带责任是“法律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事实上的最终责任”㊲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44页。。这种认识值得研究。真正连带责任(echte Solidaritt)和不真正连带责任(unechte Solidaritt)是瑞士法所作的区分,前者涉及行为人共同过错而作出的致害行为,后者涉及并非共同作出但导致单一损害的致害行为,且不考虑各自的责任是否基于不同的事实或法律基础而发生。但对于该项区分,存在着广泛的争议。㊳Christine Cappuis, Gilles Petitpierre,Benedict Winiger,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Swiss Law, in: W. V. H. Rogers (Ed.) , Uniベcation of Tort Law: Multiple Tortfeasor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 233.引自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6页。也有学者认为,承担典型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因为从行为(间接侵权行为)与主行为(直接侵权行为)竞合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㊴杨立新:《论不真正连带责任类型体系及规则》,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57页。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引诱或帮助行为与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相互“结合”才导致了损害后果,而不是“竞合”关系。“竞合”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引诱或帮助行为本身已构成了侵权行为。
简言之,连带责任的基础既可能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共同过错,也可能在于损害后果的同一性、不可分性。“知道”规则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缘于二者之间有共同的过错;而“通知”规则下的连带责任缘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消极不作为与网络用户的积极侵权行为,对于损害后果的扩大而言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两种相互结合不可分地造成了损害后果的扩大。不真正连带责任不承认有追偿权的存在,故而总是表现为一方的终局责任,这种事实上的最终责任必将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法向侵权网络用户行使追偿权,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绝非是真正的公平。虽然网络用户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及其偿付能力的有限性等特征,且不容易被追查,但绝不能以此否定网络用户的责任承担,法律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追偿权是分散风险、保障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益、促进网络产业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愿不愿意行使追偿权以及能否行使追偿权,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来选择。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应承担真正连带责任,其中任何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均可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基于“危险控制力理论”和“损害原因力理论”㊵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46-47页。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追偿权符合侵权责任法“合理分配危险”的理念以及鼓励网络产业的发展的政策精神。
5.公共政策需要必须服从于立法体系、立法技术和立法成本的检视
著作权间接侵权法定,从立法体系而言将与《侵权责任法》关于“单独侵权与共同侵权”的立法模式相抵触,在立法技术上以“破釜重铸”方式重构著作权侵权规则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且具有高负担的立法成本,因此贸然修法是不合时宜的。
(三)小结
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诞生于自我矛盾体中,将著作权侵权硬生生地分割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类,又没能论证这种二元结构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何独特适用优势,导致理论与实务、立法的严重脱节,更没有回答《著作权法》若确立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该如何协调其与《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侵权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是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的一大弊端。
三、展望:著作权共同侵权制度之构建
(一)著作权共同侵权的法理基础
倡导以“间接侵权”为引介重构著作权侵权规则体系的学者和实务者均对共同侵权制度产生了误解:认为共同侵权必须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直接作用于被侵害的权利,或者说二人以上均实施了侵权实行行为,着眼于被侵害的“权利”。所以在认定著作权共同侵权时,大多数人主张就每一行为单独加以评判,是否属于侵害著作权的实行行为,是否单独足以造成著作权的损害,倘若某行为不属于直接作用于著作权的实行行为,则丧失构成共同侵权的前提,而应以“间接侵权”单独承担责任。
这一观点实际上将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加害行为混为一谈,事实上我国《侵权责任法》上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远不止于此。
在我国,共同侵权的法定化最早成形于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30条㊶《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中作了原则性规定。为了助益司法审判认定,1988年出台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作了补充性规定,教唆型、帮助型侵权由此成为共同侵权的子类型。当时对于共同侵权的认定还是采取“主观说”。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则改变了这种做法,增加了客观关联(“行为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这是司法实务对传统民事立法中狭义共同侵权行为采纳“主观说”且固守“共同过错”标准的一种修正。2009年《侵权责任法》对共同侵权行为的体系结构与规则设计体现于第8条至第10条中:第8条属于一般共同侵权的原则性规定;第9条旨在规范教唆型、帮助型共同侵权;第10条吸纳了共同危险行为。毋庸置疑,第8条、第9条采纳了“主观说”,而第10条则有承认无意思联络或客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之意旨,系采客观说。
考察两大法系与我国立法与司法状况,可以归纳出共同侵权的两大要点:一是在行为类型建构上逐渐趋于一致,分化为共同加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教唆型与帮助型共同侵权三大类,判断标准亦从严守“主观说”到兼顾“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标准。如《德国民法典》第830条㊸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30条。规定了共同行为人(Mittter)、参与人(Beteiligte)、教唆人和帮助人(Anstifter und Gehilfen)三种类型㊹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5页。;《日本民法典》第719条㊺参见《日本民法典》第71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5条㊻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5条。基本仿照《德国民法典》第830条的结构,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共同加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和教唆(或造意)帮助型共同侵权。英美传统侵权法将共同侵权行为区分为“同一”侵权行为和“分别但一致”的侵权行为㊼徐爱国著:《英美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而《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更是详细列举了三类共同侵权行为㊽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876. (1965).。对于“共同关联性”的理解,德国学者认为应以共同行为人或参加人(Teilnehmer)的故意为必要㊾Larenz / Canaris,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2, C. H. 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3 Auぼage,1994, S. 567.引自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5页。;日本民法学界形成了“主观说”与“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以各行为人之间有意思联络为必要;“客观说”主张共同侵权行为不考虑行为人主观状态,只要存在行为客观关联即可,通说采“客观说”㊿参见于敏著:《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266页。。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也经历了从“主观认识共同”向“行为客观关联”转变的过程,通说认为,“台湾法”现采客观关联共同性理论,不以过错为要件,注重损害后果的同一性与不可分性,“数人的过失行为竞合而造成同一损害者,仍应成立共同侵权行为而负连带赔偿责任”[51]邱聪智著:《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22页。。二是以连带责任为基本责任形式,合理分配风险乃连带责任旨趣所在,该连带责任的正当化基础又在于“基于意思而形成的一体性”(即共同过错)和“基于因果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性”(可能因果关系)[52]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7-70页。。
我国司法实践中常依据民事共同侵权理论来规制教唆、引诱或实质性帮助他人直接侵害著作权的行为。2006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4条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性质确立了五类具体共同侵权行为方式:(1)针对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三种,即“参与型”“教唆型”与“帮助型”共同侵权;(2)针对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有两种,即“明知”规则下的共同侵权和“通知—删除”规则下的不作为共同侵权。但上述解释仅适用于网络侵权领域,对何为“参与”、行为人是否需要共同过错等语焉不详,以致与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共同侵权体系缺乏一致表达和制度衔接。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回归民事共同侵权的视角,以民法规则的解释来表达和塑造著作权共同侵权制度。
本文认为,著作权间接侵权论完全可以由民事共同侵权制度来代替解决,其与共同侵权既无共存的必要,也无共存的平台。日本、美国通过判例形成的著作权间接侵害理论或“辅助侵权”“引诱侵权”及“替代责任”之所以没有获得立法认可,反而颇受各界非议,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体系冲突无法协调。因此,所谓的著作权“间接侵权”不过是建立在对共同侵权狭隘理解的基础上的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一种不得已的暂时性措施,其与修正的共同侵权规则不能并存于著作权侵权责任体系之中,应当予以摒弃。
(二)构建著作权共同侵权的几点思考
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划分决定著作权共同侵权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共同加害行为(均为实行行为);二是教唆型或帮助型共同侵权(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结合),教唆行为不限于精神上鼓励和怂恿,还应包括物质上的诱导,而帮助行为亦不限于物质上的帮助,二者均以侵害著作权的实行行为的发生为前提。具体而言:
1.共同加害行为应采“客观说”认定标准
共同加害行为原则上要求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均为实行行为,各行为人具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问题是当各行为人不具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时,是否可以构成共同侵害著作权呢?本文以为,此时应类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5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采客观认定标准,即二人以上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亦构成共同侵权。如深圳迪优美特电子公司、深圳泰捷软件公司与上海霖合文化传播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泰捷公司开发了“泰捷视频TV版”软件,迪优美特公司作为涉案播放器的生产商将该系统预置在涉案播放器,系以“分工合作”方式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5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知民终字第1368号民事判决书。同类判决还有北京网尚公司与广东中凯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赣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2.扩大侵权损害后果的行为应构成共同侵权
著作权领域,扩大侵权损害后果的行为包括两类:一是直接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存续期间,行为人知道侵权事实后有义务且有能力制止侵权行为却对此不加控制、听之任之致使损害进一步扩大的行为。通常发生于“市场管理者与商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于自知道侵权事实起就损害后果的扩大部分,应当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因为行为人在知道侵权事实后的不作为是导致损害后果扩大的直接原因或近因,与扩大部分的损害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而且其主观上属于“实际知道”,与直接侵权人在损害扩大方面达成了某种暗合的“合意”。基于“合意”而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是民法上共同加害行为的基本形态。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便是以共同侵权作为连带责任的立论依据的。
二是直接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已发生,客观帮助行为导致其损害后果扩大。如深层设链行为对被链接网站侵犯他人著作权损害事实的扩大。这里并不要求设链者主观上“明知”,“过失而不知道”亦可构成共同侵权的归责基础。如在北京易联伟达科技公司与深圳腾讯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深层链接行为虽然并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但该行为为被链接网站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和便利,使得被链接网站的传播行为得以“扩大和延伸”,因此在被链接网站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深层链接者具备过错时应与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5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应当指出的是,侵害著作权实行行为的发生是认定共同侵权的前置要件。以视频聚合行为为例,如果被链者本身不构成侵权,则视频聚合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单独认定,即通过法律解释能否将其涵摄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范围。正如学者所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两个要素为“提供作品”和“可获得作品”,而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要件可理解为“未经许可+传播作品”,判断是否传播作品应从传播主体和传播范围加以考察。“视频聚合平台作为新主体扩大了作品传播范围,打破了原有利益格局,故应构成直接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56]李芬莲:《著作权法视野下视频聚合行为法律定性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而不是所谓“间接侵权行为”。依此逻辑,如果被链者本身亦构成侵权,视频聚合平台与其具有共同过错时才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属于共同加害型侵权责任;没有共同过错时,则应当由双方各自承担责任,视频聚合平台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终局责任。
3.扩张解释帮助型共同侵权以取代“辅助侵权”规则
依传统民法共同侵权行为基本理论,由于帮助者与直接侵权者的行为相互结合、相互关联,造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损害后果,即帮助行为、直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均有相当因果关系,只是二者的原因力或作用力不同。一般而言,帮助行为是次要原因,实行行为才是主要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为祂原因。因此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都规定帮助者与直接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著作权领域,帮助型共同侵权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坚持帮助型共同侵权的成立以直接侵权事实的存在为必要条件。如在上海幻电公司、上海看看牛视网络公司与华视网聚(常州)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二审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侵权责任,须以网络用户实施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为前提。[57]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
其次,帮助者必须实施了帮助行为,而不是侵害著作权的实行行为。对于帮助行为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该条显然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扩大损害后果的行为”和技术提供型侵权纳入帮助型共同侵权的范畴。除此之外,对于“帮助行为”还可以扩张及于场所提供型帮助侵权,如本文开篇所列的华强公司与锦东市场经营管理公司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就以锦东公司未履行应负的经营管理及监督责任,为被控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帮助和便利,认定其与涉案侵权商铺构成共同侵权。[58]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73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美国辅助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规则在客观要件上要求以作为方式提供身体力行的实质性帮助显得过于狭隘,实不足取。倒是日本的三种模式可资借鉴,但日本学者与法官在探讨“帮助侵权”的法理时,完全不在共同侵权的框架范围,而孤立地去判断帮助侵权行为的性质、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由此产生了两大缺陷:一是扩大了著作权侵权的适用范围,导致帮助他人合法利用作品亦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二是由于脱离了共同侵权的范畴,著作权人一般只单独起诉帮助行为者,法院不再追加直接行为人为共同被告以作为共同诉讼处理,那么帮助者完全可以以没有被帮助者和直接侵权行为为由进行抗辩。同时,这种做法也会加重帮助者(工具或技术提供者)的责任,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因此,应回归传统民法共同侵权的视角,对日本著作权判例中的“帮助侵权”予以修正。
最后,帮助者必须具有过错。过错不应限于故意,因过失而帮助亦包括在内。例如被链网站存在大量侵权视频,而设链者因疏忽或过失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便设置相关链接,无形中对被链者侵权获利提供了帮助,设链者应当承担帮助型共同侵权责任。美国版权判例中形成的辅助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在主观要件方面采“知道(Knowledge)标准”,包括实际知道(Actual Knowledge)与推定知道(Constructive Knowledge),或者称之为“明知”和“应知”,分别对应我国侵权法上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因此辅助侵权的主观要件能为帮助型共同侵权所包含。
4.以教唆型共同侵权包容引诱侵权内涵
美国版权判例中的“引诱侵权”必须具备三个要件:(1)须有第三人直接侵犯版权专有权利的行为事实存在,这是适用“引诱侵权”规则的基本前提;(2)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具有怂恿或促使他人侵权的主观意图,在这里当然仅限于故意,过失不存在引诱的可能性;(3)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客观上采取了导致侵权事实发生的实质性措施,且该措施与第三人的直接侵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以上三个要件基本与我国教唆型侵权的构成要件并无二致,只是二者使用的手段不一。“引诱侵权”以物质性诱导为主,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本身具有诱导性;而我国民法中的教唆侵权以精神上鼓励或怂恿为主。但这只能说明,我国传统民法中的教唆侵权适用于著作权领域时,应当进行适当扩大解释,将教唆的方式扩展为精神性鼓励与物质性诱导兼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该条对传统民法上的教唆行为进行了适当扩张解释,包括“技术支持”等物质性诱导,对著作权的保护是相当有利的,值得借鉴。如在北京博图公司与中文在线数字出版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手机之家网站资源组成员xbzzr将涉案侵权作品上传至手机之家网站论坛,供用户下载,该资源组成员系由博图公司在其经营的手机之家网站上公开招募,主要负责在论坛发布电子书资源等,被告博图公司根据发帖量、点击率、回复数等指标每月对资源组成员进行考核并给予资源组成员imobile币、手机话费及其他物质奖励,且博图公司对于资源帖实施了编辑、分类、推荐,博图公司的行为属于以言语、奖励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构成教唆侵权。二审则认为博图公司同时构成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59]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941号民事判决书。
另需要说明,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是否可由教唆侵权来规范?
从文义解释看,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是指那些极有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被学者称为“间接侵权”。[60]王迁、王凌红著:《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制造或持有其唯一功能用于“直接侵权”的工具就是典型的例证。尽管这种工具尚未被用于实施侵权行为,但一旦被他人使用则势必造成著作权人实际损害的发生。因此这种工具高度的现实危险性,以“间接侵权”为手段可以有效地化解危险,防止损害的实际发生。[61]王迁、王凌红著:《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很显然,这是对英美版权判例中引诱侵权(Inducement Infringement)规则的简单复制。之所以会有上述观点,一方面是我国基于著作权法定原则而确立的著作权权利体系及法律责任具有封闭性,对于侵权预备行为未能概括于中,试图通过列举绝对权的方式来保护著作权的办法根本不能起到事先预防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48条对于侵害著作权的责任承担以实际损害为前提,故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仅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四种情形,侵权预备行为尚未造成实际损害,仅具有导致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而这种盖然性足以对著作权人的利益构成现实威胁。以上四种责任方式基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由于教唆侵权适用须有损害后果的实际发生,因此无损害事实则单纯的预备行为不具有可归责性,本文建议应于著作权法中增加“消除危险请求权”,并结合《著作权法》第50条诉前保全措施予以解决。
从请求权的角度,著作权人基于权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而发生请求效力,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等。[62][62] 戴谋富:《即发侵权抑或知识产权请求权之选择——兼议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选择》,载《科学管理研究》2008年第2期。前二者皆针对实际侵害。消除危险请求权针对可能发生的侵害,这种侵害具有高度盖然性。在著作权领域,“制造或持有其唯一功能用于‘直接侵权’的工具”,从功能的唯一性可判断该工具有侵权的高度盖然性,应依消除危险请求权请求其停止制造或销毁此类工具。如果对方拒绝,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63][63] 李逸竹:《视频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对间接侵权理论之质疑》,载《网络法律评论》(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页。然而,在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并非以请求权为基础展开,而是以民事责任为线索来构造。《民法通则》第六章第四节专门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共有十种,不加区分地涵盖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各种责任方式。《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八种具体的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且可以单独适用,亦可合并适用。这些责任承担方式,有的具有预防功能,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有的具有回复功能,如恢复原状、返还财产、恢复名誉等;还有的具有补偿和惩罚功能,如赔偿损失。从法理逻辑来说,针对不同阶段的侵害行为应当采用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损害尚未发生或仅有发生的可能性时,则应当采取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损害实际发生且能够恢复原状的,应当采取回复性责任方式;损害已经发生且不能恢复原状的,采补偿性或惩罚性责任方式,以填补损害。于著作权而言,进口或持有侵权复制件具有潜在的侵害著作权人利益的危险,损害尚未发生,故而应采取预防性措施,通过消除危险来预防损害后果的实际发生。
《著作权法》第47条、第48条规定的四种责任方式,完全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前提,过分强调“无损害即无责任”,徒增诉讼成本与著作权保护的成本。事实上对于著作权人而言,预防损害比填补损害要有意义得多,损害赔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济方式。因此,应当确立消除危险责任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而对于“危险”的理解应限于现实的危险,其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如前述制造或持有唯一功能用于侵权的工具便具有这种现实的可预见的危险,而制造自主复印机本身基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并不意味着有被用来侵权的现实威胁。尽管著作权是无体财产权,且侵害行为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实践中多以事后救济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侵害著作权人利益的危险就没有救济的必要,采用消除危险责任有助于著作权人及时排除对其非常不利的危险。
另一种方法是诉前保全措施,包括诉前禁止令和诉前财产保全。即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则可以向法院申请采取禁止令和诉前财产保全,以防止危险变为现实损害。例如,知道或有理由认为其知道侵权复制品而仍然持有,这种行为大多是为后续出租、出售行为做准备,著作权人知道该危险源明显存在时,即可采取诉前禁止令要求持有者销毁复制品以排除侵权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16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23号)均对诉前责令停止侵权措施规定了一个原则性标准,即对侵权可能性的认定原则上应当达到“基本确信”的程度。
总之,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在内容和功能上均可为共同侵权所代替,因此应回归传统民法共同侵权规则的视角来审查这种“间接行为”与“直接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侵害著作权共同侵权的完整规则体系,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结 语
立法的科学性不仅要求法律规则的制定应当具备法政策上的合目的性与法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更要求法律术语的表达符合立法习惯,不违背常识。著作权“间接侵权”本身就是一个背离常识的非规范化法律用语,不宜在立法文本与裁判文书中使用。
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应当借由共同侵权制度的构建予以化解,遵循从“单独侵权”到“共同侵权”的判断规则。首先应当穷尽一切解释方法对法定著作权进行解读,力求探究各种著作权的真实含义,既不过分扩大,又不极度限缩,以辨别行为是否属于侵害著作权的法定范围。其次,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牵涉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范围,不构成直接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但又对著作权人的利益有所妨害,则应当根据该行为的性质为帮助行为、教唆行为或参与行为,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共同侵权规则,来确定其与直接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和责任分担。具体来说:(1)应当修正《著作权法》所构造的封闭式的责任承担方式,确立消除危险责任为保护著作权人合法利益的一种法定责任方式,以此与诉前禁令和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共同致力于防止侵权预备行为转化为侵权实行行为。(2)将扩大侵权损害后果的行为纳入共同侵权的范畴来考虑,具体又划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市场管理者与商铺”损害扩大型共同侵权和“深层链接者——被链者”损害扩大型共同侵权。(3)应当对传统民法中的教唆型共同侵权、帮助型共同侵权加以修正。教唆行为不限于精神上的鼓励和怂恿,还应包括物质上的诱导,而帮助行为亦不限于物质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