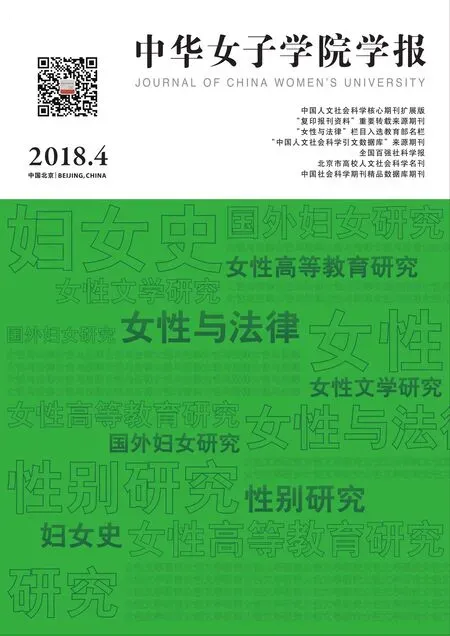近代护理职业女性化中的性别协商
马冬玲
一、问题的提出
女看护之说传入中国已久,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女性外出工作少,以及“男女大防之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的存在,使得早期护理职业对女性是关闭的。早期协和医学堂附属医院是男医院,医学堂和护士学校只招男生。1906年创建的北京协和护士训练学校,当时只招收男生。[1]可见,男性并没有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中国护理教育与护理职业之外,而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中国护士历史来看,男护士过去是曾有光荣之一页的,而且中国护士能有今天的地位,也是过去男护士用血汗苦斗的结果,所以奠定中国护士界的基础者男护士实有力焉。”[2]但是到了1945年,一些护理学校招生已开始仅限于女性。[3]
护理职业女性化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是如何与特定社会文化特别是性别文化协商的?长久以来,职业与性别的关系研究更多地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是如何在职业进入、职业升迁、职业退出等环节被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所排斥的。[4][5][6]然而,现实中女性职业空间的扩展表明,她们如何打破性别隔离进入特定的职业领域,同样值得研究。
什么职业适合哪个性别?其背后是性别规范文化的争论与协商。本研究关注护理这一职业,是如何经历了对女性从关闭到开放乃至女性化的过程,以探讨上述问题,并主要从职业空间、服务对象、职业特征与职业回报四个方面,讨论这一过程中性别与职业的互动过程。本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职业与性别的理论探讨,还可以为女性进入新的职业领域提供实践借鉴。
二、职业空间与性别解放
在女性进入护理行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打破“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古训带来的公私领域隔离,创造机会使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国内知识分子积极推动男女平等,支持女性平等接受教育和参加公共劳动,使得女性谋取社会职业所承受的阻力由大转为较小,为女性得以进入护理职业创造了社会大环境。
维新派的强国保种探讨,以及新文化运动先驱对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吸纳,促使他们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妇女要彻底解放,获得人格独立和社会地位,须以“经济独立”为基础。[7]职业便日益成为妇女解放的中心议题。《大公报》编辑吕碧城认为,女性需要“自养、自立”。[8]198秋瑾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倡导女性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等养活自己,“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1921年在《妇女杂志》关于妇女与职业的讨论中,陈问涛提出:“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9]韶先则认为:“女子受职业教育后,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则对于自己的地位也可以增进。”[10]有的推动者从两性能力的角度入手,认为男女在能力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女子也有工作的能力,且可从事所有职业。[11]有的推动者还从减轻男性负担的角度推进。[12]
正如前文所述,早期护理职业的空间并不对女性开放。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探讨为妇女从事社会职业打开观念上的大门,从而进入职业生活的空间,很难想象女性能够走出家门,进入护理职业。新文化运动以后,“职业女性”这一新的社会角色已经获得其话语和制度层面的合法性。[7]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妇女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妇女界中一支中坚力量,几乎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都有女性的身影”。[13]护理行业也不例外。尽管受传统性别分工意识的影响,女性可以进入的职业仍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义务存在明显的关联,但是护理这一新兴职业的出现,无疑给女性提供了经济独立和参与社会的空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护理专业知识的女性,其中一些人甚至走上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她们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和社会贡献的评价,有助于提高女性群体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尽管护士收入不高,但相对有限的工作机会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可以养活自己且能独立的工作机会了。尤·琼恩在自传中描绘了她接受一位逃婚的农村女孩成为实习护士的经历,在她的帮助下,这位女孩用做护理挣来的钱换得了家人对其婚姻自主的认可。[14]琼恩能够接受女孩做自己的帮手,反映了她本人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应该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应该在社会上工作,同时她认为女孩有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由于当时护士相对于普通老百姓其受教育水平更高,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收入体面,她们被称为“护士小姐”,得到了患者和社会的尊重。
妇女进入护理职业,虽然并非是近代思想启蒙的直接后果,但是女性个体解放、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话语成为女性进入现代护理职业的一个促进因素,使得护理职业开了女禁。
三、服务对象与性别隔离
早期女医界也从护理职业服务对象的角度着手,推动女性进入该职业,其中包含了对传统性别规范的利用与超越。
性别隔离发源于古老的女体禁忌,被男权社会将原本保持中立立场的安全保障措施置换为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性别政治工具。[15]由于“男女大防之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的存在,女护士护理男病人这项工作,在1918年前成为社会与国人不可思议、医院难以改变的事情。①关于当时是否有男护士护理女病人的情况,未能查到相关资料,暂不讨论。[16]18清末时的广州博爱医院,风气早开,男女实行同校,但分左右座,中间以帐幔隔开。上海仁济医院、武汉普爱医院也分男女医院。[16]6为此,早期中国女医界力图使用各种策略争取在医学领域的空间和位置,其中包括利用“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发展“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的主张,以赢得社会认可。继之,女医界又利用护理工作的科学性一面,将女性适合护理所有病患的观念推向全社会。
“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这一主张,最早由医界女先驱张竹君(1876—1964)明确提出。在她建立的《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里,她这样写道:“夫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且往往有隐情不能言者。以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若外症之在下体者,更无论矣!伊古以来,妇女之枉折者,不知凡几,岂不大可悲耶?”她强调,“女性之身体”不同于“男性之身体”。张竹君认为,女人之病比男性多且复杂,并且以男性治疗女性之病会因女性“有隐情不能言”而存在很大缺陷。1907年,上海《女子世界》的另外一篇文章《女子之新职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女子之事,唯女子能知之,男子之不能深知女子之事,亦尤女子之不能深知男子之事也。譬如女子而为医,则其与女子以便利者,甚无量也,且能与女子以职业于人类经济界上亦大有裨益云。”[11]
护理是疾病治疗的环节之一。“男女之别”,不仅体现在疾病治疗部分,而且存在于护理部分。这种主张既被父权制社会所认同,也因考虑了患者伦理道德规范之需要,而得到女性患者的拥护,成为一个相当有效的策略,使得同性护理成为合法,也为女性成为职业护士创造了空间。20世纪一二十年代,北京的医院里,男医生和男护士负责男病人的医疗与护理,女医生和女护士负责女病人的医疗与护理。外籍护士于1912年在苏州博习医院开办男生看护学校,之后又外请女护士服务于女病房内。[16]18
但是,这种要求男女在空间上、身体上的隔离的“男女有别”规范无法实现让女护士护理男病人的问题。当时,中国的护理先驱认为,“女护士不能护理男病人”这一习俗严重影响了护理事业的发展。1914年,美国护士信宝珠在《训练中国护士之法》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变更风俗,否则,护士则不能成为完美之护士……护士必须兼看护男女病人,方能为一完整之护士。”[16]18
由是,他们着手对中国护士进行性别改造。这种诉求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方法加以实施。1918年,中华护士会第四届全国护士会员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改变“女护士不能护理男病人”的决定。具体的做法是,先由外籍女护士陪同中国女护士共同工作,并要求中国女护士在男病房工作时举止端庄文雅,以逐渐改变男病人对女护士的看法。[16]18-19改造中,以现代医学科学、客观的态度看待患者的身体成为策略之一。当然,由于早期民间家庭护理中的主体多为女性家属,她们的护理角色从家庭扩展到劳动力市场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这些举措逐渐打破了孔孟“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束缚,在中国近代护理学史上可称为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女护士不能护理男病人”的历史被改变了。当然,这项工作的变革并非一帆风顺。据1920年调查,在男病房内实行由女护士看护,在全国医院中仅有7所。在中华护士会的推动下,1920年以后男女同校风气大开,各校才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到1934年,65%的医院(167所医院中有101所)由女护士在男病房开展护理工作。[17]
四、职业特征与性别气质
西方护理职业走过了男性化/非性化到女性化的历程。当时在中国的西方护理先驱秉承西方的护理理念,遵循南丁格尔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护士”的观念,通过宣传等形式逐渐将护理职业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男性不适合从事护理的社会氛围。
西方的护理历史表明,男性在其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在中国,男护士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女护士共同从事护理工作。北京同仁医院、湖北普爱医院、保定思罗医院等还开办过男护士学校。[16]61915年,中华护理学会第二届全国护士会员代表大会提出,需要培养男护士。1918年,北京协和医院护理主任霍华德(Howard)提出了培养男护士的看法,认为男护士将是长期的工作需要。1922年,社会上开始讨论“中国男护士的价值”,认为男护士在将来若干年间仍适宜护理男性病人,尤其在偏僻地区更能体现男护士存在的必要性。1928年,第九届全国护士代表大会通过男女护士和护生的工作服样式,可见男护士依然是考虑的对象。1930年的第十届全国护士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护士代表130人参加了大会。[16]31直到1935年,一则招考护士的消息要求仍写道:“不论性别,均得报名应考”,录用额数为“男女各五名”。[19]当时的文化认为,男护士的存在必要性不仅在于男女的身体禁忌,还在于男性在护理工作中的体力优势。“护士学校随医院而增加,西人每感女性不及男性工作迅速,于是招收男护士,男女护士日见其多。”[20]
虽然一些男性从事护理工作,但是传统的女性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护士职业的社会角色。[21]211护理职业的女性化,首先来自南丁格尔等护理先驱对护理职业的理解。他们虽然强调护理的知识性,但坚持在护理和女性气质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性。事实上,南丁格尔把母亲和管家的最优秀品质赋予在其所理想的护士形象中。[21]213她对护士提出的职业期望是:责任心强、清洁、有自我牺牲精神、勇敢、头脑冷静、工作努力、遵从医生、像慈母般温柔,就像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天使”。[22]54-56在其代表作《护理札记》中,南丁格尔更是提出:“每一个女人都是护士。”[23]可以说,她对护理的理解是女性的本能加上护理知识。在这一背景下,护理被看成是对女性来说自然且适宜的职业。[24]218-224
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职业一样,“护士职业伴随着近代医学和西式医院传入中国,而成为一个新兴职业”。与西方护理职业化的过程不同,中国的护理专业化没有单独面对医生的挑战,也没有经过西方那种与医师的艰难博弈过程。这是因为,护理是作为西医学总体的一部分进入中国的。当时争议的焦点不是医护的专业位置问题,而是中西医之争。当西医决定性地取得合法地位时,西方护理的一套知识技术和伦理也进入中国,包括职业的性别特质。
随着对西方护理职业的了解深入,在护士会等护理机构的宣传和护士团体领袖基于自身对护理职业特性理解造成的垄断之下,社会上渐渐认同护理职业与女性气质是相匹配的。一方面,护理职业所需要的温柔沉稳气质与女性特质紧密联系。“论护士工作,在先进各国皆女性为之,纵有男性亦是凤毛麟角,以女子性情温柔,态度和蔼,于此事颇为适宜,亦是女子近代最高尚之职业,男子性质不相近,无庸赘言。”[25]1940年,燕京大学校方请协和医院的护士演讲,对该校的护士生活及课程概况略加解释。当时,其演讲题目为《以护士为职业》,其中提出:“在中国现状下,护事职业颇占重要地位。尤以女子最适宜从事此业,盖彼等赋有温柔之性情与沉稳之耐性也。”[26]另一方面,护理职业与女性的母职,即“护婴”角色紧密联系。例如,1935年解冰士在《医事公论》撰文表示,受过护理训练的女性虽有在医院从事护理事业的,“亦有多作‘新娘’‘太太’们在家‘护婴’了。吾敢言之:护士事业绝非男子职业,乃将来贤妻良母中的一种训练”。[20]
随着对护理职业性别特质看法的改变,护士一职被视为女性的专门职业。社会上开始认为男子学护士已不合时尚,甚至认为男护士的存在是畸形的。解冰士提出:“根本护士的始祖南丁格尔她是女性,她主办的护士学校没有产出一位男性来。这种畸形的中国护士界招收男性,是社会上不需要的。”[20]田维范也认为:“护士在中国根本是畸形的,女子充此业,也蒙各界所赞许,同时我也说过,不近乎男之本性,因此男护士在医院已无立足之地,这是铁般的事实。”[25]
时任中国男护士改进社领导人的花新人认为,社会上关于护士的合适性别是女性的看法导致了男护士的窘境:“因要适合目前社会需要和迎合民众心理起见,男护士乃渐渐地被淘汰过去。”他也认为,当时的中华护士会对男护士的偏见起了不利的作用。“去年男护士界曾发动组织中国男护士改进社,而中华护士会不但是不加以同情援助,反而捏造许多反宣传来破坏。”[2]他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护理界有关护理职业与性别气质的争论。
五、职业回报与性别角色
如果说,职业的性别特征女性化给了男护士一大打击,那么随着女护士的增加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带来的职业回报的下降,又给了男护士再次被排挤出去的理由。
一是护理职业女性化对男护士的就业形成挤压,男护士失业问题严重。由于社会日益接受女性更适合护理职业,加上女性对职业回报的要求更低,男护士丢饭碗的情况日益严重。1918年第四届、1922年第六届、1932年第十一届全国护士会员代表大会交流的学术文章中,有《培养男护士是长期需要的工作》《中国男护士之将来》《中国男护士的价值》《今日中国男护士之出路》等论文关注男护士的职业发展问题。[16]177-179到1935年,领有中华护士会文凭者,“计4805人,男性占1477人,女性占3328人”[20],显然女多男少。早先训练出来的男护士渐渐流失,“继任护士事业者,仅占男护士总数十分之三”。[20]这使得男护士的出路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935年,田维范在《医事公论》上讨论男护士的饭碗问题。“近来使我惊讶!在各报医学周刊医事杂志,时常见到讨论‘男护士’问题,其内容要点,很明显的,是闹饭碗的恐慌!”“因受种种摧残乃至于无条件下频遭生计之摧毁,随时随地均感受不堪言喻之苦,失业者徒增,固不必言,而暂时得维持现状者,亦寥寥无几。”[25]男护士的境遇太不良,“像‘出路’、‘失业’、‘前途’、‘生存’种种问题是与日俱进的追逼过来”。“全国之男护士既无法在各医事机构立足服务,又不能凭所有能力自由努力以求最低立足之余地,欲升学求深造更苦无转机以求收容,四面楚歌,到处不同,危胁交加,出路何在?”[25]
二是国家医事政策的改变影响了男护士的职业发展。1935年以前,男性能够参与到护士职业中,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是当时初中毕业者的一个较好出路。“四载毕业后,在医院工作者很少,到各城市乡村独立门户开诊者,比比皆是,在军法时期,当军医处长助人者,颇不乏人,而工作的效能,与野鸡大学毕业,手执行医证,挺胸鼓肚者,并无差异!故一般无力向学的青年心目中则羡慕矣!”[25]然而,“年来政府已渐上轨道,对于医事建设,亦认真加以整顿,过去男护士之出路,早已断绝并加取缔”。这种政策改变的影响因素较多,可能与社会需求、医界发展、劳动力供给等均有关,但客观上导致了男护士发展前途受限。“军医的调理严格了,护士是不合格的;那卫生事务所快伸张到农村去,取缔无执照的医生们;医院里为着迎合社会人心理而单用女性,永不能进去了;中国男护士将往那里去?”[20]
三是护士职业的收入不再能满足男性养家者的角色之完成。早在1888年,《申报》就在其刊出的《论妇女做工宜设善章》一文中指出,妇女做工对于家庭有益处。“妇女做工,得钱谋食,真贫家之一大养济院,原不必遽行禁止。”[27]但社会主流只是将女性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男性仍被期待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对近代上海女店员的研究发现,当时管理者认为男职员所得为“家庭工资”,女职员则支领“个人工资”,家庭责任的多寡合理化为男女工资的差异。[28]1935年后,转做军医或赴农村任医职的机会既失,医院也为女护士所占据。男护士失业状况严重,即便能够继续担任护士,其生活费用和待遇也十多年不变。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更是不合水准,对于承担养家主要责任的男性来说,委实不堪重负。“现在细微月薪之收入,既不能尽人子孝养父母之责,又不能负担儿女教育之费,对于国家对于家庭均无成绩可言,溷度一生,令人不胜悲戚。”[25]1935年刊登的录取护士的月薪仅有15元。[19]当时的调查显示,这是北平医院护士的平均工资水平(该调查显示,当时低级警察工资为13—16元,低级职员14元以上,电力公司雇员17元以上)。[29]如果一位男性以此收入养活一个家庭,那么生活就会比较拮据。
为了解决男护士的职业发展问题,中华护士会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1936年,中华护士会特组织一个“男护士问题专门委员会”,调查关于男护士之全部问题。1939年,男护士失业问题较为突出,为减少失业之纷扰,中华护士会建议男护士可兼任技士工作等,以使护士职业有所保障。[16]37有关心者建议停止招收男护士[2],还有的建议强化继续教育,或是大规模集训[3],特别是分门(性别)训练,以充分利用男性工作迅速的优势。[25]但是,历经20多年的努力,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47年,“男护士的出路是目前医事界上一个严重问题”。[3]1948年10月,第三届(总第十六届)全国护士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议案中,仍包括“男护士的出路应如何解决”的问题。[16]49
从社会和男护士自身的角度来看,护理不再是一个适合男性的职业。由于护理职业被广泛看成是女性特质和优势的体现,而不符合男性特质,但男性作为养家者的性别角色规范也在起作用,男护士的处境尴尬并日益退出。由此,护理职业逐渐排除了男性,成为女性专属的职业。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到1943年10月16日止,女性看护人数达到4472人,女性西医人数达到1197人,约占到当时医护人员总数的37.78%,比其他行业的女性人数多得多。[30]
六、小结与讨论
检视中国护理职业女性化的历史,性别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性别隔离的文化以及女性作为天然照顾者的意识形态是女性从事护理职业的合法性理由,男性应该承担养家责任的角色负担与护理职业无法承载这种期待的冲突则使得男性被排斥出去。
这是一个与传统性别文化相协商的过程。首先,现代的关于妇女独立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话语为女性进入职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性社会环境。护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公私领域的划分,伴随着妇女解放的进程,从私领域中女性的家务劳动发展,延伸到公领域,成为劳动力商品的。护理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与当时妇女解放的话语相结合,得到妇女解放派的支持,给了女性进入该职业的空间。同时,这个过程中又有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利用。例如,利用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突出护理对象对女护士的需求,以解决服务对象与文化传统中男女授受不亲理念之间的冲突;利用对女性温柔沉稳等性格特质和母职(护婴角色)的要求,以及西方护理职业的女性化特征,将女性、母性与护理的职业需求结合起来,使得女性适合做护理的观念深入人心;最后,护理职业的女性化还通过降低男护士的职业回报将男性排挤出去。可以说,无论从职业提供的机会与回报,还是从职业本身的要求来看,中国近代护理职业的女性化都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护理职业女性化的性别协商过程表明,传统性别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有着可以协商的空间,甚至同一套性别规范如性别隔离观念,既可能成为限制某一性别从事某一职业的借口,又可以成为促使某一性别从事某一职业的理由。此外,尽管行动者往往是有意识、有目的地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对传统性别文化进行反抗,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存在妥协和权宜的。为给女性的职业参与寻求空间,解决妇女参与社会生产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推动者总是利用手头可用的资源去争取独立的空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虽然这种对性别规范的妥协有其合理性,但是长期来看,却存在着对女性特质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化。现代护理职业的女性化过程显示,职业与性别之间的适配性并非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可协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