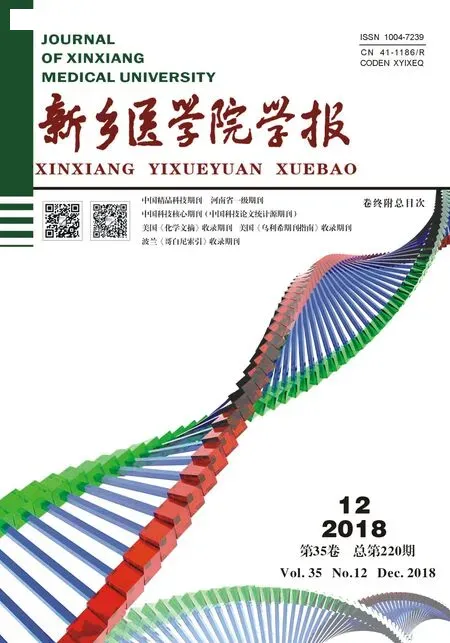系统性红斑狼疮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进展
李虹艾,李帮涛,崔 兰,海元平,黄 婷,向 伟
(1.南华大学附属海南医院儿内科,海南 海口 570000;2.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儿内科,海南 海口 570000;3.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海南 海口 570000)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多器官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脏器受累严重。该病好发于女性,特别是育龄期妇女,我国SLE患病率为70/10万,而女性患病率高达113/10万[1]。目前,SLE确切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但已确定遗传与环境因素在其发病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相关研究揭示了表观遗传修饰在肿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疾病发病中的影响机制[2]。表观遗传修饰是可遗传的、可逆的、不改变DNA本身序列的基因修饰方式,主要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等。表观遗传修饰通过参与调控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影响免疫细胞分化发育、免疫应答相关分子活化及细胞因子分泌表达等,进而参与免疫调控,许多受表观基因调控的信号分子和受体在包括SLE在内的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过程中出现失调[3-5]。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甚至发现“表观遗传干预”在这些疾病中的治疗潜力,研发出一些能够修改表观遗传标志的药物,这些都为免疫紊乱以及疾病发病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3-4]。本文主要就SLE表观遗传学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SLE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表观遗传修饰在SLE致病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机制
1.1DNA甲基化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领域最早发现的、也是研究最为成熟的DNA修饰现象。DNA 甲基化是指在DNA 甲基转移酶的作用下,由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SAM)提供甲基,将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cytosine-phosphate-guanosine,CpG)的胞嘧啶甲基化为5-甲基胞嘧啶的过程,是调控组织特异性基因表达而不改变DNA一级结构的可逆过程。DNA甲基化的发生部位多在CpG岛,它控制转录因子、转录激活物和RNA聚合酶,在真核生物中,DNA甲基化与基因表达调控、发育与衰老调节、基因组印迹及X染色体灭活等方面密切相关[6]。DNA甲基化受DNA甲基转移酶 (DNA methyltransferase enzymes,DNMT)调控。哺乳动物的DNA甲基化主要由DNMT1、DNMT3a 和DNMT3b 3种酶完成,其中DNMT1属于维持甲基转移酶,DNMT3a和DNMT3b属于从头合成甲基转移酶[3,6-8]。DNMT1负责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进行重复甲基化,维持DNA的持续甲基化状态[9];DNMT3a和DNMT3b参与DNA甲基化的从头合成,对尚未甲基化的DNA链进行甲基化,使得DNA甲基化独立于原有模式[10]。
生理性的DNA甲基化与基因表达调控、发育和衰老调节、基因组印迹及X染色体灭活等方面密切相关,而异常的DNA甲基化在多种疾病如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1-14]。JAVIERRE等[15]发现,同时患有SLE的同卵双生子的DNA甲基化模式表现不同,揭示了DNA甲基化在SLE发病机制中起着独特作用。研究表明,SLE患者总体DNA处于低甲基化状态[16-17],且CD4+细胞CD70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水平与SLE活动度呈负相关[18]。随着表观遗传研究技术的发展,目前DNA甲基化的研究已从单基因甲基化发展到全基因组甲基化研究,研究样本也由最初的外周血白细胞进展为各种细胞亚群,如CD4+T细胞、CD8+T细胞、单核细胞等。研究揭示了SLE患者异常的DNA甲基化,如多种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Ⅰ型干扰素及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肿瘤坏死因子等甲基化降低,插头蛋白3基因调节性T细胞特异性去甲基化区甲基化升高[19]。
SLE患者淋巴细胞DNA甲基化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失控激活有关。蛋白激酶C-δ(protein kinase C delta,PRKCD)的活化导致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s,ERK)减少以及DNMT1活性降低,从而导致DNA甲基化程度降低以及一些共刺激因子表达增高,这些与疾病的活动性直接相关。有研究表明,编码PRKCD基因突变是导致儿童SLE早期表现的因素之一[20]。而导致DNMT1活性降低的另一个机制是蛋白磷酸酶2A的表达增加,它能抑制ERK信号通路以及DNMT1的活性[21]。除了DNMT1活性降低,袁敏等[22]研究发现,在发病的MRtApr狼疮鼠的CD4+T淋巴细胞中,DNMT3b表达水平明显降低,CD70分子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且二者呈显著负相关,从而提出DNMT3b的低表达使得CD70启动子区域CpG岛不能充分甲基化,而导致CD70分子表达水平升高,造成T淋巴细胞功能异常而导致SLE的发病。
1.2组蛋白修饰除了DNA甲基化,翻译后的组蛋白在表观遗传水平上也能调控基因表达。在真核生物中,组蛋白是由4种核心组蛋白(H2A、H2B、H3和H4)的2个单体组成的八聚体。组蛋白八聚体形成含有染色体组DNA的复合物(147个碱基对),这些复合物被称为核小体。组蛋白修饰主要包括乙酰化、甲基化、泛素化、磷酸化、瓜氨酸、ADP-核糖基化和脯氨酸异构化等,其表观遗传标志具有高度特异性,能决定细胞和组织的表型和功能[23]。异常的组蛋白标志是导致包括SLE在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炎症紊乱的重要病理机制。组蛋白乙酰化与组蛋白H3赖氨酸4甲基化是决定分化方向的关键调节因子。在SLE患者的CD4+T细胞中,组蛋白乙酰化和组蛋白H3赖氨酸9甲基化水平都出现降低[24],也有研究发现组蛋白H3低乙酰化水平与SLE活动度有很大相关性[25]。
1.3微小RNA(microRNA,miRNA) miRNA是一类源于内源性染色体上的非蛋白编码的单链RNA,长度为19~25个核苷酸,能够与靶mRNA特异性结合,使靶mRNA降解或者抑制其翻译,从而对基因进行转录后的表达调控。成熟的miRNA能够识别靶基因发挥生物学效应[26],目前研究表明,多种miRNA参与免疫细胞分化,调控细胞因子、转录因子、凋亡基因等的表达,调节机体免疫应答,与疾病发生、发展相关[27]。miRNA参与多条信号传导通路,其在SLE中可能的发病机制有:(1)干扰素通路持续过度活化;(2)树突状细胞的持续活化;(3)DNA低甲基化;(4)细胞因子异常分泌;(5)Treg细胞的异常;(6)雌激素、病毒等其他机制[28]。
miRNA可作为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或治疗靶点,在人类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SLE、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已经发现多种miRNA 的表达改变[29-30]。研究表明,miRNA在SLE患者中存在异常表达,且与其活动性相关,其中 miRNA-21、miRNA-155、miRNA-148a、miRNA-126在活动期SLE中表达明显增加,miRNA-146a、miRNA-125a、miRNA-142-3p、miRNA-142-5p、miRNA-142s及miRNA-31表达降低[29,31-35]。而王万鹏等[36]研究发现,严重肾衰竭的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LN)患者miRNA表达下调,且miRNA-130b-3p在早期LN患者中表达增高,与LN的肾脏损害相关。TRZYBULSKA等[37]研究发现,miRNA在体液中能够稳定存在,并易于检测。这些研究都提示miRNA有可能成为SLE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miRNA还可间接影响DNA甲基化而参与SLE的表观遗传发病机制。有研究表明,miRNA-21、miRNA-148a和miRNA-29b可以通过抑制DNMT1而使DNA甲基化水平降低,引起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38]。其中,miRNA-21作用于Ras鸟苷释放蛋白1而抑制DNMT1表达,与疾病活动性相关;miRNA-148a直接抑制DNMT1表达;miRNA-29b通过作用于特异性蛋白1而对DNMT1进行负调控[38-39]。
1.4长链非编码RNA(longnoncodingRNA,lncRNA) 在非编码RNA中,除了已被证实参与SLE的发病并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的miRNA外,近年来发现,许多lncRNA在SLE的活动组和非活动组之间出现了差异表达。彭武建等[40]运用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技术筛选并得到一批SLE差异表达的lncRNA,发现SLE患者外周血中uc003ngn、uc003wbg、uc01010q、uc003wax、uc010jsn、HMllncRNAl 145等表达显著上调,ue010cik、AK022005、uc010nwn、uc0109dp、HMllncRNA678、uc010imt等表达显著下调,提示这些差异表达的lncRNA可能参与SLE疾病发生、发展的调节过程,但当时并未分析其与SLE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在此之后,lncRNA 与SLE的相关性研究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如陈兰芳等[41]研究发现,lncRNA 核富集常染色体转录物1在SLE患者中明显高表达,并与其疾病活动度呈正相关。WU等[42]研究发现,SLE患者外周血中lncRNA 0949和lncRNA0597的表达明显下调,且lncRNA0949的表达与SLE患者的疾病活动度及器官损伤程度呈负相关。
2 表观遗传学机制在SLE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2.1表观遗传位点的诊断价值研究发现,干扰素诱导蛋白44启动子中的2个CpG位点的低甲基化程度对SLE具有非常大的诊断价值,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达90%以上[43]。除此之外,炎症递质白细胞分化抗原11a、IL-6、炎症递质白细胞分化抗原40L、炎症递质白细胞分化抗原 70、IL-4、5-羟色胺1A受体和穿孔素等分子基因的启动子区域甲基化程度对SLE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价值[44-47]。
2.2表观基因组作为治疗靶点治疗SLE的传统方法包括抗疟疾药物(可用氯喹和羟氯喹)、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剂(甲氨蝶呤、霉酚酸酯、环磷酰胺)等。与恶性肿瘤治疗不同的是,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机制复杂,其表观遗传模式尚未明确,因此,表观遗传治疗策略的研究也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将表观遗传修饰作为治疗手段仍具有较大前景。2016年,HE等[48]在《Nature Medicine》发布了IL-2调控免疫平衡治疗SLE的最新成果,提出低剂量重组人IL-2能够抑制SLE患者体内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显著降低SLE的病情指标。该研究首次报道了低剂量IL-2对SLE 的治疗作用,为临床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新的理念。
2.2.1DNA甲基化在SLE的免疫调节治疗药物中,甲氨蝶呤可在DNA甲基化过程中通过消耗SAM来降低DNMT1活性[12,49];而环磷酰胺则通过诱导DNMT1的活性而增加DNA甲基化[12,50]。因此,甲氨蝶呤和环磷酰胺的表观遗传效应均可以解释其在治疗SLE过程中表现出的效果。而抑制DNA甲基化也是药物性狼疮发病机制中的一种假说,一些能够抑制ERK信号途径的药物如肼苯哒嗪、普鲁卡因酰胺等可诱发SLE,表明ERK途径缺陷通过减少DNMT1表达、调节DNA甲基化而参与药物性狼疮的发病[51]。
2.2.2组蛋白修饰由于SLE患者T细胞中组蛋白乙酰化水平降低,提示增加组蛋白乙酰化程度可能对SLE的治疗有益。早期研究表明,应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HDACI)可以通过改善MRL/lpr小鼠组蛋白低乙酰化状态而降低疾病的活动性[52]。最近研究发现,抑制Ⅰ型和Ⅱ型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HDACI ITF2357可以降低MRL/lpr小鼠体内炎性细胞因子,改善其肾脏病变[53]。但是,在癫痫患者中应用HDACI制剂丙戊酸有时会导致狼疮样症状[54]。因此,现有的表观遗传治疗因其可能出现弊大于利的不良反应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2.2.3miRNA在SLE治疗中,目前尚无特别类型miRNA阻断的相关数据报道。而在丙型病毒性肝炎和恶性肿瘤的治疗方式中,一些可被小分子靶向作用的miRNA已经进入了临床前研究阶段[55-56]。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miRNA作为靶向治疗工具也极具前景,但是,如何解决其非特异性不良反应仍是目前的主要挑战。
3 结语
SLE是一种侵犯多系统和多脏器的全身结缔组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57-58],致病机制复杂,其表观遗传学机制中主要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等[59],这3种因素并非单独作用,而是存在交叉,相互影响,如miRNA可通过抑制DNMT1降低DNA甲基化水平,组蛋白H3赖氨酸18可通过HDAC1及DNMT3a导致高甲基化[60]。SLE患者的免疫细胞存在异常的基因表达,而表观遗传失调是导致异常基因表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与表观遗传学有关的分子机制,越来越多的新生物标志物也被揭示出其与SLE及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相关的遗传倾向性[61]。SLE患者淋巴细胞具有高度特异性的表观遗传模式,因此,表观遗传学研究在寻求个体化治疗靶点及作为疾病生物标志物方面具有很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