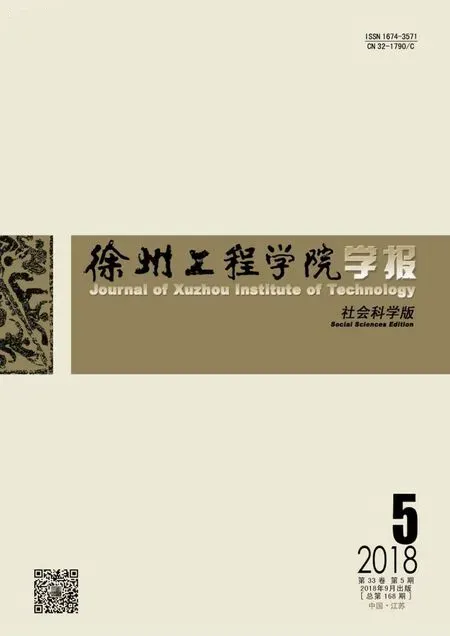革命历史叙事的“当代化”
——以《苍茫大地》为例
刘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革命历史”具有题材上的特殊性,不仅是讲述革命者如何“抛头颅洒热血”夺取政权的故事,同时还带有“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奋斗”的教化功能,在当代文学史中形成了一条绵延至今的线索。从1950-1970年代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到“新历史主义思潮”下的《灵旗》《红高粱》,革命历史的讲述方式曾经发生过沧海桑田般巨变。由于不同时间段对“革命历史”的理解视角不同,这个当代文学史中的“叙事母题”呈现出多变特征。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当代化”的脚步一如既往,《亮剑》《历史的天空》《延安爱情》等作品表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不同质素,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这一波作品还缺乏精准定位。本文拟以张新科的《苍茫大地》为例,关注、分析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叙事“当代化”中的新动向。
一
虽然“革命”是革命历史叙述的关键词,但对“革命”本质的叙述却在当代文学中不断变化,甚至发生阐释上的“不兼容”现象。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具有毫无争议的正义性。《红旗谱》中的朱老巩为穷乡亲出头,大闹柳树林,死前留下遗言说与地主老财“势不两立”,将复仇与革命合一,而且作为“遗产”传之后人。《红日》开端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双方都携带了历史定论的基因。以“革命”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中,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个人、民族和国家从受压迫到获得解放,迈入一个理想的人类生存境界,是毫无疑问的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由于上述阐释方式与20世纪中国历史具有“互文”关系,故而得到推崇,并在1950-1970年达到登峰造极程度,摒弃了任何质疑及其他历史阐述的可能性。1980年代,一元化的“革命历史叙述”呈现出捉襟见肘的一面,此前边缘化、被遮蔽的历史随着学术的发掘及阐释空间的松动而得到显露,暗合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历史书写”的认知[1]。《灵旗》《红高粱》等作品仍然是叙述“革命历史”,但是重心相比1950-1970年代,已经发生了偏移。两部作品都使用了“后设视角”,从“当代”和“个人”的角度回溯“革命历史”,因此,此前的“湘江战役”“抗日战斗”叙述中不被关照的内容浮出水面,历史阐释不再定于一尊,也开拓了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叙述新局面。“为了女人而当了红军逃兵”(《灵旗》)和“土匪为复仇抗日”(《红高粱》)的情节设置颠覆了此前“革命历史”叙述一元化时期对革命起源和过程的讲述,在发现新的叙事空间的同时,也“告别革命”,解构了宏大叙事。在新世纪,“革命历史”叙述仍然不断发展,出现了再次“回归革命”,“重述”“革命历史”的现象。不过,讲故事的人与故事的讲法,都已经发生了变化。1950-1970年代历史的讲述者通常都有革命亲身经历,因此带有胜利者的自豪感;新世纪的作家不再是当年历史的参与者,故而,他们拉开了时间距离,采取了追忆、回溯视角。随之,叙述理念也从高亢大声地论述“历史的必然性”转变为幽暗深入地探索革命者的内心。
在上述文学史背景下,《苍茫大地》出现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当代”如何理解“革命”。在被“新历史主义”拆毁的瓦砾中,能否重建被信任的有关“革命”的可能?采取宏观理论的宣讲方式显然已经过时且令人反感,专门从事解构又无法建立起符合历史潮流的叙事,因此出现了对革命“初始化”情境的“还原”思路。“人性”这个新时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尺度,介入到理解革命者心态,被运用到了对“革命”问题的重新阐释中。《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参加革命的目的“不纯”,本来想到国民党那里发财,阴差阳错遇到了共产党游击队;《亮剑》中的李云龙经常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根本无视党的领导,这些“瑕疵”并不影响他们最终历练为革命者,反而比那些刻板、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更有血有肉,符合人性。在这里,“革命”并非抽象的名词,也不是后来被添加了诸多预设内容的理念,而是从生活本源中生发出的人的关于自我的超越要求。张新科显然认同了这个理念,他把人物置放在具体而微的叙述中,不带先验情绪,回归到“人”的感情深处,寻求革命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朴实自然而又真切动人,丰富了当前文学作品对“革命者”的认知。
《苍茫大地》聚焦的是一个神秘的、被历史湮没了几十年的人物。《苍茫大地》开端是一个引子,一位76岁的老人叶瑛寻找自己失踪53年的丈夫,从而牵连出一个与法国求学时的朱德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的男人的故事。1950-1970年代的作者讲述革命历史时一般不区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因为当时历史和现实之间是无缝对接的状态,作者是亲历而不是追溯,更不需要依据史料考证。《苍茫大地》借用引子提醒读者,写作故事的年代已经与故事的发生年代具有了一段差距。无疑,这个发生在“当代”的引子不再像以往的革命叙事一样指向未来,而是带有回溯和反思的视角。“这个男人是谁”“为何到现在被提起”等带有噱头的问题中,隐藏着有关革命的“起源”问题,也包含多年后的反省。在“革命考古学”的视角中,“重述革命史”的工作,就在疑问中开始。
与以往的叙述总是把革命者设定为无产阶级不同,早期共产党人许子鹤虽然在广东长大,但父母是南洋商人,因此生活优渥的他在参加革命前的人生一帆风顺。在《苍茫大地》中,许子鹤完成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轨迹:倾向、同情革命,入党,领导革命斗争,最终献出生命。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此履历的不在少数。但是,为何许子鹤却在1927年后销声匿迹,直到19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还不知所踪呢?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对象。《苍茫大地》详细讲述了许子鹤与“革命”发生关系的机缘,将许子鹤的人生经历与宏阔历史背景结合,尤其是将许子鹤思想放在了近代转型的时空中,因此,他的上下求索就与民族国家的“寻路”过程合二为一。
许子鹤生在南洋,后被父母送回广东老家,跟父亲并未迎娶的童养媳——他叫她“大娘”长大。为了回报大娘对自己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许子鹤发誓好好学习出人头地。刚开始读书时,许子鹤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其学习的目的是朴素的“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并无大志,这与他的年龄、思考有关,也说明革命者并非天生,而是逐渐从生活经历中获得革命信仰。本来许子鹤的专业是数学,但是他受到革命引路人恽长君的鼓舞:“你学数学,数字失去了规律,失去了公理,失去了正确排列与组合,就是一群杂乱无章且毫无意义的数字!那么,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领地,她的人民就会脖架钢刀,身披枷锁,变成无巢之流莺,无穴之奔兔,无渊之枯鱼。”[2]在王纲解纽的20世纪初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声音战胜了专业治学,许子鹤性格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发挥。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在山河破碎、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的时刻,不能不被抛之脑后。《苍茫大地》借恽长君的来信问许子鹤:“请问,中华的光明在哪里?绝不在洋人列强那里,绝不在北洋政府那里!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黑暗,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冲刷耻辱,民族复兴的朝阳才能在中华大地上喷薄而出,冉冉升起,才会金光普照,滋润万物。”(第45页)如此气势磅礴的宣言,怎么能不鼓动起一位跃动着爱国情怀的少年的心呢?实际上,作品中的群情激奋的氛围并非生造,当时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名言,早已在北大青年学生中流传甚广。因此,从追求生命的完善角度上讲,许子鹤主动选择革命道路顺理成章,《苍茫大地》用朴素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革命”与“救中国”“为人民”一体,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
二
对革命历史小说来说,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涉及知识分子形象问题,就复杂得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作家开始有所转型,将书写的目光聚焦工农兵,《铜墙铁壁》《高干大》等作品相继问世,一批工农兵人物前所未有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49年后,书写工农兵得到提倡,一时成为风潮,此不赘述。相对来说,知识分子的角色有点尴尬,他们在革命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在文本中却很少成为主角。《红旗谱》中的贾湘农、《敌后武工队》中的李正都是知识分子,实际上起着领导革命的作用,但是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语境下,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在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虽然几经讨论,但是并未得到根本变化。在新时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中,此前被遮蔽的历史细节被“打捞”并成为叙述核心,但是本来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仍旧被疏忽。在《白鹿原》这部深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品中,具有传统知识分子风范的“一代大儒”朱先生始终控制着白鹿原上人们的思维心理,而鹿兆鹏、白灵等早期共产党员的活动和思想虽然深刻影响着白鹿原历史走向,但仍然概念化,缺乏更为生动鲜活的记叙。因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因,在早期革命理论传播和建党等工作中起到了重要影响的具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却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阐述,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
相比较起来,新世纪革命历史叙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悄然改变。《亮剑》中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赵刚开始不被草莽英雄李云龙重视,但他以人格魅力和知识水平折服了对方,使李云龙不得不表示对知识分子的敬畏。不过总的来说,赵刚仍然是一个敲边鼓和衬托性的角色,是作品对大众文化趣味的迁就。《延安爱情》中的辅仁大学学生、富家子弟彭登科追随参加革命的同学苏贞来到延安,虽然是一代人经历的写照,但知识分子与革命间的关系仍属被动。《苍茫大地》则扭转了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次要、被动的地位,许子鹤一直是作为男一号而存在,也因之牵引出此前作品中少见的早期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就人物形象来说,《苍茫大地》选取的许子鹤的形象是以往文学史未曾着力描写过的,也是文学与史学成果互动的结果,是革命历史叙事“当代化”的重要表征。许子鹤的原型许包野是雨花台烈士,小说中的留学德国、领导地方党组织斗争等情节均来自人物传记[3]。许包野是早期旅欧支部的共产党员,获得过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厦门、河南、江苏领导过地下斗争,他的人生和革命经历本身具有传奇性,本来早就应该受到重视,但意义一直未被充分发掘。张新科选择许包野为书写对象,本身有拓展题材领域,深化革命历史叙述的意义。将许包野烈士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当然需要文学化的剪裁和点染,张新科站在“当代”的视角,给予了独创性的思考和写作。张新科不是单纯按照许包野的履历来结撰作品,而是把他放在激荡的历史风云中,细致描摹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以文学家的眼光考察革命烈士的心路历程。由此,《苍茫大地》成为鲜见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书写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进行革命斗争的作品,这个变化体现出作者张新科别具只眼的史识、文笔。
《苍茫大地》恢复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初期的地位,揭示出以前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影影绰绰并未得到明确表达的事实[4]。《苍茫大地》重要的意义在于,塑造了一群在历史转型期苦苦寻找民族出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以拯救国家危难为己任,正是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到现代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是广为人知的说法,但是如果没有早期知识分子的译介,革命的主体工农兵又怎么能够了解和接受呢?没有早期知识分子的传播和将苏联革命模式引入中国,中国革命的“起点”难以想象。也可以说,《苍茫大地》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了以往“革命历史叙事”忽略的“革命前史”。作品中专门安排了一个章节来叙述许子鹤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革命理论。许子鹤此前因为民族立场而同情革命,但是并没有充分接触到革命理论,因此想法和思考都是自发的。通过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尤其是与伊万诺夫教授的切磋讨论,许子鹤理解了马克思“个人解放”的解释。由此,许子鹤成为一个革命的“发动者”,因为他充分掌握了革命理论并怀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在这里,许子鹤已经进入了追求真理并付诸实践的阶段,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使命感的“新人”。在描写这个过程时,《苍茫大地》没有进行纯理论化的演绎,因为那样会使人物僵化为思想的傀儡。伊万诺夫给离开苏联回国的许子鹤的临别赠言是:“搏击长空的一只东方雄鹰,既然不能在高加索上空翱翔,不能在伏尔加河流域徜徉,那就回到古老的辽阔的苦难故乡去吧,用你的天赋之魂、锐眼利爪,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匡扶正义,造福人间吧!”(第135页)这样励志的语言并不复杂,但是对于不断追求理想,急于报效祖国的许子鹤来说,正中下怀。慷慨悲壮、雄姿勃发的主人公,由此成为一个具有超越境界的甘愿为情怀而牺牲的现代的“人”,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动力。《苍茫大地》封面上引用了亚历山大·仲马的诗句“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最值得的愿望啊!”,突兀来看会令人觉得过于激进,但放回到历史场景中,并非不可理解。此前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不乏将革命作为信仰的工农兵革命者,他们的激情也往往被归纳为阶级出身,但是《苍茫大地》补充了知识分子通过理性思考的历史事实,一直追寻到了他们“为何富于牺牲精神”的源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苍茫大地》描写的知识分子不仅局限于许子鹤一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历史转折期的思考和应对,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救国/启蒙”道路的寻求汇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坚韧、奉献的民族伟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他们用澎湃的激情和血肉之躯为民族文化注入强心剂,这种令人血脉贲张的场景再没有重来,而这也许是张新科创作《苍茫大地》的原因。1950年代的《青春之歌》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景:“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们。但是随着人群激昂的呼喊,随着雪片似的漫天飞舞的传单,随着刽子手们的大刀皮鞭的肆凶,这清一色的队伍渐渐变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兵士,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都陆续涌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来了。他们接过了学生递给他们的旗子,仿佛开赴前线的士兵,忘掉了个人的安危,毅然和学生们扣起手来。”[5]这段描写可以视为早期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的隐喻。青年知识分子也在产生分裂:卢嘉川、江华出场时就是坚定的革命者,余永泽的理想则是一个大学教授,王晓燕从静观转向革命,戴愉叛变。无疑,许子鹤正是当年卢嘉川等革命者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复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在风云激荡的时刻,才能够看出许子鹤的选择的艰难与准确。
小说中次要人物许子鹤的同学、旧友的人生选择,正与他相呼应,共同完成了时代风潮中的“人各有志”。许子鹤和王全道是旅德同学,当时感情甚笃,水性出色,许子鹤还曾经救过不会游泳的王全道一命。回国后,不同的人生追求令他俩分道扬镳,并阴差阳错成为各自的劲敌。许子鹤被俘后,面对“许博士是个学问人,我建议不要在政治上争个你长我短了,去做学问吧,政府几所大学还缺校长呢!”(第433页)之类的劝降,统统拒绝,就是因为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固有的“为生民请命”“九死未悔”的理想自然地附着在了许子鹤身上,形成“当代化”的契合,《苍茫大地》也因此完成了作为革命者的许子鹤与“传统人格”的对接。
三
从小说中可以感受到,许子鹤智商超常,性格坚毅,常能以出人意料的方法完成艰巨任务,是一位似曾相识却又标新立异的传奇英雄,这正是《苍茫大地》贡献给文学史的“新”的人物。在革命历史小说写作史中,传奇性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招牌,《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等1950-1970年代的作品都有一个与通俗演义故事相似的外壳。其中,“智取威虎山”“肖飞买药”“刘洪扒火车”等情节紧张曲折,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杨子荣、肖飞、刘洪、李向阳、小兵张嘎等形象生动活跃,深入人心。在“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作为“补史”的传奇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余占鳌(《红高粱》)、黑娃(《白鹿原》)等土匪大行其道,改变了革命历史叙事的人物生态。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叙述的传奇特征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如鱼得水,一批生龙活虎的传奇英雄被塑造出来。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既有革命者为事业英勇奋斗的一面,同时个性明显,具有戏剧张力,适合影视剧传播,表现出革命英雄的“新样态”。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过于追求情节的离奇和人物的“有戏”,革命历史叙述经常被研究者归类到通俗文艺的分支,反而削弱了作品的严肃性。张新科构撰许子鹤人物形象时,沿袭了传奇化倾向,同时对原型进行了加工,关注了以往作品中很少接触到的革命者“起源”问题。如果说以往的革命者的“传奇”是革命事迹的话,许子鹤留下传奇则是精神归属的哲学问题,更为耐人寻味,正如封底所追问:“一个富家子弟,一个人中龙凤的留德博士,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及荣华富贵的前程,走上一条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路?一个智力超群的数学天才,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谱写出怎样的传奇篇章?”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段,许子鹤的传奇不是革命集体中的,而是带有不可复制的个人性。
与以往革命历史叙事大多强调主人公“苦大仇深”,以便阶级站队不同,张新科塑造许子鹤时,着力渲染他智力超群。被逼无奈、反抗压迫固然是很多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但其中也隐藏着为了“活命”而革命的逻辑,而早期革命者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考察一下早期革命者,《苍茫大地》中许子鹤出于“热爱革命”而参加革命的经历才是大多数,他们并非为了个人在现实中名利,纯粹是为了造福更多人的理想——这种带有宗教情怀的心理,因为与革命理论有所龃龉,并不被后来的书写者所重视。许子鹤学业优异,有多条辉煌的人生道路供他选择,而他经过比较毅然参加革命,更能凸显出革命理论的强大感召力。作品多次描写许子鹤过目不忘的天赋,将其打造为一个“最强大脑”,与以往传奇英雄迥然不同。许子鹤是学习天才,尤其有数学天赋,北大毕业后又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因此,许子鹤选择革命就不是偶然的,“他看任何书都会像读数学书一样,一是要弄懂‘书理’,也就是书中的规律和逻辑,二是要通过阅读,回答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有关共产主义的真正目标,是萦绕在许子鹤头脑中很长时间的问题,他在北京大学时就曾思考过,但他那时没做深究。很快,许子鹤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第77页)如同数学运算一般,数学博士许子鹤坚定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利他”和超越的,不为普通他人所理解,因此才更为罕见和珍贵。
许子鹤的爱情故事同样与众不同。革命家既然献身于事业,当然就无法兼顾到爱情,因此革命历史叙述中的爱情往往被残忍排除。在这个革命和恋爱纠结了一个世纪的叙事线索中,难以有两全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自身魔咒。回看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尽管《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和“小白鸽”的故事很动人,但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遮掩暧昧。《灵旗》等“新历史主义思潮”中的爱情,常常是为了解构革命话语长期的霸权,因而显得张扬乖戾。到了新世纪,武歆的《延安爱情》《北平爱情》“报复性”地大肆演绎了“革命+恋爱”这条革命历史叙事中从未被正视过的线索,将“爱情”与“革命”的关系做了颠倒。在《苍茫大地》中,许子鹤的爱情纯真美好,但他为了革命事业毅然放弃,让人在扼腕时生出无限敬仰。许子鹤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了导师的女儿克劳迪娅,并赢得姑娘芳心,但是由于家中已经为他定了亲,故而两人无法相爱。许子鹤回国后,痴情的克劳迪娅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救他于危难,但许子鹤始终没有接受她的爱情。克劳迪娅深爱许子鹤,终身未婚,“这跨越两大洲和六秩光阴的爱恋不单昭示了克劳迪娅海一样深的情愫,更见证了一位殉道者从未屈服的灵魂”。(第445页)从写作技术来看,许子鹤的革命道路漫长艰辛,当然不能携带一名洋妻子,这是故事发展的需要,但正是“隐而未发”的状态,让许子鹤的人生更加充满传奇意味。许子鹤与叶瑛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感情甚笃,因为许子鹤参加革命的原因,两人聚少离多。叶瑛在许子鹤“失踪”(因为地下工作而无法与她保持联系)后独自带大孩子,锲而不舍地寻找,终于在四十多年后才得知丈夫人生历史真相。以悲剧而告终,许子鹤的爱情如同他的数次出人意料转折的一生,终成遥不可及的传奇。革命的浪漫总是要以爱情的凄美结果为代价,在革命者高大的形象背后,注定有爱他的女性的无尽泪水和伤心往事。
由于工作需要,许子鹤多次以传奇般手法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而这也是《苍茫大地》的主体部分。在系列故事中,作者借鉴了推理小说的写法,紧张刺激、悬疑跌宕,将许子鹤机智冷静、思维缜密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查出并处决叛徒徐凤山的过程中,“王全道、熊昌襄针对徐凤山的藏匿地点设了一明一暗两招棋。许子鹤决定将计就计,也对应布下一明一暗两个局。双方不同的是,王全道、熊昌襄把力量用在‘明棋’档案室上,而许子鹤表面上盯着‘明棋’,实际上,他要集中全部人马寻找未知的‘暗棋’所在。”(第358页)最终,许子鹤运用超常智慧,推理出了叛徒的位置,并用化学知识将其毒杀,漂亮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另外,许子鹤还策划执行了营救谢方理、烧毁运载档案卡车等行动,动感十足,引人入胜,完全可以作为动作大片的脚本。
作为长篇小说,《苍茫大地》当然也存在议论过多、细节需要更精致等瑕疵,但重要的是,早期传奇革命者许包野已经从雨花台烈士转换为文学形象许子鹤,他的生命力将随着作品得到更广泛扩张。其中,刚健雄强的民族活力,以及人性中对崇高、牺牲的追求和赞美,则是许包野、许子鹤两个人物承载的更大的话题,而这也是直到今天“革命历史”仍然具有魅力、被反复叙述的主要因素。
小结
20世纪中国有着阐释空间广袤的文学富矿“革命历史”,而如何将其编码到作品中,却随着对革命的认识深入不断发生变化。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每位涉足其中的作家在时代风潮和个人心性的促使下,都会交出个性化的答卷。“变”中有“常”的是,在历史中总有为了民众理想忘我的奋斗者,他们作为“民族的脊梁”理应得到后世的铭记。在作家和读者已经远离历史现场的“当代”,《苍茫大地》以情怀为出发点,向怀抱理想并为之牺牲的革命者表达了敬意,也为革命历史叙述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