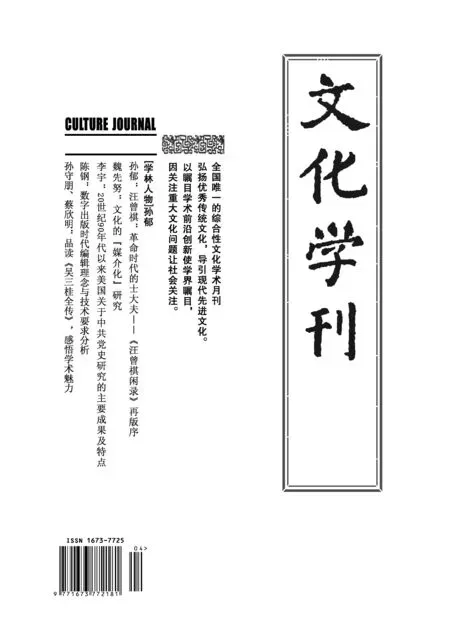骚体的早期演变及《文选》选录标准
李篮玉(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对中国文学的众多文体都产生过影响。虽然骚体文学的地位从未被质疑过,但是关于它的分类问题,众家各执一词。《文选》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对骚体文学有着开创性的认识,对后世的文体分类有很强的借鉴、研究意义。所以本文除了梳理从汉至南北朝时期对“骚”的认识的演变外,将重点谈论《文选》对楚骚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楚辞的独特性,还对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一、骚体的演变
《说文解字》:“骚,扰也。一曰摩马。”《说文解字注》进一步阐释:“摩马如今人之刷马,引伸之义为骚动……此于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曰犹。”由此可知,“骚”字从“刷马”这一动词意义引申出“骚动”“忧虑”等义项。
自屈原的《离骚》产生以来,对“离骚”的释义便层出不穷。司马迁最先对“离骚”进行解释:“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后,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写道:“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再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题:“离,别也;骚,愁也。”虽然对“离骚”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基本都承认“骚”所包含的愁思、苦闷之意,这很符合骚体文学的感情基调。
清人王兆芳便认为古代文章的文体名称常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的篇名相关联。《离骚》便具备用其篇名为其文体命名的影响力。《文心雕龙·时序》总结:“爰自汉室,迄于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考虑到楚辞本身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所以刘勰与萧统为之在“赋”之外另立“骚”。
虽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被后世文人所赞赏、吸收借鉴,但是楚骚体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汉书·艺文志》与《七略》都没有“楚辞”或“骚”类,而是设有“诗赋”类,将楚辞归入诗赋之中。在汉代,人们还经常将“辞”“赋”并用,比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会景帝不好辞赋。”《汉书·王褒传》:“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到了东汉末年,王逸注意到“骚”的独立性,将“骚”与其他文体分开,用以专指屈原的作品。在《楚辞章句》中,他将屈原的作品称为“离骚”,将《离骚》奉为《离骚经》。虽然王逸注意区分“骚”与“赋”,但是他仍将一些汉代文人的楚辞作品称为“赋”,所以对“辞”与“赋”还是没有严格地区分。到了魏晋时期,人们继承汉朝的看法,仍把“辞”与“赋”连称。如曹丕《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再如左思《咏史诗》:“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意识觉醒,文体意识增强。这时期的孔逭最早将“骚”与“赋”分为两个文体。据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孔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目录。”虽然“骚”成为独立的文体,可是屈原的作品并未被收录在“骚”类中。随后,梁人阮孝绪第一次将“楚辞”作为图书目录种类,编于别集、总集之前,据记载《七录·文集录》云:“文集录内篇四:楚辞、别集、总集、杂文。”这一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颇深。虽然楚辞独成一类,但是这并不等于“骚”成为独立的文体。真正将“骚”与“赋”进行实质性区分的是《文心雕龙》与《文选》。《文心雕龙》于《诠赋》篇外另设《辨骚》篇,并将其作为“文之枢纽”的一部分。但是刘勰更多的是强调楚辞的情感、体式等方面,对于其文体的独立性仍未进行彻底的区分。相较之下,《文选》对“骚”“辞”“赋”三体的分类更彻底。在“骚”类下,《文选》选录屈原、宋玉与刘安的作品,而在“赋”类又选录了楚辞代表人物宋玉的作品,这就将“骚”与“赋”明确区分开。在后面又立“辞”一类,这便将“骚”与“辞”分开。“骚”既不归于“赋”又不归于“诗”,而又与“辞”彻底分开,这种文体分类方法反映了萧统独特的文体观以及他肯定楚骚文学异于诗赋的独特性。
二、《文选》对骚体作品的选录标准
《文选》的骚类下选录屈原、宋玉与刘安等三位诗人共17篇作品,其中屈原选录10首,宋玉6首,刘安1首。从选录的年代来看,正好反映了开创(屈原)、继承(宋玉)、发展(西汉刘安)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萧统对文学持有一种发展观。《文选序》云:“盖踵其事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2]”这是将自然现象推演到文学创作之中,表达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与萧统选录的标准相符。
南朝的文学有一股浮靡之风,针对这种过于看重辞藻的华丽而忽视内容与情感的现象,萧统很强调“文”与“质”的关系,即不仅要有文采,还要保证言而有物。《文选序》记述:“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3]”屈原忠君爱国、洁身自好的高贵品格是萧统选录屈原将近一半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离骚》正因为兼备文质,所以才会在南朝时期继续被奉以“骚经”之名,也反映了南朝时期很重视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文学。
在所选作品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选录了《卜居》与《渔父》两篇作品。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用骚体文学的一个鲜明标志——“兮”字,所以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骚体作品。但是《文选》仍然选入这两篇,说明比起形式,萧统更注重作品的内容与情感,尤其是楚辞独特的哀志伤怀的抒情特征。从未被选入的作品也同样可以看出这一选录标准。比如《橘颂》,这篇作品是屈原早期的代表作,这时或正准备入仕途,或在仕途上意气风发。全诗虽然同样抒发了作者的情感,但是整体洋溢着积极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格调,刚好与《离骚》所奠定的哀婉风格相反,因此没有被选录。再如《天问》,虽然全诗一问到底,气势磅礴,但总体上是在问自然与人事之道,抒情并未占主要成分,再加上不符合骚体的形式,因此也未被入选。
《文选》在选文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厚今薄古”的选文倾向。那么为何在骚类下只选录了离南北朝较远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作品,而未选任何汉朝中后期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骚体文学作品呢?这与汉以后的文学创作环境有很大关系。自两汉开始,虽然文人吸取楚骚的特点进行骚体文学创作,并以此发展出新的文体——赋,然而由于经学化阐释的繁复性与毫无创新的摹仿性,“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4]”(《文心雕龙·诠赋》),使得汉赋走向灭亡,未能延续下来。与赋体相近的骚体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使得创作内容难以与屈原与宋玉媲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越来越注重辞藻的华丽、形式的反复,内容反而越发地空洞无物,情感也趋于无病呻吟。所以即使是厚古薄今,也没有选任何“今”之骚文。
虽然萧统很看重内容与情感的抒发,但在南朝主流的文学审美影响下,他在选录过程中依然将文采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骚体文学本身就具备文采赡丽的特征,其作品大多都“耀艳深华”“辞采绝艳”,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南朝文人重文采的审美情趣,甚至将其作为文学新变的参照与动力。
萧统尊崇儒家思想,再加上他的太子身份,所以《文选》中的作品需要具备儒家的“风雅之道”。儒家提倡文学作品的功利性,强调其社会功用。从“讽谏”“教化”的角度来看,屈原的作品揭露了黑暗的现实,明确了自己忠贞不渝的志向。这为文学创作树立了榜样,又有助于让读者意识到华美的文辞、真挚的感情与内容的讽化性都很重要。
骚体始自屈原,由宋玉、景差、唐勒等人传承下去。由于骚体的形式与赋体接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者被视作一种体裁。直到南北朝时期,梁人阮孝绪第一次将“楚辞”单独设为一种图书目录种类,而刘勰与萧统也分别在《文心雕龙》与《文选》中注意将“骚”与“赋”分开。刘勰将“辨骚”一文当作“文之枢纽”,给予骚体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萧统等人通过《文选》的选录来表现对优秀骚体作品的衡量标准,可简单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具备哀志伤怀的感情基调;二是文质兼备;三是具备社会教化功能。
[1][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3]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