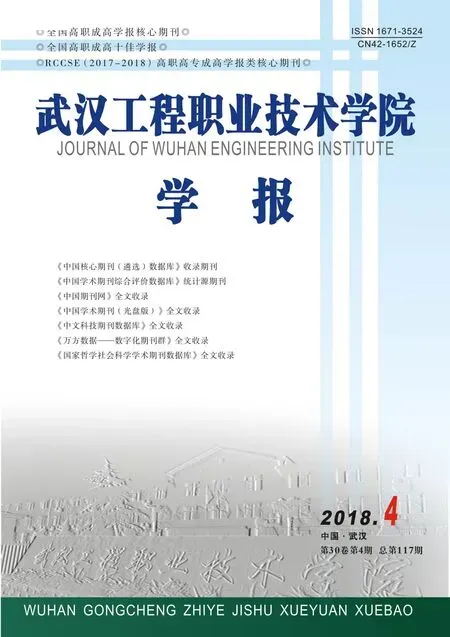杜甫诗歌特殊对仗形式分类举隅
纪孟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650500)
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他一生作品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技巧纯熟。杜诗尤善七律,众所周知,律诗非常看重诗句对仗,特别是颔、颈二联,要求严苛,须对仗工稳,方能为诗作增色。不止律诗,五七言绝句中对仗规则也十分整肃。杜诗对仗,多细细研磨,精心雕琢之句,足以体现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创作风格。杜甫曾在诗中自述:“更得清新否?遥知对属忙。”(《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显然,他一直在对仗方面苦下功夫,不停研究,不断创新并且颇有成效。在他的近体诗中,对仗时的句法结构十分灵活。本文仅列举几种特殊对仗形式,一窥杜甫诗歌对仗形式多样之风采。
1 借音对与借义对
借音是利用同音字来造成对仗,借义是利用一词多义来造成的对仗。借音对和借义对在对仗中合称“借对”,“借对”又叫“假对”,是借别的字的字音或字义来进行对仗的一种方式。在借对中,经常会使用典故、歧义,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迷惑后,带给人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奇感受,取得豁然开朗的审美效果。
1.1 借音对
借音对,作为一种特殊的对仗形式,又可以称为声对。在两个句子里面,如果它们相对的词语在意思上没有关联,表面看起来不能相对时,恰巧有一个字的字音能找到和其同音的字来与另一字相对,那么也可以算是一种工对。
且看例句:“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轻。”(《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三)。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提及同类的词对仗,应特别注意:颜色自成一类;数词自成一类;方位自成一类的规则,“珠”字与“白”字不能相对。而此处杜甫是使“珠”借“朱”之音来与“白”字相对,如是,便符合了颜色名词互对的道理。
再来看杜甫的《独坐》:“沧溟服衰谢,朱绂负平生。”如上一例,遵循颜色相对来看,明显“沧”字是借“苍”之音来与“朱”相对。杜甫在《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中的“东郭沧江水,西山白雪高”亦效此法。
1.2 借义对
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一书中对“借义”对做了如下解释:“一个词有两个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来与另一词相为对仗,这叫借对。”[2]这种借对,实际上是指“借义对”。借义对往往因为一字两用,所以在表现诗句内容同时,又可以取得对仗工整的效果,在诗句和楹联的运用中都显得十分经济,言约词丰。
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是我们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就学到过并且非常熟悉的诗歌,在其中就有明显的借义对示例。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3]杜甫在挥毫写下这两句诗时,正是在羁旅途中偶遇李龟年,回首往事心生感慨。出句的“寻常”或是作“普通、一般”讲,断然不能与对句的“几度”相对。然而,“寻常”这个词,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为“平常”,在这里明显不是取它常见的释义,而是把“寻常”作为古代的长度单位来与数词 “七十”相对,这样巧妙借义就化解了表意与对仗规则的矛盾。
在《曲江二首(其二)》中有名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诗人典去春衣换酒钱,处处欠下酒债,其原因就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把酒当歌,在追求及时行乐的 同时,又融入国家兴衰与自身命运的感叹。这里的“寻常”亦是借义来与“七十”相对。
在《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中,杜甫更是妙绝,因为“行李”中“李”字有“桃李”的“李”之义,所以就借之来与下句的“茅”相对,因有“行李淹吾舅,诛茅问老翁”之句,李树对茅草,岂不别有风味?
杜甫对仗,体格不拘,手法多样,纵横驰骋,运用自如。从上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到,杜甫那个时代,对于借对的使用,还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但借对一格并没有很好的继承和使用至今。究其原因,从后人对借对的看法与评述中可以略知一二。俞弁在《逸老堂诗话》中说道:“唐人多此格,何以穿凿为哉。”我们可以从其言语中读出他对借对完全持有一种赞赏认同的态度。但是,也有后人借口工整,进而加以指责。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认为借对是“穿凿可厌” 之举,《蔡宽夫诗话》中语气更为不屑,讽刺借对为“痴人说梦”。所以明清以来,很少再有诗人在诗中使用借对。
2 当句对与隔句对
当句对和隔句对是非常有趣的两种对仗形式。当句对不但是出句与对句相对,而且出句与对句本身句中有对。隔句对则是一联出句与对句并不相对,而是两联之中出句与出句对,对句与对句对。
2.1 当句对
当句对,作为一种特殊的对仗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对偶修辞。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对偶的两句中,既有本句自对,又有两句互对。当然,两句相对是对仗最基本的要求,而本句自对就是其独特之处。由于本句自对造成一种优雅的停顿,衬以两句互对的节奏,在朗读中自然流露出属于对仗的那一份形式美。关于这种对仗形式,《瀛奎律髓汇评》有云:“句中各自为对,即就句对,一名当句对,此诗家常格”。[4]
在杜甫之先,就有诗人追求这种独特的对仗形式,在诗文中使用当句对。在诗歌中,当句对经常在五律中得到运用。杜甫接触到这种对仗形式,便格外钟情于它。从数量上看,杜甫在一生的创作中,只使用了八次当句对。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把当句对运用到七律中的人,而且运用的巧妙得体,浑然天成。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自杜甫《白帝》一诗。“戎马”与“归马”,“千家”与“百家”都是当句自对的表现。杜甫诗歌一直擅长用概括的话语来反映恢弘的场面或深刻的社会悲剧。在这首诗中,战争惨烈、十室九空的悲剧场面用短短两句诗就反映出来,对比明显,用法高超。这种当句对与杜甫在曲江所作的《曲江对酒》一诗中的“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有异曲同工之妙。桃花杨花争相斗艳,黄鸟白鸟颉颃而飞。落英相逐,透露出花之娇媚,飞鸟蹁跹,展现出鸟之欢欣,精妙传神,字里行间也流溢出诗人闲暇愉悦,醉心自然的心情。
2.2 隔句对
隔句对,往往是四句诗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对仗形式特殊在它打破了对仗中出句与对句形成对仗的常式,采用第一句与第三句相对,余下的第二句与第四句相对的变式。单单只看前两句,貌似未用对仗,不合标准。但当你结合整体来看,却能形成工整的对仗。隔句对往往能翻新意,初读时觉得平平,渐渐就能感觉到诗人别出心裁的安排,细细想来有枯木茂秀之感。古人称这种对仗为扇面对,当古人把隔句对以两句一行的形式写在扇折上时,随着扇面的舒展,首先映入眼帘的必是一三句,其次是二四句。这就很好解释这种对仗形式的独特性,也能很好解释隔句对为什么会有“扇面对”这一高雅的别名了。
杜甫诗歌中关于扇面对的例子本就不多,这里笔者从《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一诗中节选了四句,如下:“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按照常规,四句本当两两相对,实则不然。细细看来,“得罪台州去”与“移官蓬阁后”正好相对,与此同时,“时危弃硕儒”也和“谷贵殁潜夫”恰好对上。很显然,这便符合了前面所说的隔句对的要求。
3 叠音对与列锦对
叠音和列锦,也是诗歌对仗常用的一种方法。叠音是同音字的重叠,列锦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罗列。与列锦相比,叠音最适合用来表达缠绵的情致和舒缓的节奏,而列锦往往在有限的话语中蕴藉着可谓无限的韵外之韵,味外之味。
3.1 叠音对
叠音对,是指在对仗时,在相对的位置上均有叠词出现,词语的重复形成连珠的态势,因此它又叫做“连珠对”。叠音对两字相叠,读音相同,给人朗朗上口之感。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诗中叠字最难下,唯少陵用之独工。”[5]一个“独”字,就可以体味到杨慎对杜甫叠音对的使用的高度赞誉。据统计,杜甫一生创作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用叠字修辞的诗有三百多首,可见叠字、叠音、叠音对在他诗歌中的分量。这里不对这种对仗形式的本身作更多的分析,而是专注于这种对仗形式带来的独特韵味和效果。
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之二)》)蛱蝶深深隐于花丛,蜻蜓款款游于水上。两个叠音词相对,点出了当时蛱蝶与蜻蜓不同的动态,生动有趣。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对这两句诗的评价很高:“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气格超胜。”[6]今人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对这叠音之词也道出自己的独特体会:“其所写之深深、款款,却使人读起来……正自有无限爱惜之意”。[7]
再来看“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之三)》)暮年杜甫寓居夔州而作。燕子展翅,渔人泛舟,本是状平常之景。句中却将“泛”这个动词叠用,绘信宿的渔人,不顾疲倦,依旧从容泛舟。“飞”也按对仗的要求叠用,状清秋的燕子,不在乎时之凄凄,依旧频繁飞翔。
3.2 列锦对
列锦对,又名“叠句对”。列锦对有很强的辨识度,因为这种对仗的句子中有且只有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列锦对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相继陈列,华丽优美,就如同一匹匹锦缎,让人应接不暇。这种名词的叠加,展现出几组看似无关实则可以相互联系的画面,形成一种流动感,读者往往要加以联想和想象,才能参透画面纵深处的阔大意境,体会到凝练、简远和含蓄的美感。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列锦对的难度比较大,那些陈列的名词,看似没有逻辑联系,实则以情相连,处处透露着诗人别出心裁的推敲和安排,表现出诗人的匠心独运和汉字魅力的至高玄机。
“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是杜甫诗歌《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中的句子。
日月为笼,苍生不过笼中之鸟,困兽而斗;乾坤为水,万物无非水上飘萍,身世浮沉。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援喻设譬,由物及人,感慨人生短暂无常,自身渺小无依。“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都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整个诗句虽构不成因果,可诗人在喟叹时却给人一种浑然圆润的感觉。
4 交络对与流水对
把交络对和流水对列为一组,是因为两者都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对仗形式,属于对仗的一种变格。一般的对仗,都是出句与对句相同位置上的词语相对,而且如果不考虑平仄相对相粘,出句与对句可以颠倒顺序。而交络对则是不同位置上的词语交错相对,流水对则是有先有后,不能前后颠倒句子顺序。
4.1 交络对
《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关于交络对有如下描述:“第十九,交络对。赋诗曰‘出入三代,五百余载’。‘三代’与‘五百’即交络对。”交络对,又名错落对,常见的别名还有蹉对、交股对等。它往往在表面上形成一种宽对,而把本应一一对应而形成工对的词语错置到两句的不同位置上。交络对中,两联诗句往往因表意需要,不得不调整位置,这是诗人在创作中,表意与格律发生冲突时,进行的一种折中的处理办法。 杜诗中亦有交络对的范例,如下: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出自杜甫的诗作《长江》。这两句诗按照常理形成工对的话,应作这般:“众水会涪万,一门争瞿塘”。“众水”与“一门”相对,“会”与“争”皆为动词,“涪万”与“瞿塘”地名相对,毫无瑕疵。但若不拆分,连词成句,那么“一门争瞿塘”这句诗,在表意上就显得不明朗。所以诗人用交络对来安排这两句诗歌的内容,方显恰当。
4.2 流水对
流水对又名“串对”,组成流水对的两个句子,既要满足诗句对偶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要使组成对仗的两个句子在语义上呈现固定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关联包括顺承、因果、假设等。由于有了这一层逻辑关联,使得诗句自然连成一片,不能单独表意,所以称为“流水对”。流水对是诗意一脉相承,诗句脱口而出,顺理成章成流水滔滔之势。流水对妙在难以成句,难以成对,创作的难度决定了它的高度,因此这种对仗形式一直享誉不断,受人追捧。诗歌中如果加入了流水对,就显得灵动了许多,更耐人咀嚼回味。
在《收京三首》之二中有这样两句诗:“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忽闻”和“又下”明显在语义上具有承接关系。《秋兴八首(之二)》中有例句:“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石上藤萝月,洲前芦荻花”,这十个字是恰当的工对,加上“请看”“已映”,效果就和之前大相径庭,“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已成流水。再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句诗可以简单译为:立刻穿过巴峡与巫峡,途经过襄阳再转向洛阳。四个地名相互排列,穿插其中的“即”“便” 二字便成了联系这两个诗句的纽带,使两句诗在语义上相关,一气呵成,气势如虹。杜甫借此来抒发自己听闻捷报后的激动与惊喜,胸中翻滚出沛然的波涛,纸上倾泻着诗人如火的激情。正如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所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8]最后来看“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九日崔氏蓝田庄》)这两句诗句与上面的例子相似,仅从语义上就能明显判定其为流水对例句。总之,杜诗中使用流水对的频率还是相对较高的。
5 结束语
杜甫一生创作上不断翻新求变,这种不懈的追求使他的诗歌魅力经久不衰,艺术境界臻于完美。而对仗体式多样,特殊对仗形式的广泛运用,是杜甫诗歌众多艺术特色之一。杜甫诗歌对仗在形式上博采众长,又自创新格,对仗工稳典丽,富于变化。这使他的诗歌的意蕴更为丰富,结构更为灵活,语句更有弹性。这样多变的对仗体式,不仅值得后人研究、欣赏,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