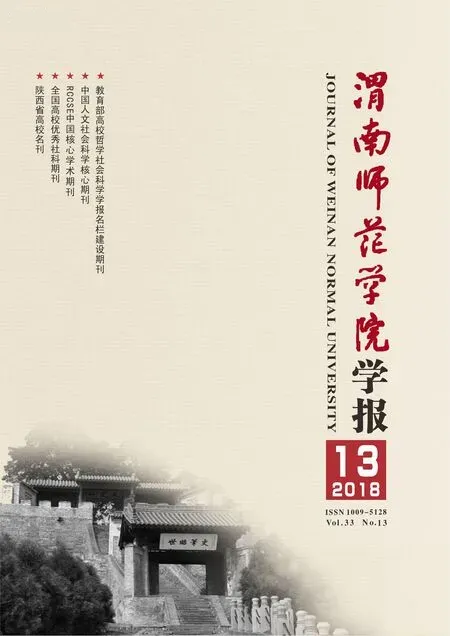谈谈《〈史记〉人物大辞典》的出新和不足
郭 楚 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最近,学者段国超、丁德科两位教授主编的《〈史记〉人物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史记》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整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值得我们共同庆贺。
一
《史记》中所写到的人物,主要描写者数千言,次要写及者千余言。还有几百言、几十言、几言,长短不等的,共计有4000多人。这么多人,要把他们一一写到,不要说有的数千言,就是仅仅提到,也不容易。那么,这部《〈史记〉人物大辞典》编得如何呢?它本身有什么特点和出新之处呢?笔者以为它除了编撰者自己所说的有追求“人物全、资料细、文字简”的特点,并且在这三点上也已取得成就外,在词条的编撰上还有不少出新之处。这出新之处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编撰者编撰《〈史记〉人物大辞典》,其人物词条内容,虽说都来自《史记》,以《史记》为凭据,但部分词条内容却超出了《史记》,较之于《史记》有新的拓展。如“褒姒”条的最后一段:
今陕西临潼零口与新丰两镇间的戏河,原叫伏羲氏河,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天下故,遂改今名。今戏河旁代王乡宋家村附近有个碰颡坡,史传褒姒被掳后不愿受辱,便在此碰颡而死,遂有此地名。今坡旁尚有褒姒墓。[1]14
这段文字内容是《史记》所没有的,是编撰者根据地方文史资料和后人的研究成果加进去的。这段文字加得好!它使褒姒这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更翔实、更具体,古今相互印证,更为真实完整。又如“司马迁”条就更为典型了。司马迁死了,词条说:“今陕西韩城芝川镇附近有他的祠和墓,而且还是我们国家首批重点文物单位。”说到《史记》的名称和历史价值,词条说:
《史记》原名叫《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后来才叫《史记》。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汉武帝太始二年,也即公元前95年,共记载了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130篇,计52.65万字。它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鲁迅曾将它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773-774
作为词条,全面评介司马迁,有这段话好,还是没有这段话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一是《史记》编撰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死后,《史记》写及的不少人物,包括汉武帝、李广利、苏武、桑弘羊、李陵、张安世这些人还活着,他们一生的活动,司马迁能写全吗?即使死在司马迁前的一些人物,司马迁也未必能写全。因此,《〈史记〉人物大辞典》人物词条的内容,吸收后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后人的评价,拓展《史记》的内容,是必然而且必要的。
《〈史记〉人物大辞典》的人物词条,能广泛采集后人的研究成果,吸收地方文史资料,不限于《史记》本身,这是智者之明、技高一筹,令人赞叹。
第二,在《〈史记〉人物大辞典》中,编撰者对词条人物的评价和《史记》文本自身对词条人物的评价有所不同,岂只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有所纠正,有所批评。批评了谁?批评了《史记》文本作者司马迁和后来的一些世俗者。如“张汤”条,司马迁是把张汤列入“酷吏”来写的,其事迹见《酷吏列传》。而《〈史记〉人物大辞典》的编撰者,是把张汤看作循吏来写的。虽整个词条的内容来自《史记》,但词条从头到尾未有一个“酷”字,亦未见有一个“酷”的例证,倒说他是“一代廉吏,也是一代杰出的法学家”[1]1107,评价很高。
按照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执法者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酷吏,一类是循吏。所谓酷吏,是说他所用刑法残酷,一味迎合君主个人的好恶;所谓循吏,是说他执法宽平,慎刑、恤刑,不受贿赂、清廉,有民本思想而不盲从君主。这两类执法者的划分始于汉代。司马迁,也许因为自己的遭遇与当时的执法者张汤有关(司马迁受宫刑时,张汤是御史大夫),心存芥蒂,主观上把张汤看作酷吏,把张汤写进《酷吏列传》。但他那“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和“唯实”的唯物史观,严格控制着他手中的那支笔,使他无法凭空写出“酷”来,相反,倒是写出了张汤的“勤政、俭朴和办事的认真”。他主观上想把张汤写成“酷吏”,例证是什么?一是“与赵禹共定诸法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二是“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三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四是“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等等。意思就是说他与赵禹共制各种律令,专力制定苛细严峻的法律条文,用以控制在职的官吏;他在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皆穷根究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因汉出兵讨伐匈奴,而且山东发生水灾和旱灾,灾民迁徙逃亡,造成国库空虚,他奉命铸造银币和五铢钱,统一货币,还极力支持国家专营政策,打击富商大贾等等。这有什么不对呢?这不是站在国家和朝廷的立场上办事吗?怎么能说是“酷吏”呢?也正因这些措施损害了那些贪官污吏、富商大贾的利益,所以他得罪了李文、庄青翟、朱买臣、王朝、边通这些人,受到这些奸人的诬陷,最后被逼自杀,死时,家产总值不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所得的赏赐,没有其他额外的收入。他的兄弟和儿子们想厚葬他,没有钱,最后用牛车拉着棺材(有棺无椁)出葬。也正因此,汉武帝后来发现张汤之死是一桩冤案,不得不追究责任,杀了王文、朱买臣、庄青翟这些人。
又例如“李陵”条。天汉三年,李陵出征匈奴,于匈奴腹地遭到围攻,在“内无粮食,外无救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遂降匈奴”。后在匈奴被招为驸马,并死于匈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写及自己在汉武帝面前为之辩解,为人廉信忠勇,立过战功,这次是矢尽无援的情况,所以兵败被俘,但“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希望汉武帝能从轻处理。这显然是为叛徒辩解,至于“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则完全是推测的话。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或者《史记》文本在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如果说李陵投降匈奴可以谅解,那么李陵的朋友苏武在匈奴牧羊十九年,誓死不降,又该做何种解释?两种情况一样吗?对此,《〈史记〉人物大辞典》的“司马迁”条是这样说的:
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司马迁也有失明智之处:一、李陵毕竟是投降了匈奴的,难道投降敌人也有可以辩解的理由?如果投降敌人也有可以原谅之处,那么李陵的朋友苏武在匈奴牧羊十九年,誓死不降,又该怎么评说呢?二、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时间很长,应知汉武帝的专横、残暴个性和汉武帝与李广利的特殊关系,应想有些话该不该说,因为说话也总该看看对象是谁。当然,这件事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还是汉武帝。汉武帝的专横、残暴,无论是对李陵还是对司马迁都带来了严重后果。[1]773
这段话令人耳目一新。它既批评了司马迁的迂腐和不明智,也批评了后来某些人的一种世俗看法——只揭露汉武帝的专横、残暴,而对司马迁的迂腐和不明智不说,甚而辩解。似乎作为史圣的司马迁在思想认识上不会有错误,或者说有错误也不能批评。
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进行辩解,把张汤作为酷吏写进《酷吏列传》,这说明了司马迁思想和世界观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史记〉人物大辞典》在写作“张汤”“司马迁”“李陵”“苏武”这些词条时,不完全按司马迁《史记》所写去写,意味着对司马迁认识上的偏颇是一个纠正,是一个批评。后来的一些世俗者,谈到“李陵事件”,不能批评司马迁为李陵的投降辩解是一个局限,甚而还要去掩饰司马迁在认识上的局限,这同样是认识上的模糊和不懂历史的表现。
第三,清一色的白话——辞典语言的革新。这本人物辞典,近7000多个人物词条,其中主词条也即实际的人物词条有4000多个。这4000多个人物词条,30多个撰稿人来写,要有统一的语言风格和繁简度,是很难的。但现在却是清一色的白话,清晰、简洁、流畅,这是很不容易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特色。举个例子,如“灌何”条:
(?—前147)西汉诸侯。一作灌阿。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人。颍阴懿侯灌婴之子。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灌何嗣父爵为颍阴侯。汉景时,曾任将军,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卒,谥号为“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895;《史记通解》882)[1]271
短短不足100字,即把灌何这个人的生卒年、谥号、社会关系、主要事迹说清了,文字简洁、流畅、清晰、明白。过去编辞典者,讲究用专门的“辞典语言”,也即半文半白,是多么枯燥无味!殊不知,现在“辞典语言”的概念早起了变化,连整篇文章都可以作词条了。何况“辞典”这种人民群众人人都需要随时翻阅的工具书!
二
《〈史记〉人物大辞典》的出新之处不少,但主要是以上三点。下面谈谈它的不足。
第一,有些人物词条的编写,文字详略长短,与人物主次、事迹多少和影响大小多有失衡。《史记》实载人物4000多个,但有主有次、有轻有重,事迹多少和影响大小也不一样。一般地说,这就决定了《〈史记〉人物大辞典》中人物词条的文字长短也会不一样。主要人物、重点人物,司马迁专门为其立传的人物,事迹多一些,影响也大一些,人物词条的文字也就必然会长一些。这才是正常的。以此来看《〈史记〉人物大辞典》,有些词条虽有长短,但并非正常。有些人物属非主要人物、非重要人物,事迹也不多,影响也不大,但词条却写得很长,如写蔡泽用字1400余,写邴吉用字990余,写卜式用字1300余,写晋惠公用字660余,而写炎帝、尧、蚩尤、妲己、窦太后、共工等不足300字甚或不足200字,是否合适呢?写黄帝、吕后、廉颇、孟轲、墨翟等,均不足1000字,而写李斯、陈平、范雎、曹参、苏代、苏秦、赵高、周勃等,动辄3000多字4000多字,有的还5000多字6000多字,难道合适吗?显然这里没有一个合适的度,一个统一的“度”。有的人写得细,有的人写得粗,有的人写得概括,有的人写得具体。整体看下去,没有主次,没有轻重,不相和谐,失之平衡。其原因是对写词条没有统一的要求,全书写成后,也没有按统一要求统稿。这样的写法,容易给读者造成误导,历史人物的主次轻重在读者的大脑中混乱。当然,解决这问题也容易,即按统一的“度”、统一的要求统稿就行。
第二,《〈史记〉人物大辞典》属工具书,工具书是从读者的需要出发专门为读者服务的,《〈史记〉人物大辞典》即是专门为读者查找《史记》中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服务的。读者要查找,怎么查找?作为工具书即要给予读者各种查找的方便,如懂汉语拼音的人可以通过词条第一字的音序查找,不懂汉语拼音的人,则可以通过词条第一字的偏旁部首去查找,或通过词条第一字的笔画去寻找,等等,方法多样,查寻方便。《〈史记〉人物大辞典》现只有通过音序去寻找这一种方法,显然是不够的,满足不了所有读者的需要。建议这本辞典再版时,能在词条查找方法上着眼改进。
第三,一般地说,学术著作特别是工具书都是有序言或前言的,有时序言或前言兼有,这是因为,从形式上看,一本学术著作特别是工具书,它的完整构架是“序言+文本+后记”三部分,缺少了哪一部分,即被视为“构架不完整”;从内容上看,序言和前言有指导读者阅读、认识和研究文本的作用,是读者需要的。而这本《〈史记〉人物大辞典》没有序言甚至也没有前言,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读者阅读这部辞典,不只需要了解《史记》中的人物,对《史记》的性质、价值和出版意义也希望有所了解。就是说,这部《〈史记〉人物大辞典》,作为工具书,其“工具”的含义也应包括序言或前言在内。因此,建议这部辞典在出修正版时,能把所缺的序言或前言补进去,使之更趋于完美,因为这样对读者更为有益。
以上是我阅读《〈史记〉人物大辞典》后的一点看法。因为它本身带有原创性,本身就是创新思维的产物,它的出新点,自然不只是我所谈的以上三点。作为新事物,它的不足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
四
《史记》是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写了4000多个人物,“人”在这里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历史,掌握了“人”、了解了“人”,就等于掌握了、了解了人类的历史,《〈史记〉人物大辞典》的编纂者首先想到给《史记》里的人写传、编辞典,这是智者之举,是他们善于思考问题、善于抓事物主要矛盾的结果。
但是我们说《史记》是我国2000多年前的一部“百科全书”,说明《史记》里所写的不单是人,还写了各种人所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科技活动、军事活动、民族活动、外交活动、语言活动、文艺活动,等等。从《〈史记〉人物大辞典》的编写,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个启发:既然需要编写,也能编写《〈史记〉人物大辞典》,那么,是否也需要编写,也能编写《〈史记〉经济辞典》《〈史记〉军事辞典》《〈史记〉政治辞典》《〈史记〉科技辞典》《〈史记〉外交辞典》《〈史记〉民族辞典》等一系列辞典?我看是完全需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只需要我们组织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力分头同时去做,或一部一部地分头连续去做,且付出一定的财力就可以了。这是我在学习《〈史记〉人物大辞典》后所想到、所期望的。如果这些辞典都编纂出来了,那将是我们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史记》研究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