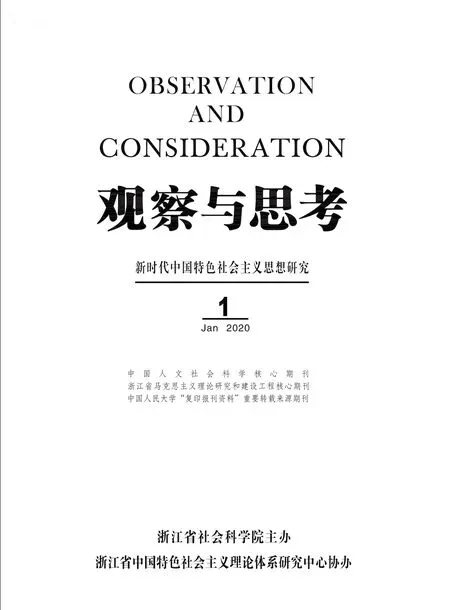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道德利他考察
周 楠 姚 永 明
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从理论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愿景设计一脉相承,展示了清晰而温暖的“人类情怀”。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发展和自觉外展,具有积极的“道德利他”品质,是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为使世界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正确方向演进而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道德利他本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次向世界阐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实关照和未来憧憬而发出的道德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缘自人的类本性,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奉献与回报的结合,是德性与幸福的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情感和理性统一的“道德利他”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既有丰富的情感,也有强大的理性,能形成鲜明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关注人现有状态的研究,是由应然性向实然性转变的过程,是哲学思辨向现实世界的一种转变。①参见左亚文:《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本之维》,《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的一种回应。②参见杨宏伟: 《“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路径》,《理论学刊》,2017年第2期。从人的情感出发,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归属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而从理性出发,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根据自身情况寻求快速发展,同时认为,发达国家遵守国际新秩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与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是对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乌托邦式的幻想,它是必然世界通向自由王国的桥梁。因此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奉献与回报结合的“道德利他”
从理论上讲,道德利他行为的发生一般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客观公正的道德判断、理性思考下的道德选择和情感激发下的道德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人类福祉的道德行为。行为主体有自愿、自觉的行为欲望,道德利他之行为就是要对他者(人类社会)给予奉献。通常,人们在讲到“奉献”时是不求回报的,那么,道德利他行为主体在实施利他行为而牺牲自身的利益时,有没有要求回报的权力呢?笔者认为,因为道德利他的“他者”对象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将“奉献”与“回报”统一起来。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一种美德必然能够得到适当的报答,得到这种报答对于美的本身也能够起到鼓励的作用。③参见艾四林、王明初主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提倡回报,并不否认道德利他主体的道德品质,主张道德回报,主要是为了在利他行为主体与接受利他者之间达成道德共识和某种利益均衡,这一观念与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共赢”、“共享”的目的是高度契合的。也正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导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行动深化,目前,已经得到“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这是世界对“中国奉献”的初步回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追求德性与幸福同步的“道德利他”
一般来说,无论是在道德理论探讨,还是在现实道德实践中,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经常是一对矛盾。人们常常认为,道德和幸福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以至于二者不可兼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德福“二律悖反”。笔者认为,幸福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体验幸福的种类或层次也是多样,其中就有“道德的幸福”,如助人为乐。这就是说,幸福本身应当包含对道德的要求,而道德利他品行作为一种德性,也是幸福本身应有之义。道德利他行为主体的幸福是与他者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道德,就是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社会,乃至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智慧。在道德利他实践中,一个人之所以做出利他的行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因而会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高层次的道德感,同时还会生成高层次的幸福感。由此,追求德性的过程就成为了追求幸福的过程,实现了“德性”与“幸福”的统一。个体的道德利他行为是这样,国家的道德利他行为也是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强调要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要把他国的发展看作本国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追求本国人民幸福的同时,让他国,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道德利他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利他判断,但从不同的维度来展开道德利他行为,却是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其内涵非常丰富。
(一)从“利他纯度”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己他两利”
道德利他在纯度上分为为己利他、己他两利和无私利他等几种。其中“为己利他”中的行为主体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完全把“他者”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己他两利”中的行为主体能将自身和他者利益兼顾考虑,把自己和“他者”放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在共同体之内“己他”两个方面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己他两利”的典型,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发展,互惠双赢、互惠多赢、互惠共赢。“己他两利”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普遍、最易被人接受的利他形式,彼此双方或多方,将对方的发展视为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主动地、积极地为对方提供方便、机会和条件。当然,“己他两利”行为的发生需要双方或多方有共同的认识,任何单方面认为的“己他两利”是不能实现的。
(二)“利他广度”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普遍利他”
道德利他中“他”还有“特定对象”和“普遍对象”之分。“特定对象”的道德利他主要表现在针对血缘、学缘、地缘、业缘等的利他,这些“缘群”分别构成了包括行为主体在内的“两方共同体”。而“普遍对象”的道德利他则是将自身以外的全部“他者”都视为与自己同等地位者而实施的利他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论上讲属于“普遍对象”的利他观念,即在中国看来,只要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在出发点上并不排斥任何“特定国家”,这也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多元性所决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同,而且,“不认同国家”还会成为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广、行为实施的负面力量。
(三)“利他频度”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经常利他”
道德利他进入到行为阶段,就有偶尔为之的利他和经常而为的利他以及持续而为的利他。通常,人们都认为经常和持续而为的利他更值得肯定和赞赏,因为经常和持续而为的利他似乎更能够反映行为主体一以贯之的道德品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偶尔甚至一次性利他行为的道德光辉,如个体利他行为中的“见义勇为”。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群体利他,其建设是国家行为,其建设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可谓建设任务也重,其建设效果的显现也慢,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行为必须是“经常和持续利他”,需要建设主体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出于理性”“成于坚持”和“终于意志”的“经常利他”。
(四)从主客体关系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道德利它”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即参与者是多元的世界各国。而建设的客体、对象和建设的成果是面向全世界、全人类社会,甚至是面向自然界的。这是因为,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从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的角度看,世界是一个“共荣俱损”的统一体;从军事科学技术,特别是核武器发展的现实和趋势看,仅仅是“合法”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现有核弹就足以数十次地毁灭地球,况且,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极力地争取拥有核武器的权力。然而,在联合国“公信力”经常受到质疑而式微的情况下,由于个别超级大国在处置国际关系时,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推行霸权主义,在弱小国家面前“秀肌肉”,激化矛盾,甚至任性地武装干涉别国内政。逼得极少数几个不确知是否真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时放出要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狠话,这种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态势,超过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核竞赛,经常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爆发的边缘,令世界和平面临更大威胁。同理,由于二氧化碳过渡排放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发展工业而导致自然环境污染等,也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今世界已经被客观地安放在了同一条船上,“同舟共济”理应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因此,当道德利他行为主体产生有利于自然界或全人类的行为时,虽然在主客体关系上只是“利它”,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不可超越的伦理关系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它”,当然也属于“利他”的考察范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议道德利他的实践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在中国又一次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时,为加强不同制度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经验”而提出来的“道德利他”倡议,若要使此倡议成为现实,首先需要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同,更需要各国人民的积极实践和不懈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道德利他观念和行为的统一
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从道德利他的实现过程来看,道德利他自然地包括道德利他观念的产生和道德利他行为的实施两个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现实和未来愿景的积极倡议,当前仅完成了道德利他的意愿表达,要真正地使利他观念产生利他的作用和效果,需要全世界各国在认同的基础上积极地实施利他行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人们只有正确的道德判断,而没有实施利他行为的种种情形。当今的世界各国,即便有相对一致的道德价值判断,但更多的还有利益的考量,“国家利益至上”是许多国家指导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需要致力推动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实践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道德利他行为,它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而群体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群体,主要是指若干个无组织化的个体的集合,这里的个体,主要是单个的人;广义上的群体,则特指有组织性的个体的集合,这里的个体,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多个人组成的组织,还可以是多个组织而形成的社会,乃至国家。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道德利他行为,它的行为主体应该是人类、全世界,也就是世界各国。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一个社会制度形态多元、国别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宗教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尽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由于参与成员过多、关系复杂、谈判成本较高等因素,形成共识并共同行动机制的成本较大、推进困难。但我们乐观地看到,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在气候、能源、水资源、粮食、反恐、疾病等各领域的安全合作与制度建设在不同的层次开展,并有进一步扩大加深的趋势,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在实践上可行的现实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缘于“自愿”或“志愿”的道德践行
从行为理论上讲,人的行为一般可分为“被迫行为”“自发行为”“自愿行为”和“志愿行为”四种,国家行为同理。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方面的“自发行为”,也不可能通过“被迫行为”而实现。这就是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必须是“自愿的”或“志愿的”。“自愿”主要是指世界各国主动而非被迫地实施利于他者的行为,是认同基础上的“愿意”;而“志愿”则主要是指世界各国有愿望并志向于实施利于他者的行为,是“愿意”基础上的“追求”。二者从道德动机和目的上将道德利他行为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显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国,中国是出于“志愿”的道德利他行为主体,其行为表现出了较高层次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品质。而其他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此倡议的国家,目前尚处于“自愿”的道德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观念到行为、从倡议到现实,直至最终实现,其间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