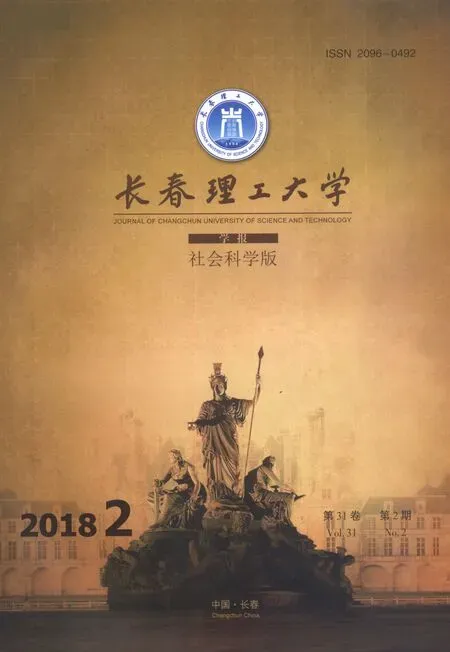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
王进文,张 军
(1.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2;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进程的有序推进,使城乡人口水平空间上的流速持续增快、城乡元素交互流动状态甚为活跃。然而,由于受到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农村人口迁出率提高、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弱化等现象日益严重,村庄碎片化、地域空心化等趋势也渐趋明显。另外,市场经济理念和理性化交往原则对乡村社会诸多领域的侵蚀日趋严重,并由此引致农村社会底层生态产生了重大转向,如人际关系属性从感性化转向理性化、交往方式从非正式化转向正式化、交往理念从互助共享转向精于算计……正是在此情势之下,村民间的“守望相助”“温情脉脉”之感逐渐消隐,疏远化、离心化趋向愈加显现。这一切“破败、残缺、暗淡”的农村社会生活片段似乎印证了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言“农民的终结”[1]的客观事实,抑或深刻体认了李培林所称“村落的终结”[2]的前瞻洞见。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在另一个镜像中我们可窥视到异样情境:北京社区中的“浙江村”“河南村”;高校社团里的“老乡会”“同学会”;海外城市中的“华侨区”“唐人街”等等,不胜枚举。毫无疑义,这两种巨大反差画面的共存,必然会促使我们生发出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这一切何以可能?应该说,社会记忆之功能或价值的被发现和再审视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省思视角。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者看来,记忆是一套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思想谱系和话语图式,重构于过去、应用于现在、映射于未来。鉴于此,从社会记忆理论视域出发,探察当下乡村记忆的特征、载体形式以及式微成因,并据此探索乡村社会记忆的复归之路径,这将对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繁荣具有实质意义。
一、社会记忆研究:一个历时性的概述
在以往较长的时间里,诸如记忆、自杀等词语被视为个体独有的心理状态或精神活动成了心理学研究范畴中的概念工具,而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因未能发掘出其附有的“社会属性”而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应该说,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静默期后,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通过划分“社会事实”的双重类型重现了这些概念的整体面貌和总体性质,并着重对“集体意识”“集体表象”等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之意涵给予了再度审视。在此基础上,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并界定其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3]。”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关于记忆、集体记忆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学术场域转移的现象。基于前人的立论基础和概念分析,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但其意涵因缺乏统括性、整体性、系统性建构而显得略微含混和模糊。如果说,哈布瓦赫的研究旨趣是跨文化族群中固有的集体记忆,那么康纳顿更专注于某一社会中的集体记忆即社会记忆如何承续和保持等问题;如果说,哈布瓦赫很大程度上只将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视角而使其研究文本显得僵硬、抽象,那么康纳顿则通过把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社会记忆运行的手段或方式而使其研究内容表现得更加具体、充实。在借鉴上述二者的有益成果后,美国社会学家施瓦茨(Schwartz)指出,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当下的重视和康纳顿对记忆连续性的解读都太过于狭隘化、教条化、片面化,因此其尝试借助于文化符号学的解释框架将集体记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有机相连接[4]。此后,罗宾斯(Robins)等人探究了行动者在社会记忆中扮演了竞争性关系、阳·阿斯曼(Jan Assmann)关注了文化以及回忆对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性[5]等学理发现,均直接或间接、显在或潜在地对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做出了批判性、丰富性、增补性的有益贡献。
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档案价值或功能的被挖掘和再省思,以及国外社会记忆研究论著的“西学东渐”,围绕乡土社会这一场域而展开的具有本土化、原生性特征的社会记忆研究持续深入,其学理成果颇为丰富。例如,就理论分析而言,基于哲学的研究视域,加之对社会记忆发展脉络的细微缕析,我国学者孔德忠认为,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6]。从经验研究来看,景军通过对大川村的历时性田野调查考察了群体需求与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内容的动态影响,以及记录了大川村的现代历史并展现了人们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中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7],等等。可以说,这些研究无论在政策探讨和学理建构上,还是实践操作和实务调查方面都拓宽了我们对其理解和认知的视域与维度,并为乡村社会记忆的复归和重构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累积。为有效廓清乡村社会记忆的本质意涵,本文中乡村社会记忆指的是,人们围绕乡土社会场域展开的立足于生产生活实践而创造的一切具有实践性、功能性和情感性特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以信息集合的方式完成其编码、存储和调用过程的总称。
二、乡村社会记忆的特征及其载体
(一)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特征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开篇即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血缘、地缘、姻缘等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而人际关系的有序开展、持存维继则是凭依于为村落共同体所共有的乡村记忆。这种乡村记忆伴随着村庄落成、村落变迁和发展等过程不断下沉、积淀和凝固,进而为村民所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它是村民建构村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以及在代代相传中赋予生命以意义的重要媒介。然而,值得省思的是,乡村记忆在形成、累积和凝聚之后并非如“一潭死水”般迟滞不变,相反其每时每刻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被村民或调用、或强化、或转移,因此其总是保持着生命力、鲜活力和动态性。换言之,乡村社会记忆并非一个静态迟滞的旨在记录与表达的话语系统,而是一个相对动态演化的功用性和情感性兼具的文化集合体。正因于此,在传统社会中,乡村记忆不会随着人口代际继替而消隐,更不会因个人意志的转移而变化。另外,乡土社会村落域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乡村记忆呈现出特具化、地方性的特征。应该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地域特色风情不仅形塑了我国文化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完整性,而且标明了乡村记忆的差异性和多重性。质言之,乡村社会记忆的动态性、地方性、相对稳定性、多重性等特征生发于乡土社会中的日常性实践活动,而日常生活实践的自然展开也重构和丰富了乡土记忆的意涵以及维度,二者交互作用、相辅相成。
(二)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载体
乡村社会记忆的载体形式和存在样态是丰富多样的。它不仅包含抽象意义上的符码、空间等外在形态,还涵括了具体的、实践的仪式、建筑等客观实在物。在一般意义上,就乡村社会记忆的存在形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口头传承记忆;二是体化实践记忆;三是文献记载记忆;四是器物遗迹记忆[9]。具体言之:首先,以乡村故事、乡村传说、乡村方言为表现形式的乡村记忆在话语表达和口耳相传中得以传承和延续。其次,以赛龙舟、龙灯会、丧嫁活动等为主的实践活动,使村民在同一时空场集合会聚起来,并在“集体欢腾”中获得了自己的力量和社会位置,形成了彼此间亲密的关系,拥有了共同观念、情感和记忆。再次,家谱族规、契约文书、乡村方志等文字既刻录了村落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图景,更为村民重构村庄意识、集体理念提供了可靠依据。最后,以乡贤祠、村牌、古井、老街等代表的客观实在物,因框定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轨迹、见证了村落形态变迁的过程而成为乡村社会记忆体系建构的支撑基点。然而,任何一种乡村社会记忆的传承和流播不仅需要借助于相关媒介载体,更需要一个相对持续性的时间场和稳定性的地理空间环境。因为这种特定场域所型塑的村庄空间结构“既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村庄形态与生活交化空间,也建构着村庄历史变迁中村民对村庄的形态与范围的认知与记忆。”[10]而传统社会的低流动性、熟知性、地理边界清晰等特征为乡村社会记忆的延承和传递提供了时空机制。概言之,乡村社会记忆会因其基本载体的存续而被呼唤,也会因村落时空场的渐进稳定而得以重塑。
三、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归因
人既是乡村社会记忆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享用者,也是遗忘、破坏、颠覆乡村社会记忆的始作俑者。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风驰电掣般地扩张和侵入,一场席卷全球的轰轰烈烈的制度性变迁以及经济转轨路程由此开启。在此期间,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助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产生断裂态势、城乡经济差距持续拉大、城乡文化理念渐趋分野等问题愈发突显,并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区开始被遗忘、乡村社会记忆逐渐模糊以至消隐。应该说,作为现代性基本表征的工业化、城镇化、科学化、制度化,不仅从诸方面引致了乡村的自然以及传统走向终结,而且使乡民陷入了本体性安全危机以及自我认同困境,而这些都构成了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前兆和先声。具体言之,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成因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以往城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地域形态和空间格局,撕裂了乡民的生活空间和仪式空间,进而使得乡村记忆的承载媒介以及稳定性的时空机制就此失效。另外,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约束下,城镇化的伴生物即城市规则开始对承载着以规则、理念、风俗、传统等基本内核的乡村记忆的文化要素进行了驱逐和排斥,并在市民持久的刻板印象影响下,对创造乡村记忆的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规约,使乡民割断了其与过去、历史的联系。在此期间,为了进入、适应以至融入城市社会,乡民历经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历史阶段,并对乡村社会记忆进行了或主动、或被动的删繁就简式的有选择性的保留,由此乡村记忆呈现出片段化、零散化、残缺性趋向。
第二,高度流动性和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引致了农村“三留守”现象的日益凸显和中青年主流群体的高度“缺场”。这意味着因缺乏主流中心主体对体化实践仪式和口头言传活动进行重复操演和反复实践,乡村社会记忆在时间源流中会被淡忘、弱化甚至隐却。加之“法治”下乡、“民主下乡”等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理念的冲击,乡民的交往原则从道德礼仪转到制度化契约、交往理念从价值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进而打破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村落人际关系、削弱了村庄共同体成员间的共识度和一致性,由此村庄经由了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的转向,村庄关联度不断降低,乡村社会记忆的凝聚向心功能逐步丧失。
第三,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潜在渗透及其“政治话语”的构建。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步伐加快,政府为了化解潜在性危机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开始有选择性地表达了“国家在场”的态度,其中包括了对乡村社会诸多传统的介入和重构。应该说,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记忆体系的侵蚀方式是复杂而多元的,它既“可以运用暴力工具捣毁民间仪式的场所和道具,也可以通过特定知识和规范的灌输促使受众自动放弃这些仪式”[11]。例如,大力普及科学常识、推动农村丧葬仪式从土葬到火葬的改革、推进清明节祭奠仪式的现代化等措施都直接体现出政府的“在场”权威,但同时也摧毁了乡村社会记忆得以存续的传播介质。不仅如此,国家通过对诸如国家公祭、国庆阅兵式等纪念活动加以可视化、固定化,建构了有别于个体认同和村庄记忆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记忆。应该说,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与记忆和政治话语,村民所内化的乡村记忆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和次要角色,由此乡村记忆力也从强趋弱以至丧失。
四、乡村社会记忆重构的可行路径
乡村社会记忆生成于村庄共同体的过往日常生活实践,浸润于乡民的当下生活图景和未来发展路向。它能勾连起村民对尊师重教、勤劳朴素、和睦进取等优良品德的想象,也起着凝聚村庄共识、深化村民关系、建构乡土认同、增进公共福祉等基础性作用。而“现代性”的下乡冲击了乡村固有社会结构以及底层秩序,也引致了乡土社会逐渐衰败、乡村人际关系日趋松散、乡村原生文化的正功能愈加减缩。有鉴于此,如何重新唤醒与调用存在于每个村民脑海中的既有乡村社会记忆,通畅乡村社会记忆流播和传布的渠道,并使之服务于美丽乡村建设和治理乡村社会生态,成为了一项时间久长而意义深远的系统性工程,更是一种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有益工作。此外,这也标示着乡村社会记忆的修复与重构需要多元主体的社会支持和组织介入,由此应探索一条可行性与可及性的现实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推进就地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加以城乡推拉力的共同作用,农村中青年主流群体流向城市,村庄人口迁出率逐年升高,使得乡村因缺乏乡村记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而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而就地城镇化克服了以往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引致的高度流动性的困境,满足了村民在既有熟识的地域场内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即就地市民化的期待。这种转换使得乡民离土不离乡,并身处于乡村社会生态和话语体系之中,因此互动主体和交往场景的熟识性为唤醒和重构乡民彼此关联的乡村记忆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其建构村庄认同、凝聚村庄共识的可调用的有益资源。另外,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和践行,为如何推进物质丰盈、精神富足、文化昌盛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的策略参考。应该说,新型城镇化战略基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机制、统筹城乡一体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政府要注重保存农村既有的社会生态和文化资源,全面切实做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和核查,尽量维持乡村的纪念空间、公共场域等地域格局,进而达致人—自然关系和谐与乡村记忆承续的统一。
其次,推进“乡村记忆工程”建设,有序开发乡村记忆资源。从乡村社会记忆消隐的现实成因来看,政府在修复和重构乡村社会记忆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此外,随着文化符号资源的被发掘和社会记忆资本化渐趋明显,乡村记忆作为一种本土特色资源而为各地政府所竞相追逐和争夺。在此背景下,“乡土记忆工程”建设有序展开。作为一项意义深远的浩大工程,一方面基层部门既要在立足于尊重村落民俗乡风、利用既有文化设施等基础上加大对乡村档案文本进行收集与整理、对兼有地方性、意义性的建筑物进行保护和维修、对民间仪式与民俗实践进行记录与操演的力度,也要给予充分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此外,在我国步入网络社会之际,加快乡村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可视化、电子化步伐不仅能将乡村的潜在记忆显现化、抽象记忆具体化、流动记忆稳定化,而且能吸附更多人关注甚至参与到乡村记忆的保护以及开发过程中。另一方面,政府要有序开发乡村记忆资源,打造乡村记忆品牌,引导和激发乡民参与乡村记忆工程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进而使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村民和乡村记忆的传承者获得文化层面上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以及物质层面上的经济收入和利益,最终助推其走向“文化自觉”甚至“文化自信”。
最后,发挥乡村精英引领作用,开展乡村社会文化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乡村社会记忆生发于特定场域和具体实践中,它由村庄成员所创造和再生产。这意味着外在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如制度化、政府政策导向和经济支持、公共性文化机构的宣传和报道等)只能为乡村社会记忆提供流播和弘扬条件,而唤醒和重构乡村社会记忆的原初动力还需要从具体而现实的乡村社会去找寻。应该说,作为一项复杂而持久的文化建构,村庄内的每个主体或组织都是乡村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有鉴于此,作为村庄里的能人和权威,乡村精英可依凭其具有的经济实力、政治威望、文化能力来深度挖掘为乡村共同体所认同和共有的地方性知识,并发挥其讲好乡村故事、述说乡村历史、延承乡村记忆的先锋榜样和带头示范作用。另外,社区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单位,既要充分调用农村社区内部资源,开展为乡民所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活动,营造保护乡村记忆的良好文化氛围,还要推动“社区的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结合”[12],进而使其在反复操演和持续实践中将乡村社会记忆内化于心、形表于里。
作为一根生发于过去、映射于现在、导向于未来的精神纽带,乡村社会记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乡土实践中影响人、约制人、塑造人。它不仅具有抽象层面上的符号意义和文化价值,而且有着稳定乡土秩序、凝聚村庄共识、强化乡村治理等现实性功效。尽管现代性的狂飙突进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等社会现实,使得乡村社会记忆因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渐趋式微以至消隐,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我国城乡关系渐趋由“刚性对立”转向“柔性和谐”,加之“乡村记忆工程”“乡村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应对措施的及时出台、乡村文化资源的健康有序开发,已发生中断甚至消隐的乡村社会记忆重新受到了政界和整个社会的深度关注和深入省思,其复归以及重构之路也已铺就。因此,我们有理由深信乡村社会记忆能被延续,乡愁必将被记住,乡情势必被留住。
[1]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5.
[4]李红武,胡鸿宝.国外社会记忆研究概述[J].学习月刊,2011(6):36-37.
[5]张俊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之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6-7.
[6]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4.
[7]景军.神堂记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6-7.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1.
[9]丁华东.讲好乡村记忆——论乡村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的定位与方向[J].档案学通讯,2016(5):54-55.
[10]邓棋.延续与分化:转型期乡村记化的传承机制及启示[D].合肥:安徽大学,2015:18-19.
[11]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5-46.
[12]许晓芸.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社区记忆:式微与重建[J].甘肃社会科学,2014(2):1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