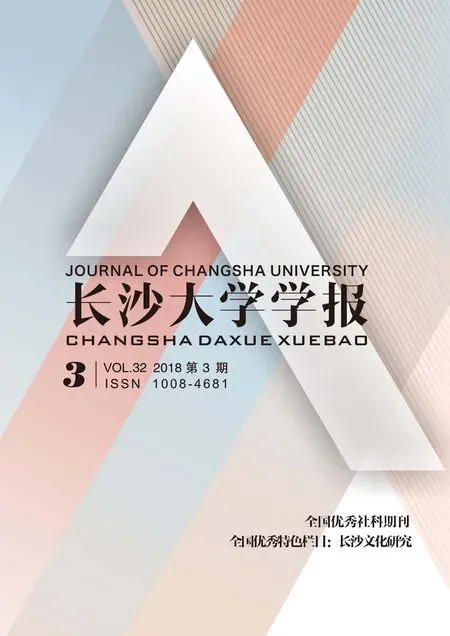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回归的可能
阳桂红,瓦秋盛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 知识分子及其公共性危机
关于知识分子的词源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源于19世纪的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当时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而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俄国人士,他们是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群体,当时便被称为知识分子[1]。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来源是1894年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他们站出来为因具有犹太人血统而遭污蔑的上尉德雷福斯进行辩护,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的人士被他们的敌对者蔑称为知识分子[2]。这两种知识分子通常被当作传统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坐在咖啡馆等民间公共场合中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并且深刻积极地影响着社会大众。
从社会现实功能角度看,其公共性表现为:“第一是面向(to) 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3]。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本身还体现为自由批判精神,公共性本身是针对社会公众而言的,表现为大家都可以自由进行言论批判,否则不能称之为公共性。从哲学层面看,关于公共性还有另一种普遍解读:即把西方传统哲学本质看作对具有公共性、普遍性的元叙述或元真理的追求,并成为后现代主义者们超越与解构的对象。西方传统哲学从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都试图对人的认识、道德和生活预设出公共性的规范和“第一原理”[4]。而本文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进行自由批判交流的言论思想促进元真理与价值的生成作用,其言论思想本身不能替代元真理与价值本身,这间接指出哲学层面的公共性本身带有虚妄性,或者说关于公共性的哲学讨论是个伪命题,不宜作过多解析。
随着时代推进,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社会现实功能开始消退,即其所具有的公共性产生危机。在大数据时代前期,从知识传播的载体角度可以划分为文字时代与后文字时代。在以文字为媒介中心的文字时代,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文字影响社会公众,“在这个时代中,话语、信息和意愿都通过文字传输,公众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大半是通过阅读文字”[5]。然而90年代的中国同欧美70年代一样出现知识体制的专业化现象,产生一大批学院派的专业知识分子,几乎只埋头于专业知识的研究,他们的公共性几乎丧失[6]。且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电子媒介的兴起打破了纸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图像或形象逐渐取代了文字进入后文字时代,“视觉符号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比如电影、电视、广告、摄影、形象设计、体育运动的视觉表演、印刷物的插图化等等,有人形象地称之为‘读图时代’或‘视觉文化时代’”[7]。在这个时代里,同时产生了一大批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借助大众媒体影响社会公众,不过他们更多地是为个人利益、某个集团或者某个阶级利益代言,常常扮演着哈耶克所言的“贩卖观念”的文化商人,不能站在公共立场维护公共利益。无论是在学院化的文字时代,还是大众媒体兴起的后文字时代,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而是市场化的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在塑造知识分子:“媒体已经市场化,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不再是哈贝马斯所讲的一个自觉参与的公共舆论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舆论的利益集团)与政治家(权利的利益集团)合谋,甚至滥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使用公共话语,从而导致真正的知识分子被舆论边缘化,但是媒体的作恶却使得知识分子的名声受到极大的破坏, 因为人们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承担公共角色”[8]。由此传统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逐渐丧失。
二 知识分子公共性回归的可能
直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从记录符号变成了有价的资源,并从符号价值逐渐延伸到具有认知、经济、政治等诸多价值的财富[9],它将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图景、知识发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将通过数据财富的形式影响着社会大众。“所谓大数据,从字面来看,就是规模特别巨大的数据资源,但实际上,大数据不仅仅只是数据规模巨大,更重要的是数据数量的变化引起了质变,数据不仅仅是自然或社会现象的数量表征,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本质变化。”[10]在这个时代,数据成了一种新财富,它与传统财富易被消耗不同,数据财富是可以交叉复用,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真正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11]。而数据本身又需要通过知识分子对其进行创新性分析来释放它潜在的无限价值。在这种数据财富与知识分子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因此可能发生质的变化。知识分子可能从经济基础、政治立场与言论思想三个维度上获得解放而重拾公共性。
(一)知识分子经济独立的可能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以资本脱域为社会现实基础的时代。“脱域”一词在吉登斯《现代性后果》中主要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2]。资本以其追求扩张别无选择的秉性,总是不断突破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向外部空间延伸或突破,其“脱域性”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使当今时代成为资本脱域的时代[13]。知识分子根据资本脱域的现实在经济基础上可能获得解放。
当今资本意识渗透至各个领域,任何人无法抗拒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本身蕴含着自由精神,它将打破一切阻碍它自由发展的东西。在资本脱域的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不仅仅表现为文化资本,还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资本当作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者“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积累起来的劳动,也是一种铭写在客体与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与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14]。 在他看来,资本主要有三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外,还有表现这三种资本形式的符号资本:“当我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三种形式的资本的各自特定逻辑,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是误识了这些资本占有和积累的任意性,从而把握了这几种资本的话,我们就说这些资本采用的形式是符号资本”[15]。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不仅拥有以财产权形式被制度化的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的经济资本,其个人品质如社会声望和地位还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同时本身还拥有以隐蔽形式存在但可以转化为经济与社会资本的文化资本。他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本之间又可以自由转换,在大数据的价值链中,它们被转化为数据财富,这些数据财富可能产生更多的商业价值,知识分子从中可以获取更多报酬。这样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并非仅仅依赖于体制的工资或者媒体邀约费用,他们可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因此,资本意识泛化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财富能为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获利方式。知识分子再也不必过分依赖国家体制与大众媒体,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仅可以转变为社会资本,还可以兑换为经济资本,这些资本变为数据财富之后,他们可以借助数据财富的力量取得一定的自主性,从经济基础上获得一定的解放,可能回归至可以自由批判的公共舆论空间以维护公共利益。
(二)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独立的可能
从政治角度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根本上决定其政治立场,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过曲折性评估,导致知识分子的命运多舛。而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阶级意识淡化的时代,是以工农阶级知识分子泛化为现实基础的时代。知识分子可以依据阶级意识淡化的事实而更自由地创造发挥自己的价值,他们可能摆脱政治立场的束缚而取得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先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16]。但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暧昧不清的。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认为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又重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没有确认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观的事实”[17]。这不仅为后来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埋下伏笔,还导致文革时知识分子双重人格化。用杨凤城先生的话讲,文革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扮演着革命者与革命对象的双重角色:其中一部分是革命对象的角色承担,另一部分则是革命者的角色承担;无论对于知识分子的整体而言还是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而言,这两种角色均有着交替出现或者同时共构的复杂变换,两者并不能等量齐观,当时知识分子为革命对象的角色则是彰显的[18]。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必然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且无论过去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进行曲折性的界定或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暧昧态度,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工农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普遍缺乏知识与受教育的机会。而当时的各类资本基本处于固化垄断状态很难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进而不可能保障当时的社会福利。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陷入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焦躁状态,即整个社会处于阶级斗争意识泛化的时代。
大数据时代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淡化的时代。其一,基于资本脱域的现实,人人都可能是资本家或是工人,即每一个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具有双重的阶级身份,相互为对方打工或服务来获取报酬,这些报酬转变为数据财富。这导致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能简单地以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与否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而应以数据财富占有的多寡为阶级标准。由此在数据财富的世界里,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家与文化打工仔双重身份,其身上的阶级身份意识逐渐淡化。其二,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不能笼统地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应以数据财富产生经济效益的正负作用来衡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尤其进入知识分子泛化的时代,工农阶级多数演变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几乎都已经接受过一定的知识教育与技能的培训。如果说过去研究和探讨的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和科学内涵,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能否将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从而也让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和丰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重要思想,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应坚信“知识分子已经工人阶级化”这个思想。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身份与工人阶级身份不再以二元对立的阶级冲突存在,而是以和谐共存的阶层存在,这样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可能独立,从而发挥其积极影响,重返自由批判的公共舆论空间以维护公共利益。
(三)言论思想自由的可能
知识分子言论思想的自由不仅需要上述一定独立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立场为前提条件,还依赖于客观的公共舆论场所的构建状况。大数据时代所建构的公共舆论空间,不仅颠覆了传统信息、文化传播的方式与社会舆论形态,还让舆论主体获得了强有力的保障而在理论上有可能更好地运用表达自由的权利[20]。这给知识分子言论思想的自由提供了客观的物质载体,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知识分子在言论思想上可能获得解放,从而取得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如果说知识分子言论思想的功能在于看清过去与预测未来,从而更好服务于人类,那么大数据时代将颠覆这种思路。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的思考,而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21],并根据预测的结果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数学运算与海量的数据的结合运用本身体现出大数据时代的流动性特质,它不仅消解了知识与思想的过剩状态,还将知识与思想数据化之后推动着技术智能化发展,让数据替知识分子进行“发言”,而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在于发掘数据本身价值与运用数据创造更多价值。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交流的公共舆论空间将被同质化为公共数据平台。这个公共数据平台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把它传播出去,是很多人努力追求的目标,互联网使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句话,网络使少数人垄断信息和文化的圣人时代宣告结束。”[22]这体现了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交流的公共舆论的自由流动性。
大数据时代知识分子公共舆论的自由流动性特质所引发的变革,倒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在此巨大时代转型中重获自由的批判精神、正义感与社会良知,返回各个公共舆论场合中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与批判,并将再次深刻、积极地影响社会大众,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将重获公共性。
参考文献:
[1][2][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齐萌.论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主体性——兼议福柯与德里达消解主体性之异同[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4).
[5][7]徐艳.文化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J].学术探索,2004,(9).
[6]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黄万盛.知识分子困境与公共性危机[J].理论探索,2008,(6).
[9][10][11]黄欣荣.大数据哲学研究的背景、现状与路径[J].哲学动态,2015,(7).
[12][13]汪传发.资本:人性与物性的双向追问——全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述评[J].哲学动态,2006,(10).
[14][15]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6][17][19]韩亚光.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3).
[18]杨凤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4).
[20]兰军.互联网特征的悖论[J].世纪桥,2010,(23).
[2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扬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2]李河.得乐园·失乐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