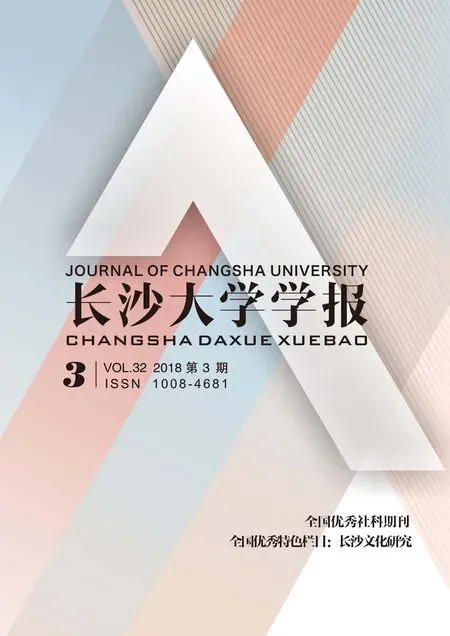家与狱之间的身份探寻
——《土生子》主人公别格身份建构的叙事空间解读
王 飞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土生子》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在伯纳德·贝尔所著《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TheAfro-AmericanNovelandItsTradition)一书中唯有《土生子》的作者理查·赖特出现在了章节的大标题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部小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社会、文化、政治效应,更在于其对此前黑人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此后黑人小说的影响和启示。《土生子》与其他美国黑人小说共享一个鲜明的主题——黑人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和建构。学界对《土生子》的研究视角不同、方法各异,也有涉及其主人公别格身份问题的探究,但鲜有通过空间叙事研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解读。本文便是基于后殖民身份建构研究对其进行空间叙事解读的一个尝试。
一 叙事空间与身份建构
空间概念在西方传统叙事学研究中长期备受冷落。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正如宁一中在比较中西小说的差异时所指出的,与中国小说注重叙事空间不同,西方的小说更注重叙事时间[1]。但空间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其实也为部分文论家所论及,如巴赫金在其小说理论中提出的“时空体”(chronotope)概念。后经典叙事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则表明,空间概念在叙事研究中占据着愈加重要的地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
在西方,空间概念之所以一直会被忽略,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叙事学家仅将叙事中的空间看做一个物理概念,而空间概念却同时也包含了社会文化内涵。由于文学批评界形式主义的退潮、文化社会因素在叙事研究中的回返,空间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空间概念和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瓦格纳(P. L. Wagner)在《重读文化地理学》(Re-readingCulturalGeography)一书中认为,地理经验、空间分布和自我认同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影响之关系[2]。空间划界其实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划界,而生活在一种相对而言闭合的空间中的个体或者群体自然而然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身份认同与建构。空间既是一个实体内部的东西,如一个国家中的公民身份、甚至是个人的身体空间;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实体与其外部间的关系对比状态,如不同社区、不同种族之间的权力协商。空间概念的这一特点其实与身份认同、自我(他者)建构以及主体(间)性的概念是一致的。
闭合空间是身份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空间跟时间一样是一个延续性的概念,即是说,某一空间总是会与其相邻或相关的空间发生关系。在空间与空间发生关系的时候,也便出现了空间越界或者“空间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空间解域概念是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及《千座高原》(AThousandPlateaus)中首次提出的,是指空间越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解码。正如张在新所言,空间解域的结果便是背叛主流社会的道德,打破文化代码固有的约束,并放弃在社会框架内约定俗成的身份和地位[3]。根据后殖民研究,身份是永远处在建构过程中的,其会在闭合空间形成的初现身份基础之上,随着空间解域而逐渐建构。而闭合空间、空间解域与身份建构的关系对于注重空间叙事的美国黑人文学来讲更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二 黑人之家:闭合空间中的身份抗争
从《土生子》一书的标题“native son”可以看出,赖特此书有三个重点:其一,与种族相关的空间叙述;其二,与空间相关的身份建构;其三,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此书分为三卷,即“恐惧”(fear)、“逃离”(flight)和“命运”(fate),与之相对应的有三个空间场景,即别格·托马斯的黑人之家、道尔顿一家的白人之家以及别格杀人后沦入的监狱。黑人之家是一个闭合空间,为别格提供了单一的初现身份;进入白人之家的行为是为空间解域,通过空间越界别格获得了新的视角;而监狱为别格提供了运用这种新视角进行反思的机会,也即一种有助于其身份建构的心理空间。
家在《土生子》一书中有多重含义:首先,书中既有黑人之家也有白人之家;其次,家在其空间含义来讲,范围由小到大,从家、房子、家庭、社区推进至国家;再次,家既有其空间含义也有其心理含义。正因为家有空间与心理的双重含义,赖特才能够将空间意义上的家和心理意义上的监狱联系起来。小说中的监狱不仅是在杀人后别格身陷囹圄的监狱,连本应该给别格带来温暖的黑人之家、为其提供工作的道尔顿白人之家都成了监狱。在空间意义上,别格各个层次的黑人之家都是闭合空间(而空间闭合也正是监狱的特点),通过进入白人之家以及杀死白女孩玛丽、黑女孩贝西等事件,别格进行了激烈而悲壮的空间解域,最终监狱里基于外在及内在对话的反思促成了他反本质主义身份的建构。可以说,通过空间解域与身体暴力,别格将家和监狱的有形空间概念进行了心理空间的置换,而此种置换正使他从闭合空间中形成的初现身份中解放出来,解构单一的本质主义身份,进而建构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文化身份。
小说开篇描述了别格的黑人之家,空间上拥挤、狭窄、黑暗,空间的狭小又带来别格一家人的心理“羞耻”感。而通过白人女孩玛丽的描述,黑人的房子酷似监狱。小说中到处出现的“墙”的意象更是强调了空间的狭窄和对房子里居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挤压。与之相似的“帷幕”意象,象征隔绝,体现了别格与自己家庭的异化、以及黑人家庭内部的分裂。别格憎恨黑人之家,说明他厌恶闭合的黑人家庭空间;他憎恨自己,说明他想要解构他的闭合的黑人身份。墙和帷幕围起来的黑人之家是一个狭小、拥挤的闭合空间。与安于现状的其他家庭成员相比,别格对这个闭合空间充满愤恨,决不允许自己在身份方面与其进行认同。他的准暴力解域行为其实首先是从其家庭成员身上开始的,他对他们冷漠甚至残暴。他将家的空间概念强行打碎、将家庭的亲情关系毅然瓦解,使得自己初现的单一黑人身份得以解放,进而为他的身份探寻铺平了道路。
黑人社区被限制在国家、城市的一个狭小角落,更是一个十足的闭合空间。别格对其的空间解域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在内部的破坏、向外部的逃离。他与这些伙伴平日里 “总是抢黑人”[4],破坏黑人内部团结。白人在空间上对黑人的限制,使得别格们只能在黑人社区内部以抢劫、殴斗等暴力方式来发泄对白人的仇恨。黑人社区里也到处是“墙”的意象,明确指出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设置的障碍。杨卫东认为,“‘墙’的意象一而再地出现,表明种族歧视的美国对于黑人来说是毫无自由可言的一所大监狱”[5]。黑人们被限制得无从选择,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教育、居住地局限在“城市的一个角落”[6]。一方面,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得别格及其黑伙伴成了黑人社区内部的罪犯;另一方面,别格们的犯罪行为却正好成了他们对黑人社区闭合空间的解域实践。而与其他黑伙伴们相比,别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最终通过给白人道尔顿一家做家庭司机而跳出了闭合的黑人社区空间。在逃离黑人社区前,别格的暴力指向了自己的犯罪同伙——黑人伙伴。别格对黑人之家的解域是逐步进行的:首先是与自己家庭成员的言语决裂;其次是与黑人伙伴的暴力冲突;最后是对女友黑女孩贝西的残暴杀害。他的解域行为,从物理意义上讲,是由家庭到社区再到种族;从情感意义上讲,是从亲情到友情再到爱情。
身份认同除了与物理空间关系密切,还与特定的物理空间中所产生的情感状态息息相关。心理学研究者给身份建构做了如下定义:“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7]。小说第一部分的标题 “恐惧”其实已明确指出:在黑人之家时的别格被无所不在的恐惧感所笼罩。恐惧是他的生存现状,也是他几乎所有行为的深层原因。恐惧这种内心感受,一方面体现了别格对闭合的单一身份的反抗(因为这种闭合的身份是具有种族本质主义的白人和黑人强加在他身上的);另一方面预示了他的身份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身份探寻。恐惧的黑人之家实际上成了闭合的监狱空间,这种空间势必给别格建构一种罪犯的初现身份,这种恐惧心理正是其有形的黑人之家空间向情感的“暗恐”(uncanny)监狱空间转换的推动力,与之相应出现的是别格初现的单一黑人身份认同向多元的文化身份认同转变的肇端。
三 白人之家:空间解域中的身份探寻
正如对于黑人来讲,黑人之家是个闭合空间;对于白人来讲,白人之家也是个闭合空间。闭合空间形成的只能是单一的本质主义身份。而别格在小说中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协商者、一个越界解域者。在黑人之家中的黑人和在白人之家的白人,都不能拥有身处边界区域的别格所具有的双重视角。从黑人之家逃离、进入白人之家,是别格对闭合空间解域的第一步,即解域了黑人社区空间。而他进行空间解域的更重要的一步却是对白人空间的解域。白人之家的舒适空间开始时给别格的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却逐渐显现出其监狱般的闭合性质。
与他对于黑人之家的经历顺序相反,别格经历白人之家的过程是由外向内的:从社区、房子再到家庭。与别格的黑人之家截然相反,白人社区安静、宽敞,白色的房间明亮、宽大,墙壁平滑,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房间,在这里别格甚至也有了自己的房间。空间理论认为,房间是一个人扩大了的主体,也就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别格一进入白人之家,便有了自己的房间,这一点使得别格误以为自己有了更为体面的身份。但是,别格没有像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s)里的主人公配克拉那样进一步沦陷,天生黑皮肤、却想戴白面具。别格没有被空间舒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深知这张惬意的白面具是虚构的、危险的。事实上,舒适的白人之家却是别格的另一所闭合的监狱,而正是在这所白人构成的监狱中,别格成了真正的杀人犯。进入白人之家时,他不理解道尔顿夫妇的语言使得自己成了一个“外国人”和他者,这种不解在别格内心产生不安、焦虑、紧张甚至是恐惧。在黑人之家时别格一直压抑的恐惧感在白人之家以更为强烈的方式回返了。
别格进入白人之家意义重大:第一,与道尔顿的白人之家相比,别格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黑人之家,通过两个家的对比、在家的边界思考自己的身份;第二,白人之家舒适的陷阱使得别格警醒,继而对白面具的身份陷阱进行解域;第三,正因为进入了白人之家,才引出后来别格杀害白人女孩玛丽和黑人女孩贝西的事件,而两个杀人事件,通过对黑白身体的消灭、对友情爱情的斩杀,达到了对黑白两个空间的终极解域。
别格的空间解域行为常常是和他的恐惧感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焦虑、恐惧感是身份危机和身份探寻的表征。而别格在白人之家的恐惧随着盲人道尔顿太太在厨房的突然出现而加深,也正是道尔顿太太深夜出现在女儿玛丽房间使得搀扶醉酒玛丽进房的别格恐惧达到了顶点,这是整部小说恐惧感的巅峰,也正是这一恐惧感让别格失手误杀了玛丽。失手杀死玛丽,使得别格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友情、终止了他较为体面的职业生涯。而由于担心女友贝西有可能会泄露自己的犯罪秘密,别格用砖头在黑暗中砸碎了她的头。杀死玛丽是失手,而杀害贝西却发展成了蓄谋。对于空间/身体的解域,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身份的术语,从自在状态发展到了自为状态[8]。
杀死玛丽和贝西的解域意义在于,首先,玛丽代表了白人身体空间、贝西代表了黑人身体空间,两个身体空间的消亡,预示着与之相连的两种对立的本质主义身份的消解;其次,玛丽代表了跨界友情、贝西代表了界内爱情,而在黑白两个空间仍然处在闭合状态时,这种友情和爱情都是不能开花结果的;再次,玛丽代表了民族、贝西代表了种族,如果还存在单一的本质主义身份的话,美国民族的黑白种族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玛丽代表横向的空间关联、贝西代表纵向的历史传承,即使有像道尔顿这样的白人对黑人的支持,只关注横向的空间关联、不顾纵向的历史文化因素,所谓的种族友好也都是不可靠的。
通过进入白人之家的空间越界,尤其是通过暴力杀人解构身体空间,别格激烈、悲壮甚至残暴地实施了他对黑白两个闭合空间的解域行动。但对两种身份的解构,必然会给他自己带来一种零身份状态,也即身份危机。在身份处在危机之中时,别格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监狱中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自身的反思,对身份进行了积极的建构,向死而生。
四 监狱中的对话:心理空间中的身份建构
小说的前两部分“恐惧”、“逃离”中描述的是一个孤独的别格形象,而且他的孤独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而愈演愈烈。但是小说的第三部分“命运”却是把别格置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此时的监狱外在来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对话场所,内在来看是通过交谈对别格的一次心理治疗。通过与其他人的对话以及深入的内心思考,别格在心理空间中重建了一种反本质的多元身份。
监狱中别格的身份建构是一个曲折、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的内心成了一个斗争场所,众人与他的对话内容时而起到消极作用、时而却产生积极影响。而直到小说结尾别格的多元身份才真正得以重建。白人警察伯克利用“甜言蜜语”欺骗别格,是对别格身份建构的一个沉重打击,使得他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而对所有后来的对话者都拒之于千里外。此时的别格重又变得“孤独”。相反,黑人牧师对别格的布道使得别格开始思考爱与恨的问题,“对自己人的爱以及对别人的恨同样使他有罪恶感”[9]。爱与恨其实也即归属感、身份认同的问题,单纯对黑人的爱以及对白人的恨在身份认同方面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反本质多元身份的建构,首先要排除心中的仇恨,其次是要扩大自己爱的范围,也就是既要爱黑人也要爱白人,建构多元身份认同。与共产党员简的对话使得别格开始将白人视作“人类”,此时别格终于意识到黑人、白人同属人类,说明他的归属感在范围上有了扩展,与开始时黑白对立的本质主义身份认同产生鲜明对照。行刑前别格与麦克斯的对话是促成别格身份建构的最终推动力。虽然麦克斯不是个合格的听众,但是他的话语促使别格开始深入思考自己以及别人的身份。
临刑前别格的最后两句话是:“告诉我妈,我没事”,“代我问先生……问简好”[10]。从开始的痛恨、厌恶、抛弃黑人之家,到现在对黑人母亲的关心;从开始害怕、仇视、不信任白人,到现在与白人发生融洽的关系。别格的这两句话明确告诉我们,在身份认同方面,别格不仅回归了黑人认同,而且与白人在人性认同上也达成了一致。所以,我们可以说,监狱中的别格在与他人对话、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在心理空间中完成了反本质多元身份的建构。
身份建构是几乎所有美国黑人文学历久弥新的主题,因为美国黑人天生具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谓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csiousness),或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流散意识”(diasporic consciousness)。特殊的生活现实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而如何应对生活以及这样的意识,其实就是他们的身份探寻实践。黑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及结果千差万别,有的回归黑人传统、有的强行带上白面具、有的则建立与世隔绝的黑人乐园。而别格通过逃离、暴力等方式对闭合空间中形成的本质主义身份进行空间解域,并最终通过与众人对话在心理空间建构的多元身份体现了作者赖特所持的后现代反本质的身份观,对于美国黑人文学创作、美国黑人身份建构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宁一中.中国古代评点中的“结构”与西方结构主义的“结构”之比较[J].中国外语,2007,(9).
[2]Wagner P L.Culture and geography:Thirty years of advance[A].Re-reading cultural geography[C].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4.
[3]张在新.笛福小说《罗克珊娜》对性别代码的解域[J].外国文学评论,1997,(4).
[4][6][9][10]理查·赖特.土生子[M].施咸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杨卫东.规训与惩罚——《土生子》中监狱式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J].外国文学,2002,(4).
[7]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
[8]Woodward K.Understanding identity[M].London:Arnold,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