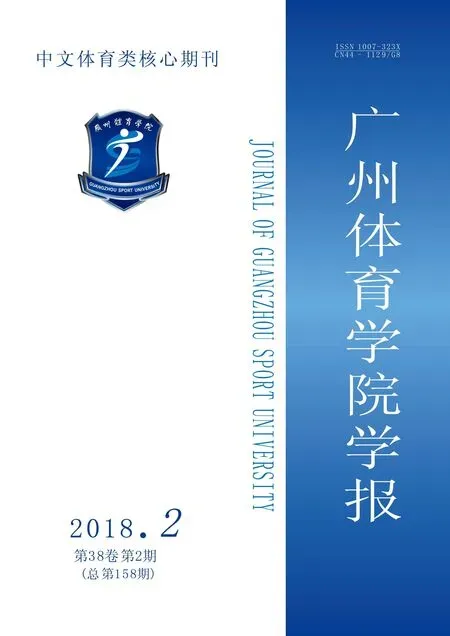户外运动生涯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王春光,李贞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体育系,广东 珠海 519088)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后,户外运动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开来,短短几十年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很普及的运动。尤其是近些年来,户外运动不仅在项目上发展迅速,更是在内涵上发展成为人们提升生活质量的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成为人们日常消遣、休闲娱乐、节日度假以及外出旅游的主要选择。根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参与户外运动的人口为1.4亿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49.2%。[1]根据COA的统计,2014年我国有3.8亿人进行体育运动,占总人口的27.79%,进行户外运动的1.9亿,占总人口的13.9%,其中进行户外休闲运动及徒步旅行的人口达1.3亿,占总人口的9.5%,年龄分布集中在26~40岁,约占户外运动旅行人口53%,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大专以上学历者占80.4%。[2]
随着我国户外运动人口的不断增长,户外运动旅行动机和目的地研究也随即提上日程。如何更科学地预测和了解户外运动旅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使目的地管理者能够通过对不同户外群体的动机模式快速地做出反应,有效地指导不同发展阶段的户外体育旅游目的地的规划、管理、经营和发展,已成为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运动人群多样性的需求,和研究方法上的难度,并且不同项目、不同文化背景下所构建的动机模型也不尽相同,因此体育动机的研究是体育跨学科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Moscardo等人(1996年)认为,人类表现出来的各种出游模式是目的地决策过程的结果,而决策过程又受到参与者动机和背景的影响。[3]因此,动机激发和产生了户外运动者出行和选择的行为,进而共同决定了户外运动旅行目的地的兴衰。对体育旅游目的地和管理机构来说,缺乏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识别和测量户外运动者出行和目的的动机特征,同时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划分户外人群的目的动机。但Pearce和Lee提出的旅行动机生涯模式(Travel Career pattern)理论,不仅较系统地整理了前人的研究理论,并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多种动机因素之间的动态联系,为我国户外运动旅行动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另外,结合Crompton提出的游憩目的地的认知模型,进一步将户外运动旅行群体的特征和动机与目的地联系起来,通过对户外运动者的年龄特征、旅行经历等简单有效的分析和预测其行为爱好与特征,从而也为户外运动旅行目的地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
2 理论依据
2.1 旅行生涯模式理论
旅行生涯模式最早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心理学家菲利普·皮尔斯(Philip Pearce)提出的旅行生涯阶梯(Travel Career Ladder)模型(简称TCL模型)。[4]

图1 旅行生涯阶梯模型(TCL模型)
旅行生涯阶梯模型以层级形式将需求动机直观地展示出来,如图1所示,放松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其次是安全保障的需求、关系需求、自尊与发展的需求,最高需求则是自我实现需求。TCL概念模型将旅行生涯假设为类似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模型,主要观点是人们的动机随着经历的不断增加,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与满足。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会系统性地经历每个阶段,一般情况下都是沿着阶梯需求由下至上逐步发展,但也可能因为健康、收入等因素而较长时间稳定在同一层次上,因此可以科学地预测其动机模式。在旅行生涯模型提出的同时,Holder对户外滑雪旅行者进行了实证性研究。Holder根据滑雪经历的多少将研究对象分为4类,分别对其5个动机需求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滑雪经历的旅行者对不同需求水平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经历较多的研究对象更清楚自身的需求,同时对运动的体验要求也更高,而满意度却相对较低。[5]
为进一步完善TCL模型,Pearce和Lee对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和韩国等东方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和情境下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和情境下的研究者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TCP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的14个动机因素中[6],处于较高层次的研究对象更重视“目的地涉入”和“追求自然”等外部导向的动机因素;处于低层次的受访者则更重视内部导向的动机因素,例如“安全感”、“发展”、“独立”和“浪漫”等。动机因素划分为两类型,一类是例如“新奇”、“放松”、“关系强化”等普遍存在的动机因素;另一类是例如“刺激”、“隔离”、“社会认同”等不太重视的动机因素。TCP理论框架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后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

图2 旅行生涯模型(TCP)理论框架
如图2所示,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涵盖了3个动机层,各层都由不同的动机因子组成。普遍动机位于模型的核心层,是所有动机中最核心和重要的部分;中间层次为旅游动机,是内部导向转为外部导向的动机,也是系统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最外层是相对稳定的动机,也是相对不太重要的部分。
2.2 游憩目的地认知模型
Um和Cromptom(1990)提出的游憩目的地认知模型(见图3),基于动机是人们对目的地特征及情境限制的认知角度,区分了“认知”和“动机”、“态度”,并提出在目的地的选择中,“动机”和“态度”比“认知”的影响更大。[7]

图3 憩息目的地选择模型
Cromptom认为人们对目的地的认知过程是内外变量联合作用的结果,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的形成受到外部变量和旅行者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8]游憩目的地认知模型用“动机/态度”的研究取代了对“形象/认知”的研究,对目的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为止对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划分基本都在沿用憩息目的地认知模型。因此,在旅行生涯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憩息目的地选择模型理论,能够更科学地判断出行动机和行为特征,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规划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3 研究过程与方法
研究初期对户外运动协会成员以及凤凰山野外徒步露营地户外运动者共计2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记录和录音通过Nviov 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发现访谈者提及到的动机因素远不及TCP涵盖的因素和内容,因此决定完全引用Perrce的旅行生涯模式动机量表。这样做不仅可以研究获取国内户外运动者自身的动机需求,更能挖掘国内户外运动者更多隐性的动机信息。
研究实施从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在考虑到户外运动旅行者出行平衡性及数量、特征的前提下,分类型选择国内户外运动者集散地云南果然青年旅社、成都老宋国际青年旅社、济南乐沃营地、晋祠滑雪基地、九州岛水上基地,对户外运动者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收集语言资料20份,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57份,其中有效问卷534份,有效回收率89%。通过SPSS 19.0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通过Nviov 11分析软件进行访谈数据管理和处理,获得户外运动者出行动机和户外经历等相关数据。
表1户外运动旅行经历水平交叉列联

4 结果与讨论
4.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543位研究对象中,男女比例为59.2:40.8;有35岁以下者42.7%,35岁以上者为57.3%;学历程度均较高,有22.5%是硕士以上学历,有50.1%为本科学历;收入情况集中在2000至4999元、5000至7999元、8000至14999元三个档次,分别占27.3%、27.7%和22.9%,占到总受试者的77.9%。国内户外运动旅行经历者较多,占71.4%,国外户外运动经历者较少,占28.6%。如表1所示:
在特定值大于1的条件下,根据14个需求因子分析71个动机测量项,并保留了载荷大于0.4的测量项来分析和解释14个需求因子。依据α系数大于0.7是信度监测较为可靠的结果,当测量项较少时α系数可适当降低至0.6。结果表明,所测量的14个维度中有仅有“独立自主”动机维度的α系数为0.67,其他13个动机项α系数均高于0.7。
按照平均值由高到低的排序次序依次赋值,再根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序后发现(见表2)。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新奇”和“自我发展”是户外运动者最重要的三种出行动机,其次是“自我实现”、“目的地涉入”和“逃离/放松”,而“独立自主”、“安全感”和“浪漫”是最不重要的动机。这个结果中,与TCP理论中动机因素重要性排名比较,“自我发展”和“社会认同”项排名上升,“自我发展”提升为最重要的动机因素,“社会认同”由原来并不重要的动机因素,提高至相对重要的动机因素,这可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专业性较强户外运动的特殊群体的原因。在其他动机因素名排列中,也有个别排序发生了较小的变化,但与TCP理论的动机重要性排名基本相同或非常接近。
4.2 动机、经历水平和年龄分析
在形成旅行动机模式的过程中,经历和年龄共同影响出行动机。[9]通过对国内户外运动经历、国外户外运动经历和年龄3个变量进行分析,将3个变量转换为0—1的标准化数据,并通过样本数据K值聚类分析,一类是高户外运动经历群体,有261人,占49%,这类群体国内外户外运动经历较多,年龄也偏大,另一类是低户外运动经历群体,有273人,占51%,这类国内外户外运动经历较少,年龄也偏小。同时,采用默认的判别分析方法,将三个变量一次性放入函数来估计判别函数,结果显示特定值为2.83,相关系数为0.87,有较强的相关性;Wilk's Lambda值为0.24,卡方检验值为932.00,说明两类样本之间的区分度也较好,分组区分度非常显著。为确定那个变量的作用最大,采用判别函数系数和载荷进行分析。
4.3 户外运动旅行动机分析
通过判别系数与判别载荷分析发现(见表1、3),发现国内户外运动经历是最重要的变量,随后是国外户外运动经历和年龄。户外运动经历和水平较高者,年龄也相对较大,学历也较高,占70.9%,男性比例为68.9%,月收入水平在5000元以上者占82.4%,年均出行9次以上者占78.2%,其中有过国外户外运动经历者占54.4%;户外运动经历和水平较低者中,男性比例为61.2%,月收入水平大部分集中在5000元左右,仅有12%的人国内户外运动经历年均9次以上,有过国外户外运动经历者更是少数,仅占4%。
表2户外运动旅行需求因子分析

注:Mxp.表示均值;Exp表示方差解释量;保留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变量

表3 典型判别函数系数与载荷
在经历水平对动机影响的研究中发现“自我实现”、“逃离/放松”和“安全感”三个动机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11个动机因素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高户外运动经历者更注重“自我实现”的动机因素,而低户外运动经历者更注重“逃离/放松”和“安全感”动机因素。户外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虽然较短,但随着经济水平和国民意识的提高,尤其是一些专项户外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和建立,户外运动旅行与目的地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很多群体和个人已经把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随着健康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事业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或经济收入较好的人群,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
4.4 户外运动生涯模型的构建
根据不同的户外运动经历和不同的年龄组,划分“经历少,年龄小”、“经历少,年龄大”、“经历多、年龄小”、“经历多、年龄大”4个不同的动机组,为进一步区分动机与年龄分别对动机模式带来的影响,明确4组动机间的差异性,对4个组的动机均值计算,利用组间均差值与总均差值的差,得出4组交叉比较数据,将2次比较值均高于平均水平的设定为该组的核心动机,仅有1次高于平均水平的为中间层动机,剩余动机为外围动机。如图4所示:

图4 户外运动生涯模型
新建立的户外运动生涯模型,针对动机因素在不同年龄和经历的群体间的差异,利用不同户外运动经历和年龄划分出4类不同的户外运动生涯模式。户外运动经历多,年龄大的人群更重视“自然”、“怀旧”、“隔离”和“自我实现”;户外运动经历多,年龄小的人群更重视“新奇”、“刺激”、“目的地涉入”和“社会认同”;户外运动经历少,年龄大的人群更重视“逃离/放松”、“安全感”、“关系强化”、“独立自主”和“浪漫”;户外运动经历少,年龄小的人群更重视“社会认同”和“个人发展”两大动机因素。结合Um和Cromptom提出的憩息目的地选择模型,对于发展初期的户外体育旅游目的地来说,主要吸引的目标群体是户外运动经历丰富且具有冒险精神和自信心理的人群。Plog的游客心理特征模型将这类型群体定义为“异向中心型”,也可称为“冒险型”,[10]因为这类型群体更重视“新奇”、“刺激”、“目的地涉入”和“隔离”。如果目的地有较好的自然资源,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和体育文化特色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较小的资本投入,吸引经验丰富,年龄较大的户外运动者,因为这部分群体更注重“自然”和“隔离”。如果目的地具备一定的特点和体育文化特色的情况下,可以从“新奇”和“目的地涉入”的角度来进行规划和设计。对于发展时间较长,户外体育旅游建设较成熟的目的地来说,应该更多地关注户外运动经历较少的群体,这类型群体更关注“个人发展”、“社会认同”、“目的地涉入”、“逃离/放松”、“独立自主”、“安全感”和“浪漫”等动机因素。通常这类型群体属于“自向中心型”和“近自向中心型”也可以称为“依赖型”或“近依赖型”。[11]如果目的地选择的服务对象是经历少、年龄小的群体,就应该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认同”需求方面加以满足,如果目的地选择的服务对象是经历少、年龄大的群体,就应该从强化目的地的体育文化内涵发展和加强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考虑。
5 结语
在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对户外运动生涯模型的构建,及时有效地填补了户外运动研究方面的空缺。不仅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户外群体运动生涯特征,系统地分析不同户外经历和年龄群体之间选择和参与动机因素,准确地把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户外运动群体的心理动机和特征,为更好地规划户外运动者的运动生涯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在体育旅游和体育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结合Um和Cromptom提出的憩息目的地选择模型,使目的地管理者能够通过对不同户外群体的动机模式快速地做出反应,有效地指导不同发展阶段的户外体育旅游目的地的规划、管理、经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OutdoorIndustryAssociation.调查显示美国近半数人口热衷参与户外运动[EB/OL].http://www.51luying.com/portal.php?aid=5771&mod=view. 2015-01-19
[2] COA.数据显示中国1/10人口加入户外运动行列女性比重增加[EB/O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261656.html.2014-07-31
[3] 李天元. 旅游目的地定位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 旅游科学,2007(4):1-7
[4] 周玲强,李罕梁. 游客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发展: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的拓展和应用[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31-144
[5] 李罕梁. 国内游客的出游需求和行为影响机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6] 吴茂英,Philip L.Pearce. 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研究中的应用[J]. 旅游学刊,2014(1):39-46
[7] D.Fodness.Measuring Tourist Motiv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4,21(3):555-581
[8] 张波. 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三种典型模式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2006(7):69-74
[9] 岳祚茀. 旅游动机研究与旅游发展决策[J]. 旅游学刊,1987(3):32-36
[10] Um,S. & Crompton,J.L.Attitude Determ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0(17):435
[11] Um,S.Pleasure Travel Destination Choice[J].VNR's Encyclopedia Of Hospi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