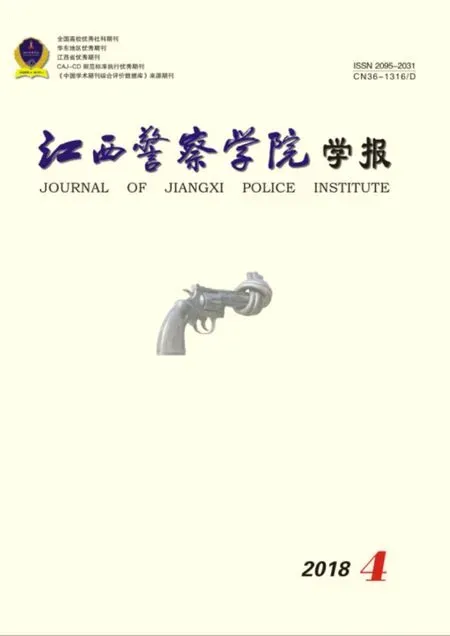将“情绪失控”纳入限制责任能力可能性思考
熊子楠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英国刑法理论中的情绪失控概念
英国刑法里,谋杀和过失杀人两种罪名的客观要件(actus reus)相同:非法致人死亡,主要区别体现在主观要件上(mens rea)。谋杀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杀人或者致人重伤。在过失杀人中,非故意的过失杀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并不存在故意杀伤的意图。即使满足了谋杀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法院仍然可能因为符合以下两种之一的情形——被害人的挑衅(provocation)和杀人者的精神失常(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将谋杀罪减为过失杀人罪。
情绪失控(Lost of Control)是英国于 2009年颁布的《法医与审判》法案(Coroners and Justice Act)第56节第七款中新提出的概念,用于替代原先的挑衅(provocation)作为新的一种减轻罪责辩护事由(partial defence),将因威胁而恐惧、绝望纳入到情绪失控的范畴当中,是指行为人出于情绪失控杀人的,将承担过失杀人(manslaughter)的刑事责任而不是谋杀(murder)的刑事责任①Section 56(7)of the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
根据英美刑法理论②参见 Denis·J·Baker所著《text of criminal book》。,情绪失控的主要原因是行为人的情绪处于极度愤怒或极度恐惧、绝望当中,出于愤怒而情绪失控比较好理解,有一句谚语称:“往往当感性与冲动失去动力时,理性才自此接管了人本身③Reason only controls individuals after emotion and impulse have lost their impetus。”,认为行为人因暴怒而失控时的情绪使其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出现了大幅降低,自由意志遭到了蒙蔽,而事后恢复理智时,行为人往往会对失控时实施的杀人行为表示后悔之情。
关于出于恐惧而造成的情绪失控,例如在一个家庭暴力案例中,受虐者(多以女性为主)不堪受辱杀死了施虐者,原因不仅是施虐者长期以来的暴力行为,还有施虐者在实施暴力行为后,对受虐者进行了下一次施虐的预告后,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可预期的下一次施虐预告成为了导致受虐者情绪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
情绪失控的作为杀人的减轻罪责辩护事由与情绪失控在其他犯罪中的减轻事由不同,作为法定的减罪事由,有着明文的严格适用规定。法案第54节①Section 54 of the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规定:
第一款 当被告人一人或作为犯罪团伙之一杀人时,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将不承担谋杀的罪名:
第一项 被告人的行为或过失行为杀人源于被告人的情绪失控。
第二项情绪失控有发生的合理前提。②Section 55 of the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
第三项 假设与被告人同性别年龄的、具有正常忍耐力与自制力的一般人处于同等条件下,可能同样会情绪失控。
第二款 第一款第一项中的情绪失控是否是短暂的、突发性的在所不问。
关于被告人杀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情绪失控理论曾遇到质疑——情绪失控(尤其是因恐惧而失控)是否应当纳入自我防卫的范畴。即如果行为人因恐惧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属于自卫的话,自卫在英国刑法中属于完全免除罪责辩护事由,被告人将免责并无罪释放,行为人杀伤被害人的行为就得到了正当化(justified)。英国学者柯林·霍华德③Colin Howard,Criminal Law,(Sydney:the law book company ltd.,1977)at 79。认为,在被害人有相当过错的情况下,定被告人最严重的谋杀罪名是不公平的。而学者安德鲁·阿什沃思④Andrew Ashworth,“the doctrine of provocation”(1976)35 Cambridge L.J.292。认为,在被害人进行了有严重过错的挑衅行为情况下,被告人的杀人罪行方面存在着部分正当性。而学者丹尼斯·J·贝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提出观点——就罪行方面个人不能被部分杀死,被告人不可能辩称其杀害被害人的某一部分行为是正当的。认为正当化事由出于其排斥性只能是一有俱有,一无俱无,不存在“部分完全免责事由”。然而就罪责方面,贝克认为被告人情绪失控时主观上的杀害被害人的故意是有正当理由的,由于被害人错误的、具有相当程度的挑衅行为导致被告人丧失了理性的控制能力从而情绪失控,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杀害了被害人。
在英国,在除谋杀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中,情绪失控也是减轻罪责的事由之一,由法官进行裁量是否适用,情绪失控没有使用的限制,即使是一名袭击他人的醉汉,法官在裁量时也会考虑其有情绪失控的情节。
二、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罪责能力论述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责任能力被表述为“对特定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罪责非难,认为其行为是有责的先决条件时他具备正确认识社会要求并以该认识而行为的一般能力[1]”,简称为社会行为能力或符合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能力,只有当行为人在行为时具备该能力,才能认定该行为是有责的反社会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缺乏“社会适应能力”,则不具备符合义务的动机构成,不能期望其符合规范的行为,讨论行为人其行为的罪责问题就不再有意义了,因此责任能力是确定罪责的先决条件。
(一)无罪责能力中的情绪爆发和失控
根据《德国刑法典》[2]第20条⑤行为人行为时,由于病理性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错乱、智力低下或其他严重的精神病态,不能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或依其认识而行为的,不负责任。和第21条规定,学者克劳斯·罗克辛认为,深度的意识错乱这个概念与病理性的精神障碍并立,说明该概念应是非病理性的、通常心理性的意识错乱,其内容有基于筋疲力尽、过度疲劳、睡意朦胧、处于催眠状态中或状态后的行为,特别包括了情绪激动的特定形式。与之相对的,处于正常裁量范围内的意识错乱都应当予以排除[3]。那么,“意识错乱”概念要与病理性精神障碍等价,那么“深度的”这个词所包含的程度应当强到能够破坏或能够动摇有关人的心理结构的水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以强烈的情绪波动乃至情绪失控为基础的行为人是否应当被视为无罪责能力,也引起了当时社会和法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一问题随着精神病学的精神疾病概念的推广影响下被给予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仅有几个例外的案件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深度意识错乱的强度评价也非常之高:一名处于最激动状态下进行行为的行为人也能够存在德国刑法第20条规定意义上的意识错乱,这种受到高度刺激所产生的“情绪激动的爆发”排除了行为人对当时行为的操纵能力,甚至瓦解了行为人的理性控制机构,近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高度,从一般预防的基础上开启的无罪可能性也被认为开了一个宽广的缺口,人们认为适用的解释不是位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遥远地带,而是在犯罪的正中心开出了一片空白的“安全区”,扩大了对“缺乏社会适应能力”人群的定义,并且担心将来可能会出现法官在相当数量的杀人犯罪中,宣告行为人无罪的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状态,因此最高法院提出强调情绪激动的无过错性来限制深度意识错乱的无罪责能力事由的滥用。
罗克辛提出了支持的意见:
1.不是任何情绪激动的情况都符合“深度意识错乱”,“深度意识错乱”的认定有着严格的认定标准。
2.一种与行为构成有关的罪责原则,在各种冲突的情况下,只要人们不是自己违反法律的文字来牺牲预防性利益的,就仅仅是可信的。
3.由于无罪责能力的无罪会支持犯罪的论断时没有说服力的。
4.强调过错性的重点,同时也是为了否定一名情绪激动的行为人基于原因自由行为而行动的无罪性,使其承担刑法上的责任,因为情绪激动的构成行为往往是一种长期持续冲突的结果,大多数体现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出现、加剧、爆发,在前两个阶段中,行为人内心经历的委屈和紧张仍处于孕育转化之中,在爆发阶段才会导致理性控制能力的丧失和情绪激动的爆发。而在加剧阶段,如果行为人在与自身的攻击性倾向作斗争的同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去防止可能发生的情绪爆发而是放任其爆发后果的产生,那么这种结果的产生就能够成为刑法责任性的基础,从而拒绝其情绪爆发的无罪。
学者雅各布斯持相同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罪责应当是一种一般性预防的归咎,有目的决定,即目的给予了罪责概念以内容,如果情绪爆发的状态要被归咎责任,那必须是在对冲突有其他的处理方式的可能性时才可允许,否则,不存在使得法共同体(Rechtsgemeinschaft)期待落空的后果。因此,如果在情绪爆发的状态之中不存在其他处理方式的可能性时,行为人无法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而导致情绪爆发与爆发后果的产生时,其无罪性才能得到认可。
(二)重大减弱的罪责能力中的情绪失控
重大减弱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仍有能力理解构成行为的不法,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行为。其理性控制能力的分级以自然人能够轻松或困难地被规范所推动,在此概念下的、此种控制能力下产生的罪责通常都得到了减少。因此德国刑法第21条①行为人认识行为违法性的能力,或者依其认识而行为的能力因第20条规定而显著减弱的,可依第49条第一款减轻其刑罚。创设了一种减轻处罚的基础,并且在实践中,这个条文的出现频率远高于无罪责能力的无罪,并且在第20条的四种情况②分别是在轻微的麻痹性或者精神分裂性的损害中;在开始动脉硬化症的或者衰老的痴呆性表现中;在癫痫病或智力低下的轻微形式中;在具有轻微精神病作用的脑损伤中;在情绪激动、吸毒引起的心醉神迷状态、神经官能症、心理变态和本能性不正常中;以及在一种由自杀目的引起的爆炸案件中。(介入了生物性和精神病学性的检验结果后)都能够得到适用。
从原则上说,人们同意立法者批准通过第21条开启的特殊刑罚范围必须要求行为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水平与正常的平均水平明显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接近无罪责能力的水准。
就精神激动被纳入选择性从轻处罚范畴而言,虽然这种从轻被限制在了一种严格的使用范围内,并且必须另外把挑选从轻的刑罚幅度看成时强制性的,但是都体现出了德国刑法的一种倾向:就是禁止“向一种生活方式罪责的追溯[3]”,即只有当一种罪责在行为构成实现本身中存在时,才能够成为刑法责任性的基础。在行为以外的“生活方式的罪责”不应当允许被替代性地追溯。这种罪责通过行为人本身的错误举止行为,才使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种“有罪责的”生活方式不是有罪责的构成行为的满足要件,而只有实施行为本身才是应受刑事处罚的。否则会瓦解罪责原则在构成要件行为中的界限作用,对国家的法治也会产生影响。
三、情绪失控、精神障碍、精神疾病与刑法
一个健康的人不应当仅是不生病,而是身体上完满强壮,精神上积极乐观,对大多数的环境都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总而言之,就是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或者是精神健康③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衡量人的“精神”与“心理”两个概念的维度均为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行为三个方面,且无论从概念解释还是实践应用层面,均很难将此二者区分开来,故“精神”与“心理”概念应为等价。)兼具,才能称为真正的健康。所以与之相对的,人的疾病也分为两类:一是生理疾病,二是精神疾病。
现代人由于繁重的生活压力、收入水平与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等原因,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精神障碍,例如适应障碍、冷漠孤僻等现象,另外,精神障碍有轻有重,精神问题也有大有小,严重的精神障碍自然就成为了精神疾病——例如严重的冷漠孤僻、过重的生活压力带来的适应障碍等均有向抑郁症转化的可能性。
凡是出现精神异常的症状或体征都可称为精神障碍。根据病因可分为非器质性精神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根据发病程度可分为重性精神障碍、非重性精神障碍。现代临床心理学所涉及的精神障碍一般指神经系统非器质性变化,包括心理正常与异常两大类。心理正常自不多说,后者相当于躯体疾病中的亚健康状态,包括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和可疑神经症;心理异常是指心理活动处于动态失衡状态,包括确诊的神经症、变态人格、癔症与精神病等。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指突然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短时间精神异常、短时间恢复到正常精神状况。而受严重精神刺激而导致的情绪失控、情绪爆发的症状则属于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在其中,又以冲动型人格障碍为主。冲动型人格障碍患者主要特征为情绪不稳定及缺乏冲动控制能力。暴力或威胁性行为的暴发很常见,在其他人加以批评时尤为如此。该类患者常因微小的刺激而突然暴发非常强烈的愤怒和冲动,自己完全不能克制,其时可出现暴烈的攻击行为,这种突然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和平时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不发作时是正常的,对发作时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但不能防止再发生。这种冲动发作也常因少量饮酒而引起。由外部刺激所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最常见于心因性精神障碍,发病因素与个体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密切相关。
社会因素方面,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都市人口密集,各种声、气和水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交通拥挤,竞争激烈,住房困难,待业,下岗,自然灾害,人际关系矛盾增多,所有这一切均易令人焦虑、紧张的因素,都成为精神障碍的重要根源。
心理因素方面,心理因素与精神障碍存在相互联系的表现,心理障碍或者心理疾患主要是由于本我欲望要求和超我道德间潜意识矛盾冲突而产生焦虑和情绪防御反应的结果。为了减缓个体的本我与超我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焦虑,个体自我发展了各种防范焦虑的手段即心理防御机制。个体心理异常或精神障碍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其心理防御机制过度偏用,以至于人格的发展或其他的有效功能受到了损害。
现代各国刑法对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判定,不仅仅只关注刑法学的标准,还以兼顾精神卫生学标准,将两者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判定,在判定过程中,一方面是从医学或心理学上来观察认定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从刑法学上来看待行为人是否因精神障碍引起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的丧失或减弱。二者缺一不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精神障碍的认定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符合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四、情绪失控与激情犯
综合比较英国和德国刑法关于情绪失控的不同规定,自然会发现情绪失控这一概念与我国的激情犯罪概念比较相近,情绪失控与激情犯罪在刑法意义上应当是属于包含关系,激情犯罪中,因正常诱因而导致的激情犯罪行为部分与情绪失控重合,在激情犯罪的内涵中,情绪失控与因非正常诱因而导致的激情犯罪行为部分互为反集。
(一)激情犯的概念
激情犯中的“激情”是情感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状态,其状态的强度在其他情感中最高、持续性最短、可化解性最低,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等特点。因此激情犯是指当事人在某种外界因素刺激下因心理失衡、情绪失控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其基本特征有:存在诱因,情绪强烈、持续时间短、事后有悔意等。
(二)激情犯的认定
激情犯与其他类型犯罪的区别即在于行为人在犯罪时是否基于激情而实施,而界定激情的标准有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以及混合标准。客观标准是以一般人标准来衡量在类似情况下是否会产生激情反应,主观标准则更多考虑行为人自身的因素与其当场的实际反映,混合标准采用了主观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我国一般采用的是混合标准,综合考量一般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行为人的特定情况。
由于我国鲜有关于激情犯罪的明文规定,因此认定激情犯罪大多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激情犯罪的诱因理由繁多,主要有:被害人过错、婚姻家庭纠纷和感情纠纷以及邻里纠纷、工作琐事等纠纷、突发性临时起意、义愤、被告人的控制能力弱等因素[4],总结得出,我国的激情诱因种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诱因,另一种为非正常诱因。
相较我国,国外刑法对于激情犯罪有严格的成文规定,例如大陆法系中《德国刑法典》第213条[2]规定:非故意杀人者的责任,而是因为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致故意杀人者当场义愤杀人,或具有其他减轻情节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英美法系中要求激情应当产生于被害人所做的某个或某些足以使得任何正常的人突然、即时丧失自我控制的行为,而且这种激情应当使得被告人在当时情绪失常并无法控制自我的意志。其激情诱因按种类应当属于非正常诱因。在激情犯罪方面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大,在我国例如当事人之间,双方相互斗嘴斗气导致对方实施了犯罪的情况也可能被认定为是激情犯罪。
(三)激情犯的刑事责任
首先,就客观而言,激情犯罪应当实施了应受刑罚处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对个人或公共社会的法益造成了侵害,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例如激情杀人的行为侵害了受害者生命权法益,激情抢劫的行为侵害受害者的财产权法益。但如果行为在激情状态下没有造成实际的物质或非物质性损害事实或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其次,激情犯罪应当是触犯刑法规范、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行为人由于激情诱因而实施的激情行为违背了刑法所设置的规范义务,符合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则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激情行为不违反刑法规范而违反的是民法、行政法等法律规范的,则属于行政、民事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
另外,从主观上来看,激情犯这种在情绪失控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了犯罪的犯罪者,他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应与同样情形下的一般的犯罪者有所区别,因为激情犯罪在主观构成要件中与一般犯罪存在差别。就激情犯罪自身而言,根据激情诱因种类的不同,也应当做差别考虑。出于正常诱因即一般人处于类似情境下同样会进入激情状态的情况,例如义愤或者其本人、家人受到被害者的虐待或重大侮辱的情形,往往存在被害人过错的原因,因此减轻了行为人的罪责,在量刑情节上可以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关于出于非正常诱因实施激情犯罪方面,有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如果被害人或第三人主观上都不存在过错,并且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也皆属正常的状况下,而行为人却认为是莫大的刺激并导致情绪失控进而实施了犯罪,这应当归咎于行为人的人格缺陷问题,即行为人的人格缺陷致使其陷入激情以及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从而实施犯罪。而且人格缺陷这一点应当值得刑法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此时,行为人的人格缺陷和尚未完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共同构成了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同时由于激情诱因的性质不符合一般评价的标准,因此不存在正当化的依据,也不能对其刑事责任起到缓冲作用,故对此种类型的激情犯不存在从宽处罚的理由。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此种类型的激情犯往往具有手段残忍性、盲目性和危害结果严重性等特征,而在司法实践中从重处罚也不乏其例。[5]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将行为人的激情犯罪归于其“人格缺陷”的理由不够充分,完全以客观界定标准来认定对于自我控制能力低于常人的做法有失公平,其次刑法禁止“向一种生活方式罪责的追溯”,在之前的导言中也曾提到过,现代的生活节奏与压力远比过去二三十年要来得快速和沉重,精神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或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人群相比过去而言也庞大得多,如果按照前者的观点,刑法应当非难人格缺陷的话,无疑将极大地扩大刑法的处罚面,会将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群纳入到刑法的射程之内,这无疑是代价高昂且不合理的。刑法仅处罚激情犯罪行为本身,不会非难精神障碍,也不应对精神障碍人进行特殊对待,故对此种类型的激情犯不存在从宽处罚的理由,更不应当从重处罚。
五、将情绪失控纳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范畴的意义
情绪失控这一概念属于激情犯罪的子集,激情犯罪这一概念目前在我国的法律规则中还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激情犯罪这一概念已经开始逐渐地被广泛运用开来,出现了有的激情犯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的激情犯罪又与其他犯罪受同等对待。同一种类犯罪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处断态度本身就较为不合理,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犯罪范围相较其它类型犯罪更大,这样将导致民众对法律的可预期性下降。
另外,在情绪失控类的犯罪中,行为人由于理性的丧失,意志受感性主宰,很难认为行为人后续的行为中存在自由意志的支配。而激情犯罪中,由于激情诱因有大有小、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其中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不甚明了,在研究归责方面会面临一个较复杂的局面,而将情绪失控从激情犯罪概念中剥离出来纳入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中,能够净化激情犯罪概念本身,而且由于情绪失控中,其意志受到了妨碍,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当然地发生减弱,因此将情绪失控归入限制责任能力范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