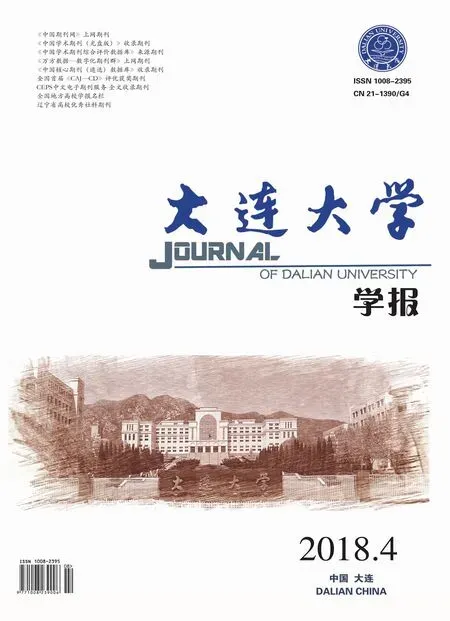末代皇帝溥仪与末代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关系探究
陈 宏
(伪满皇宫博物院 科研中心,吉林 长春 130051)
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先后出现过三个傀儡政权:溥仪为傀儡皇帝的伪满洲国、德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和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在这三个傀儡政权中,有两个“末代”:末代皇帝溥仪,末代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1]溥仪与德王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扶植的两个傀儡,他们从寻求复辟、同命相怜的封建帝王,到投靠日本、充当傀儡的合作伙伴,再到殊途同归、重获新生的普通公民,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们同时在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相互间曾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他们所走道路殊异,遭遇各别,最终却经历相似,殊途同归。通过探讨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来龙去脉,以汲取历史教训,启迪后人。
一、同为末代 道路殊异 遭遇各别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满族,是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1908年光绪皇帝病危,慈禧太后立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命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溥仪就此登上末代皇帝宝座,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逊位后依然保留皇帝尊号,在紫禁城内过着君臣如仪的帝王生活。1917年7月1日,张勋率辫军拥立溥仪第二次做皇帝,至12日再次宣告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部鹿钟麟将军驱逐出紫禁城,暂时移居载沣所居北府,继而躲入北京日本公使馆。[2]1925年2月23日,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日本租界。1931年11月10日离津出关,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新京”(今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苏军的俘虏,在苏联度过了五年囚居国外的生活。1950年8月初,溥仪被引渡回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年的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0年3月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劳动,1961年3月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逝世于北京,终年61岁。1964年3月,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字希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世袭贵族,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独立运动的指导者。1908年6岁时袭札萨克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通称“德王”。18岁亲政后,逐步改革旗政,兴办学校、工厂,编练武装。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他游历北平、南京、武汉、沈阳等地,会见蒋介石、张学良、班禅活佛、何应钦等政要,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军方面联络,德王与云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等王公于1933年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两次举行内蒙古自治大会,通电要求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6年德王出任察哈尔蒙政会副委员长,同年2月10日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成立“蒙古军政府”任总司令、总裁。“七·七”事变后,德王、李守信等人投靠日本,出任伪蒙疆政权首脑,历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主席,“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蒙古自治邦”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蒙古自治邦解散,德王寓居北平。1949年至阿拉善旗,与旗札萨克达理扎雅等发起“西蒙自治运动”,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并任主席。[3]同年底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后遣送回中国,以伪蒙疆首要战犯身份被关押在张家口,1963年获特赦释放,后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曾主编《二十八卷本词典》(蒙文),发表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966年5月23日在呼和浩特去世,终年64岁。
二、没落帝王 同命相怜 天津拜会
封建王公的世袭制是封建帝王制的产儿,因封建社会存续长,所以遗毒很深。辛亥革命打破了清朝的世袭罔替制度,也许是同命相怜,即使溥仪被赶下台,出于同为王公世袭者的德王也始终把溥仪奉若“君主”,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身上,非常期望溥仪复辟。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乘黎元洪政府危机之际,存侥幸成功之想,拥立已退位的溥仪在北京复辟,那时德王就把他实现远大“抱负”的赌注押在了溥仪身上。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无不愤慨,“誓与民国同命运,不和逆贼共戴天”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失败后,张勋等逃入荷兰使馆,参加复辟的穆特蕡阿(德王的姐夫)逃到了蒙古国,其他所有参与者也都缩手缩脚地躲了起来。溥仪非常痛心,德王也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没有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而深感遗憾。[4]
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暂时住进什刹海醇王府。也许是“唇亡齿寒”,抑或是“惺惺相惜”,德王对这个被时代废弃的末代皇帝依旧旧情不减,他骨子里遗留着浓厚的“忠君”思想,就想携带重礼赴京晋谒溥仪。
德王知道这件事必须偷偷进行,如果公开就会遭人奚落和妒嫉,老盟长和某些王公也会反对。于是,他暗暗偕同他姨夫,即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音达赖( 汉名福海 )夜赴北京,通过外蒙驻京王公那彦图引见晋谒溥仪。那时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仅得一面,未得多谈,聊表慰问之意就匆匆告辞了。德王和补音达赖等连夜返回张家口,通过各种关系向张家口富商筹借一万银元巨款又到北京,前往醇王府见溥杰,表示愿赴天津再谒溥仪。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打来电话,向溥杰询问祖母病情,溥杰趁便转达了德王的意思,溥仪说:“可以前来相见。”于是德王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银洋用布袋缠在腰中,套穿宽大外衣秘赴天津,继由补音达赖通过内部关系联系,经溥仪和天津日本租界当局允许,才进入张园。听说是蒙古王爷携带重礼而来,手头拮据的溥仪自然很高兴。德王见到溥仪即行三叩九拜君臣大礼,对他出宫表示深深的同情和痛惜,并当面奉献一万元银洋,以示“忠君”之意。君臣之礼对溥仪来说习以为常,可这万元银洋重礼确实令他感动不已。为此,他对德王的印象极深。德王也很满意,曾对补音达赖说:“人在饥饿时,你给他一块糠饼他就会记住你;在他吃饱时,你送块牛肉也记不得你。”回旗后德王又挑选一批良马送给溥仪二弟溥杰,德王这样做,不仅是想表示对“帝王”的尊崇,更想借溥仪的余威来抬高自己。[5]
三、投靠日本 受控关东军 充当傀儡
十九世纪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不断扩大侵略活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力逐渐强盛,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生产发展受到阻碍,加上人民的反抗,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日本统治者强烈要求对外侵略,企图从中寻找出路。其“大陆政策”就是一个旨在征服中国和世界的侵略政策。1927年6月——8月,日本内阁“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的召开加速了日本推行其侵华的“大陆政策”的步伐。日本的田中奏折将“满”、“蒙”并称,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其鲸吞东北和内蒙古的嘴脸跃然纸上。20世纪30年代,“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叫嚣充斥报章杂志,连篇累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 事变,我国东北开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占领东北三省之后,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3月9日利用清废帝溥仪建立“满洲国”。进而进兵热河,占领内蒙古东部三盟。其阴谋是还要建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因为蒙古族和满族这两个少数民族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王朝,清王朝虽被推翻但还有一个末代皇帝,扶起来还有一定影响。蒙古王朝被推翻虽已久远,可是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牧业经济维系,还是北方一个强盛的民族,仍保持着封建王公制度。如果再找一个代理人收拾蒙事,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整个北方就任由日本摆布了。这是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极为重要的战略步骤。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搞“满蒙政策”。对东北、内蒙古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既要进行公开的军事占领,又要实现隐蔽的政治阴谋,以达到“以蒙制蒙,以满制满”之目的,溥仪和德王就是日本扶植起来的“满蒙”的最高统治者。不同的是溥仪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由清朝废帝而变的“满洲国皇帝”,德王是自己成王后再投靠日本的一方之王。溥仪称“帝”,满洲称“国”,而对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则只称其是“政府”甚至“军政府”,并未同意其建立“蒙古国”之要求,因此溥仪称“帝”,德王称“王”。伪满地域也包括整个内蒙古及东北、华北、西北,即我们今天讲的“三北”七八个省的部分地区,领域不断扩大。扶植这样两个重要人物,既掩盖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又蒙蔽了国际视听,同时还维护和稳固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可谓达到了“一石多鸟”之目的。
实质上,溥仪是一个毫无实权、地地道道的傀儡皇帝,就连举杯祝酒,甚至点头微笑都要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他充任“执政”后不久,在日本关东军授意下,于1932年9月15日,派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伪满皇宫勤民殿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将东北广袤的土地出卖给了日本侵略者。德王也是如此,日本在德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上还设立了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联络部,因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兴亚院联络部长官都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太上皇,一切都要听命于他们而行事。德王这个主席的权力,仅是公布法令、教令、教书、大赦、特赦、授勋等,虽然还有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无权过问,可谓是高高在上的傀儡。可见,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自始至终是完全由日本培植并由日本支配一切的。
四、奉日之命 “满蒙合作”“新京”会晤
日本卵翼下的伪满洲国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加紧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勾结,从而进一步成为日本侵略者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日本侵略者也大力鼓吹“日满亲善、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在日本关东军监督下,作为两个傀儡政权的代理人——溥仪和德王,本着 “效忠日本天皇,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你来我往,相互勾结,就连他们在“新京”的三次会晤也都带有殖民政治色彩,并且都是在日本关东军监视下完成“政治使命”后的小心而顺便的拜访。
德王与溥仪,本来就是旧交,德王又有“忠君”思想,溥仪流落天津时,他曾去三叩九拜,溥仪成了伪满“皇帝”,他又特意穿上清朝蟒袍、马褂,戴上朝珠、顶戴,拍下叩拜之像,并派蒙古旗协理钟昆赴伪满送呈溥仪以示“尊君”,而且他还三次赴“新京”拜访溥仪。
第一次是1935年12月。德王同迪力瓦和浦、中岛万藏等乘坐日本人送给他的飞机前往“新京”,会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关东军参谋长西尾。正式参与晤谈的则是板垣征四郎和田中隆吉。主题为“蒙古建国”相关事宜,在许多方面达成一致,起草了协定,并呈交关东军司令部,待修改后成文。德王乘机提出要拜见溥仪,取得关东军司令官允许后,他先与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经通报,溥仪非常高兴地传话召见。溥仪和德王,亦有“老友”情谊,德王叩拜问安,又祝贺“登极”。溥仪也显得“实在”了,再也不是“稳坐受叩”,他把德王拉起,让他坐在身边,一边让侍从“看茶”,一边打量着德王的“变化”。德王想从溥仪嘴里掏点儿“重要的东西”,不料溥仪却很谨慎,除了说日本人“对他好”外,再就没有别的“看法和感受”了。会见后,德王又由关东军安排观看了日本军队的演习,并到大连火车头制造厂参观。[6]
第二次见面是德王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新京”来缔结“满蒙协定”。他首先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而后又访问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等。双方议定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后,德王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根据该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满代表,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满币,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地区内流通使用,由此双方发生了经济关系。签字后,“满洲国”设宴款待蒙古访问团一行,德王又搞了“答谢宴会”。[7]德王再度晋见溥仪,按理本有“两国相交”意味,德王亦应尊重自己的“身份”,但顾念过去的关系,他对溥仪仍以臣属之礼相见,溥仪也挥手让座,温语有加。德王谈起这几年的经历以及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了牢骚,埋怨日本人“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兑现”。尤其令他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溥仪说:“你的话太硬了。”于是匆匆结束了会面。嗣后溥仪受日本人指使又召见德王,授予他“武德亲王”的“钦任状”,也完全是在演傀儡戏。接着,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派人陪同德王一行到奉天(今沈阳 ),参观了兵工厂和东陵、北陵等清朝皇家陵园。
第三次见面是德王在伪满“建国十周年”之际访问“满洲国”的时候。他拜见溥仪时作了交代:“现在皇帝在日本帮助之下已经登极,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我今后将把忠于皇帝之心忠于蒙古事业。”溥仪也以贵宾之礼相待,宴会时也改口称德王为“贵主席”了。
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德王与溥仪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对日本军国主义卑躬屈膝、出卖主权、镇压抗日力量、奴役人民,签订了大量的反动法令,给东北人民和内蒙古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五、沦为战犯 十年改造 重获新生
1945年8月19日,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溥仪等人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先后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度过五年囚居国外的生活。1950年8月1日,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10年的改造生活。
德王的经历也大体相似。日本战败前夕,德王企图寻找后路。他曾与东蒙代表密谈,寻求东、西蒙的“共同出路”,将集中双方军队,组建“蒙古自治国”。但因苏联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靠蒋介石。在北平“闲居”三年,他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国民党官员、美国记者等,广泛建立关系,为“内蒙古自主自治”开展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没接受“留在北平迎接共产党”的建议,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即因形势所迫,起初打算路经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通过亲属关系与外蒙建立联系,于1949年12月29日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8]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引渡回国,在张家口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三年的改造生活。
溥仪和德王回国之初几乎都失去了生的希望,因为历史上任何被赶下台的皇帝和王公,最后的结局都是走向断头台。溥仪和德王又都是搞分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不会饶恕他们。然而没想到管教人员中没一个横眉冷对,都温和有加。监狱的规格、待遇反而比苏联、蒙古提高了。[9]建国初期我国政局稳定,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大好,使溥仪和德王重温旧梦、东山再起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老实接受改造。在“惩办与宽大、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党的改造战争罪犯政策引导下,管理所工作人员细致入微、润物无声的工作和人道主义待遇,使溥仪和德王渐渐解除疑虑,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当他们得知政府不但宽待他们还照顾了他们家族时,溥仪和德王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1959年溥仪被特赦,1963年德王被特赦,两个“末代”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恢复了政治权利,最终殊途同归,起死回生,寻到了光明。这是只有在中国这块伟大国土上才可能出现的奇事,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成功。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对“双胞怪胎”,德王和溥仪作为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从最后挣扎、一起倒台,到最后走向光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恰好是我们国家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历史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