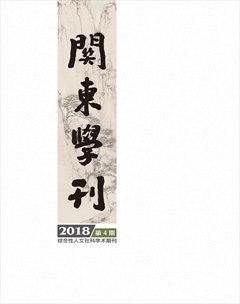新媒体时代的文体新变及其意义
周海波 王云龙
[摘要]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媒体比之于文学自身更重要,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它更是文学审美的评价尺度,一种改变文学的新的美学原则。应当承认网络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而且是有别于其他文学的一种文学形态。网络语境中的写作,已经大不同于报刊时代了。网络文学首先考虑的就是商业利益,在海量传播和迅速传播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商业利益,文学的文体形态也因此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并不一定完全是新媒体文学,网络化传播载体也不一定完全造就了网络文学。一些坚持文学立场的作家,一方面在对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又不得不使用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文学传播。这种矛盾的状态恰恰说明新媒体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文学;文体形态;文学史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的传播方式和形态,是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新的数字传播媒体,它包括所有的以数字传播形式为主的媒体,它主要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传播手段获得实现,主要形式则有网络媒体、数字终端媒体、数字电视媒体。新媒体的“新”,主要是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新,诸如报纸、期刊、电视等,新媒体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任何人都可以是传播者,也都可以是接收者,而且传播者与接收者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交流,它既是一种载体,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现代科学技术的表现,同时又包含美学观念在内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新媒体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观念以及新的价值尺度。
一
人们一般将那些以网络为平台的文学称之为新媒体文学或者网络文学,这种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写作、传播特点。正如丁国旗在《对网络文学的传播学思考》一文中所说,网络文学是“一种在电脑上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应当说,这个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目前人们对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没有更加明晰准确的定义之前,是可以接受这个定义的。但是,这个定义没有看到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例如,网络文学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这是网络文学快速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但是,网络文学在其传播过程中,同样也依靠纸媒的传播方式。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就分别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普天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以不同方式出版过。可以说,《盗墓笔记》成于网络,而又借助于纸媒得到更广泛持久的传播,从而能够为更多读者所接受。由此看来,一些网络名作同样需要线下出版为其带来必要的声誉和商业利益。因此,网络文学经由纸媒传播时,它的阅读者、参与者就不再仅仅是网络用户,而且会极大地扩大其读者对象。在这种情形下,网络文学批评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就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一是它的主体的变化,网络作家往往不再是作家,而是网络写手,这个写手的概念比较复杂,它既可能是某个具体的写作者,也可能是一个写作团队。而有些网络写手不再仅仅是一个写作者的身份,他们往往是文化传播公司的CEO、合伙人。这样的写作者很难再称得上作家,他们的写作行为也很难再称之为创作。当用某个网名在短短的几天或者几十天内上传数十万字或者数百万字的文字时,这种海量写作及其传播,无人能真正明晓写手们的写作方式及其写作态度。2006年4月到10月,月关在起点中文网站上传了近百万字的武侠同人小说,而在同一年的11月,他又上传了370多万字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到2008年,月关又上传了108万字的《狼神》、102万字的《一路彩虹》等小说。近年来,这种海量写作与上传的速度更加惊人。同样,网络文学不再是阅读,而是成为“刷屏”,阅读或读屏者以参与者的身份完成了作品的最后的创造。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文学传播等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邵燕君在其主编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她“从‘网络性出发”,对网络文学做了一个“狭窄的定义”:“网络文学,并不是指一切在网络发表、传播的文学,而在网络中生产的文学。也就是说,网络不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而同时是一个生产空间。”这里不仅是对网络文学的定义,更是对网络化时代文学特征的认同。邵燕君的观点强调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谱系中的概念,而是一个超越人类文学史的一切文学形态的新的文学类型。对此,邵燕君进行过更深入的阐释:“从文明形态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学其实是印刷文明时代的文学,它的文学形态背后有着特定的媒介形态。比如,西方现代意义上小说的诞生就是与古登堡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不从媒介的角度,而仅从文学的角度进入到网络文学研究,你会发觉走到一定时候就走不下去了。以那种眼光看,好像网络文学只是通俗小说的网络版。但即使我们把网络文学仅仅限定于网络类型小说,网络连载类型小说也与金庸时代的报刊连载类型产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因而,邵燕君提出要“从媒介革命的角度来定义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网络媒介下的一种文学形态”,这也就告诉我们,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媒体比之于文学自身更重要,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它更是文学审美的一种评价尺度,一种改变文学的新的美学原则。由此可见,新的媒体带来的是新的文学形态,也就是新的文学文体。
不过,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显然不能完全了解、不能真正概括文学的全貌。文学的网络化和网络文学仅仅是文学的一个方面。当人们特意将网络文学单列出来的时候,恰恰说明网络文学的脆弱与不成熟。例如,在概括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人们往往看重了网络文学的技术性、传播快等方面,而在实际上,当人们过分看重网络文学的外在特征时,其实是把传统文学中的一些特征略加修改后使用到了网络文学上面。禹建湘在《网络文学关键词100》中就这样概括网络文学的“鲜明特征”:“第一,技术性”,“第二,快捷传播性”,“第三,内容奇特性”,“第四,语言口语化”。这四项内容可以作为网络文学的特征,它体现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一些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宏观地而不是绝对地去看人类文学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学,都具有这几个特征。比如“技术性”,这个特征不能说是文学的特征,而只能说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特征。古代文学的生产技术与传播虽然不能与网络技术相比,但同样是一种技术,同样讲究技术性,或者说古代文学是在一定的古代所掌握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生产。比如在岩石上作画,在甲骨上刻字,那就是一种技术,而且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先进的技术,运用那种技术制作和传播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美术与诗;再如传播的“快捷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古人骑马送信和1960年代的邮局工人骑自行车送报以及当代人用飞机、高铁的运输,或者卫星传输,都只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速度,而不能以现在的网络传输与古代的骑马传送相提并论。古代的飞马奔跑与现在的高铁奔驰,从绝对速度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但从相对的观点来说则是一样的,文化传播都具有速度,都讲究速度。古代文学中文人的唱和赠送,与当下的微信传播,哪个速度更快,并不能以技术的高低而定,口头传播与网络也只能是在相对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哪一种传播速度更迅速;第三条内容的“奇特性”并不能认定是网络专属,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追求新奇怪,追求艺术的陌生化,不能说网络文学《悟空传》的内容是奇特的,而《西游记》的内容就不是奇特的;不能说《步步惊心》的内容是奇特的,而《东周列国志》就不是奇特的;不能说《盗墓笔记》是奇特的,而《水浒传》就不是奇特的。唯有第四条与网络文学比较接近,可能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网络文学这样口语化,甚至比口语还通俗、还粗陋。当然,如果我们想到《诗经》中“國风”的诗篇也带有鲜明的口语特征,我们就不会对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产生不必要的怀疑: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俗文学史,就是国语文学史,而国语,就是白话,是人人能说的国语。如果把这一观点运用于网络时代的文学,同样是能够接受的。
综上所述,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来概括和定义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是不准确的,没有真正抓住网络文学的特点。或者说,单纯定义网络文学,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其本身意义并不是太大,因为网络文学也是文学,而且它首先是文学,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文学,它应有与其他形态的文学大体相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因为时代和载体的不同而形成一些属于自己的特点。
二
文学就是文学,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但它们都是文学,是不同时代、不同传播方式和不同美学特征的文学。在一个新的媒体出现并领导和控制了人类文化的前提下,文学就是文学,它不分为网络文学或者非网络文学,它只是运用网络为载体的一种文学,如同以报纸为载体的文学或者以墙壁为载体的文学,它们都是文学的一种存在方式。报纸文学、杂志文学、电视文学等等这些概念,主要是为了研究者的方便而定,或者出于某种需要而提出来的。无论是甲骨布帛,还是墙壁岩石,无论报纸杂志还是网络,这些不同的载体既是为文学的记载与传播提供一定的物质形式,而同时又带来一种新的美学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越来越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带动下,总是以超越人们想象力的速度带给人们巨大的惊异,以新的文学形态刷新人们的审美经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文学随着书写工具和传播媒体、传播方式的演进,表达情感思想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作品规模越来越宏大。人类文明的初期,由于书写工具极为简陋,因而在简单的书写符号中所“创作”的作品的形式极为简单,在简单的结绳记事、岩刻的形象以及符号中,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比较单一。当四言诗以及后来的诸子散文出现的时候,传播媒体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五言诗甚至七言或者更多言的诗行出现时,竹简、布帛的书写已然向纸张书写的形式发展。唐代雕版印刷、宋代刻板印刷以及胶泥活字版印刷,在促进入类创作趋向更复杂的表达方式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文学在特定的传播方式下,开始走向市民社会。唐传奇、话本、拟话本的出现,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而当报纸期刊出现后,文学从语言、文体类型等方面开始真正走向“现代”。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化时代的文学,不仅仅是传播媒体平台的变化,而且也是一种书写方式的变化,也就是邵燕君所说的網络文学的“网络性”问题,在网络状态下的写作,与此前任何一种书写方式都不相同。网络时代的写作甚至区别于纸质传媒时代的都市流行文学写作。面对新兴的报纸期刊,比较早地适应了这种新的传播媒体的一批文人,紧紧抓住了现代传媒与市民大众的关联,将自己的作品以一种“流行的”方式推向读者大众。不过,都市流行文学的作家们还是作家,是一种适应新媒体的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他们的写作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写作方式,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精神劳动,是一种孤独的精神生活的体验。李楠在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时,曾对上海小报文人做过精彩的论述,她认为:“小报文人是指那些站在市民立场上具有市民文化精神的、较深地参与小报动作的文人,包括兼具小报编者和作者双重身份的文人和一部分在报纸外专门供稿的小报作者”,这些“世俗才子”生存于新旧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夹缝中。这些小报文人的写作方式是孤独的、是精神性的,或者说,他们的写作首先是一种精神生活,在此基础上才是商业活动。郑逸梅曾这样叙述过自己的经历:“明知经商可以致富,但我不会经商,也不喜欢经商。觉得商人除了少数有学问的以外,什九是唯利是图,一副市侩面孔,真是令人欲呕,所以我虽然读书穷了一世,却仍不愿我儿子为市侩面孔的商人。”此外,他还叙述了自己不愿做官而只愿读书的想法。郑逸梅是著名的小报文人、都市流行文学作家,从郑逸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仅仅为了稿费而写作,不是把写作视为一种商业行为,而主要把写作视为与读书一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的活动比较于稿费、做官都让他感到快乐和幸福。但是,在网络语境中的写作,已经大不同于小报时代的写作了。网络文学首先考虑的就是商业利益,是在海量传播和迅速传播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商业利益,以点击量、刷流量、打赏和夹带嵌入广告等方式,实现其经济收入的目的。当然,并不是说网络文学作家不注重文学写作的精神活动,他们也会注重文学写作与其精神世界的联结,注重将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注重通过一定的写作表现其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但是,网络文学写作往往是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写作的精神生活是作为一种附带的文学功能,文学的精神生活是在商业利润基础上的体现,是一种满足经济生活条件下的文学附带物。从写作主体来说,大量的粉丝支撑着一个写作团队,满足了写作者的经济欲望;从传播主体来说,快捷迅速的传播使文学文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推送给读者,从而获得足够的商业利润;从接受主体来说,大量的网民以较低的价格在电脑或其他终端上下载并浏览这些文本。因此,可以说网络文学让文学实现了在大众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大众化,让文学成为草根文化的代言者。
那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我们认为,要研究新媒体时代文学的特征,必须回到新媒体的网络文化语境、网络技术的平台,在网络与文学的广泛联系中发现新媒体时代文学的特点。
第一,文学边界的突破。所谓文学边界的突破,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创作者的边界被突破了。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认为:“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梁实秋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作家都是那些社会精英式、天才式的人物,而不是谁都可以当作家的。但是,在新媒体面前,这个创作者的边界被突破了,任何人都可以从事文学写作,谁都可以是作家。因此,就出现了诸如“网络写手”“脑残诗人”“奇葩作家”“大神作家”“美女作家”等,这些写作者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由于网络的传播而一时走红,成为社会关注的当红作家。他们可能每天都会码上一万甚至几万字,也可能他们写作的作品并不是以他们自己的姓名在网络上传播,而是以其他种种网名进行传播。但目前要对这类作家做出定评,可能为时尚早。二是文学范畴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被新的媒体所突破,一些传统文学中不被承认为文学的作品已经毫无障碍地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之中,真正的突破文学、历史、哲学或者其他门类的“大文学”成为网络的新品种,甚至出现了文字、图片、视频相结合的跨界作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经被解构,文学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三是文学的文体形态和文体类型发生了变异,一些“非文学”的文体堂而皇之成为文学。如近年来颇受争议的“口语诗”“两句话的口语诗”,这是在传统的文学领域中无法接受的文体,却在新媒体时代成为一种诗歌文体而被奉为当下诗歌的新趋向,被认为是网络化时代的新宠儿。这个诗歌宠儿以世俗化、大众化的形象,走下文学的圣殿,放低身段,悄然打人文学的世界之中。再如小说中的“接龙小说”“网游小说”“YY小说”“种马小说”“同人小说”等,这些本来与文学不怎么沾边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中,成为文学的主力,从而改变着文学的边界。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并不一定完全是新媒体文学,网络化传播载体也不一定完全造就了网络文学。实际上,在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当下,一些坚持文学立场的作家对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表达着自己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以悲悯的情怀面对迷恋于网络和网络文学的人们,以悲壮的精神对待他们挚爱着的文学,以顽强的姿态坚守在文学的世界中。因而,他们往往把自己坚持的文学立场视为“纯文学”,而把网络文学或者新媒体文学视为通俗文学或者非文学。有意思的是,当各种新媒体扑面而来的时候,或者当新媒体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一些坚守文学的作家,一方面不得不、或者很不情愿地使用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一方面却又在抵制着新媒体文学,他们也在不“情愿”中将自己的作品通过微信或微博发布出去,或者被动地通过新媒体发布出去。这种背反式的现象在新媒体阶段构成了有趣的現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坚守“纯文学”、提倡格律诗的徐志摩。1925年10月1日,向来不太看重报纸的徐志摩,接受了《晨报》的邀请,出任副刊主编。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并不是他对报纸有多少热情,也不是借报刊实现多么了不起的创造,而是要通过自己办报纸副刊把其他的副刊杀死。正如他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所说:“我自问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我来只是认识我自己,只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都不能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但是,要想在大众传媒的文化氛围中不迎合群众,不取媚社会,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他要通过把自己的副刊办出高水平来掐死其他副刊,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文化理想的表现而已。因此,徐志摩只能是通过努力改造副刊而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增办《诗镌》和《剧刊》。《诗镌》促成了新月诗派的形成,却并没有真正促成报纸副刊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剧刊》匆匆忙忙停刊,徐志摩甚至都没把停刊词写完,不仅是他即将大婚,时间紧张而不能写完,也有他对新媒体的失望与隔膜。徐志摩对待现代传媒的矛盾心态,反映了他对待文学的矛盾心态,既无法抗拒报纸的巨大诱惑,也不能不面对报纸对文学传播的力量。同样,在网络文化时代,一些作家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一些大牌的文学刊物也不能不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些在读者以及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刊物,也在试图通过新媒体诸如微信公众号等,适当进行文学作品的传播。《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当代》等与中国当代文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期刊,也在适应新媒体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其他网络传播方式。这说明传统的文学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者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相互靠近,相互融合。
正是如此,当我们在考察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在考察网络文学的同时,也要将在网络媒体时代的其他文学文体形态考虑在内,或者将传统的文学文体形态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变化,作为新媒体时代文学文体美学的一个重要参照。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存在一个多种媒体融合的问题。首先,任何新媒体都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媒体。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新媒体的出现必定会影响到传统媒体,如活字排版印刷取代了刻板印刷,而激光照排的出现又取代了活字排版印刷,但是,这些不同印刷技术并没有完全取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只不过印刷技术发生了变化,而传播方式并没有真正被取代。报纸、期刊、书籍,作为文学的载体并没有被完全代替,仍然是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近年来,甚至有一些图书出版机构特意追求传统的、古典的图书印刷的样式,毛边书、线装书等频频出现。传统文学需要报纸、期刊和著作出版,网络文学也需要以传统媒体的方式进行出版传播。在这里,无论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必须要面对不同的传播媒体。于是,我们看到,网络时代的文学的多样性,既有以网络作为传播载体的文学,也有以传统媒体作为传播手段的文学。
其次,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一个适应新媒体的过程。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支持下的传播形态,它既是新奇的,也是革命性的,报纸的出现曾引起过人们的惊慌,认为这种“野狐禅”是不会有长久存在的价值的。但是,报纸不但没有很快消失,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传播工具,最终那些反对报纸的文人,也不得不面对报纸、适应报纸,并且很快成为现代报刊的重要角色。报纸期刊这些“新媒体”成为不同人群的文化消费品,也成为不同作者的传播工具。新媒体人在适应着传统的文学,而传统的媒体人也在适应着报纸期刊。同样,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后,也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和如何运用的问题,传统文学的作家们在适应着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适应着文学与读者的新型关系,即如李敬泽所言:“进入网络时代,我们面临着‘网络性的考验。”而网络文学的写手们也不能不考虑文学创作的文学性,让自己的作品在成为商品的同时能够为文学史所接受。
最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都应考虑其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性追求问题。文学首先是文学,无论报纸、期刊还是网络,对文学而言都仅仅是一种传播载体,尽管不同的传播载体会带来不同的美学观念,带来不同的文学价值尺度,但只要被称之为文学或者自认为是文学者,不可能不考虑其文学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不少学者提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的文学性问题。邵燕君认为,诸如类型小说等网络文学,其“商业性不排斥文学性”,也“不排斥独创性”“不排斥严肃性”,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作为文学创作具有特定的文学性,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在追求文学的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在追求着网络文学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