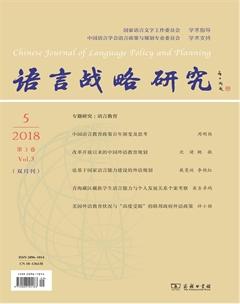科学史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出版物中语言的规范要求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刘兵
作为在科学史领域中从事教学、研究、写作的人,在自我介绍时,我通常会说自己是一个科学史的研究者,或者说科学史工作者。这两种说法其实在修辞上都有着国内的语言烙印,因为用英文来说,本应是historian of science,标准的翻译就是“科学史家”,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说“家”便有“自大”“不谦虚”之嫌,尽管在翻译国外文章时并不会绕来绕去地也替别人“谦虚”地译为科学史工作者,而且在国外交流时,也会直接使用historian of science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显然,这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中,对同一对象语言描述、理解与接受方式上有特色的差异的表现之一。
作为科学史工作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一个在高校从事科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或者说“学者”(这一称呼在某些场合用来指称自己时似乎又有些“自大”之嫌),主要的工作便是讲课、指导学生、读书和写作。其实,这些日常工作,也都与语言使用相关,因而会对语言问题有些想法或感触,也是很正常的。但在现在学术研究愈发分工细化和强调专业性的情形下,语言研究也是专业学术领域,非语言学科专业的人要讨论语言问题,从学术专业化的角度来说,似乎是一种越界。但语言的特殊性又在于,它偏偏是也要为非专业语言学科研究所使用的东西,一个使用者对于自己使用的东西有想法,即使不那么专业,或许也还是可以被宽容地允许的。尤其是,当语言研究与现实中对语言的使用的管理相联系时,更有许多可以“吐槽”之处。
在撰写期刊论文或图书出版时,曾有一种非常突出的感受,即编辑们在编辑作者的文字时,会非常严格地按照出版物文字使用规范来进行修改。有时,当作者觉得这种规范并不合适时,却又毫无办法,编辑会解释说,如果出现了不规范的情形,出版物便会被认为有差错,而差错率又是考核出版社和编辑的硬性指标。于是作者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坚持自己的文字用法,会让编辑和出版社为难,甚至导致无法出版;顺从那种规范的要求,又实在令作者难以接受。其实,这里关键的地方,在于对语言文字在出版物中规范的要求是否合适?应该由谁来制定规范?规范的强制性是否过于硬性?当这种强制的规范与社会上人们对语言更广泛的使用习惯不一致时,是否仍有合理性?
举个例子吧。在涉及诸如像科学、科学史等方面的出版物中,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通俗普及性的读物,对计量单位使用的某些强制规范,就非常令人费解。例如,距离,就一定要用“千米”,而不能用“公里”,更不能用“英里”“英尺”“英寸”了。但在现实的日常语言中,有多少人会用“千米”来作为距离的单位?如果人们在说到距离时真要是用“多少多少千米”,不会显得很怪异吗?更极端地说,那还像是正常人在说话吗?
如果退一步讲,在作为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关联并不密切的学术交流中,使用一些与日常语言表达不太一致的专门概念或可能为某些规范辩护的话,那么,在明明是面向普通公众进行普及传播的出版物中,为什么还是一定非要用那些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极少使用的概念呢?这种不一致,究竟是为了用语言来达到有效的传播普及,还是为有效的传播普及制造障碍呢?语言的规范化,本来就应顺从在自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及使用的习惯,而我们在出版物中的那些并不符合这种要求的规范,为什么改变起来又是那么困难,那么滞后呢?
再退一步,如果文字內容涉及的是历史,历史上的人物会用屈从于今天这些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来讲话吗?比如,如果在科学史读物中讲到牛顿,牛顿会用“多少多少千米”这样的方式来说话、来写作吗?如果不能,那我们硬要在中小学科学教材和科学史普及读物中一律使用“千米”作为距离的单位,那反映出来的还是当时的历史场景吗?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嘲笑一些电视上所谓的“历史剧”中的人物用今天的语言在说话,并觉得这很可笑,但实际上这不是正与在规范下要求用今天的概念来写作表达,在逻辑上很有相似之处吗?在那些强制性规范下,如果我们真要以更接近当时历史实际的方式去描写历史,我们写出来的文字,能够出版吗?
对于这样怪异的现象,人们当然可以质疑。极端些讲,或者用学术的语言来讲,也许可以说在这些并不合理的强制性规范背后,带有着明显的“权力”的影子。而用调侃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问:出版物中语言的规范要求与日常语言(我更愿将此看作“正常语言”)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历史写作的人称两难
田 松
小说写作有两种常见的视角,个人视角(第一人称视角)与全知视角(或曰上帝视角),前者用第一人称,后者不出现人称或用第三人称。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小说中,作者就是小说中的“我”,作者只能描述“我”之有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全知视角的小说,作者无所不知,最典型的是说书人,动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上帝一般,了解每一枝里的所有事,洞悉所有人的内心。
每一位人文学者都是一个凡人,肉眼凡胎,见知有限。小说作者可以使用全知视角,那是因为小说中的世界原本就是作者创造的,作者就是自己小说的上帝。而作为一个学者,当我面对世界、社会以及我个人进行书写的时候,我只能以第一人称,只敢以第一人称。罗素写《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在我看来,他所写的只能是他个人认为的、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所以,人文写作应该是第一人称写作,且只能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写作。有人文学者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敢于用全知视角写作,我称之为认识论的傲慢与僭越。
历史写作同样也是人文写作。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另一位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学哲学家汉森说,观察渗透理论;科学史家江晓原说:描述当头,观点自在其中……这一切都在说,纯粹的不附着任何理论的客观的描述是不存在的。江晓原教授曾在《天学真原》的序中写道,如果今天还有人相信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历史,那是一个不及格的历史学者。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由某个具体的人写出来的,既然是人写的,就不可能是绝对的超越的永恒的“本来面目”。
文史哲之中,历史是最不方便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第一人称写作的历史,就变成了自我陈述,那应该是自传。历史作为history,并非“我”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于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写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面的故事,就成了历史学家的使命。
科林伍德说: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在讲述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时候,不必告诉读者,地球是怎么想的;但是,一个历史学家仅仅描述了恺撒在某年月日某地被刺杀是不够的,他还要告诉读者,恺撒为什么被刺杀,杀手是怎么想的。
杀手是怎么想的,史学家怎么能知道?
科林伍德又說,历史学家要有能力在自己的心里重演整个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讲出主角的心理活动。这样一来,写历史如同写小说,而且是写全知视角的小说。
这就成了历史写作的人称两难。一方面,你不可能是上帝;另一方面,你必须努力成为上帝。
尼尔斯·玻尔解释互补原理,如果两件事不能同时进行,但又都很必要,只能交替进行,那么这两件事就是互补的。他举例说,用一个词去交流,与分析一个词的意思,这两件事是互补的。当你使用一个词去与人交流的时候,你就不能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当你分析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这个词去与人交流。当你说,把那个“杯子”给我递过来,你是在使用“杯子”这个词;当你说,什么是“杯子”?你是在分析这个词。这两件事不能同时进行。
历史学家有两重职能,一个是讲故事,一个是研究过去的事;前者是应用史料,后者是分析史料。这两件事是互补的。在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时候,他要站在全知视角,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他分析史料的时候,他的第一人称才会明确地出现。
我在讲科学史课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个两难。比如我讲古希腊,讲阿基米德,讲他的生活世界,他的国家,他的科学活动,我应该讲一个上帝视角的完整的故事,往事历历,如我亲见。这样的课才生动,才能吸引听众,才算是一堂好课。如果我写书,也只有这样写,才能有读者。
但是,在我讲的时候,我感到心虚。庄子曰,何以知其然也?
多年前,我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件事?最结实的回答是:这事是我亲身经历。不久前微信公号上又流传邓晓芒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回答,他就说,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都死了,就死无对证。亲身经历,是他最大的底气。
但是,我不可能亲历古希腊。一个史学家所讲的绝大多数事件都是他不可能亲历的。正如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可能把教科书里的所有实验都一一做过。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件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这回答就比较复杂了。这句话的另一种问法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件史料?
物理学家敢于讲他没有做过的实验,因为他信任做过那些实验的物理学家。物理学一代一代传下来,以往的知识成了默认的底色,成了缺省配置。历史一代一代传下来,信任也一代代传下来,某些关于古代社会的共识积淀下来,希腊也好,春秋也好,历史学家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都如亲历,穿越一般,上帝一般。
但是,史学家的另一个角色另一重功能,则是要研究这些故事。我在复述的同时感到了心虚,仿佛庄子在问,这事我是怎么知道的?于是这课的讲法就变了,我只能说,按照丹皮尔或者麦克莱伦第三的描述,古希腊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就出现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这样讲故事,故事不连贯,不好听,如果是给研究生讲,还好,美其名曰教他们做学术,做科研;给本专业的本科生讲,也勉强说得过去;作为通识教育课给外专业学生讲,一定是失败的。第二个更严重,丹皮尔和麦克莱伦第三,也没有去过古希腊啊,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所以我必须追溯下去,不但要看丹皮尔《科学史》,还要看他所参考的文献;不但要看麦克莱伦第三《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也要看他参考文献所参考的文献。这样无限追溯下去,我必须读希腊文、拉丁文,才会感到踏实一些,才能不那么心虚地说,根据我的研究,古希腊是这样的。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历史书的写作也是这样。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个故事讲得越是连贯,越是生动,越是可疑。但若是处处有来历,则难免结结巴巴,干瘪乏味。
历史写作,尤其是通史写作,就处在这人称两难之中。一个勉为其难的解决方式是,用全知视角讲故事,用个人视角做注释。外行看故事,内行看注释。
一个跨文本写作者的语言选择
江晓原
作为一个长年以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同时进行写作的人,我很长时间没有思考过语言的选择问题,一直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进行写作。
我的大众文本写作要早于学术文本的写作,20世纪80年代之初,我还在念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记得我发表第一篇杂志文章是在1983年的《天文爱好者》上,那篇文章报道了我的一个小小“发明”:一种计算过去、未来任意年份某月某日是星期几的新公式。这是和一个其他专业的同学在教室闲聊“模数学”的产物。
在早期的跨文本写作中,我没有留意语言问题,只是将文章写得文从字顺而已。但稍后我开始大量阅读前贤的学术文本,却产生了困惑。
就如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的那样,大部分学术文本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选题远离现实、语言枯燥乏味、叙事缺乏技巧等。公众之所以对学术文本望而生畏,主要原因往往是前面两者。当我开始批量阅读学术文本时,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语言,甚至让我怀疑起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也要一辈子以写这样的文章为业吗?后来虽然有《万历十五年》安慰了我,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况且那书原是用英文写成,再从英文译成中文,也许这道工序使得作者更加重视了语言问题。
许多人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大众文本只要让语言“生动流畅”即可,而学术文本则可以连“生动流畅”也不必了,只要代之以“严谨规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学者当然拒绝了跨文本写作,他们认为只要写“严谨规范”的学术文本就够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学者不进行跨文本写作也确实没什么大问题。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些从事跨文本写作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在进行学术文本写作和大众文本写作时,应该使用两套不同的语言,或者说是两套不同的话语。这种情形在西方,以前倒是渊源有自。比如学术专著用拉丁文写作,而通俗作品则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写。但在使用同一种文字时,这样两套语言的选择是不是有问题,还不好说。我的感觉是,这和作家创作语言风格迥异的作品,似乎还不是一回事。
我们很容易看到使用这样两套语言的实际例证:一些学者写“严谨规范”的学术文本当然没问题,这时他们还可以尽情使用各种“学术黑话”,既不担心别人看不懂,说不定还以此为荣;当他们偶尔进行大众文本写作时,就力图“生动流畅”了。不过他们追求“生动流畅”手段,却不是将问题尽可能地阐释得清楚明白,而只是增加一些废话,或增加一些出于想象的细节。事实上,很多人以为“通俗化”就是给文章注水,但写文章毕竟不同于加工饮料,注水效果是很差的。
仅仅将注意力锁定在回避“学术黑话”上,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所谓“学术黑话”,并不等于专业术语。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使用“学术黑话”来指称那些公众看不懂,真让学者甚至让使用者自己来解释也只能似是而非的措词和表达。这种“学术黑话”可以让使用者躲在它们背后,读者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作者也不想让读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作者想让读者知道的只是:我在说一些话。因为使用“学术黑话”的作者其实并未真正弄明白自己说的事,但是情况又需要他说一些话(比如需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来应付考核,或需要做一个发言来充充门面),这时使用“学术黑话”确实很有效果。
无论是在学术文本还是大众文本中,在极少数情况下,“学术黑话”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学术黑话”即使偶尔能够让初学者感觉高深莫测,总体来说既无助于自己思想的传播,也无助于自己学术声誉的积累,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使用“学术黑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然也就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由于长期以来,在我的审美体系中,使用“学术黑话”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至今尚未考察过这个观念是如何进入我的审美体系的),所以我无论在大众文本写作中,还是在学术文本写作中,都极力避免“学术黑话”。以前学者丹尼尔·希利斯在谈到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时曾这样说:“我对道金斯唯一的不满,就是他将自己的思想解释得太清楚了,读他的书常常会附带着产生一种幻觉,认为事情比它们实际上要简单得多。”而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写作时的追求,我希望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论证解释得清清楚楚,哪怕为此被人误以为我写的文章“浮浅”也在所不惜。而当田松教授评论我的学术专著“像侦探小说那样好读”时,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近这些年来,在周围朋友的提示之下,我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原来我在长期的跨文本写作中,一直在使用同一套语言(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我在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写作中,都在使用同一套表达方式,差别只是我在学术文本的注释中给出了参考文献而已。
我可以为这个现象举出旁证,例如,最初我总是先写学术文本,然后再写它的大众文本,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过程也可以逆过来,先有大众文本,再将它学术文本化。由于使用了同一套语言,在这两种文本之间的转换操作是相当容易的。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仍然习惯让学术文本先发表。
当然,在跨文本寫作中,究竟是采用同一套语言好,还是采用两套语言好,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许每个写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都会影响他的选择。
责任编辑:姜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