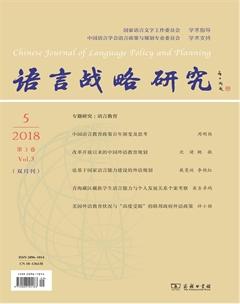青海藏区藏族学生语言能力与个人发展关系个案考察
提 要 本文选取4位已就业的青海藏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的语言教育选择与个人发展轨迹,将语言教育选择置于资本场域中,综合分析语言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特质。研究发现语言具有资本特征,语言教育选择策略是基于多种资本价值衡量与博弈的后果,占据不同资本优势的个体在教育流动与个人发展中较容易获得成功。
关键词 语言能力;个人发展;藏汉双语;个案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5-0040-06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50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bilitie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ibetan Students in Qinghai
Yingji Zhuom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has become an invaluable asset for individuals, and the choic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may exert lasting influence for student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personal advancement. In this case study, four Tibetan students from Qinghai Province have been sampled and interviewed in order to reveal to what extent their language education in school has played a role in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sets itself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choices as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 analysis is framed within Bourdieus theory of capital, assuming that every language in the linguistic repertoire is empowered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s.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with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petencies tend to be more successful in career than those who are versed in Tibetan only. As such,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all be enhanced in schools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are populated.
Key words language abilities; personal development;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cases
一、引 言
在中国青海H地区,每一个适龄藏族小孩都会面临一个择校问题,即选择汉校或藏校。选择汉校,所有课程均以汉语授课,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语答卷,谓之民考汉学生。选择藏校,则接受藏汉双语教育(H地区的做法通常是使用汉语教授汉语文课程,其余课程使用藏语授课),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一般使用藏语或汉语答卷,谓之民考民学生。这种以语言选择为导向的学校选择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这种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发展?本文通过分析4位藏族学生的语言教育选择策略与个人发展轨迹,运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探讨以上问题,并揭示教育选择背后语言资本逻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布迪厄颠覆了语言工具说,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它标志着更深层次的经济权力关系。他将语言与社会、经济、阶层、文化等因素相联系,剖析语言背后的资源与权力关系。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本质上不存在高低之分,但是语言的社会性导致了不同语言获得不同的资本价值。语言作为一种象征资本,象征着其人文素养、教养背景和社会地位。因此,语言能力在本质上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发生在各个社会空间的语言交际通常会受到参与者社会、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影响与干预。语言的经济资本性质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西方经济学家证实。Chiswick和Miller(1995)分析了主流语言的流利度对收入的影响,以澳大利亚为例证实了假設:主流语言的水平被认为是3个基本变量(语言的表达、第二语言的习得效果以及从语言水平获得的经济收益)的函数,相比其他变量,收入与语言技能有最高的相关度。克里斯纳·彭达库尔(Krishina Pendakur)和拉维·彭达库尔(Ravi Pendakur)等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总结出,掌握双语或多语言的能力可以使人胜任不同地区间的工作,增加就业者从事国际贸易和旅游工作的机会,并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优势。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也已有较成熟的研究。张卫国(2008)指出,虽然获取一种语言技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是一旦人们掌握这种语言,人们就可能有更多的交际机会,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位或较高的收入。也有研究关注藏族高校毕业生的语言水平与就业的相关性,发现汉语在就业中被赋予的高度价值不仅体现在就业考试中,也体现在这一价值连带的工作职位、工资等经济效益中(英吉卓玛,张俊豪2016)。
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中,语言的文化资本不仅是一种目的,也是个体与群体借以追求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语言的文化资本具有主动、积极的一面,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也消解了文化领域的非功利的神话。布迪厄指出语言的文化资本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表征人们身与心的人格特质;第二类是图书、工具等文化产品形式;第三类是文化的制度化形式,例如学生在班级中学习知识的状况、学习成绩及排名。这3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作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体制化状态的文化(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Bernstein(1962)的语言编码理论有力地说明了不同学校的教育资本的差异性,他分析了语言、社会化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在各自的言语活动中使用各自的语言规则。他将语言分为复杂型与封闭型两种类型的代码,这些代码在社会化背景中对不同语言进行了分化。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高宣扬2004)。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分析藏汉两种教育模式下个体的语言教育选择与个人发展情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二、案例分析
1. H地区双语学生双语能力与升学相关性调查
青海H地区为藏族聚居区,藏族人口约占68%,藏语为该地主要使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H地区的双语教育发展迅猛,双语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底,H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总数272所,其中小学114所,民族中小学(藏校)104所(占中小学总数的91.2%)。民族中小学(藏校)在校生37 267名,占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85.6%。H地区的藏族孩子到了入学年龄都需要在藏校与汉校两种模式中做出选择。一般情况下,农牧区的藏族家大多愿意将子女送至藏校,城镇的藏族家分情况将孩子送至藏校或汉校。
为考察H地区藏族学生整体双语水平及其对升学与个人发展的影响,笔者抽取了H地区藏校某年级学生近一年的双语成绩与高考成绩,查考其相关性。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学生双语水平与升学之间的联系,笔者将文科与理科班级的数据分别制作成图1和图2。
图1 理科班学生双语水平与高考成绩
图2 文科班学生双语水平与高考成绩
图1和图2可以看出:(1)该一年级77%的学生藏语成绩高于汉语成绩。理科班藏语平均成绩为104.96分,汉语平均成绩为88.34分;文科班的藏语平均成绩为107分,汉语平均成绩为91.55分。这说明藏校学生的藏语水平普遍高于汉语水平。(2)理科班的藏文标准差为19.69,汉语标准差为22.24;文科班的藏语标准差为16.62,汉语标准差为28.41。两个班级的藏语标准差均小于汉语的标准差,这说明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总体的藏语成绩离散程度低于汉语成绩,也就是说,藏校学生的藏语水平相差不大,而汉语水平差异较明显,汉语水平对升学的影响程度高于藏语水平。
2.材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源及滚雪球的方式进行典型个案抽样,选取4位接受了藏汉不同语言教育的藏族学生作为代表性个案,运用访谈法,了解研究对象的家生活情况与求学生涯经历,分析他们的语言教育选择与个人生涯发展,阐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这4位藏族学生来自青海H地区,在完成了不同程度的学业后,现已在不同的岗位就业。详见表1。
表1 个案学生的基本情况
个案 出身 父母职业 学校选择 优势语言 学历 就业情况
R 城镇 县教师 藏校 藏汉双语 重点本科 市级公务员
Z 农村 农民 藏校 藏语 大专 临时工作
D 牧区 乡镇公务员 汉校 汉语 大专 临时工作
Y 城镇 县教师 汉校 汉藏双语 普通本科 省级事业单位
3.个案介绍
案例1:R生于城镇,父亲是教师,母亲是一般企业职工,R的父母较重视R藏汉双语的学习。在访谈中了解到,他们对R的期望是既学好国家通用语也能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R父母的做法是:上学初期送至汉校学习汉语,同时在家由父母教藏语,到小学四年级转入藏校,同时在课外时间对R提供汉语和其他科目辅导。R因在汉校打好了汉语基础,转入藏校后汉语成绩和同学相比占有优势;同时,R的父母不断为R提供各科辅导,因此R的学业成绩一直位于前列,并受到老师与同学的喜欢,最终考入北京某重点大学。据R回忆:“在大学期间,我参与了学校各类社团活动,专门去参加提高汉语能力的活动,交流能力与组织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大学毕业时,可以比较流利地使用藏汉双语。”R在整个学业生涯中,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藏族传统语言文字与文化知识,也很好地掌握了国家通用语,属于较理想的平衡双语人。R毕业后在家乡的市级单位从事有关藏汉双语岗位的公务员工作,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
案例2:Z的父母为当地农民,只会讲藏语,家成员间基本使用藏语进行交流。在为Z选择学校时,他们听从亲戚建议,为让Z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将其送到汉校。然而,Z在进入汉校后出现了各种问题。例如,无法与老师同学用汉语交流,不能完全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等等。逐渐Z性格變得十分自闭,学习成绩也不理想,不受老师与同学欢迎。据Z讲:“我在三完小(汉校)的时候,每天都盼着放学,因为,老师讲课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听不懂,布置的作业也几乎没有全部完成过,班里的同学也不和我玩。”在Z三年级时,老师请来Z的父母,说明Z一直以来学习与各方面不佳的情况,建议转校。Z的父母听从老师建议将Z转到藏校。回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与文化环境当中,Z慢慢地打开了心扉,开始主动与老师同学交流,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Z这样描述转学后的心情:“来到寄校(藏校)我感觉很亲切,第一次感觉老师那么重视我,同学们很喜欢我,而且老师选我当了汉语文课代表。”在汉校积累了3年的汉语基础,使Z在汉语学习上十分自信,其他的科目成绩也渐入佳境。直到高中阶段,Z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然而Z所在班级学生当年高考成绩都不理想。Z进入一所普通大专。毕业后,因Z拥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如今在县城谋得一份工作。
案例3:D的父母来自牧区,在县城当公务员,父母主要使用藏语,汉语能力欠佳。D的父母为能让D将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将D送汉校就读,D进入汉校后很难适应汉校语言文化环境,甚至有些排斥。老师(汉族)也常常无法理解D的一些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在D的家文化背景中可能是被允许和理解的)。据D回忆:“我小学阶段是最痛苦的,老师总是批评我。”D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D的自卑感也愈来愈强。在汉校,D从最初的排斥到被动适应,经历了心理上的挫折;尽管身处汉语环境中,D的汉语能力得到了进步,可是学习成绩一直都不理想,最后只能进入一所普通大专,如今在各类临时性岗位中游走。D与其他就读藏校的同学相比,优势是操持较流利的普通话,但是D也从未有机会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身边也很少有藏族朋友。D代表着既不能融入本民族群体又不能很好地在现代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人。
案例4:Y的父母均为城镇教师,会讲藏汉双语,他们对Y的语言使用要求十分严格,Y的父亲告诉笔者,“我们对Y的要求是,在学校需使用纯正的汉语,在家需完全使用藏语,不可杂乱使用。”在为Y择校时,Y的父母经过询问比较,认为县城内汉族学校的教学质量高于藏族学校,为了Y能够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将来获得更多的升学与就业机会,就将Y送入汉族学校。同时,Y的父母在家中给Y授藏语。在汉校,Y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加之父母的引导,在初中阶段攻克了二语学习、家校文化差异、身份认同等困难,实現了文化适应,学业成绩很优秀。最终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还有过留学经历,现今在家乡的省级事业单位工作,拥有较理想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Y对自己的教育选择与求学经历的看法是,“我现在所获得的较理想的发展与我的汉语能力分不开,在汉校学习给我带来的是更多的教育选择与发展平台。但是母语文化学习的欠缺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4.案例分析
以上资料表明,家的文化资本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教育选择。R与Y的父母做法为:Y进入汉校,父母同时给Y辅导藏语言文化知识;R进入藏校,父母同时给R提供汉语与其他学科的辅导。这说明R与Y的父母都意识到,无论是考虑将来发展还是完善个人文化素质,双语双文化是最佳选择。在学校中,R与Y 获得了更多形式的文化资本,例如,获得图书与参考资料(文化产品),受教师与同学的喜欢(文化人格特质),取得优异成绩(制度化文化),因此,R与Y获得了教育生涯上的相对成功,实现了身份的向上流动。
然而,这种文化资本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量,也不会带来质的改变。在Z和D的案例中,Z的父母来自农村,尽管最初为获得较高回报,有意识地将Z送至汉族学校,但在Z经受挫败后又送回藏校。这是由于Z的父母所持的文化(藏文化)与学校文化(汉文化)不一致,原生家的教育经验与价值在学校被忽视。Z的父母无法给予他学校文化知识,致使Z在陌生的文化环境(汉校)中感到孤单无助,得不到老师与同学的理解。D的父母尽管是公务员,但是其文化资本能力有限,同样无法给D提供较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与语言资本。因此,相对于R和Y,D和Z属于较低层次文化资本者,这些低文化资本的个体是相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而言的,他们的受教育路径与生活境遇不容乐观,不具备精英群体的特征,在班级里处于从属地位,经常受到排斥与边缘化。这些缺失文化资本的个体在其教育路径与生涯中会面临许多困境,面对这些困境,他们只能自己找寻生存策略。
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工作中的高收入,还体现在学校场域中因语言资本而获得的奖学金与奖励等经济价值。在以上案例中,R和Y之所以能够在相对发达地区获得相对稳定与高收入的工作,与他们较好的双语水平有关,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汉语能力。语言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继承自家的那部分,在选择何种学校、在何地上学很大程度上由家的资本背景决定。汉族学校就是以复杂型代码为基础的社会化产物。优势家出生的学生(R和Y)与汉族学校文化环境相似,他们掌握复杂型语言(汉语)的能力较强,而劣势语言家出身的学生(Z和D)首先需要克服语言障碍,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与优势阶层的学生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语言作为重要的资本符号,能够伴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到资本转换中,通过转换,对个体的教育成就与身份流动产生影响。在以上4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文化资本拥有较强的转换力,在不同场域中转换为制度化与合法化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R与Y在学校场域拥有的较高文化资本(学习成绩好)带给他们的是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向上流动的砝码(本、硕、博),并且这种文化资本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学校场域内的社会资本,即良好的社会评价与地位(受老师与同学喜欢),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它的直观形式是奖学金或奖励。在社会场域内,R与Y拥有了收入较高的职业,在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工作与生活,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
三、结 语
本研究分析了青海H地区4位藏族学生的语言能力与个人发展轨迹,发现语言教育选择背后的资本博弈过程。究其根本,这一结果是资本再生产、学校教育体制与社会制度的产物。研究民族地区个体语言教育选择与个人发展相关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1)对于面临择校、择教学语言的个人而言,应了解语言能力对教育成就与身份流动的影响,对未来生涯发展有较为客观清晰的认识和规划。(2)民族地区的汉校应普及民族文化知识,提升教师的多元文化素养,避免身在汉校的藏族学生缺失认同感,成为文化边缘人,出现学业失败等问题;同时,民族学校应提升汉语教学水平,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加强双语类其他学科的教学质量。(3)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建构适宜少数民族学生发展的学校教育体制,制定适宜少数民族学生发展的语言教育政策。(4)在民族地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就业通道与社会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高宣扬 2004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1998 《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英吉卓玛,张俊豪 2016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藏族大学毕业生藏汉双语水平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以青海省T县藏族大学毕业生为例》,《民族教育研究》第3期。
张卫国 2008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Bernstein, B. 1962. Social Class, Linguistic Codes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Language and Speech 5(4), 221-240.
Chiswick, B. R. and Paul Miller. 1995.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2), 246-288.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