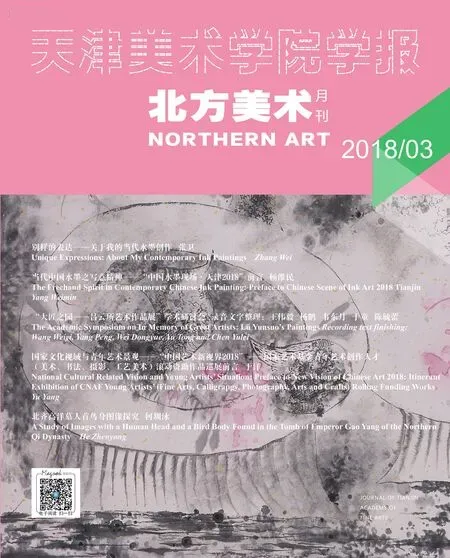“大匠之园
——吕云所艺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
录音文字整理:王伟毅 杨鹏 韦东月 于童 陈毓蕾
Recording text finishing: Wang Weiyi, Yang Peng, Wei Dongyue, Yu Tong and Chen Yulei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执行主编):首先是艺术感动了大家,吕云所先生艺术的魅力召唤大家来共同见证展览,出席他作品的学术研讨。两年前,吕云所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吕云所先生的遗作展,今天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也就是吕云所先生生前工作的地方举行一个规模更大的回顾展。这个展览很显然比在中国美术馆的规模和研究层次上更加深入,那么之所以更加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作品的数量比较多,通过我们这五个展厅近三百件的展品,非常全面地展现了吕云所先生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晚年的作品,大概应该分成几个时期,各位专家可以畅所欲言。
第二,这个展览不仅有最重要的代表作,像我们开会的这个展厅展出的应该是他20世纪90年代进行太行山山水探索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再次,这个展览还很好地展现了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就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美院美术馆策展人员为这个展览做了诸多的努力。吕云所先生留下了很多的草图,让我们看到这个展览作品的艰辛创作历程。有些草图是用水墨来做的,有些是用素描来完成的,我觉得一个中国山水画家用素描来创作他的小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他作品里面看到的不仅仅是吕先生画的太行山,而是他对太行山山石造型结构的总体提炼,并在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符号化、象征性、纪念碑式的一些探索。这样的太行山应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视觉意义上的太行山,他进行了笔墨现代性的一些探索,我相信这些草图有助于我们对他作品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在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吕先生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从事创作和教学的一些作品和画稿,也就是说他在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的还有人物画。所以,新时期以来很多重要的人物画家,我们也可以看到吕云所先生对他们的影响。在这个展厅里面可以看到他画的连环画的作品以及手稿,不管怎么样这个展览提供给我们探讨的话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并举行研讨会之后,今天移至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还能够进行学术研讨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展览作品的完整性,其次就是能够请到像杨德树先生、王振德先生,他们都是吕先生的生前友好,对吕先生非常了解。所以,今天的研讨会有一些吕先生的生前友好对他的回忆,使我们感到更加真切,其次请到了林木、顾森和舒士俊先生,他们从外地赶来,从学术的深度上可能再一次会对吕云所先生的艺术创作进行一些新的评析。

吕云所 山月 106×100cm

吕云所 收获季节
吕先生回到自己艺术家乡的展览,在天津美术学院有他的辉煌,也有他的痛苦,也有人、事对他的“折磨”,这种“折磨”可能不仅仅是生活经历上的,可能还有在艺术探索上的。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次展览除了20世纪90年代,还展示了新世纪以来吕先生在中国画探索方面一个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要不要变?或者他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不管怎么样,探讨的话题的的确确是很多的。虽然对吕先生做过一些研究,但是今天的展览还是对我有很多新的启发,相信大家也有同感。
首先请杨德树先生先发言。
杨德树(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今天,吕云所艺术作品展览组织这样一场研讨会,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交流机会。开始我有一些怅失,思考他的过去,有一种追思的意思。我想在这种热烈的、隆重的展览会中大量的作品面前,使我们有一种高度的兴奋、一种快乐感来研究、讨论、学习吕云所的艺术。因为,对于艺术的研究我们还是实践得多,研究得少。但是今天对于吕云所先生的状态、吕云所先生的艺术,对他这么多年的积累,我自己感觉还是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吕先生与我是同学,是共同生存、共同成长起来的好弟兄、好朋友、好同事。他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非常地成功。他离去了,这是自然规律,人都是要走的,挽留不住,但是他的一生奋斗在教学的第一线,这位弟兄的一生都交给了课堂,交给了画室,交给了创作。吕云所先生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家,他20世纪60年代初接受比较系统的教育,天津美术学院有许多优秀的中国画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师。在那个阶段,1965年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认真的学习过程。我说吕云所先生全科,山水、花鸟、人物,无不经过比较有影响的优秀老师的指点,有那么几年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我们学校人物画的老师多数是聘请过来的,由中央美院和其他有成就的艺术家聘请过来兼课或者讲学,所以有意要培养一部分自己的学生。吕云所、陈冬至,我们先后七位同志留在学校,任务就是开展人物画教学的努力,做人物画教学的准备。吕云所的人物画在60、70年代,都是在我们共同的人物画的创作环境中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创作连环画、带学生、搞课堂教学。我们的前半生一直致力于创作中国人物画的当代形象。“文革”以后一路蹉跎,一下十年,我们共同过来的弟兄和朋友们不愿意回忆这蹉跎的十年,但是历史就这样写过去,蹉跎的岁月里我们每个人不断地寻找机会,来寻找自己所理想的那些事物、那些理念、那些学问。教育上属于一个非常时期,艺术上也属于一个非常时期,所以我们共同走过那个蹉跎的时期。

吕云所 律动系列之二——枝的交织

吕云所 河畔人家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又迎来改革开放、恢复教学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家,一个执着的艺术的殉道士,人物画一直到最后也在他的研究课题里面。但是由于教学的需要,在80年代初,因为教学分工他抓起了山水画。对于山水画他有所偏爱,吕云所具有深厚的大山情结,对巍巍太行有深刻的感性认识。我说他情系太行山,这一点还有浓厚的乡情、浓厚的太行情结。他的作品最后立足于他的故乡,立足于培育了他一生的精神家园,为我们留下了他闪光的作品。大家共同认为他最后一个时期追求积墨山水和当代山水有机统一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他把历史上形成的北宗山水和积墨山水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作品里表现出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形成了很空灵、很松快、很直率这样的一个崭新的山水画面貌,而且不愧于当代的革新的局面。他用心探寻过山水画的现代语言,但是他最后回归到传统和现代精神的结合,根基在自己的真实体验,这一点成就了吕云所先生的艺术。对于吕云所先生的艺术跟他教学上的成就、教学上的成果,在此不想多谈,咱们有专题的研讨,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经历表现一种深切的怀念和学习。
邹立颖(海军政治部艺术创作室主任):上午看了展览,我感觉分两大块,第一部分是人物画,吕先生人物画虽然走的是徐蒋教学体系,但也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第二部分是山水画,首先对他的作品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有现代气息。因为我是画水墨人物的,对水墨的敏感度也比较强,他在画面整体上满构图,有现代的感觉。这种现代气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用抽象的笔墨,第二是抽象的造型。他作品中的山我认为都是吕先生心中的山,他生在太行,长在太行,立足于太行,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我们都知道,生活是艺术之母,优秀作品都是生活的馈赠。他主要以写生的方式深入体验生活,扎根生活,以此入手,提炼出他心中的太行景象。他对太行山的认识、归纳太行山的语言和形体上的塑造都有抽象的元素。我认为现代中国画如果要有时代气息想向前发展,那么抽象的造型和笔墨是离不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吕先生的抽象笔墨,他的画很多是用积墨法,在重墨线的边缘留有亮光,就是在造型上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个借助光但是没有表现光,第二用山的纹理结构重新组合,这种山的画面感觉和视觉冲击力就比较强,有很多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吕云所 溪边牧歌
林木(四川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今天的展览是一个全方位的展示,看了以后很感慨。吕云所先生多种风格、多种题材都表现得很精彩,以前对他的了解是山水画,今天看到人物画也画得这么好,连环画画得也不错,小品也很精彩,真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大画家。
吕先生最著名的还是画太行山,这让我很感慨。因为吕先生是太行山出生的人,在那儿成长,表现太行山跟一般人走马观花的表现就不一样。他偏重于对太行山哲学方面的理解,有的艺术家偏重于太行山抗战英雄业绩的一些联想。从太行山本身要表现出很有价值的一些特点,应该说吕云所先生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山水画的发展来看,近一些年山水画有一种偏向于笔墨本身的表现,看一个人的山水画就看笔墨,落笔是否地道,这是一个主导性的山水画趋向,可能在江南一带的山水画家比较明显。那么山水画本身给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和这种体验所传达出来的一种情感意象,在当下山水画里面表现得不是太理想。吕云所先生的太行山在恢复中国山水画意境和情感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看吕先生的太行山水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在看吕先生画的时候没有先关注他的笔墨,看完后感觉他笔墨还相当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吕先生所有的结构、笔墨全部在表现他的情感意象。所以,他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不是笔墨本身,而是太行的情感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超凡的气魄,在我们今天画山水画里面能够达到像吕先生那种气魄与气势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都注意了,他那个题目《太行浩气》《浩荡雄风》《太行天下脊》《苍山涌墨》一系列的积墨太行,笔墨都是完全服从于他的情感意象的,今天来讲,在山水画上应该是大力倡导的。
比如说他也画太行的夜山,让我想到和黄宾虹的夜山有区别。黄宾虹看到的更多的是墨法本身,积墨本身,当然他的杰出贡献是在墨法方面,在笔墨方面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意象,他在一般人觉得笔墨很难发展的情况下,创造出全新的理念,黄宾虹的思维是服从于笔墨意象的。但是吕云所的笔墨山水画服从于太行山的情感意象,他与重笔墨的画家有一个重大的原则性区别。他这种意象方式在结构方面又发生变化了,很少是平视更没有什么仰视,他是凌空俯瞰,具有一种浩大的中国的宇宙观在里面。所以,他太行山的表现产生一种浩大的宇宙倾向,而这种倾向又通过节奏与韵律的表现来达到,它的各种各样的内部形态比如说S形、反S形等等都构成一种常见的节奏,我还注意到他有一幅画两个折线,这么折过去,那么折过去,他用这种结构方式来达到一种强烈的运动感和力量感。他的律动系列,墨韵的意味是很强的,在节奏与韵律中追求呈现强烈的运动感,这方面吕先生是非常自觉的。由于他对节奏与韵律能很好地把握,画面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运动感、跳动感。我与顾森先生看画的时候一直在想,吕先生一直在探索,探索过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
这次展览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他的小稿都附在旁边,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展览中不多见,把一个画家在构思这幅大画的时候的很多想法、初步的构思都呈现出来。看那些小稿的时候,大家都说特别精彩,精彩是因为它随意、天然、灵动。
通过这些小稿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吕云所先生构思这幅大画时候的一些思路,他一幅画可能有好几个感觉,怎么表现它,用小稿子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一点也是吕云所先生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王振德(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今天我特别感动,因为在老学长过世以后能举行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和研讨。学校领导非常关心吕云所先生,还有在座的理论家、艺术家非常关心老学长的艺术,特别是我觉得吕先生的教育非常突出的一个成果,就是他的孩子吕大江在自己的先父故去以后,还这么为父亲的艺术操劳,在中国美术馆展览以后在天津搞这么大的展览。大江在吕云所先生的晚年把自己心定下来,认真地传承吕云所太行山的艺术,确实在清华高研班里面他的画有很大的进步,做人的格调上、作风上、为人处世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体现了吕云所的教育,从社会到家庭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所以吕云所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愧为天津美院的好教师,也不愧为美术界的非常突出的教育家。我听过吕云所先生的课,因为我们是老邻居,在美院的北院一块住了十年,南院住了十年,搬了以后还是邻居,一个金碧园,一个金辉家园,所以他很欢迎我听他的课。他的课每节课都认真地备课,他那一本一本的备课日记都在窗户下面,因为屋子当时很乱,都在上面摆着。他的日记和备课本大江应该好好整理整理,非常重要的,很多都可以放到学校让学生看,讲得法通理明。上课时他一边讲一边画一边说,说完以后学生不提意见他拽着你,你有什么不懂你再提,诲人不倦,往往下课以后跟学生说起来没完没了,非常热情,倾囊相授。
吕云所先生吸收了孙其峰先生一边讲一边画的教法,上课时他一边讲各种树一边示范,讲松树就比画松树的姿势,两胳膊下垂,昂首挺胸,柳树、槐树,手舞足蹈,全情投入。在讲课的时候忘了自己,真是激情式的讲课,他是全面地理、法、情、意地讲。吕云所干什么事都是探其究竟,融会贯通,最后合为一体。吕云所在教育方面桃李满天下,退休以后又在社会上结交了很多画太行的高手,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在海外的时候无论是新加坡还是美国,也有一些人跟他学画,所以他影响遍及海内外。
1962年到1966年那时期从《漳河畔》到《老来红》就是去欧洲、非洲七国展出的作品,都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他是五年打基础,五年中指导他的都是名师,从北京来的,他的画受到张德育等老师的影响。他留校以后就进行了探索,这个时期的画受到王颂余、李智超等人的影响,主要是孙其峰的影响。
受形势影响,“文革”当中他主要画连环画;改革开放以后五六年的时间,受到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画律动系列;大致1987年以后潜心作画,苦熬苦修,五年时间画黑太行系列。太行系列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他对当代绘画的表现方法融会贯通,一个是有传统的画法,再一个是有现代写生这种新的山水画法,再就是吸收了外国构成中抽象表意的画法。他把当代几种山水表现方法合为一体,成为吕云所表现太行黑色系列的画法。吕云所作为太行人表现太行的风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一个是黑色系列阶段,第二个是他到清华搞高研班以后。他原来画的太行大概是河南西洱河以东,他的家乡涉县一代的太行。涉县以东的太行是比较苍凉的,草木比较少,所以他画的有沧桑感,但是浑厚大气,画出了太行的风骨、太行的浩气、太行的雄浑。这也是他对千年历史的回顾,太行沧桑的回顾,对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回顾,还有他对早年生活的回顾才有了黑色太行系列。
当时我记得袁立山先生说吕云所热天也不休息在里面画太行,老师傅特意让我陪着看画太行,说画太黑了,但是吕云所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画的太行是他对太行的总体印象,画太行的雄浑博大,也画他自己那种苦难的、苍凉的记忆。吕云所从1987年到1993年第一个阶段的太行,大致是他内心的这种感情、整个修养的体现。这时候他已经形成了以《漳河畔》为基础的太行风、太行画派。他是兴于太行,即留校出名是画太行《漳河畔》,经过现代思潮之后他又坚定了画太行,把表现太行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所以,黑太行的出现就是吕云所把感情、智慧、功力甚至灵魂都献给太行,把太行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太行系列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受到了林木、陈醉、顾森还有刘曦林等理论大家的肯定以后,提高了他的信心。
吕云所在黑色太行之后又变成了绿色太行,所以绿色太行就在手法上不是像原来的以感情、以志向、以理想来画太行,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是在技法上面一定有所复归。所以,不管是早年老师教的这些技法综合运用,还是在清华大学高研班任教时候的山水反映了他复归传统的面貌。这时候吕云所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把太行系列纳入到国学的修养当中。他70岁以后苦读国学,见面的时候他给我背《大学》,背《中庸》,讲《论语》,所以他特别有追求,特别有激情,也愿意在传统上更进一步。然而年龄不饶人,吕云所的故去使大家感到无限的悲痛也替他惋惜,但是他作为北方山水画的大家创立的太行山水画派,作为天津美院涌现出来的教育家,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崇敬,也值得传承。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时间过得真快,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但是吕云所先生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一直很深。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就是在一个研讨会上面,一下子好像很熟悉了。他一直跟我在一起聊天,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样一个画家不仅仅跟你讨论问题,而且不停地追问问题,真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年纪差不了多少,给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很透明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赞扬人很多,批评人也很多。
第二个,他是非常善于思考的人。第三,他是勇于钻研的人,不懂的东西愿意问,不耻下问,而且他追根到底,什么都要追问到底。有时候谈起一些很具体的人对他的评价,尤其像我们做理论工作的不太轻易在背后说某个人的好话或者坏话,就尽量含蓄地回避一点,直接对某个个人具体评价传出去不太好,毕竟是私下的聊天。但是,我觉得他很勇敢,而且很执着,这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看吕云所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他的画非常有气魄,有一种气势,这种气势不是制作出来的,这点很了不起。我们可以有很多联想,他画太行作为一个典型的拿手题材来看,我们如果有古人情结的话,会有一种盘古开天地的感觉。他画出了盘古当年开天的时候一种神秘感,甚至一种苍凉感和一种恐怖感,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崇高,是我们中华民族深邃的精神内核所在,这个很好。如果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可以联想毛泽东的诗词“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就是那么博大、高远的感觉,如果有抗日情结的话,铜墙铁壁、气焰千万丈这些都有。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诗意,他画很多画,深藏着他自己对故乡的那种热爱,他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生活的体验我们可以在他的画里面感觉到,并得到一种启示,是打开你心灵的钥匙。因此,他的画不是做作的,不是制作出来的,是他自己融化在大自然里面的精神体现。山水画就是把山画出一种精神来,所以,各路英雄不管是大家,不管你是学者,不管你是一般的劳动人民,看他的画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一种共鸣,这是他的画的好处,这是我的一个深刻感受。
这次展览了不起,他的儿子吕大江继承父亲的事业,把他父亲这些遗产拿出来让大家更多地去学习,尤其展览了他早期慢慢被太行山水所淹没的以前画的人物画,我觉得这个挖掘出来很重要。他的人物画画得很好,尤其牛、牧童这个题材画得非常有诗意。为什么有诗意?这个也很不容易,而且我说了他有钻研的精神,刚才王振德先生也说到他学国学,背《大学》。改革开放后他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后现代的那种理念甚至构成方式,这是很好的借鉴。所以,他的画形式感非常强,点缀一些小动物很好。因此,功夫深的人画什么都可以画得好,这就是有本事的人永远都有本事,任何地方、任何困境里面都会发出他的光辉。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种学问的深度和自己对学问追求的意义,恐怕在座的年轻一代以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老年一代都要很好地崇敬他,学习他这样一种精神,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舒士俊(《朵云》杂志暨《书与画》美术月刊副主编):画太行山我印象最深的就两个画家,一个贾又福,一个就是吕云所。另外,我感觉吕云所这个名字,本身跟太行山密不可分,这个名字本身有一个魔力,这个“吕”字,两个方正的口就是太行,而太行是云之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是对画家画风的暗示,可能这个问题有点玄。李可染的画以染为主,石鲁的画很奔放,实际上也是名字的一个反映。我觉得名字对于画家本人是一种心理暗示,一种使命感的暗示。所以,吕云所最后放弃人物画,魂牵太行,是必然的归宿,这种归宿是使命感在驱使他,因此,他做出来的成绩和一般没有使命感的画家是大不相同的。
再回过头来看吕云所对于形象的把握能力非常强,对于用笔的节奏感,用笔的灵性、弹性非常敏感。他的用笔像展厅里一幅《狂歌漫舞》的作品,让我想起宗炳说的山的韵律,动起来可以让整个山没有间歇,吕云所用笔的灵性能够达到这么动人,他的使命要归复到太行,要归复到大山,而大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远古。吕云所这个名字也好或者自己孜孜以求的追求也好,他就体悟到了大山跟云结合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看展厅里边很多画都是大山跟云的结合,大山是阴的,云是阳的,这个阴和阳的纠结呼应造就了他的特殊表现题材,也形成了他的画的一个特殊的气格,所以这个气格让人很难忘。
而且,他与贾又福的追求不同的就是他是从全方位来的,抓住了云和山的关系,但是又非常讲究用笔。他用笔这里面有很多幅讲究动,但是大山深层次的东西又有静的东西,然而他的个性是很奔放的,他要掌控自己的个性,所以看得出他的一个努力就是后期把自己动的笔往静里走。其实李可染早年的笔也很动,后来跟齐白石学习后才慢慢地静下来。吕云所原来用笔很动,我上次跟他说,比如说你这样要飘到山谷里面去了,后来他慢了下来,最后沉了下来。所以,他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的力气,用笔从原来很动,然后慢慢地静下来,慢下来。接下来就是用墨,他的山水有一个阶段笔性很厉害,而且大多数是干笔,而后期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最后的太行写意的有一些小画非常精彩。我昨天用手机都拍下来了,这是他接下来努力的方向,所以说这样有使命感的一个画家,如果老天再给他五年时间、十年时间,面貌会有更大的变化,我很为他惋惜。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刚才舒士俊先生讲他很为吕云所先生惋惜,我每次谈到吕云所先生艺术的时候首先非常惋惜他这个人去世太突然。我们接触最密切就是后期,因为我们当时带一些学生,他来讲课,我们一起出去考察,一起办展览,一起参加评点,每次出去就是将近一个星期,出去了很多次。这中间,他跟我谈了很多他对于自己画太行的一些体会,实际上就是有一种心里面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那么在笔墨上想表现出来也没有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困惑。从他这次展览上我看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工作,但是戛然而止,没有走下去。
从他这个画,我想到北京画院有一张齐白石的虾。齐白石的那上面有一个题词,大意就是说我画虾经过了三次变化,开始是一种形式,要求逼真,最后是求墨色深浅。齐白石的意思就是说画到最后并不是画一个虾而已,而是在笔墨的深浅上下功夫,整个的笔意神采就足了,这是齐白石追求的画,半个世纪走出了这个路子,走到最后。其实吕云所也是走这个路,我们从他后面看到的画也是追求一种色调深浅,这个事情不可能回去了,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他留下的这些画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他真的是用心在画。
但是,这里面真正打动我的是吕云所自己用心画的这些画,你读他的画可以读得出来。比如山水里面人物不多,点景是牛,群山万壑中间,山上有一头小牛停在那里,我觉得那就是吕云所,他在那儿体会他的太行,那只牛在画面上很孤独,因为每个人在追求艺术表现突破的时候都有一种孤独感。我看那个画非常打动我,还有他很多那种一头牛的画是吕云所对自己的表达,他把自己的心意放进去了。郑板桥最后两年时间,画到精神飘落处,更无真相有真魂,把魂画进去了。吕云所的画也是把他的魂画进去了,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何延喆(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吕云所是我的老师,我和吕云所老师私人交往非常深厚,来往比较密切,而且吕云所先生的历次展览活动我几乎都参加了。我还给吕云所先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几篇发表在杂志上。尽管吕云所先生作品看了很多,对这次展览尤其期待,这次他大半生作品都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里展出,每次看他的展览都有不同的感觉,因为我的年龄也是在逐渐增加。回顾过去,回顾历史,感觉他的展览又进入到一种像古人所说的那种深情状态。什么深情状态?上下千古浑然不知,我慢慢自己沉淀,才开始对他的作品各个层面的问题进行追问和思考,此时此地再进行一番说明,感受比以往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总之收获非常大。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一点,刚才几位专家学者提到了,当代画家有相当一部分把生活视野投向太行山,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正成功的画家并不多。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广州搞了一个南北画家画太行的活动,当时参展画家一共28位,其中有一对父子兵,大江也参与进来了。在这次展览活动当中有三个画家比较受关注,吕云所先生、贾又福先生,还有一个河北省的白云乡,因为这三个人生活在北方,跟太行山的接触比较密切,很多表现太行山的画家都是以采风的状态来画太行。而吕云所先生跟刚才提到的那两位北方的画家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吕云所先生家乡就在太行涉县,太行涉县在什么地方?在古代是隶属于林州,在1949年以前属于河南,当时叫豫北道,它离荆浩写生的洪谷只有几十公里,而且吕云所先生从小生活在那里。有的专家提到太行山是中国历代北派山水的摇篮,早在一千多年前,荆浩在这些地方画画。当初我们天津美院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做了很多,温县那个村,包括孟县这些地方都在太行山脚下,所以中国山水画经历了一个从北派郭熙到李唐的一脉相传。因此,吕云所先生在表现太行跟其他的画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地域因素和个人的特殊阅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提到了吕云所先生是非常好学的人,他在文章里提到对画家有三个要求,一个是学识,第二才华,第三神采,这可以用舒士俊先生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他注重山水画这个气场,山水画气场尤其能够体现画家的生命状态和艺术成果。吕云所先生的画之所以打动我,是他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特点,所以就像舒士俊先生说的特别能感染人。
第三点,应该感谢组织这次展览的天津美院美术馆馆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不仅从宏观上让我们看到了吕云所整个艺术发展的心路历程,同时,从微观上让我们看到吕云所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比较容易让我们对吕云所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思想以及他在画坛上的位置能够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解读。吕云所曾经在他的文章当中写过,他说中国山水画不以模拟自然为能事,好的山水画是能承载画家精神内涵的载体,是画家对现实乃至整个宇宙的组合。他认为山水画有两种,一种是抒情的,一种属于大山水,这种大山水,他特别关注洪谷子的精神。吕云所先生的山水画好看,同时便于我们观赏,便于我们玩味,他的作品让人进入到一种生命的自觉状态里面去体验,体验什么?有限的人生在哪?在那千秋永在的自然里。
王伟毅(天津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处长、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这个展览准备了一年半以上,准备展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山水画由古典转向现实题材和现代主义转换的时候应当考虑社会因素对于艺术家的影响,比如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艺术家观念的影响。有人讲过近代山水画史就是观念史,我想这样说不为过,在这方面吕老师是很好的研究个案,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研究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下面提出两个问题,就是作为古人的山水画和其他题材的古代绘画一样是历史上文人的一种自我修为的方式,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很多古代的画家都是业余艺术家,他们首先是文人,写字画画重在自我修养的提高。而在准备吕老师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发现吕老师小的画稿草图2000余张,有的一张大幅作品会有超过十余张的草图,而且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他的晚年。我想除了他的画面推敲研究之外,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吕老师通过草图手稿去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呢?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手稿更具艺术价值。
第二个问题,吕老师是通过写生进入山水画创作的,与早一代或者两代的艺术家不一样。大家从三楼的手稿展厅当中可以看到,年轻时候的吕老师画过很多速写写生,
是非常具有西画传统的写生,与古人的完全不同。但是到了晚年,20世纪90年代前后创作的山水画又离开这种西画学习打下的基础。我有一种感觉跟大家交流,就是这种追求人书俱老的画面是有意为之还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现在还想不透。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书俱老的成熟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这种风格的追求下,往往失去了艺术作品的一种鲜活感,而使画面缺乏生机。我这样说没有对吕老师有什么不敬,因为作为艺术创作者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最主要的是自由挥洒的思绪,以这种思绪去感染观者。

吕云所 太行暮色图
杨维民(天津画院研究员):对于吕老我比别人多了一层敬意,因为我和郝青松和吕老都是邯郸人。当我开始走进这个专业的时候,就知晓了吕先生的大名,尤其我们是河北人,是邯郸人,是太行山下走出来的人。吕老是邯郸也是河北省近现代继王雪涛之后为老百姓喜爱的艺术家,当然邯郸也走出来像方力钧这样的当代艺术家,但是吕云所先生另立一面旗帜。我和吕先生后来有幸近距离接触过两次,这两次是同一天,有一次从武汉回邯郸,恰巧在卧铺车厢碰到了吕老,吕老第一次也看到我做的展览画册的时候欲言又止,我知道吕先生有话要说,所以说晚上到了邯郸以后我又去宾馆拜访了吕先生。吕先生当时对我策划的展览里面的参展画家,真的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尤其最近看到尚辉先生主编的《美术》杂志里面,中央美院袁宝林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是来探讨天津的津派应该是成立的。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谈论一个京津画派,把天津置于北京之下一起谈。但是就吕老的画作、吕老的这种创作、吕老的艺术思想而言,我觉得如果海派是一个海纳百川的现代画派,津派也是可以成立的,津派更多应该像一个融汇中西的画派。吕先生很执着,他在天津美院从事教学和创作有很多的历程,也是按照西式的艺术教育成长起来的画家,接受近现代的学院派教育,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经历,这就构成了一个奇特现象,有的人是向另外一极走得多一点。我觉得吕先生的性格天津美院的很多人是知晓的,我也略知一二,和吕先生近距离两次接触我觉得吕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真的是从自己内心感受出发来画画的人。看展厅里面的作品,刚才我也请教了郝青松博士,吕先生也以当代艺术手法尝试了一些作品。一个艺术家永远向前探索,但是最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那些东西是很难取舍的,吕老是天人合一。他从太行山走出来,他初中毕业走到了天津,整个的这个人生经历,从大山里出来,然后去学习艺术,同时也回到大山去体味去创作,整个把他的生命和太行山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吕老师不仅是继王雪涛之后邯郸走出来的现当代艺术大家,今后如果有学者在研究津派绘画时,吕云所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荣铁(西藏文化厅副厅长):这次来看到吕云所先生这么多的作品,真正打动我心灵的是太行。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自由表达情感的对象。在太行系列里面我见到了他的太行精神,艺术家最重要的是精神的体现,没有精就没有神,精神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观念,不在于笔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画必须要有笔墨,我个人的意见笔墨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作品能打动观众,让观众能产生共鸣,产生一种思想灵魂的撞击,这是太行精神给我的一种力量。
第二,讲他的太行语言。一些艺术家画很多的东西,山水花鸟都画,可能语言很多,但不是很准确。我觉得吕云所先生他的语言很准确,他的审美要求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想表现的这种境界,这时候追求浑厚、苍茫,用单一的笔墨通过黑白的方式,展示他追求的中国画的一种更高的人文的精神气质。他不是靠色彩,实际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用单一的这种墨色的变化来把自己所表现的对象展示出来,形成他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审美语言,找到了语言就是一个画家对中国文化向前推进的一步,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即他的审美语言。
第三,人文精神。一个艺术家不光要有精神和语言,还有他的人文,人文就是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很多搞艺术的人可能更多地注重自己的情感流露,然而艺术的情感流露恰恰要与中国大的文化脉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把自己的精神融入整个的时代脉络里面去了,展现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和整个的文化是合拍的,同时也真正为中国文化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吕云所先生在古人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笔墨语言,找到自己的人文精神。
卢永琇(天津美术馆副馆长):今天看到这本吕先生的画册,又看到这个展览,给我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一种冲击力,就是他的山水作品所反映的大气和这种人物画创作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的情感,这两点尤其是山水画所表现的这种断崖式的山的险峻,利用构图和笔墨来表现气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美术馆的一个副馆长,我在策划一个连环画的展览,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也看到了吕云所先生在早期创作的一些连环画的作品,这个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由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家对社会的影响,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对于社会中普通百姓的影响,这些对我们社会的审美,对普通人的审美,对时代精神的引领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重点研究的课题。
杨惠东(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我读硕士时候的导师范保文老师和吕云所先生算是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现在回顾他们这一代人在进入高校的时候有两个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就是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体系在全国确立主导地位,第二个就是对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中国画进行改造。我觉得这两个大的时代背景对他们这代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主要是写生,把师古变为师造化,从功能上、从审美取向上、题材表现上都和传统的中国画有了极大的不同。他们这一代人进入高等美术院校,立足于西式教育,而不是立足于传统的摹古式的教育方式,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观察视野与基本立场。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画发生最大的变化特别是山水画领域就是有这种出世的情怀到入世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我想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像山水画领域由以往的体现高超的出世情怀,还有这种王朝的怀古的幽情不见了,毛主席诗意开始出现在山水画当中。太行山在中国美术史上很少进入中国画家的视野,为什么50年代以后太行山成为山水画表现非常重要的题材,我想就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政治寓意。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画家,可能对于传统、对于艺术与生活的这种处理会有自己的选择。到了80年代之后随着环境宽松,这批画家在面对新的形势也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探索。我记得8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也是一批中年画家像吕云所先生这么大年纪的中年画家他们的展览。他们习惯了传统的创作,如何面对新的形势,他们就是有不同的选择,我想这种不同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画家今后在美术史上的定位。
郭雅希(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展览有好几个系列,但是最感动我的就是黑色积墨太行系列。看到这个系列我非常激动,概括地说是四个字,第一是奇,第二是险,第三是苍,第四是厚。奇就是有一种出奇制胜、奇而不怪的感觉,险就是有一种悲壮的感觉,苍就是老辣的感觉,厚就是深厚、博大、浓郁的感觉。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审美之境,但是我所感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后来想到一个广告词,我豁然开朗,就是品质的背后是品格,品格的背后是品位,它的这个审美背后还有一种人格的东西是更让我感动的,也就是说支撑画面的不仅仅是才华,也不仅仅是太行山的题材,而是他的人格的东西。他的这个奇就是一种真诚,因为我也接触过吕老师;他的险就是一种非功利,这与他的做事的方式,还有那种真诚的投入、忘我非功利、不在乎结果得失有很大的关系;他的苍就是有率真,不雕饰,不迎合;他的厚就是一种深厚的修养积淀。概括来说他的人格有一种大气不小气、厚重而不轻浮、无畏而不患得患失的感觉。这种感觉形成他绘画的这种太行之境,实际上是人格之境。把司空见惯的太行山画得不寻常就是奇;不求功利地把自己的人格融入其中,把那种生命的体验融入其中,还有把自己生命中的那种坎坷经历融入其中,就是一种险和苍;再有就是他把对民族命运的认识和理解也融入其中就是一种厚。从吕老师的画里面我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作品如果能够真正感染人,应该是技法+人格+志向+品位。技法不用说了,人格就是他的那种真诚,那种非功利的率真,深厚修养的积淀,体现出一种奇、险、苍、厚的审美境界,虽然梵高画油画,但是梵高的画也有这种境界。吕老师的志向就是从1962年毕业之后,仅仅20岁立志一生要画太行开始的,时至今日显然积淀是非常厚的。吕老师有一句自勉格言:“脚要站得高高的,眼睛要放得远远的,脑子容量宽宽的,手底做得实实的。”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思想容量大,画风实,就是他的品格的定位,他对自己品格定位很高也形成他的不同寻常的品位。
韩昌力(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第一,我觉得吕云所先生的绘画是不是画的太行山真无所谓,我也不认为吕云所就是画太行山的代表,如果大江把吕云所先生的定位放在这里真是小看了吕云所先生了,看小了视野就短了。
第二,从当代艺术现代艺术的观点来看,艺术的现象无所谓,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很重要。这里非常感谢吕云所的家属,而且刚才我听说王伟毅馆长的策划很重要,作为搞理论的理论家,吕云所先生的展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个案,从学习、创作的过程一直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个案。这个个案我们很少见,我这个年龄段的可能还经历了一点,尤其杨德树先生、王振德先生他们经历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和“文革”时期一直到今天,这个艺术的过程是跟我们现在在座的学生学习的历程不一样的,这个个案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尤其搞水墨的,这个艺术家怎么成长起来的,他的痛苦等等我们是否关注到了?
第三,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曾经有其他画家展览的时候我就说,吕云所是天津美院的,美院应该珍惜这一批画家。天津美院和其他美院发展过程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并不在于体制,很重要的在于有不同的艺术家。
姬俊尧(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因为和吕云所教授是上下届的同学,后来在“文革”期间到80年代我们两家住在一个楼上,那个时候教课任务并不繁重,所以经常在一起聊天,尤其晚上。这个时候在八几年,正是黑色太行的创作时期,那时天津美术学院经历地震以后好多教室都不用了,他当时也不教山水,我记得他那一段是在工业设计教素描。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当时美院的画室,就在南院一个棚子里面,临时在那儿作为画室,所以,这一批的黑色系列都是在那个时期画的。因为当时我经常去,还有我们这里的一个叫李津,我们三个经常去那聊天看他画这批黑色太行。当时他跟我说他为什么搞太行,因为他是太行人,所以用积墨的方法来画出太行,到现在随着时代的推进,我觉得他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确实在天津美术界是独到的,而且将来会有更大的影响的。
郝青松(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讲师):对吕先生的作品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作为北派山水的代表,这个问题其实就回到了对南北宗的反思,南北宗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时间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画的问题以及南北宗的历史问题,历史已经显示出空间关系来拯救时间问题的,空间关系包括了东西南北上下。我这样理解的。首先事实上来自西方冲击的中国画的现代危机是个伪问题,西方和现代我觉得都是为了拯救南北宗的文化内向危机,要这样来理解它。吕先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认真研究过现代艺术的山水画家。
第二个,今天要重新认识北派的当代意义。什么是燕赵精神?吕先生的作品里面是可以看到的。像范宽《溪山行旅图》里面人在那种山道中的感觉,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代性来说并非是天人合一的,而是天人之间的张力,又要逃离大山,又离不开大山,我和吕先生的老家距离有十华里(5公里),非常近的,所以有相同的感受,在太行里面特别想逃离,出来之后又特别怀念。

吕云所 元气 69×138cm
所以,看吕先生的作品,好像都是局部的,扑面而来全部都是大山,人就在那个里面,人对这个大山的抗争和束缚,整个画面都是大山,满满的,好像是个局部,但是却有像宇宙一般的宏大感,这是南北关系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吕先生的作品里面很明显有两大符号,一个是山一个是云,其他的都不多见,人都是很少的,甚至没有的,就是山和云。山是根基,云是超越,越到后期从山到云欲加超越,丘壑被笔墨解构,北方原本凝重的太行山居然在他的笔下如此灵动,这是上下空间关系。
我说他的作品就是以东西、南北、上下这样一个三重的空间关系来反思了一个和时间有关的历史的山水问题。谢谢!
尚辉:好!今天上午的研讨会都已经开到下午了,大家还意犹未尽。研讨会的重要原因是吕云所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富的素材可以进行探讨,我觉得这次研讨会和北京的研讨会并不完全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对吕云所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成就特别地感奋,有很多的话要说,所以很多专家对吕云所先生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更多的评论和描述。
第二个就是这个展览是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天津美院和吕云所的这种关系让我们欲言又止,有很多话似乎想说但是又没有说开,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吕云所和天津美术教育,也就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贡献,他作为一个人物画家的贡献和山水画家的贡献。
第三个就是我们从他所在的位置谈到了津派,津派的绘画和吕云所之间的关系。
第四个当然就是刚才大家探讨的北派,太行山水作为北派山水的摇篮,那么今天吕云所所创作的太行山水毫无疑问是北派山水的当代性的表现,这种当代性的表现并不仅仅是画具体的山,而是如何表现这个时代的气象和他个人的感怀、阅历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话仅仅是展开,因为时间关系的确没有让大家再面对面地探讨,好在我觉得好的学术研讨会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也期待我们很多的学者会通过这样一个研讨会能够写出更精彩的文章,写出更多有关吕云所先生的研究性的文章。
吕大江(吕云所先生之子):大家上午把学术问题谈了,感谢尚辉总编,感谢诸位专家、老师、同学们、朋友们,谢谢大家!
(以上文字未经研讨会发言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