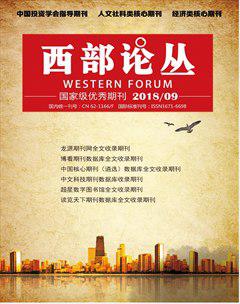对历史真相和个体存在的追问
谢莎
摘 要:余华的首部中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以一个少年的成长史为主线,写下了文革时代一群畸零人的命运。在这部有着极端个人视角的心理化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绝望的呼喊和反抗声。作家将先锋叙事与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紧相融合,以先锋的形式将我们引领到历史的通道口,启示我们自行发掘历史深处的真相以及真相背后个体存在之痛。
关键词:先锋;历史;呼喊;个体存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刚过而立之年的余华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呼喊与细雨》时,曾蔚为大观的先锋派早已消然分化。彼时的文坛,新写实潮流正大行其道。对于这部出版时易名为《在细雨中呼喊》的小说,也自然而然地被评论者视为作家的转型之作,认为余华自此从先锋写作走向世俗写真。这部小说以一个少年的成长史为主线,写下了文革时代一群畸零人的命运。通过少年家史的演绎对历史现场做了想像中的还原。在这部有着极端个人视角的心理化小说中,余华再次以先锋的形式考量历史真相背后个体存在之痛。
一
无庸置疑,在当代作家中余华是极其讲求写作技巧的一位,他自觉汲取过众多文学大师的艺术养分,其创作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同样,我们看到,《在细雨中呼喊》走得也不是中国传统小数的路数。先锋意味着自由,对余华来说,井然有序的写作从来就不是他所追求的。而与此前作品的确不同的是,这一次,余华贴近历史,将先锋叙事与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相融合,使我们既始终对小说保持着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又被貌似碎裂的文本所传达的现实能量所震惊。
小说的开篇非同凡响,1965年的“我”在飘着细雨的黑夜中被“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惊醒,这个女人持续的呼喊,长久的无人应答让“我”恐惧而惊慌。“我”真切地感受到,“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此后,一个陌生男人如旗帜般在风中作响的衣服声被“我”当作了对这“呼喊”的回应。而第二天,这个男人死于非命……在这短短几百字里,作家不仅提炼出了“细雨”“呼喊”“死亡”三个笼罩全篇的中心意象,还交替出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我”三种不同的叙述声音。有评论者指出,“细雨”与“呼喊”两个意象诠释了人在细雨般绵密、压抑的生命状态中苦苦挣扎、呼喊的生存图景。“细雨”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本真存在,它包含着生存的苦难和苦难的生存,“细雨中的呼喊”充满了试图逃脱苦难与不幸的努力,然而“旷野的呼告”并没有等来拯救者,这“呼喊”要么无人应答,要么引向死亡。“死亡”的终极指归,象征着存在的虚无[1]。这似乎也映证了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论断:“孤独、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宿命[2](P3)。”而类似“我看到了自己”这样的表述,让作家巧妙地在童稚的眼眸与成人的视角之间自由转换,从而使得“全部的叙述里,始终贯穿着‘今天的立场,也就是重新排列记忆的统治者①。”也因此,第一人称的“我”成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从容地带我们走向那些在细雨里呼喊的人们。于是,我们听到历史深处传来无数呼喊声,有女人哭泣般地呼喊,有男人狂暴的喊叫,还有一群孩子细小的哭喊声……
女人的呼喊总在试图穿透黑夜。小说中重点塑造的三个女性形象“我”母亲、冯玉青和“我”养母都是软弱无助的,唯其绝望后的喊叫犹如划过黑夜的闪电,凄厉而鲜亮。“我”母亲始终慑于父亲的淫威,哪怕在父亲和斜对门的寡妇搞上后,父亲“每晚先钻进寡妇的床,然后再钻到母亲的床上”,她也敢怒不敢言。她唯一爆发的愤怒是在弥留之际的那个晚上,“这个一生沉默寡语的女人开始大喊大叫,声音惊人响亮”,所有的喊叫声都指向父亲,对自己一生的苦难作了清算;冯玉青曾是“我”眼中青春美的化身,然而先后被两个男人抛弃的遭遇让她的美丽残酷凋零,命运对她的歧视,逼迫她开始了皮肉生涯。当被警察抓捕之后,“这个话语不多的女人,面对审讯她的人,开始了平静的滔滔不绝,‘你们身上的衣服,你们的钱都是国家发的,你们只要管好国家的事就行了,我身上的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国家发的,我陪谁睡觉是我的事,我的东西自己会管的,不用你们操心。”麻木而苦涩的自我辩白令人无比心酸。比起“我”生母和冯玉青,养母李秀英一直生活的生活之外,她疾病缠身,孤独地活在自怜自慰的幻想中。而她“有着过于强壮的男人和过于虚弱的女人”的家庭终因男人的婚外情而毁灭。丈夫死后,她凄然地發出了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片在空中呼啸而去。”她最后的出走也可以看作是对命运的耻辱和生存重压最大程度的反抗。
如果说女人的呼喊大多来自男人的背叛和抛弃,那么男人的喊叫呢?如何理解祖父对着天空的吼叫,如何理解父亲响亮的哭喊以及养父王立强的声泪俱下?更何况,等待这些男人的最终命运都是死亡。想解决这些疑问必须跟随叙述者返回历史现场,向那个特定时代要答案。这部充满了呼喊声的小说也无处不渗透着政治历史的元素。祖父作为一名出色的石匠,曾“满怀着造桥的雄心大志”,然而他经历最多的却是饥饿和贫困。祖父临终时对着飞扬着雨水的天空喊出了他的愤怒,那诅咒般的吼叫足以震动一个荒凉的时代。那个时代贫瘠不堪,容不下怜悯,却又异常地令人想入非非。小说中,弟弟孙光明救人淹死了,“我”的父兄在悲伤还未停息之际便慷慨激昂地将儿子塑造成了英雄,试图以儿子的死换取一官半职。而空洞的幻想悉数破灭后,父亲孙广才迅速堕落,他粗鄙、淫乱、偷盗、酗酒,成了彻头彻尾的无赖。直到母亲的死让他惊觉到“罪”与“死”的恐惧:“这天半夜村里人都听到了来自村外毛骨悚然的哭声。我哥哥听出了那是父亲在母亲坟前的痛哭。”最终,他在醉酒的夜里跌入粪坑龌龊地死去。与生父相比,养父王立强的命运显得悲凉而悲壮。这个高大、强壮,明朗、健康的男人,给过“我”短暂的父爱。与妻子长久的病态生活让他的身心备受压抑,他提心掉胆地经营着婚外情,可还是被那个时代道德的踏实卫士现场捉奸,最终走向毁灭。
就这样,在“我”这个无限自由的叙述者的导引下,作家向我们讲述和显示了一幕幕幽暗的人生片断,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以孙光林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带我们走向了一个与成人相呼应又相对立的少年世界。
二
在《活着》自序中,余华说,他曾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童话作家。在他营造的或冷漠或温情的文本里,总会跳出一些让人无法漠视的孩子形象:《现实一种》中的皮皮、《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活着》中的有庆、《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一乐……这些少年形象构成了余华小说中一道鲜明的风景,也正是这些虛构的孩子,每每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初看时,他们仿佛置身一个热闹非凡的孩童世界,然而,他们相继发现了自己的不幸。
譬如,六岁的“我”因为贫困被生父抛弃,寄人篱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得以重返家庭,却无“家”可归。因为“我”与祖父一样,成为日益困窘的家庭累赘。“我”能得到的只有家庭成员的冷漠、疏远甚至殴打,尽管“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亲情的依恋和对家庭温暖的渴望。然而,被渴望的一直存在于渴望之中,“我”再次被抛弃了,“我”同样生活在细雨飘扬的黑夜,在无人应和的呼喊中忧郁地成长着。
与“我”一样,上文提到的孩子无不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先后经历被抛弃乃至死亡的命运。父亲身份的缺席、母亲形象的孱弱让他们如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里的“我”发现的那样——“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之后,这些原本骄傲、天真、纯洁的少年渐渐变得阴郁、虚弱、粗野和放荡不羁。青春期蓬勃的欲望让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中。这群无处藏身的少年,以恐惧的方式体验着欢乐,随时有跌进罪恶深渊的可能。比如哥哥孙光平,他曾是父亲的骄傲,也曾经对父亲无比崇拜,然而在发现生存的丑陋后,哥哥沉闷忧郁、自暴自弃,竟像父亲一样爬上了风流寡妇肮脏的床。知识、暴力、性,究竟什么才能改变命运?高中毕业的哥哥无从知晓,却在田间劳作的老农身上“触景生情地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最后那部分”。那个时代没有为哥哥提供更好的出路,他的梦想到达不了彼岸。所以在“我”有幸赶上高考恢复的时候,他才会悄悄代“我”交报考费;在“我”上大学期间寄来一封封空白的信。哥哥的举动仿佛是无声的呼喊,让“我”听到了他痛苦而空洞的心声。
小说中,苏家兄弟与“我”和哥哥是一对平行线索。苏宇与哥哥一样,因为家庭的阴影心灵饱受重压,即便少年无间的情谊也没法儿驱除他内心的惊慌和压抑,为寻求解脱,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对他作为个体存在的疏忽导致了“苏宇之死”,回光返照的时刻,“他向弟弟发出内心的呼喊”,而“回答他的是门的关上”。
这些孩子对应了开篇出现的喻像“白色羔羊”:脆弱而无人守护,呼喊却无人应和。理应作为“牧羊者”的父母以迷失或隐匿等不在场的方式推卸了职责,那么师长呢?他们是否代之做了孩子们精神上的牧羊者?答案是令人遗憾的,牧羊者或无力自保或成了施暴者,精神上的,身体上的,让这些孩子过早的像成人一样成为畸零人。
然而,面对这些无助的孩子,余华的心定然是异样温和的,否则他不会以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频繁书写孩子之间的情谊。克尔凯郭尔说过,“在看见一个人绝对孤独地处在世上时,会使人最痛苦地被感动” [3](P7)。小说中,“我”与苏宇的友情让人感受到一种明亮的温暖。两个少年互相分担家庭的秘密、身体的秘密,试图减少对罪恶的恐惧,他们在月光下忧伤而生动的微笑,无法不让人为之动容。之后“我”与鲁鲁的友谊仿佛是“我”对苏宇生命的延续,“我像苏宇当初对待我一样,对待着鲁鲁”。因为“这个孩子脸上洋溢出来和所有人对抗的神色,以及他总是孤立无援,让我触景生情地想到了自己。”鲁鲁,这个被遗弃的孩子,骄傲、坚韧、对待友情专一而霸道,他对“我”的重视和疼惜,足让小说中所有的成人汗颜。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作品的魅力来自细部描刻的劲道和想象力唤起的真实感。在余华看来,“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②《细雨》正是从这样“记忆”开始书写,让我们在看到场景的同时谛听到了命运的判决,也明白了何谓“漫长”和“波澜壮阔”。这个智慧的作家,带着狡黠的笑容,以先锋的形式将我们引到历史的通道口,启示我们自行发掘历史深处的真相。在无数微小的细节里我们明白无误地感受到那真相充满反讽意味,比如父兄“英雄家属”的梦想,比如曹丽的交待材料(这一笔无法不让人联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比如林老师的螳螂捕蝉、张老师的黄雀在后……所有这些人身上显露的历史都绝然不同于历史学家笔下所写,因为后者的历史只负责记录强者和时代的轨迹。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史学家关注的只是公众记忆中的重大事件,小说家则关注个人记忆中的生活断片;史学家关注庙堂关注阶级,小说家关注民间关注人性;当小说贴近历史,重要的是要真切地传达历史感,而不是换一种修辞言说历史。还是米兰·昆德拉说得好:“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一小说才能说出东西。”
是的,小说的意义来自对人的存在的发现和询问。《细雨》,一个优秀小说文本,记录了那个非常年代中世俗平民作为个体存在的悲剧命运,空间化的历史中氤氲着恐惧和颤栗的生命体验。在历史的边缘、生存的边缘、欲望的边缘处,“人”们被凌辱、被压抑、被抛弃,却不曾停止渴望,他们呼喊,哪怕走不出黑夜与死亡。作为一个个孤独存在的个体,明知冲决不了历史的罗网,依然固执地彰显出冲决罗网的勇气,难道我们还能向他们要求更多吗?作为一个坚持为内心写作的作家,余华冷静地传达了对命运的终极追问,以及与绝望和虚无相对抗的姿态,难道我们还能向他要求更多吗?
足矣。
注释:
① 参见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意大利文版自序,第3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
② 参见余华:《活着》,英文版自序,第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 吴宁宁.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生命意象[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1).
[2][3] (丹麦)克尔凯郭尔.颤栗与不安:克尔凯郭尔个体偶在集[M].阎嘉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