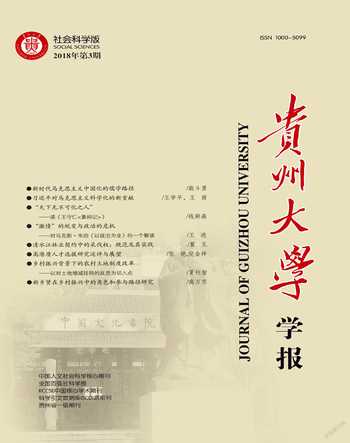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研究
张明 安尊华
摘 要: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中,田地买卖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前期(元年至十五年)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研究,表明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波动的总趋势是缓慢增高的,而田地价格增高是由于自然、社会、政治、灾害、地权等因素的影响,从中可见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土地市场具体历史实景之一斑。
关键词:民国前期;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059-07
Abstract:Land trade is one of important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society. Through study on land price of Qingshuijiang area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6), it is shown that the land price increased slowly,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as nature, society, politics, disasters, land rights and so on, and thus we can get a realistic view of historical land market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Qingshuijiang area.
Key words:early Republic of China;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Qingshuijiang area; land price
在中國传统农村社会中,田地买卖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由此形成的各个时期田地价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民国建立后,仍然延续了部分土地私有制。各地地价,千差万别,无一准绳。民国初年,中央政府财政部曾制定国税、地方税法案,拟由县级地方政府制定本县的财政预算和决算。实际上,县级财政薄弱,无力完成。当时军阀割据,他们凭借实力,肆意征税。税额增加,农民负担加重,不得不将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田地出卖,以换取必要的周转资金。民国十六年酝酿政收支系统,到十七年正式确立中央 、省和县三级财政体系,规定田赋、契税和营业税、房捐、船捐等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民国年间,贵州田地买卖仍活跃。因此,本文以民国元年至十五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清水江流域的平均田地价格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以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县高酿、瓮洞、柳寨等地和锦屏县的土地契约文书中的卖田契约为研究对象,从中选择能反映面积、成交价全面信息的文书加以讨论、分析,寻求田地价格波动的总趋势,分析影响田地价格的诸多因素,进而揭示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土地市场的具体历史实景。
一、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的抽样情况
课题组成员在天柱县柳寨(侗族)的文书中找到民国元年至十五年具有典型意义的田地买卖契约共43份,其中记载面积和卖价的32件,另外11件只列出卖田数量,不标亩数,比如用收禾多少或其他运、边等计量单位,无法计算单价,作为田地一宗或数宗卖出后,标有卖价,但难于折算,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这个问题是整个清水江流域,抑或贵州省境内存在的共同问题,对于土地买卖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折算困难。虽然有数以万计的文书,但剔除看不清、标注不明、书写不完整、破损、卖价处或面积处的文字不清楚,甚至缺损等,加上文书储存了六十至五百年不等,各种因素制约了田地面积计算,以致田地价格的统计,只能得出一个近似值,或者说,是一种趋向值。为简便起见,现将与田地价格有关的文书样本列表1如下:
通过对上表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得出以下两点:
第一,第一阶段(民国元年至五年)田地价格的平均价约为561文/边;第二阶段(民国六至十年)田地价格高,平均田地价格约为1 676文/边(不排除文书释文有误,导致数字不准确,以致出现田地价格的单价过高的情况)。第三阶段(民国十一至十五年)田地价格的平均价约为1 010文/边,对于前两阶段而言,有所上升。平均价为每亩1 298文/边。
第二,民国元年至五年的田地价格与后文所列的田地价格基本吻合,民国六至十年的田地价格,显得略高:平均价格约为每亩七点二两,最高接近每边三千文,每亩一万八千文,合每亩银十三两。民国十一至十五年,平均田地价格逼近每边两千文,每亩近一万二千文,合每亩银六两。其中最高卖价达到每边四千五百八十文,每边的价格达到银二点三两,合亩价八十余两。这种高价,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独立的一丘水田,地理位置好,属于村民所说的滥田或秧田,十分便于耕种和管理,收成有保障,二是买卖双方没有任何亲戚或近邻关系。文书中说,卖主龙照全“先问亲房,无钱承买,自己请中问到坪坝村龙荣炳名下承买”。两个村的人,虽同为龙姓,但已非至亲,田的价格倚高亦属于正常。
这里需要说明清水江流域田地面积的计量单位和银钱比价。清水江地区丈量土地主要以石、挑、箩、运、斗作为计量单位。[1]696乾隆初年天柱县三里的均摊案之后,推行了摊丁入亩制度,把“边”定为税亩的面积单位。当时制定了1至50边的固定税率。习惯上,边作为计算清水江土亩的单位。柳寨在民国年间的银钱比价有两种情形,民国九年以前主要是清代的制钱和“当十铜元”, 十年以后因外省铜元流入,铜币价值降低。[2]民国十年以后,本文统一按银钱比价1∶2000换算。
民国时期典卖田地银与钱的折算办法,主要根据文书所载的信息进行整理而得。如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蒋永德断卖契云:“杨宗佑得买蒋永德土名亚梭田壹坵,收禾四稨,产价钱三千壹百捌十文,合银贰两叁钱。”(文书编号:GT-SBD-023/GT-002-063);民国二年十一月八日龙成断卖契记载:“龙道珠得买龙成土名冲坊田一坵,产价钱五千文,合银叁两陆钱。”(文书编号:GT-SBD-024/GT-002-073)。此两份分别为钱1382文折算为银1两、钱1388文折合银1两。为了便于统一折算和比较,结合其他文书,民国一至十年,统一用钱1 400文折合为银1两计算;民国十一至十六年元月一日,按银1两合钱2 000文折算;
民国一至九年,按1两折合1400文计算;十至十五年,按1两折合2000文计算。具体列表2如下,田地价格单位,统一折算成文/边。
清水江流域民间常使用的计量单位有把、边、卡、箩、运、石(担)、擔、斗、升、碗、挑、称等,常用边(稨/遍)、石、挑、运表示田的面积。面积折算办法: 1石=10.14边。1石=10斗。1挑=6边。1运=6边。2015年9月27日咨询天柱县瓮洞镇村支书蒋启金,他证实说,一运就是一挑。
由上表可知:
第一阶段(民国元年至五年)田地价格的平均价约为678文/边;第二阶段(民国六至十年)田地价格上升,达到1 026文/边;第三阶段(民国十一至十七年)的田地价格约为1 099文/边,相对于第二阶段而言,上升幅度很小。十七年的均价为960文/边。
这里基于贵州大学所收藏的清水江流域文书复印件中部分民国时期卖田契而作的抽样,其中有典卖田地,一并纳入田地买卖。87宗田地买卖中,最高一宗卖价为民国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杨昌锦卖田契(GT-WKZ-021/ GT-009-065)三百封8 880文,含山一幅、园二团,这是卖价高的原因之一。最低一宗为民国五年六月初九日吴光才、吴光林兄弟卖田字(GT-PPC-010/GT-019-022)1.8千文。中位数为34.8千文,平均每宗约50千文(50051.2文),折合银每宗田买卖在25至35两之间。一次买卖达10千文上的计71宗。超过100千文的有11宗。这些田地买卖中,另有三宗各含柴山一幅、墦地2团和园一团,这几宗的卖价皆在20千文以上。田和柴山、园、土(含阴地)合卖可以说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的一个特征。
单就田而言,面积最大的一宗为30运,卖价达钱120 810文足(折银60两);超过10运的有18宗,每运2千文以上,这些买卖每宗折银20两以上。这说明,清水江流域在民國元至十年期间,村民的经济水平并不很低。田的面积愈大,其单位卖价并不高,或者说,反而偏低。面积小的田,单价往往较高,比如民国七年五月二十日龙清汉卖田契,收花4边,钱7 500文,单价达到1 875文/边(GT-GDL-051/GT-041-057);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龙令勤卖田契(GT-GSH-034/GT-024-116),收禾10边,卖价钱80880文,单价高达8018文/边;民国十一年三月二日蒋昌全立卖田字,收谷16运的田卖价钱32800文,单价合168文/边。单价最低的是民国七年四月二十日蒋昌俅卖田山场契(GT-WHX-030/GT-008-046),收谷6运,田卖价钱7 008文,折合每边96文。田的单价高低之差达到80倍以上。不可以说田地价格与其面积成某种比例关系,影响田地价格的因素较多且复杂,田地买卖从侧面提示了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二、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变化趋势
清水江文书中所列的每宗田所卖价格有时落差较大,这与清水江流域处于河谷地带,水田与旱田区别较大有关。比如民国时期贵州境内紫云县的田地价格,“抗战以前每市亩水田好坏平均价值六十至一百元”,“旱田较低十分之二、三”。开阳县的田地价格,“积习相沿,从不论及土地面积之大小,水田大都以谷挑数目,为给价标准,而谷挑数目,常较产收益数为少”,“田之优劣,不仅以土壤之肥瘠为断,同时兼与水源之枯旺,所在之地势与气候而定其等级。上田每挑约十二元至十五元,中田八元至十元,下田四元至六元。此不通常原则而已,有时地价,每因当地经济之荣枯,人事之情形,亦受影响而已。”[3]170-171同样,清水江流域田所处的地位置、气候、水源条件、土壤的肥瘠差别、土质的优劣、当地村民的经济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多寡、交通发达与否等因素、综合地影响着田的价格。大体上说,水田地价格格高于旱田,山坡的田又低于旱田;同一各类的田中,面积很小、不成片的田地价格格则低于较成片、面积稍大(一般大于一亩)的田地。
根据民国年间天柱县攸洞、甘洞、地良水田每边的价格,从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分别为574、830、1 450、1 023、1 889;1 310、1 874、1 752、2 311、613;1 036、894、1 535、1 164、2 295;[4]180分别按民国元至五年、六至十年、十一至十五年计算三个平均数为:1 153文/边、1 572文/边、1 385文/边,平均为1 370文/边。在这十五年的田地价格中,前五年超过每边一千文,之后上升到每边一千五百文,再下跌到一千三百多文。由于采取按年排列、典型年、个人买进田地价格三个数据综合平均而得,因而田地价格比实际的田地价格高。这与本文选取的地点,计算方法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民国元至五年,天柱县的田地价格平均为678文/边;六至十年田地价格平均值为1 026文/边;十一至十五年田地价格平均值为1 052文/边,均价为955文/边。相对而言,天柱县在民国六至十五年这十年中,不同地方的田地价格比较接近,大致在每边1 000~1 400文之间。
表1和表2所列文书共119份,其中使用银两作为交易介质有15份,占12.6% 使用光洋(大洋)作为交易介质2份,占1.7%,使用钱(包括制钱、铜元钱)102份,占85.7%;根据表1、表2得所依据的文书信息,得出民国元至十五年的田地价格年平均数,制成表3:
翻检《清水江文书》第1辑[5]全部文书,得到民国前期土地买卖共计138份,其中民国元至十五年的共计72份,除去无面积记载、用田抵借钱、字迹不清等外,有面积记载的共49份。这些文书的面积记载,一般写作约谷多少担,有时担写作“石”“旦”,皆相通;另有几份用约谷多少斤和把表示面积。通过折算,得出民国元至五年的平均田地价格374文/边,六至十年平均田地价格为603文/边,十一至十五年平均田地价格为675文/边。这十五年的田地价格有所上升,但相对平稳。同样,制成这十五年的历年平均田地价格如下表:又根据《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6]所载102份民国时期的卖田契,其中民国元至十五年有30份,3份无面积,27份有面积和卖价记载;以及《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7]所载民国时期135份民国时期的卖田契,其中民国元至十五年有15份,1份无面积,14份有面积和卖价记载,共计41份,求得民国元至五年的平均田地价格为138文/边,六至十年为184文/边,十一至十五年285文/边。这个值偏低,可能与该地域的经济环境有关系。综合制成下表4:
此表基本反映了民国元至十五年清水江流域的田地价格变化情况。由此,根据表3、4、5制成历年平均田地价格变化图:
民国元至五年,河北省的土地价格大概为18 327文/亩;六至十年为60 164文/亩,十至十五年为47 133文/亩,平均为32 343文/亩。清水江流域同期田地价格对应分别为17 453文/亩、28 022文/亩、30 823文/亩,平均为25 416文/亩。平均每亩田的价格比河北省约低39%。以民国二十年(1931)的田地价格为指数100,则全国与清水江田地价格比比较如表6:[3]169
1912年全国的田地价格值指数为74,同年贵州的田地价格指数为64,低于全国10个指数,清水江流域的田地价格指数为41,低于全国33个指数。
三、影响田地价格因素探析
一般而言,影响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的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因素是影响田地价格的基本因素。自然条件指土地周围的光、温、水等环境条件,不能转化利用的和暂时不能利用的各种自然环境。作为田地,涉及地形、所处位置、种类(水田或旱田)、水源、土壤肥瘠、纬度、降雨、温度等自然因素。清水江流域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土地资源,在受到自然条件制约下能为村民提供一定数量可开垦和利用的耕地,这个数额的变化,影响着该流域田地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清水江流域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黄壤、红色石炭土、黄色石炭土、紫色土以及水稻土。作为田地,其中最重要的是水稻土,它是受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在淹水条件下长期种植水稻,经过水耕熟化而形成的主要耕作土壤。天柱县的田地该土壤占六成余。该县和台江、剑河、锦屏、镇远、岑巩等清水江流域,土壤相似,纬度较低,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山地复杂,高低悬殊,降雨丰沛,年均气温在15~16摄氏度左右。处于高处的田与坝上的田产量差别较大,引起田地价格差别。因此,自然因素是影响清水江田地价格的基本因素。
第二,社会因素是影响田地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社会因素具体包田地开发和耕作、人口数量、经济基础等方面。清水江流域经由明代和清代近五百年的开发,到民国初年,土地的开垦和耕作已经发展得烂熟。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在天柱设立“天柱守御千户所”推行屯田。当时有军屯和民屯两种方式。民屯指民耕,“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九便。”[8]77清代地方官建议撤卫置县,“若夫改卫为县,军则久已为民,裁屯弁而归有司”,[8]38屯田逐渐推广。清初在清水江流域实行改土归流,把苗疆古州、都江、清江、台拱、八寨、丹江纳入版籍,设置同知、通判等进行管理。这些地方官发现田地偏少,屯军又不熟悉耕种,于是鼓动农民开辟土地,“嗣后苗人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钱粮永行免征”,
贵州通志:艺文志:贵州府县志辑:第5册.116.
“黔中山多田少,数年以来劝民开垦,除山头地角遵旨听民自垦”[9]。这些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耕作和屯田。地方政府一方面农民开垦土地的数量在增长,另一方面土地买卖持续发展,为此该流域在清代的土地价格上升的幅度不大。
第三,田地价格的高低与该流域田地的等则也有关系。清代张广泗主张屯田,他所作的《议复苗疆善后事宜疏》指出,在设置行政体制的基础上,朝廷议论,开辟苗人绝产,安插汉民倾种,认为新附苗疆,“查新疆苗众震慑,军威就抚方始,若遂招民人分种管业,未免复起惊疑,转于新疆无益,不若暂给驻守之兵丁并兵丁之子弟就近耕种,既可便于稽察,亦可少佐兵粮等,安插汉民实属浅陋之见”,“与其招集汉民不若添设屯军”,“令屯田以资军实也”,“查苗所种水田,上田每亩可出稻谷五石,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合计屯军每户给田上田六亩,或中田八亩或下田十亩,其所收米谷可敷一年之口食。”
同①,见116-117页。
田地有上、中、下三种等则,主要区别在于亩产量不同。在实际买卖中,三种田的价格不同。当然,在文书该流域的赋役黄册注明田的等则,但典卖田契一般不注明所卖之田是何种等则,只注明产量。我们通过产量来测算田的面积。这种面积与实际丈的面积是有区别的。更何况这些田的面积大小千差万别。
第四,民国初年,政治上,贵州处于军阀统治时期,清水江流域仍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是影响田地价格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清水江地区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佃农向地主交租,地租有认租和分花等形式,多为实物地租,用稻谷支付为主。此外,该流域田地买卖主要以银两、铜钱作为交易介质,少量使用银元和其他辅币作为通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拥有的耕地数量逐渐减少,但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远高于自耕农和佃农,人均每人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大约3至4亩不等,比如民国八年时贵州省每户农户占有耕地面积约8亩,人口增加对土地的持续需求,促使田地价格慢慢上升。由于银钱比价的变化、民国七年的废两改元,货币政策的变化亦引起田地价格的变化。地主对于土地的投资热,土地趋向集中带来田地价格上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影响清水江地区田地价格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五,区域性灾害亦影响田地价格。民国九至十年,清水江流域的天柱城中瘟疫流行,城中死亡数百人,波及四乡;次年锦屏亦起瘟疫,城中亦死三百余人。[1]14两次瘟疫,流域的生计受到影响。民国十年的田地价格相对下降,这是原因之一。民国十五年六月,清水江泛滥成灾,远口沿岸田被毁,本月中旬直至九月底无降雨,田禾干枯,收成仅二至三成。这造成天柱县境内灾荒,每碗米价500文。地主在这时购进田地,囤积居奇,待人们需求田地耕种时又高价卖出,由此造成局部田地价格上涨。
第六,地权对田地价格有影响。清水江流域的地权在土地买卖时发生变化。斷卖(绝卖/死卖)田时,地权由卖主永远转移到买主手中;典卖是活卖,到典期时,卖主备得原价,可以赎回。当田地价格偏高时,农民会选择绝卖;若田地价格较低时,农民可能选择活卖,有选择的余地。当然,采取活卖或绝卖形式,关键在于卖主当时对于资金的急需程度。地权转移是流动的,田地价格亦是变化的。另外,地主招佃垦荒,不断把荒地变成熟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田地买卖市场中的田地这一特殊的商品相对得到持续的供给,从而抑制了田地价格的上涨。这说明地权亦对田地价格产生实际影响。民国初年的田地价格上升幅度并不大,只有九年、十二年和十五年超过每边一千文,其余十二年大致保持在每边六百文左右波动。
四、结语
综上所论,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的总趋势是缓慢增高的,这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田地价格变化基本同步。具体从每亩单价上说,该区域的田地价格则低于河北、广东、江浙等地区。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大致揭示了农村土地经济的特征。地主、佃农、自耕农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只要手中有充足的资金,加上自己需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可以在田地市场选择性地购进田地;当需要资金周转时,亦可以将手中的田地抛售,获得必要的周转资金。田地买卖使农民身份发生变化,佃农可以变成中农乃至地主,即所谓“佃农中农化”。[10]田地价格揭示了民国初年该区域的田地市场已经成熟,土地买卖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实态。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天柱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龙泽江.柳寨侗族村落文书调查及初步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1):31.
[3]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档案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等.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一卷[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
[4]林芊.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清水江天柱文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4:180.
[5]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高聪谭,洪沛.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44-145.
[7]高聪,谭洪沛.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8]朱燮元条陈便宜九事.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4.
[10]方行.清代佃农的中农化[J].中国学术,2002(2)
[11]康熙二十九年田雯《黔书》“改隶”.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8.
(责任编辑:杨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