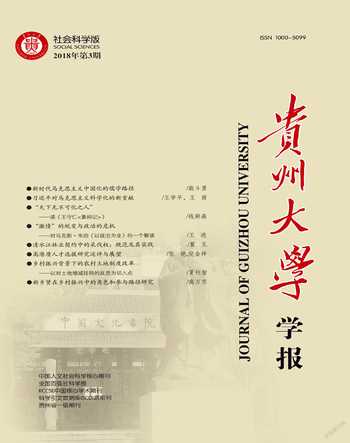清水江林业契约中的采伐权:规范及其实践
瞿见
摘 要:“蓄禁”与“斫伐”是清水江林业契约中常见的语词,也代表着清水江流域木材经营的关键节点,喻示着其背后通过契约呈现的一系列采伐权规范。在揭示二者之间紧张的基础上,清水江语境下采伐权的权利主体与行使规则均得以厘清。进而,在规范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解析中,基于采伐权的视角也提供了一种关于清水江林木经营中“多元股份结构”的新的理解。
关键词:清水江;林业契约;采伐权;规范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049-10
Abstract:Forest conservation and felling are common items in forestry contracts of Qingshui River region, standing for key points of forestry industry in this area, indicating a series of harvesting norms reflected by contracts. Based on the reveal of the tension between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felling, the subject of harvesting rights and rules of exercising these rights can be clarified in Qingshui River context. On this ground, from both a normative and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ulti-class share structure" in forestry industryemerges.
Key words:Qingshui River; forestry contracts; harvesting rights; norms
一、问题的提出:清水江语境中的采伐权
(一)采伐权概念的界定
在“木材之流动”[1]的画卷展开之前,空谷间的“坎坎之声”[2]可能才是清水江畔的主旋律——因其成就了由“木植”而“木材”的转捩,①进而才得以引叙出“商贾络绎于道”的景象。作为“清水江两岸村落社会最为重要的生计活动”,[3]第1册1林木的种植与采伐被凝结于“蓄禁”与“斫伐”这一对在清水江林业契约中往往而是的原生语词之中。以“木植”为“生理” [3]第8册205的意义在于,不仅江中所放的“巨筏”是流动的,山间“亭亭而上”的杉木也是“流动”的:之所以得以“赖蓄杉木以度民生”,[4]77正是因为清江两岸“每年砍伐数千余万株”。[4]51在“蓄、砍”交替的“木植之流动”中,“采伐”的节点即被凸显出来。②
而无论是采伐之实践,或是其背后所引发的规范性思考,都必然收敛于“采伐权”的概念之上。
虽然在学术上得到广泛讨论,
“采伐权”在学术讨论中有时或称为“林木采伐权”“森林资源采伐权”“森林的采伐利用权”等,参见如王群:《林木采伐权的法律问题探讨》,《林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32-136页;李宏:《论森林资源采伐权——兼述国有森工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采伐权的处置》,《陕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77-80页;高桂林、吳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第44-45页。
但以现行法而言,“采伐权”似乎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国家层面关于林木采伐的主要规范中(包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及《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均未明确使用“采伐权”的概念,可查知的仅有在1953年的《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让林工作的指示》中提及了“采伐权”一词。
“凡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山林所有权、采伐权、出卖权、承继权,一律根据过去归属习惯和范围,切实加以保护,并鼓励他们积极造林,增加生产。”见《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让林工作的指示》(1953年7月9日政务院第一百八一五次政务会议通过,1953年9月30日发布)。另外在地方层面,《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自治机关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发展林业。宜林荒山、荒坡、荒滩可以承包给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种植林木,享有自主经营权和采伐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可以合理流转,可以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者条件,长期不变。”然而,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基于采伐许可制度的存在,采伐权无疑具备法律上的意义。一般认为,此意义上的采伐权系指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的、得依照法定方式对林木进行采伐,获取收益(森林产品),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关于“采伐权”在法律及语义层面的定义,可参见胡玉浪:《我国关于林木物权的规定及其完善》,《林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2期,第163页;及王群:《林木采伐权的法律问题探讨》,《林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32页;李宏:《论森林资源采伐权——兼述国有森工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采伐权的处置》,《陕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77页。相较于此,如果不再执着于对权利话语的避而不谈, 本文中的相关权利话语均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而未纠结于其内涵之细部。相关领域研究中的类似态度,参见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在基本不涉及基于公权力的采伐许可的清水江语境下,采伐权的语义解释可能更为重要,即,其意味着权利主体得自行、或出售与他人进行林木采伐,并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
由于基本语境的区别,上述二者之间的关联可能并非显见,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其间隐匿的勾连或许得以展现。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采伐权与林木所有权之间的复杂联系,在讨论中前者的指涉范围或许更偏重于采伐或出卖采伐的具体行为及其决策。
(二)“蓄禁”与“斫伐”的紧张
清水江的采伐权规范建基于“蓄禁”与“斫伐”间的紧张。在杉木的整个栽种过程——开山挖种、长大成林、修理蓄禁,以至最终砍伐下河——之中, 这些“术语”在相应阶段的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中均极为常见。“蓄禁”与“斫伐”之间始终存在某种踟蹰与反复:因其各自具有迥异的价值取向,故而也存在相对宽裕的主观选择空间。
在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中,“蓄禁”与“斫伐”本身就是相互对称的概念,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对后者的否定。“蓄禁”,或可拆解为“蓄养”与“禁伐”两个层面:一方面,强调木植在此期间得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则着重于对此种持续状态的延续与保护。对这一时期的木植,契约中有时直接将其称之为“养木”、[5]第5册24、25、158“禁杉木”[5]第10册127、128或“蓄禁杉木”;[5]第16册120而对于这一状态的顺利结束,则可以被表述为“杉木禁成”。[5]第14册291在另一个角度上,对“蓄禁”的反复强调源于木植生长中所遭受的不断侵扰:大略而言,在正常采伐以外,尚有如“错砍”、[5]第12册73“盗砍”、[5]第18册179“强砍”[5]第10册42诸情形;并且,即使采伐完成,如果对木植采伐有所疑义,仍会发生如“号阻”、[5]第10册58;[6]第6册40“阻木”等现象。[7]122
在“禁伐”之外,更深层次的紧张源自二者目的间的张力。相较于主要着眼于即时经济利益的采伐,蓄禁的目的无疑更为多元。举例而言,清水江最常被提及的蓄禁规约或许是立于文斗寨的碑文:“此本寨护寨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存以壮丽山川。” [8]更为普遍的,此类因素会被归结为“培补风水”,所谓“自古及今,随其蓄禁,培补阴阳枫水。” [5]第10册146此外,在分关合同文书中,亦常见蓄禁共有林木的约定,如“其有山场一概未分,其有不论□人田砍(坎)上杉木蓄禁”的表述。[5]第7册94、187
此外,在“木植生理”的背景下,蓄禁抑或斫伐的抉择更多可能是经济上的考量。通常认为,杉木的育成时期是相对客观、固定的:《黔南识略》载,“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 [2]又,锦屏县有所谓“十八杉”“姑娘林”的风俗,即杉木成材时间为十八年左右。[9]但以清水江文书所得窥见的实际采伐时间来看,似乎远非如此:在既已分析的案例中,林木育成的期间多为30-40年,个别可达近80年,不一而足。
相关研究,可参见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刊,第35-36页;张强:《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研究》,河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8-50页。易言之,在清水江的林业实践中,对采伐时机的选择往往不完全是客观的,其至少存在两点经济上的考量:其一是木植生长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增长,如在一份“分关合同”中即展现了对木植大小的明确认知,指明“各阄油树内杉木准其四股众砍一班,由一尺二寸实木砍起”;[5]第3册6其二,则是采伐时木材的市场价格。以一份“卖杉条木字”为例:
立卖杉条木字人寨地杨天凰,因与胞兄天凤所共杉山一块,地名豪老块,自将本人一股,凭中愿卖与王寨王绘五老局长先生备价承买砍伐。其山价当日早已凭中收足清楚。因此时木业萧滌,故暂行蓄禁数月,姑待行势起色,力(立)即请伕砍伐。日后砍伐时出山,关山剩下之毛木地土仍归山主,他人不得意外相争。立此卖字为据。
卖主 杨天凰 押
凭中 杨天金(印章)、杨天良、杨宏兴、欧邦德
民国三十二年阳历八月十五日[10]G-○○一○
在此文书中具体地展示了市场导向的采伐决策过程:之所以“暂行蓄禁”,其原因即在于木业萧条,须待行情好转方才开始砍伐。这说明,即使是在木材流动的上端,木植的采伐也与市场动态相互联系,又如在“乾隆十二年七月工部对湖南巡抚杨锡绂奏文的复文”中即凸显了“时价”的重要:“务必委员知会地方官,询问苗民情愿,然后照依时价砍伐。” [7]6
当然,蓄禁的时间越长,在其它方面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愈大,文书中林木火毁的记载也并不鲜见。
类似的记载,可参见如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三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三卷),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語言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E-○○七○。因而,“蓄禁”与“斫伐”间天然的紧张关系则更具多个层面上的复杂性,而正是此种复杂性,彰显了采伐决策中有权决策者之确定,亦即采伐权规范的必要。
(三)问题与结构
基于以上对采伐权的语境限定,及“蓄禁”与“斫伐”之紧张的揭示,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在清水江的林业经营中,木植采伐权的权利主体为谁?或具体而言,土、栽之间关于采伐权的契约性规范为何?其次,专以多方拥有采伐权的情况而论,采伐决策的实践究竟如何?在结构上,大致依据采伐权的设立与行使渐次展开,通过规范及其实践两方面的考察,初步厘清清水江林业契约中的采伐权。
对于用以讨论的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依据木植生长、砍伐的顺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佃栽文书;(2)分成合同文书;(3)土、栽股份转让文书;(4)卖木分银文书;同时,在分关文书等其它类别的契约文书中,也间或记载有关于采伐权的材料。此外,就用语上须说明的是,在清水江的林业文书中,尤其是佃栽契字中,各方当事人的称谓并不统一,举例有如山主、地主、土主;栽手、栽主、佃主等名目。
关于佃契中佃主、栽手、栽主等称谓的变化,可参见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70页。本文中以山主(土股)、栽手(栽手股)指称土、栽两方及其股份。
在清水江文书中,合称山林佃契之双方时常作“土栽”。
二、土栽契约中的采伐权约定
在清水江的林业经营中,招租佃栽的模式广泛存在。在“自山自栽”的情况下,采伐权的问题显然无需讨论,山主无疑拥有林木的全部权利。但在佃栽模式下则存在疑问:土、栽之间谁是采伐权的主体,或存在何种关于采伐权的约定?一般认为,清水江的林业佃租关系中,土、栽之间分别以土地和劳力、技术入股,并约定待林木砍伐后按比例分成。[11]但藉由以上分析可知,究竟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或出卖林木采伐,将直接影响到土栽双方的收益。在此背景下,以下着重讨论两种不同的采伐权约定:即对山主采伐权的强调与栽手拥有采伐权的情形。当然,除了土、栽分别拥有采伐权的情况,也存在二者同时享有采伐权的可能,此一类别则放在下一节讨论。
(一)山主采伐权的强调
基于对林地的所有,山主在佃栽关系中所拥有“土股”在大部分情况下无疑均包含有采伐权的内容。但在特定情况下,其对于采伐权的独占,或曰对栽手采伐权的排斥,仍在契约中被强调。如“分合同字”:
立分合同字人本寨龙文明、侄荣太,情因前先领桥弟兄所栽姜凤仪、凤至、凤章、凤元、恩瑞、恩茂叔侄等之山场壹块,地名乌的,在冉俱料洞却,上凭岩洞,下凭溪,左凭岩角,右凭溪,四至分清。又壹块皆乜金粗,界趾上凭岩洞,下凭溪,左凭岩洞,右凭买主,四至分明。此二处之山土栽分为伍股,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因领桥弟兄亡故,今遗与文明、荣太叔侄二人承受,二比今愿分立合同,日后砍伐早迟,由土股不由栽手。恐栽手贰股出卖,先问地主,后问他人。恐口无凭,立此合同存照。
外批:皆乜金粗之土各是凤仪、恩瑞叔侄之私山,凤至弟兄无。
中笔 姜兴周
合同发达存照(半书)
光绪二年六月初三日 立[12]卷三193
一般来说,栽手系基于上述“分合同”而获得相应林木股份。
所谓“土主以字据管业为凭,栽主以合同管业为据。”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但此文书中着意强调的,是“日后砍伐早迟,由土股不由栽手”;在这一条款之下,栽手显然并不拥有采伐权,栽手所拥有的栽手“二股”并不意味着其得以据之在“砍伐早迟”一事上置喙。
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采伐权同时意味着发卖时参与议价的权利。在有的“分银单合同字”中,即描绘了栽手在砍伐议价过程中的缺位:“今有平鳌买客姜宣泗向家山主议买,砍伐下河作贸生理,当凭中易元芳喊价。” [3]第13册186在此幅发卖的林木中,“地主、栽手分为五大股”,其中地主三股,栽手二股。但是显然,山客在中人在场的情况下仅向山主议买喊价,栽手只是在后续分成时方才出现。在另一份“领收字”中,[3]第13册277这一缺位可能更为明显:
立领收字人王杨氏秀交,为因先年蒙文斗地主李正伦所共归禄溪之山,凭中全卖与黄闷寨陈贻茂砍伐,今凭原中,将本名应占栽手文银五两陆钱一概领清,日后不敢误听刁言生端。如有此情,任从地主中人执字禀究。今欲有凭,立此领清字为据。
凭中 尚文清、李先科、姚开儒
代笔 张世化
咸丰二年三月廿三日 立
文书中载叙,土栽所共的之山“凭中”发卖砍伐,随后栽手“本名应占”的份额“凭原中”付清領清。此份似乎是后续撰成的“领收字”可能间接表明,栽手并未参与当时与山客的砍伐议价。另外,在有的“佃种栽杉木”文书中,存有“自成林之后,仍守到砍”的条款。[6]第8册36虽未直接言明,但其中的“守”字似乎同样着重于义务性强调,即栽手须持续管护林木,直至山主决定砍伐。在这一情形之下,栽手仅得以依据自己的股份取得相应的分成,而无法参与山场整体的采伐决策。
(二)栽手拥有采伐权的情形
虽然较为鲜见,但在特定情况下,栽手同样可以拥有较为自主的采伐权。以下面的“合仝约”[13]第3册2及“佃字”[13]第3册4为例:
立合仝约人文堵寨姜金岩、乔香今有祖山一块,坐落地名鸟堵又,今出与平鳌寨姜有隆、之华、德华、德美六人佃栽杉木。自栽之后,任凭佃主修理,日后长大发卖,派作五股均分,地主得二股,佃主得三股,其木长大,任凭佃主留养,地主不得催渎坎(砍)伐,亦不许房族并外人争论异言。如有争论异言者,俱在地主理落承当,不与佃主相干。其木砍伐完,地土还归业主子孙管业。恐后无凭,立此壹样二纸合仝,日后存照。
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立
天理人心 合仝是实(半书)
立佃字人姜有隆、明伟、德美、德华、之灵、之宾等,因客亲文堵下寨姜金岩、乔香、银岩有祖山一块,坐落地名眼加者,其依山四股均分,佃主得买叁股,姜金岩占壹股,不信山林隔远,难以亲栽,有隆众等只得登门求佃。自佃栽插之后,凭从佃主修理,日后长大发卖,派作五股
均分,地主得弍股,佃主得叁股,其木既已栽插,任凭佃主蓄禁,地主不得相催砍伐。其木异日伐完,姜金岩一股之地仍旧还归。今欲有凭,此立佃字二纸为据。
乾隆叁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立
在此二份文书中均有类似的采伐权约定:“其木长大,任凭佃主留养,地主不得催渎坎(砍)伐”;“其木既已栽插,任凭佃主蓄禁,地主不得相催砍伐。”此处如此清晰地强调山主不得“相催砍伐”,一方面意味着栽手拥有完整的采伐权,得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采伐决策;另一方面也似乎暗示在一般情况下,山主是在采伐决策中较为强势的一方,常常扮演催促砍伐的角色。二者之间的利益纠葛并不难理解:基于林地的所有,山主自然希望其上之林木加快更新,但栽手可能更关心其所佃栽的当届林木的价值增长。这也具体呼应了前文所述的蓄禁与斫伐间的紧张,其实亦寓于栽手与山主关于采伐权的角力之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份文书中的栽手似乎均较为强势,“佃字”中的“佃主”甚至买得其所佃种的山场之三股。就分成而言,也是并不多见的栽手三股、山主二股的比例。
关于土栽分成比例的统计研究,参见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貴州省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林業経営の一側面——「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章滙編」平鳌寨文书を事例として》,载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三卷),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135页;洪名勇:《清水江流域林地产权流转制度研究——基于清水江林业契约的分析》,《林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期,第17页;张强:《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研究》,河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2-154页。但在另一份“合同”文书中,[3]第12册246土栽间则是同样的分成比例:
自愿种粟栽杉成林,日后此伐卖作贰股均分,地主占壹股,栽手占壹股,任凭栽手蓄禁,早齐砍伐,地主座地分粗(租)。砍尽之后,地归原主,贰比不得异言。
在此条款中,栽手也取得了完全的采伐权,且表明山主系“坐地分租”,即仅注重于地租分配,而似乎并不积极参与到包括采伐在内的经营决策之中。而在另一份经典比例(山主占三股、栽手占两股)的“佃种栽杉木字”中,土栽间也约定:“日后木植长大,栽手留禁斫伐,照股均分。” [12]第13册59这些均说明,占股多少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土栽间的采伐权分配问题。
在清水江林业契约的采伐权规范中,山主与栽手均有可能基于契约约定而获得采伐权的独占。在一方独占采伐权的情况下,采伐决策的机制即十分明了:拥有采伐权的一方作出采伐决定,而另一方则仅得要求“按股分成”。下面,则进一步讨论多方拥有采伐权的情况。
三、采伐下河:多元股份结构下的采伐决策
清水江的林业经营中,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山林股份常呈现趋于复杂的结构。
关于山林股份的复杂分割,可参见吴述松:《林业结构调整及其内生经济增长——基于1466-1949年清水江林粮兼作文书的证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9-61页。此处所称的“多元股份结构”,除表示股份的分散及权利主体的多元化,更意在指明搭建起这一复杂结构的其实是具备不同性质的股份元素。
关于多元股份(multiple share classes),可参见Nanda, Vikram K. ; Wang, Z. Jay ; Zheng, Lu. “The ABCs of Mutual Fund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ple Share Classes”,(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9, Vol.18(3), pp.329-361. 在此结构之下,关于土、栽之间的采伐决策也更为复杂。
采伐权其实是一种处分权能及收益权能的具体体现,
参见王群:《林木采伐权的法律问题探讨》,《林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32页;李宏:《论森林资源采伐权——兼述国有森工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采伐权的处置》,《陕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78页。“如果权利主体与标的物之间的利益关联被打断”,则“主体的权利必然落空”。[14]换言之,如果林木股份的权利人无法参与到采伐决策之中,则显然无法完全保障其利益的实现。在林木发卖砍伐时的采伐权,就体现在权利人对采伐决策的参与及自主之上。但在诸方均拥有采伐权的情况下,权利之行使必然受到相互限制,采伐决策的作出无疑面临合议的努力及其失败的风险。区别于意定的规范,采伐权的实践更为复杂。据此,以下将分别讨论清水江采伐实践中“二比同卖”与“各管各业”的两种采伐决策模式,并着重分析基于蓄禁之目的两个土栽股份重构的案例,以期展示多元股份结构下采伐决策的不同面向。
(一)二比同卖:林木股份的合议
相较于土、栽各自单一拥有采伐权的情况,在许多契约文书中也专门载注有要求双方在采伐问题上共同决策的条款。如“栽杉合约”:[5]第4册135
立合约栽杉人潘爵熙、潘芳万兄弟,今因有荒墦地土一块,在于土名淘金冲,上蟠路,下伙与潘常山兄弟耕锄栽杉。言定弍股均分,土主爵熙、芳万兄弟一股,栽主常山兄弟一股,不得异言翻悔。杉木荫地五年同修,日后成林发卖,或留禁、或砍伐,二家心愿,其地仍归土主。今人心不古,立此合约弍张,各执一张为据。
合同二张凭据(半书)
凭中 潘子相
潘明达 笔
嘉庆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其中言及“日后成林发卖,或留禁、或砍伐,二家心愿”,表明无论对林木实行采伐,或继续蓄禁,均应由土栽双方共同决定。此类约定在其他佃栽文书亦有,如“佃种栽杉”文书:“当面议定杉木二股均分,日后杉木长大,二彼同卖”;
“二彼同卖”处,原写“二比”,但“比”字似涂去,改为“二彼”。见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第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佃种栽杉”文书:“当面议定杉木五股除二,地主三股,栽主二股,日后杉木长大,客主同卖,不得争长兢短”;[5]第10册42“佃种开山栽杉木合同字”:“及今栽成林之后,此杉木以后共同坎(砍)伐下河,两股均分同卖”;[5]第10册198“佃栽字”:“其山土栽分为弍大股,栽手占壹大股,日后木植登林,二比砍伐出河”。[6]第10册266
同样,在分成合同文书中也有类似的约定,如“合同字”:“杉木栽成以后,四、五均分,栽主五股,地主四股,及至四年之外,栽主地主一同嵩修,若后长大,栽手地主一同发卖,不得异言”;
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第1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页。其中,“栽手地主一同”六字系专门添入的。“合同修栽木杉字”:“以后修处一体,伐砍同卖,不得异言”;[5]第18册170“合同字”:“十根地主四根,栽主六根,从此日以后,同修理、蓄禁、砍伐下河、出山关山”;[5]第20册302“分合同字”:“今先年佃与维森种地栽杉修理,木植长大,五股均分,地主占三股,栽手占贰股。日后木植長大,地主、栽手二下一同砍伐。”[12]卷三310即使在交易契约中,也有此类约定,如“断卖山土约”:“共计十股,实买山主弍股,……其山土自卖之后,候木长大,公同发卖分价,卖主不得异言。”[6]第10册390
相较于仅正面约定“二比同卖”的条款,有的契约则更加谨慎,反复强调禁止私行卖砍,如“合同蓄禁杉木约”:[3]第4册43
立合同蓄禁杉木约人中仰陆光清、光大、加池姜之豪、天保四人,得买党号杉木一块,其界至,上凭顶,下凭忠周、之豪之木为界,左凭冲湾过之豪杉木为界,右上凭路,又下凭岭,四至分明。先年加池姜文玉、之琏、宗周等,付与中仰陆廷交、廷佐二人种地栽杉,土栽约定二大股均分,地主占一股,栽主占壹股。复后栽股转出卖与姜之豪、天保、陆光洁、光大四人为业。二比同心公议蓄禁木植,日后砍伐下河,约定一齐议价,二比不得私行彫山妄卖。恐口无凭,立此合同蓄禁二纸各执一纸存照。
书立合同二纸,姜之琏存,光大存一纸。
凭中 陆光和、姜朝弼
陆光清 书
外批:合同之内,世培私山今外一块,上凭之豪、老苏,下凭忠周、之豪,土栽地主占壹股,栽主占壹股。
又,姜之豪私山一块团,地主占一股,栽主占一股。
又,外批合同之内公私所占之杉木,俱是陆廷交、廷佐二人所栽,二股均分。
道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立
在上述文书中,先说明此时蓄禁木植是“二比同心公议”的结果,进而约定日后砍伐时须“一齐议价”,并强调任意一方不得私自砍伐出卖。这类的禁止性规约在其它文书中也能见到,如“分山合同字”:“同心蓄禁,毋许那(哪)股私卖木植。” [6]第10册354
之所以强调禁止“私卖”,很可能是为了维护连片林木的完整经营。
关于林木的连片经营,可参见刘秋根、张强:《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区杉木连片经营——基于“清水江文书”的考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72-78页。如一份“招佃种山土字”中规定:“日后栽成,木植长大,土栽作为弍大股均分。栽主占壹大股,土主占壹大股。日后土栽木植,同謪发卖,不准以一人私见,邀求早砍,破坯(坏)全山。” [6]第10册325此处不仅要求发卖需要商议,更直言因“私见”而提早砍伐会带来“破坏全山”的结果。同样,在一份关于林姓祖遗山业的条约中,也规定“此山杉木,公众蓄禁,不准自行砍伐,自行私卖,若违众议,自行砍伐私卖者,众人拿伊送官”,“此山蓄禁成林,日后会众砍伐,或行卖人。” [5]第18册179
从上述诸多例证中,不难发现在契约中,各方权利人苦心孤诣地寻求维护山场林木之完整性的努力。而在砍伐发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诸方股份的合议。在相关文书中常见此类描述,如“卖污盖溪山一所,土栽共议价钱四百五十四千八百八十文”,[6]第7册439即在形式上宣告砍伐出卖乃是土栽共同参与决策的结果。类似的尚有如“地名羊培山,砍伐作贸,全山土栽议价”;[3]第12册196“全山共议”,“众山友共议”;[3]第12册200“分清单合同字”:“土栽共议”,[6]第10册304、328、349、360、446、479、482、483等等。
然而,并非所有的场景都如以上表述一般简单。在各方条件并不发达完备的年代,约齐林木的所有权利人可能并不简单。如以下“便函”,[12]卷四509即生动地展示了全体股份合议的曲折:
姜锡禄、盛富、秉魁土主等:
与格翁范姓所共之山乙块,地名包尾,今放我等平头伙砍伐下河。明日有客来买,请山主各位先生到来,双方同议要价多少。特条通知为荷。
外批:若你土主不到,客来,我苦力人就卖。勿怪言之不先也。
古历二月初五日
苦力人:宋枝杰、姜纯魁、姜敦岐、姜敦贤、吴炳文 条
此文书中所述的山场的权利人并不限于同一宗族乃至同一村寨,而由范姓与姜姓所共。依其文义,似乎范姓已经独自做主邀人发卖,仅急邀姜姓前来同议价款。并且时间紧凑,言明如果未能及时赴约,则“客来就卖”。砍伐议价无疑本应“众山友约集”,[6]第10册499再行出卖,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允许如此。又如一份卖木文书所示,“今有本寨客生陆相槐到舍议砍,因各住一方,不得先通,祈望海涵。今以其数块栽之土谱,共估价弍百肆拾八千八百文。” [6]第10册451在“各住一方”的情况下,竟得由某一股份持有者单独“估价”出卖砍伐,只得“祈望海涵”,均展现“全山共议”的话语追求及其实现背后的龃龉。
上述文字之外应当更为鲜活的故事虽不得而知,但其足以说明的是,在无论是佃栽阶段还是分合同阶段,各方所极力维持的“二比同卖”的规则似乎并不容易遵守。尤其对于具备多元股份结构的林木,权利主体既包含土、栽,又可能横跨宗族、村寨,股份的合议受制于诸多条件的约束,规范之下的实践自然也就存在诸多权宜。
(二)各管各业:权利的析分
尽管存在维持山场完整的努力,但在实践中,股份的合议显然并不容易达成,各权利主体之间始终会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一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如前所述,即起初便约定仅有一方得以享有采伐权;而如果在诸方权利人均有采伐权的情况下进入砍伐出卖的阶段,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对各自的权利进行析分,从而达到“各管各业”的状态。
“各管各业”模式中作为前提的一个问题是,林木及其权利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析分?
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林木上权利(如采伐权)是否是具体的,或曰其具体程度为何,因而是否具备确定性。显然,缺乏确定性的权利在析分上自然存在困难。就相对抽象的采伐权(harvesting rights)與具体林木的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于2004年公布的“美国-加拿大软木案”中,争端解决机构认为,虽然采伐权并未指明其所涵盖的特定木植及数目,但是针对某一特定林地的采伐权,因其所指向的可期数量的木植,及其在特定的情况下得以被采伐,均已使其具备确定性。相关报告及案情,参见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Final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Softwood Lumber from Canada, WT/DS257/AB/R (Jan. 19, 2004), para. 66; Chi Carmody. “Softwood Lumber Dispute (2001-200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0, no. 3 (2006): 664-74.简言之,在清水江的实践中,林木股权可以通过林地、木株或码子等几方面进行区分。如在一份“分山场合同”中:“埋岩为界,各管各业,” [5]第7册122即是以林地为界;又如“栽杉木合同字”中:“其杉木见十留三,栽主七根,地主三根”,[5]第12册189这意味着土栽股份并不完全是抽象收益的划分,其所指可能有具体的标的物,
有学者认为,实际中“结构调整的虚拟成分大于实际分割”,因为“只有股权转移而没有土地分割”。但依清水江的林业文书所显示,实际中股份的分割往往会指向具体标的物的分割,两类分割均广泛存在。参见吴述松:《林业结构调整及其内生经济增长——基于1466-1949年清水江林粮兼作文书的证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9-61页。即所谓“或照木株,或照码子”。[5]第18册179再如“卖养木契”:“其养木栽主一股任从买主[刘]期珍名下蓄禁耕管,与山主[吴]炳章贰家同蒿修培耕管蓄禁,出卖其钱或是木,贰家贰股均分,栽主一分,砍木退土。” [5]第5册25此处更为直接地表明双方均分的对象,既可以是出卖后的价款(“出卖其钱”),也可以是木植本身(“或是木”),明确将木植实物作为析分的选项。
在认识到土栽股份的具体程度之后,则不难理解时人对自己股份的析分实践。如在“卖嫩杉木字”中表示,“今将栽主陆股出卖贰佰伍拾根”,[5]第10册147说明栽手股所对应的林木株数是明确的。又如“卖柴山墦土嫩杉字”中的外批注明:“左下小冲所栽之嫩杉木四、陆均分,内除栽主陆股不卖。”[5]第21册170既然可以在杉木中明确区分卖与不卖的股份,“各管各业”便自然成立为林木采伐时的一种选项。再如在“合同字”中,土栽双方提前约定:“杉木四六分成,栽主六,业主四,出售之时,分股砍伐,双方不得异言。”[5]第19册224与前述极力维持“二比同卖”的情形不同,此处双方在分成合同的阶段就直接排除了采伐决策时双方合议的选项。虽然仍是栽手佃栽山主山场的传统合作模式,但双方的约定自始即以“各管各业”的形态出现。
影响采伐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些因素可以从下列材料中窥知一二。如下列“合同议约” [15]7与“分杉木字”,[3]第13册40均系因一方需要木料起造房屋而先行采伐,而另一方则选择继续蓄禁,这在相当程度上调和了“蓄禁”与“斫伐”间的紧张:
立合同议约人姜洪美、富宇、佐周、文科等,今有共木一块,土名丢又山。洪美、富宇二人占木一股,今已砍伐起造。余存佐周、文科二人一股留存蓄禁。日后另除头脚木与佐周、文科外,余九根,放在贰大股岌共均分。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四房地租早已出银一两二钱,补清相贤。文科、起风、香保、严吉凭中。
凭中、代笔文勷
乾隆贰拾八年一月十二日 立
合同各执存照(半书)
立分杉木字人姜熙猷、熙尧弟兄等,因起造房屋,需用木料,今分到培堆盛山,此山之木杉分为伍股,地主占叁股,栽手占弍股。地主之叁股分为弍拾股,姜熙猷、熙尧弟兄占叁股,前已砍完,所存之杉木,俱係姜钟碧、世模、世清叔侄等所占,日后不得异言。候二界再栽成林,地主仍照股数均分。恐口无凭,立分杉木字为据。
凭中 朱大杰
光绪拾年八月二十一日 熙豪□笔立
清水江的采伐权规范因“各管各业”的模式而极具灵活性。就采伐决策而言,既可以通过股份合议达成一致,也允许在无法达致时各自析分,成为单独完整的权益集束。以下的“信函”即展示了此种合议过程的真实情境:[3]第13册89
登熙亲翁钧鉴:
先前谈叙,不觉至今。敝合与台端所共莲花山杨姓田边之木砍伐,至今以致朽□不堪,再□无木。日前议卖与雷桥福,每两码子五元八角,包伊送江过围。晚决已卖定□,尊翁以为同意否?可能出卖之处,不日过来算账分钱,若尊处之股不卖,急速过来将木分清!晚之木以好包伕搬与客人,又不拖延。言不多叙,此请
台安!
姻晚马配崑应九月十九
这一封信函的目的,在于询问针对二人所共之林木,收信人是否同意出卖其名下的股份。问询者不仅详叙了已经议妥的价码和条款,还提供了两种选择:如果同意出卖,则不日“算账分钱”;如果选择不卖,则请速来析分共木。有趣的是,在此文书中,“来将木分清”几个字旁还加有着重的标记以为强调。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在特定情况下,权利人可以相对独立地实现其股份权益,且并不因其为共业之一部,而丧失对自己股份进行独立裁处的能力。
(三)土栽股份的重构:案例二则
在多元股份的结构之下,土栽之间的采伐决策既存在“二比同卖”的情形,也具有在无法达成合意时“各管各业”的选项。进一步,就林木的完整采伐是否得以维持而言,上述两种模式间其实也存在矛盾。而下列第三种模式则间接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调和,即通过双向的股份收购完成林木土栽股份的重构。林木股份结构因之重新回到较为单一的状态,既得以维持林木的完整,又完成了个人权利的自主实现。以下具体分析的,即是最终均指向“蓄禁”,但收购方向不同的两则股份重构案例。
1.山主收购栽手股
在一份“断卖杉木字”中,[15]230土栽二股均分,栽手之一股先由栽手吴姓兄弟处流转至姜述圣处,而后被山主姜映辉购回:
立断卖杉木字人姜述圣,为因生理,得买吴正贵、正明弟兄之木栽手一股,地主姜映辉存地租一股,因地主自要蓄禁,我述圣愿将得买栽手一股转卖与映辉叔等承修理蓄禁为业。凭中议定价银贰百贰拾四两,亲手收清。其山木界:上登顶,下抵溪,左凭冲,右凭岭。其木任从买主管业,日后卖主述圣、原主吴正贵、正明不得异言。倘有异言,卖主理落,不干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此卖字存照。
述圣 亲笔
凭中 薄玉山、姜玉宏、宏章、绍周
道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 立
山主回购栽手股的案例很多,
举例如参见贵州省编辑组编:《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山主往往也更具备维持自己林地、林木之完整的動力。相应的,在佃栽契约中也常约定有山主的先买条款,即栽手如要出卖其股份,须“先问地主”。
举例如参见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页。但上揭契约则略有不同,吴姓兄弟之栽手股先已出卖与并非山主的姜述圣,而后山主因“自要蓄禁”将栽手股买回。虽然无法确知土栽双方在佃栽契约中是否约定有先买条款,但山主的确表明基于整体蓄禁的原因而完成林木股份的重构,即将林木上的土股和栽手股均集中于山主手中,得以实现山主对林木的完全管业。
2.栽手收购土股
栽手进行收购的案例可能较为少见。在下面的“卖禁杉木字”中,
本契约,及所提及的前述契约,见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第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127页。叙述了先后两次交易的情形:首先,杨姓叔侄与刘耀祖分别土栽四六均分,杨姓叔侄先将其山内杉木六十株卖与杨光藩;随之,数月之后,栽手刘耀祖加价将前述卖出的木植购回“伙禁”:
立卖禁杉木字人杨光藩,情因要银使用,无所出处,自愿将到土名登屋冲老杉一团,上抵路,下抵杨胜祥青杉,左抵胜祥地土,右抵路,四至分明。情将廿捌年腊月内买到平灶村杨秀祥、杨连芳叔侄山内砍杉陆拾株,去银弍拾弍两叁钱叁分正,奈栽主刘耀祖名下亦应砍木玖拾株,合计此团杉木弍共应砍木壹百五拾株。今将光藩所买陆拾株移卖与刘耀祖伙禁,言定价银叁十叁两肆钱捌分正,当日银契两交,日后砍伐出河,先除壹百伍拾株头木,余下所砍所禁,仍係杨秀祥叔侄、刘耀祖四六均分,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有买字为据。
凭中 杨胜祥、胜明
亲笔
光绪廿玖年弍月初六日
在这一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土栽之间先进行了具体木植的析分,即合计杉木一百五十株,按照四六比例分为六十与九十株;随之,杨姓叔侄即将其分内杉木出售。然而,栽手刘耀祖似乎更强调了其名下亦有之份额,林木整体中部分单独出卖的情况可能并不令其满意。故而,其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近五成的溢价——出卖价格为“弍拾弍两叁钱叁分正”,而回购价格为“叁十叁两肆钱捌分正”——随即购回杨姓叔侄卖出的杉木。林木价款在短时间内的大幅溢价,似乎也间接说明了该笔交易中收购方之需求的强烈,并不是卖方所谓的“要银使用”所能完全解释的。至此,就此一百五十株杉木,栽手达到了完全管业的目的,可以静待“日后砍伐出河”。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所展现的是多元股份结构下林木采伐决策的三种可能:合议、析分与重构。这些决策安排既追求林木连片经营的整体效应,又显示出对具体股权的尊重和极大的灵活性。通过集中于采伐决策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此种股份结构下的林业经营似乎不同于常谓的租佃、共有、合伙,甚或公司等诸形式,而是在清水江的具体林业实践中造就的或许最为适宜的制度生成。
四、结论
通过对清水江林业文书材料的梳理,相关语境下采伐权的权利主体以及采伐决策机制得以说明:在规范意义上,林木之采伐权多因林地之所有而取得,但通过特别约定可以由山主或栽手排他享有;在采伐决策的实践中,存在“二比同卖”与“各管各业”两种模式的颉颃,而土栽股份的重构往往也是实现采伐意图的重要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将自清至民国的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作为整体处理,相应解析的重点因之并不在于发现采伐权规范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转变。但是,如果将更为晚近的文书纳入考察,则会发现时代背景下关于采伐权的话语在清水江语境中的悄然转变。
1979年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通过。在此背景下,
1980年10月3日,在加池寨姜文仁的家中,党样与加池两地的十一名代表就“山林问题有关事宜”达成了一份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最终被视为对其时《森林法》的违反。参见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0页。。这份作为“今后双方管业的总纲领”的协议书仅有四个条文,其第三条专门规定了“砍伐权”的问题:“今后山林的砍伐权,应由土主、栽主双方商议决定后再砍伐,不得由任何一方擅自砍伐。” [3]第5册153而与之相类的,在平略西北的甘乌所保有的一块民国元年(1912)的“公议条规”碑上写明:“一议栽杉成林,四六均分,土主占四股,栽手占六股。其有栽手蒿修成林,土栽商议出售。”
王宗勋主编:《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115页。原碑文款题“大汉民国壬子年拾月拾伍日”,查民国“壬子年”即公元1912年。在以上两个属于历史与时代的节点上,采伐权规范的问题都恰时地进入了时人的视野,并且依然选择坚持“二比同卖”的路径,而反对“各管各业”的实践。虽然“采伐权”的概念并没有自始地存在于清水江的契纸上,但是,“蓄禁”与“斫伐”这一对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语词,最终都以“砍伐权”的概念进入了清水江文书的晚近版本之中。
参考文献:
[1]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
[2]爱必达.黔南识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47.
[3]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辑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贵州省编辑组编.侗族社会历史调查[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5]张新民.天柱文书(第一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三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潘志成,吴大华,梁聪.清江四案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
[8]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9.
[9]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林业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58.
[10]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
[11]徐晓光.清水杉木要“实生菌”技术的历史与传统农村知识[J]. 貴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7-104.
[12]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13]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二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J].现代法学,2004(5):63.
[15]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北京:人民出版,2008.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