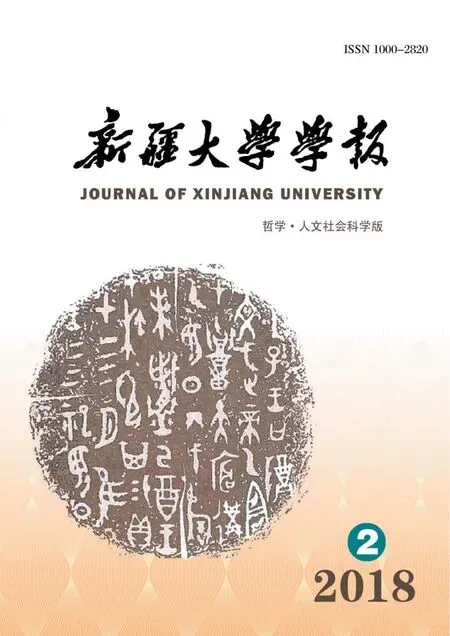《霍小玉传》《李益墓志》及史传中的李益形象比较研究*
何安平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
人生一世,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大部分人随着身体的毁灭,个人的历史也随之终结,不留一丝痕迹。但还有一些人会被后世记起,一次又一次的叙述与评论,尽管已与本人相差甚远。而这种记忆之所以可能,主要是他们留下了传之后世的文字,或他人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文字,他们活在文字中,存在在历史中。每个人一生的真实形象只有一个,然而他人建构的形象却可以有无数,从他生前直到死后的千百年间,建构的形象一直处于变动中,每一次的变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原因,这些变动形成了文学史上连续而又不同的人物形象,其原因与背景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因此探讨同一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就有其意义与价值。
唐代著名诗人李益就是一个在不同文本中存在的互有差异的人物形象。李益,字君虞,在当时诗名甚高,“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1]5784。他在后世被人提及,除诗以外,还与蒋防所撰《霍小玉传》这篇传奇名篇有关,其中男主人公即是李益,但主要形象不是诗人而是“负心汉”。李益的生平事迹多有疑问,2008年新发现的《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后文称《李益墓志》)①主要研究论文有:王胜明《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5);何新所《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0(1);朱关田《李益志浅释》,《书法丛刊》,2009(5)等。对李益研究价值极大,同时也提供了另一个李益形象。此外,《新唐书》[1]5784-5785、《旧唐书》[2]3771-3772均有李益的传记。传奇、墓志、史传三种文本中的李益有同有异,下面分别考察,再做分析。
一、李益形象
1.传奇中的李益形象
《霍小玉传》②本文所引《霍小玉传》,原文均出自汪辟疆《唐人小说》,后不再出注。中李益才华过人,“思得佳偶”[3]77-84,但久未如愿,于是托媒婆鲍十一娘代为寻找,经历数月,寻得霍王小女霍小玉。李、霍相见倾心,日夜相从,后李益出外任官,其母已为李益与其表妹卢氏订婚,李益不敢违背母意,只得顺从。霍小玉多方打探消息,无果,“遂成沈疾”。最终李益被黄衫客蒙骗并强行带到霍小玉住处,小玉痛斥李益,并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之后,含恨而终。李益与卢氏成婚,但由于李益的猜忌,以至“竟讼于公庭而遣之”。此后,李益所见妇人皆如此,“至于三娶。”结合文本细为分析,李益传奇形象可概括为:
(1)才子。《霍小玉传》在开篇即称道:“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佳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之后,霍小玉之母言小玉平日常吟李益“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之诗句,亦可见李益诗才当时广为人知。李益和霍小玉盟誓,并书之于纸,言其“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足见李益才思敏捷、才华过人。
(2)好色放荡。《霍小玉传》记李益最初之目的即为“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因此才托鲍十一娘代为寻找。与霍小玉相见后,言明言“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而小玉也心知此事,所以说“今以色爱”。
(3)有情人。李、霍爱情之起点虽为李益好色,但经过两年日夜相处,李益确实动情。李益被授郑县主簿,在小玉请求八年之期后,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此言可作两解:一、昧心欺骗之词;二、真情之词。李益与卢氏定婚亦为不得已。首先,古代婚姻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中又特别指出“太夫人素严毅”,李益若违背母意,即为不孝,《唐律疏议》“十恶”第七为“不孝”,疏议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4]1“2不孝”将处以重刑。其次,“生家素贫”,想要在仕途上较为顺利,必然需要与“甲族”卢氏这类的世家大族联姻。再者,“户婚律规定‘卑幼在外娶妻,尊长后为定婚,未成者,从尊长’。那么,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礼制(父母之命),李益不得不屈从。”[5]再从霍小玉死后,李益的表现:“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亦见其真情。小玉入葬之日,李益也是“尽哀而返”。以此再看当初李益对小玉的誓言,则可看出其中即使有不实之词,但也一定有其真情在。
(4)负心汉。李益虽然有情,但最终背盟弃约,受到当时人的鄙视。李、霍之事被推入公共空间后,李益的负心汉形象就被认定,“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他的密友韦夏卿也对李益说:“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
(5)猜忌妻妾。李益与卢氏完婚后,到郑县不久,“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馀,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最终卢氏被遣。此后,李益的猜忌有过之无不及,“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加初焉。”
总之,传奇中的李益形象是多面的,但以“负心汉”形象为主。
2.墓志中的李益形象
《李益墓志》由崔郾所撰,崔郾,生于大历三年(768),卒于开成元年(836),曾与李益同朝为官,李益有《同崔邠登鹳雀楼》,崔邠即崔郾之兄。又《墓志》中亦言“以郾斑(班)行,尝忝其后尘,中外又参其末属”,则李益与崔氏兄弟多有交往,其所述内容较为可信。
墓志首先颂扬李益,着重于其述作讽咏之不朽,之后追述其祖先的光辉业绩,“尔后龙骧列郡于荥阳,学士显名于秦府,中允翱翔于宫署,给事论驳于黄门,皆重芳累叶,迭代辉焯,焕乎史策,为时休光。给事赠兵部尚书讳亶即公曾王父也,皇朝虞部郎中讳成绩即公之大父也。烈考讳存,皇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皇朝户部员外郎范阳卢谕即公外王父也。蝉联配盛,中外叠映。总会和粹,克钟令人。”①详见王胜明《新发现的崔偃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本文所引《李益墓志》主要依据此文,后不再出注。如此显赫的名单,说明了李益出身不凡,也预示着他将大有作为,继承祖先事业,使之发扬光大。继而叙述李益自大历四年进士登第、联中超绝科,间岁,又中主文谲谏科,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秩满又为渭南县尉等一系列官职。中间特别提到德宗“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不仅中华之内,在中华之外李益作品也为东夷之人所珍视,“又见公雅什为夷人所宝”,以此说明李益声名之大。之外,又有宪宗“两征文集”,更见李益才华之著。墓志还记到李益之妻卢氏。李益有两任妻子,均姓卢,前夫人范阳卢氏,常州江阴县主簿集之女,“门风光大,坤仪弘播,音徽早谢,而懿范犹存”,然早逝,前夫人卢氏之墓志也被发现,为李益自撰,全称《唐检校尚书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从其可知卢氏名,字文嫄,享年三十七,有子五人,“容为德之表,孝为行之首,揔百艺,承六姻”[6]。从墓志来分析,李益形象可概括为:
(1)名传中外的才子。年始弱冠,就已进士登第;德宗、宪宗都称赏其文;作品还在东夷广为传播,为人所珍视。
(2)建功立业的臣子。李益授河南府参军后,“府司籍公盛名,命典贡士,抡次差等,所奖者八人。其年,皆擢太常第。精鉴朗试,遐弥攸伏。”任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在幽燕之地,宪宗嗣统元年,“征拜都官郎中,入考制试,克协汇征之告,雅符则哲之能。洎参掌纶綍,润色度,不虚美,不隐恶,文含齐律而直在其中。未及真拜,出为河南少尹,历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尽哀矜,雪疑狱,有于公之阴德;正编简,缉遗文,极刘向之美事。”铭文又再集中称赞了李益的事功:“累擅殊科,以文从吏。出佐藩服,入居郎位。运偶开泰,朝慎名器。俾掌王言,实符公议。贰尹河洛,亚职兰台。春宫再入.望苑重开。肃肃卿寺,警巡为贵;煌煌帝庭,貂蝉列侍。迈德时久,辞荣礼备。曳履还乡,挥金乐志。”
(3)孝子。《墓志》:“周旋累祀,再丁家难,哀号孺慕,殆不终制,虽丧期有数,而茹毒无穷。”充分展示了李益的孝心。
(4)道德完备之人。墓志中的李益道德上毫无瑕疵,进士登第,尽心于朝廷,忠贞不二,功业显赫,文辞卓绝,又孝顺父母,家庭和睦,真所谓“德茂天经”。
总之,从墓志来看,李益是一位完美之人。
3.史传中的李益形象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李益传记,所述极为简略,且基本内容一致,从中可分析出的李益形象为:
(1)著名诗人。两《唐书》明确指出李益以诗歌见长。《旧唐书》:“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2]3771。《新唐书》文词有异,内容相同。
(2)患有痴病。李益猜忌妻妾,此与《霍小玉传》所述类似。《旧唐书》:“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古时谓妒痴为‘李益疾’[2]3771”。《新唐书》:“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疾’”[1]5785。
(3)有过不得意之时的人。《旧唐书》认为因为“李益疾”的缘故,所以李益“久之不调”,而此时“流背皆居显位。”所以“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新唐书》:“同辈行稍稍进显,益独不调,郁郁去游燕,刘济辟置幕府,进为营田副使”[1]5785。大意相同,“郁郁”显示了李益当时的心态,是不得意的心理表现。
(4)自负之人。两《唐书》均言李益自负其才,凌忽他人,使人难以忍受,为众所不容,因此谏官举其幽州诗句有怨望语,以致“降居散秩”。
总之,史传对于李益有褒有贬,以诗人形象为主。
为便于直观,列表如下:

表1 李益形象比较
从表可见,三种文本中的李益,传奇和墓志相差极大,史传相对客观中立。
二、原因分析
1.文体差异
中国古代特重文体,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言:“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7]459,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亦言:“文辞以体制为先”[8]9等,不同的文体规定了其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的不同。
唐传奇属小说类,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认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9]486,鲁迅也有精辟的论述:“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10]41-42。则传奇是作者有意构拟出来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重视文采,主观性极大,内容较为自由,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诗文相比要小很多。《霍小玉传》亦大致符合上述所论,所述李益与霍小玉之事可能多为传闻,蒋防或许是对当时士人的此种风气颇为不满,才撰此小说。据孙棨《北里志·序》载:“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11]22。可见此种现象极为普遍,非李益一人之事。又李益有“痴病”,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亦载:“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12]38。此一事在当时应广为传播,且为真事,而蒋防则作《霍小玉传》以实之,亦是“作意好奇”之笔。《霍小玉传》集中写李益与霍小玉之事,事件集中,多细节描写,如写李益去见霍小玉之前,“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从动作行为写出了李益的焦灼等待的心情。又如李、霍相见时情景的描写都极为细致,充分展现了传奇体的特点。
墓志体制要求严格,以至于到了程式化的程度,这和传奇相差很大。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言:“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8]53!此类文章庄重典雅,寄托着子孙对于祖先的怀念与尊崇,虽说应美恶并书,但事实情况往往是颂美隐恶。墓志要介绍墓主的一生,而且由于墓志铭载体的限制,篇幅不能太长,内容多是线性叙事,墓主的形象往往就是单一、平面的。以此来看《李益墓志》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墓志中的李益是一位毫无瑕疵的完美之人,即使是当时广为人知的“李益疾”也没有任何词语涉及。墓志的文体早已规定了内容,由此可见一斑。
正史传记的体制要求又和传奇、墓志不同,史传应尽可能客观记录和评论,不带私人感情。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论述到:“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如果做不到,则“任情失正,文其殆哉!”[13]287刘知几《史通》也认为历史著作“华而失实,过莫大焉”[14]151,要求“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14]153。所以史传中的李益褒贬互参,瑕瑜互见,既写出了其才华卓绝的一面,又写出了李益的“痴病”以及仕途上的挫折和不得意。
2.作者立场与意图差异
三种文本中李益形象的不同,还有各自作者的因素在。《霍小玉传》作者蒋防,所生活的时段与李益大致相同。《霍小玉传》的创作立场很明显,就是批判李益,在文本中作者还调动社会舆论来评价李益,以突出李益的行为已遭到了公共批判,非仅是个人的一己之见。《李益墓志》的撰者崔郾,与李益多有交往,又同朝为官,受李益后人所托撰写墓志铭,除要受墓志文体的规定外,也要受人情的影响,其立场是赞美,因此大力颂扬也就是必然的了。史传的作者距离李益去世已远,又无特殊关系,所以秉持史家实录精神,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作相对客观的记录。
三种文本的创作意图是不同的,也决定了李益形象的差异。蒋防作此传的意图难以断定,因此有学者认为《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15],以李党的蒋防作来攻击牛党的李益的。另外一种可能则是蒋防对于新进士此种风气的批评(见前文),此种情况在后世亦为黄宗羲所批判:“唐末,黄巢逼潼关,士子应举者,方流连曲中以待试。其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取桂,任从陵谷一时迁。’中土时文之士,大抵无心肝如此”[16]111。无论作者目的如何,其批判的意图则是肯定的。《墓志》之作,目的是为了能使逝者的声名传之久远,既如此,则所记内容定为美善之事。官方正史传记是为了记录前代历史,并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就具体的撰者来说,如实记录历史仍是主要目的。由于如此意图的差异,也就使得传奇多虚构,墓志多颂美,史传较客观。
三、差别的启示
通过对三种文本中李益形象的分析比较及差异原因的说明,可得到如下的一些认识:
第一,对文体要有充分的认识与了解。《霍小玉传》所记之事为不实之传闻,此种情况传奇可以写,但墓志和史传则丝毫未有。关于“痴病”,墓志未涉及,史传有记载,而传奇则由此衍生出了李益猜忌妻妾以至三娶的故事,从《卢氏墓志》看,此全为附会。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唐传奇的“作意好奇”“幻设”的特点。墓志由于各方面原因必须对逝者有所回护,所以《李益墓志》在写李益到幽州任职时的情况就和史传相差极大。《墓志》在写李益去幽州之前,是在讲述李益的诗文作品为德宗皇帝所赞赏,并且传到了东夷之地,如此给人的印象是李益的才华受皇帝赏识,所以被授予官职,后又在幽燕之地,大有作为,建功立业。而史传的叙事则与此不同,两《唐书》所设置的背景是李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升迁,是“不得意”的,所以才“郁郁去游燕”,然后被刘济辟为从事,至于在这段时间李益有没有什么作为,史书无载,但《新唐书》言其“尝与济诗,语怨望”,则可推断李益在刘济手下是颇不顺心的。关于李益的为人,三个文本也相差很大,墓志和史传的评价几乎相反。《墓志》认为:“公直清而和,简易而厚,不恃才以傲物,不矫时以干进。”史传则记载:“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由此又可见到墓志的叙事并不客观,尤其涉及到对于墓主的道德、功业评判时,墓志往往文过饰非,充分显示了此种文体主颂美的特征。由此,也提醒我们对人物作评价时要综合多方材料,才能做出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
第二,充分认识史料的特征。文史研究必然要有史料作为支撑,而史料非常复杂,必须经过分析和考辨,才能正确运用以解决问题。上述三种文本中,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因为是同时代又有交往的人所撰,而且墓志必然经过逝者后代的认可,又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所以可以用来考订李益的生平事迹。但又不能一味以墓志为是,如上述李益在幽州的情况,对照李益诗文则史传所记更为真实。《霍小玉传》虽为虚构之作,但其整体的背景和所展现的世人心态又有真实之处,如所描写的京城新进士的行为,如霍小玉一般的妓女的生活状态。又如,文中提到李益与卢氏订婚后,由于卢氏为甲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而李益“家素贫”,只好“涉历江淮,自秋及夏”向四处借贷。此种现象反映了唐代的门第观念和婚姻观念。门阀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仍有巨大影响,王梵志之诗:“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17]119就是民间婚姻重门第的表现。又《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载:山东士族们“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18]6135。此虽是唐初的记载,但与《霍小玉传》相对照,则此种现象在蒋防、李益的时代仍然存在。关于唐代男女的结婚年龄《霍小玉传》也有所反映。李益与霍小玉将要分别时,小玉言:“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但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小玉之愿难以实现。贞观元年,唐太宗下《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19]54。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20]1529。虽然不一定非要如此不可,但唐代男子结婚年龄“大抵二十成人而婚者居多”,女子出嫁年龄以十五岁居多[21]249。霍小玉这一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让人感受到霍小玉的痴情,同时也更令人同情。可见唐传奇虽然可能在事件细节上虚构,但其背景却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反之,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传奇作品。同时,在比较中,也能看到正史传记的局限,正史由于为后代所修,加之体例的限制,记述一般比较简略,又容易产生错误,所以研究中必须借助墓志以至于传奇等文学作品,纠正其错误,丰富其内容,如此就可达到文史互证的效果。
第三,文献留存及内容的人为性。文献很大一部分是经过了人为选择之后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的内容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人为过滤。《李益墓志》中对于李益形象不利的材料全部去除,有意规避不使人知,把有益的方面故意放大,惟恐人不知。《霍小玉传》则由于某种意图就其一点放大,随意嫁接虚构一些事件以达到作者的目的。史传的记载只能是概而言之,而且又是后世修史,文献本已不全,史官还要在有限的材料里再提取,最终形成的传记就会极为简略,这些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利用文献时就不得不多加留意这种人为性。
第四,人物形象在不断被创作,这一变动中蕴含着“真实”。在古代,人去世后,个人形象只能凭借文字得以保存,随着历史的变迁会逐渐的模糊或者变异,创作者以自己的认识、不同的文体来塑造人物,从而使同一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呈现不同的面貌。李益形象即是如此,这对于历史还原的研究造成了不便,但却有益于文学,在不断地被创作中,文学形象的李益越来越丰富,寄托着不同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历史还原其实已不可能,也难以真正回到历史的场景,历史只是我们理解中的历史,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能够感受到其温度与情意。《霍小玉传》除展现出的唐代门第、婚姻等社会观念具有真实性外,其中李益形象所处的困境也有其现实性。李益对霍小玉有情,但又不得不服从母亲的安排,表现了一个普通士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力感,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此一类士人的普遍心态。这一李益形象的创作所包含的的深刻意蕴远远超过了墓志、史传中的李益。所以不断被创作的人物形象蕴含着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可借由此通达“历史的内心”。
中古墓志的大量出土有力地推动了近年的中古文史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涌现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目前的研究大多还是史料的考订,主要方法即使用新出文献补充或纠正传世文献,对墓志价值的开掘还不够充分,因此,多年前已有历史学者呼吁墓志研究要从史料分析走向史学分析[22]。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墓志研究,相对集中在对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和墓志文体的研究,前者成果颇丰,后者还有待推进,这当然有墓志本身的问题,新出墓志除大家手笔或少数文章精品而外,大部分是程式化的写作,文学价值不高,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本文努力在上述两种路径之外,尝试从形象书写的角度入手,希望通过不同文本对同一形象的书写来认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凸显新出墓志作为一种文体的形象塑造功能和书写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