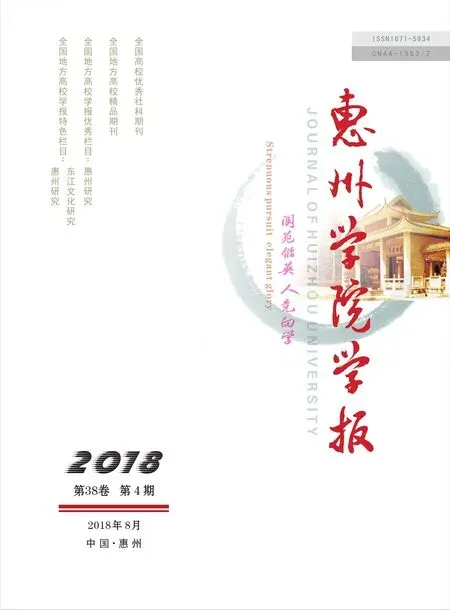裘沙、王伟君夫妇对鲁迅杂文的图像演绎1
——以《华盖集》为例
倪丽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裘沙、王伟君夫妇潜心研究鲁迅二十余年,为鲁迅小说绘制了大量精美的插图,举办了26次鲁迅专题画展,受到海内外美术界和鲁迅研究学者的广泛赞誉。裘沙还入选了美国国际传记协会(ABI)《世界5000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IBC)《国际名人录》[1]74。1977年,裘沙、王伟君萌生了创作鲁迅杂文插图的想法。裘沙说:“鲁迅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生平,而在于他的思想,而鲁迅思想的深刻最直接体现在他的杂文上。于是我继续苦思如何来画杂文[1]74”。1980年前后,他们陆续创作了《生命的路》《前驱的血》《健壮的新芽》《中国的脊梁》等6张杂文插图[2]。1991年裘沙、王伟君呕心沥血的作品《鲁迅杂文·论文一百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99年他们创作的《鲁迅论文·杂文160图》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收录了裘沙、王伟君的插图。裘沙、王伟君夫妇用图像诠释了鲁迅思想精神的深刻内涵,更以形式多样、融汇中西的艺术手法建构了鲁迅杂文的图像世界,填补了此前鲁迅杂文插图的空白。
一、强烈的批判性:对国民性的解剖
《华盖集》于1925年出版,收录了鲁迅31篇杂文。1925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华盖集·题记》提道:“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3]2”。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创作思想更为成熟,一方面延续议论时事、针砭时弊的“社会批评”,对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等深发议论,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走狗文人的屈膝谄媚。另一方面进行挖掘国民性的“文明批评”,对奴性、中庸的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刻地剖析。正是因为鲁迅高屋建瓴的思想,才使他的杂文跳脱了人与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具备了诗史的价值[4]。
裘沙夫妇只选择了《华盖集》部分杂文进行插图创作,共计22张插图。鲁迅批评时事的杂文比如讽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阿谀奉承、奴颜媚骨的《“碰壁”之后》《“碰壁”之余》,批判章士钊政治立场摇摆的《答KS君》等很少进入裘沙夫妇的创作视野。这并不代表他们对社会现状的漠不关心,而是他们抓住了鲁迅杂文的思想要旨。裘沙说:“我所追求的并非单纯的艺术,而是活的生活,活的严峻的中国人生[5]”。裘沙夫妇的杂文插图富有强烈的批判性,锋芒直指国民精神的弊端,荒谬的教育方式脱胎于畸形的国民性格心理,黑暗社会现状是恶劣国民性的衍生品。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鲁迅杂文“文明批评”的内容作为创作蓝本,揭示社会时事背后国民的精神内核,对国民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批判。
首先,批判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化。《通讯》一文中鲁迅与《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针对社会上“尊古复古”的思潮进行讨论。鲁迅以清兵入关后颁布的“放足垂辫”的诏令无法彻底执行来影射封建余毒还根深蒂固地存留于国民心中。裘沙夫妇抓取文本中的形象进行创作,他们描绘了一个身着民国服饰却依旧缠足的女子,抱着沉重的包裹坐在一旁。鲜红的三寸金莲与脚边歪斜的“禁缠足文告”形成强烈的对比。女子的旁边是一个男人的侧影,滴着鲜血的大刀依然割不断他身后的长辫。缠足女子手中的包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沉重精神负担,男人留的长辫子亦是国民心中剪不掉的封建鬼魅,(见图1①)。《忽然想到(五至六)》一文中,鲁迅揭示了帝国主义为谋求自身利益故意将舆论导向“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腐朽观念,更讽刺中国的保守者们以封建余毒侵害青年们,将中国变成僵化的、供人把玩的古董。裘沙夫妇摘取了古董的形象,画做了一个瓶身斑驳、年代久远的陶器。瓶口图案类似一个表情呆滞的人脸,以此来讽刺中国思想界盲目复古(图2)。

图1 《通讯》中的插图之一

图2 《忽然想到(五至六)》中的插图之一
《长城》一文中鲁迅对“伟大的长城”大发感慨:“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3]77”。鲁迅以“长城”为喻意在抨击封建文化奴役、毁灭人。插图中“伟大的长城”化身为一个骷髅头,而一个身着白衣的人正投入“魔窟”。隐喻封建文化是无形的长城吞噬人的生命和思想(图3)。《我的“籍”和“系”》一文中,鲁迅正面与陈西滢展开论辩,反驳“鼓动女师大风潮”之说,抨击在封建文化的压抑下失掉自我人格、僵化腐朽的庸众。插图中描绘了一双结满蜘蛛网的骷髅手,一个身披红绸的人端坐其中。“骷髅手”“蜘蛛网”和“红绸带”其实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人们被“圣贤”之名捆绑束缚,最终成了封建统治棺椁中的一堆白骨(图4)。《忽然想到(一至四)》中,鲁迅有感于国民精神不再,军阀统治黑暗腐败,揭示了尽管朝代更替、时代变化,封建文化中“腐败”的毒瘤却一直未割除的现实。插图中一个身着古时的衣饰、长发掩面的人萧索地站立着,中间写着两个大字“明鑑”,寓意以史为鉴(图5)。

图3 《长城》中的插图

图4 《我的“籍”和“系”》中的插图

图5 《忽然想到(一至四)》中的插图之一
其次,挖掘了奴性、中庸、麻木的国民性。《忽然想到(七至九)》一文中,鲁迅支援女师大学潮,抨击杨荫榆等人动用军警对学生残酷血腥的镇压,讽刺、批判封建奴化教育。鲁迅没有局限于单一事件的评说,而是揭示了深藏其后的国民精神内核,将对杨荫榆等人的指摘上升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插图中对应的是一个分裂的人物,对着“羊”一面手执短剑、面目狰狞,对着“老虎”的一面则双手合十、面容和善。杨荫榆原是进步学生,是受军阀压制的“羊”,自执掌女校后反而动用权利迫害羊一般的学生,在黑暗的统治势力前尽显奴颜媚骨。插图更形象地体现了当时中国人“遇到强者不敢反抗,遇到弱者则凶相毕露”的“奴性”心理(图6)。《忽然想到(一至四)》中,鲁迅讽刺无论在何种境况中都能变出合适的态度的“伶俐人”。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仍然自我催眠,为侵略者著书立传、高唱赞歌。插图中展现的是一件晚清的官服,官服底下是两只多彩的“变色蜥蜴”,讽刺曲意逢迎、自私卑怯的“伶俐”国人(图7)。《论辩的魂灵》中,鲁迅一一指出传统国民的荒诞逻辑,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革命就是为了图利;赞成自由结婚即主张共妻主义。图中这张流传各代的“鬼画符”代表着国民的“处世的宝驯,立身的金箴”,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学,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精神麻醉(图8)。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反动的政治党派恶意抹黑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价值,鲁迅愤而创作杂文《战士和苍蝇》。他还在文章《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做出了回应:“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6]”。插图中写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伟大的中山先生与渺小的苍蝇形成鲜明的对比。鲁迅对漠视改革者的流血牺牲的冷漠国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图9)。五卅惨案爆发,鲁迅愤而写作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他既悲愤于帝国主义的残忍掠夺和政府的黑暗无能,更将批判地笔触伸向国民的精神内核,概括出三类社会渣滓。图中分别用知了、公鸡、黄鼠狼来代表国人清谈、内斗、谋私三种人格弊端,阻碍着“黄牛”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前进(图10)。

图6 《忽然想到(七至九)》中的插图

图7 《忽然想到(一至四)》中的插图之二

图8 《论辩的魂灵》中的插图

图9 《战士和苍蝇》中的插图

图10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的插图
二、深刻的现实性:对“立人”思想的解读
裘沙说:“我们在搞杂文的时候,总在想怎样理解鲁迅思想,或称‘鲁迅主义’。我们认为鲁迅思想的核心用最直接的语言讲,就是中华民族怎样才有希望,它的病根在哪里?怎样才能在世界新潮流中生存?我们搞杂文就是想把‘鲁迅主义’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不光是国民性的批判[2]12”。裘沙夫妇曾写作《何谓“鲁迅新宗”》的论文,认为“新宗”是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王乾坤评价到:“裘沙夫妇瞄准的,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制高点[7]”。裘沙、王伟君夫妇多次以婴儿形象隐喻立人主旨。《忽然想到(五至六)》中,鲁迅呼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3]54”封建礼教吞噬了孩子们的个性,将他们都变成了麻木、僵化的傀儡,而鲁迅期望人们发出自我的声音。

图11 《忽然想到(五至六)》中的插图之二

图12 《这个与那个》中的插图之一
插图中一个赤裸的男婴儿,扑腾着双脚、大声哭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婴儿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是自我的意志、独立人格象征(图11)。鲁迅的《这个与那个》中抨击古董的守旧者,支持青年改革者。赞扬他们突破了封建壁垒,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插图中将改革者比喻为蹒跚学步的幼儿,幼儿学步虽不成样子,但母亲都恳切地希望他走出第一步。改革者作为开拓的先锋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民众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图12)。鲁迅在《导师》中劝诫青年们不必寻求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走荆棘塞途的老路,而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黄玲红评论到:“我认为青年时期的鲁迅就已认识到,在当时的时代,真正觉醒的是极少数,真正的导师是不存在的[8]”。插图中对应的是三个赤身裸体但肌肉遒劲的青年人,在风沙瓦砾的恶劣环境中寻找方向、抱头前进(图13)。

图13 《导师》中的插图
裘沙、王伟君夫妇认为鲁迅的“立人”思想也能烛照现代社会。于是,他们将现代生活的经历和感受融入创作中。裘沙说:“鲁迅的东西如果没有现代生活的感受,画出来是没有生命力的,会变成图解[2]13”。王伟君:“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生活,艺术语言的运用也离不开生活。画鲁迅的东西,用不着说哪一张画来源于哪一个生活,都有生活的感受,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现在有些人说鲁迅过时了,那时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鲁迅[2]14”。谈到创作鲁迅杂文插图的缘起,两位画家一致说是文革。一场群体的、非理性的狂欢式的运动导致了许多灾难,也更让他们明白国民的精神痼疾。在任何历史时期,人们都需要鲁迅“立人”思想的指引,需要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通讯》中鲁迅批判国民听天由命、中庸麻木的思想,缺乏为人的独立意志,呼唤思想革命。插图中描绘了一个的普通民众的头颅,头顶被打开,原本一片空白的大脑被注入橙黄色的光芒,呼应鲁迅先生提出的立人宗旨(图14)。《这个与那个》一文中,鲁迅说:“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者纷纷逃亡……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至是中国将来的脊梁[3]153”。鲁迅先生批判“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的看客们,遇到一点危机,唯恐成为最后者,纷纷作鸟兽散。插图中只有一个长跑运动员在跑道上奔跑着,另一个人则严肃地注目着他(图15)。他们展现了独立人格的魅力,不依附群体的意志,不随波逐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容易被外界的因素干扰、迷惑。鲁迅所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更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图14 《通讯》中的插图之二

图15 《这个与那个》中的插图之二
三、形式的多样性:融汇中西的艺术手法
对裘沙、王伟君而言,创作鲁迅杂文插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杂文缺乏小说的形象性和画面感,其深刻的思想性更是抗拒图像的演绎。裘沙说:“我要画杂文的想法大家知道后,有许多人都表示担心,美学家王朝闻同志很委婉地同我说:你还是搞小说好[2]11”。虽然受到质疑,但裘沙夫妇并没有放弃创作,而是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创作路径。这既体现了鲁迅杂文思想的深刻性又实现绘画的审美性。裘沙夫妇善于从鲁迅杂文文本中抓取具体的形象。比如《通讯》中的“缠足”和“垂辫”(图1);《忽然想到(七至九)》中的“凶兽”和“羊”(图6);《论辩的魂灵》中的“鬼画符”(图8);《这个与那个》中的运动员(图15)。其次,以文本中的形象为基础,进行想象演绎。他们以古董比喻守旧的封建者(图2);以化身鬼魅的长城比喻吃人的封建文化(图3);用蜥蜴比喻自私的“伶俐人”(图7);用婴儿比喻独立的自我等等(图11、图12)。
有评论家说:“裘沙夫妇的杂文插画,没有重复自己原来的风格和一般绘画模式,而是各种画法并用,各种色彩和造型并存,用不拘一格的绘画手法与鲁迅特有的杂文语言一起交汇,构成了一股震人心田的冲击力[1]74”。首先,裘沙夫妇吸收了现代派表现主义的绘画技法,运用素描、木炭画和油画的方式创作鲁迅杂文插图。其中,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珂勒惠支对裘沙夫妇产生很大的影响。王伟君说:“她的偶像是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特点是泼辣,不羞涩,不克制,‘简练、丰富、深刻’,很对她的口味[9]”。而鲁迅正是将珂勒惠支版画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对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珂勒惠支粗粝的画风也与鲁迅杂文如“飞沙走石”般粗犷、犀利的笔调交相辉映。裘沙夫妇吸取珂勒惠支的绘画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见解,运用到鲁迅的杂文插图中。《牺牲谟》一文中鲁迅描写了两个人物的对话。道貌岸然的士绅高唱改革论调,实则封建顽固、中饱私囊,漠视改革者的流血牺牲,妄图脱下他们身上仅剩的一条“破裤”,攫取最后的利益。鲁迅以此讽刺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虚伪。插图中裘沙夫妇采用素描和木炭画的方式,运用简练、粗粝的线条勾勒人物形象。不求形似,只求“神肖”,舍弃了琐碎细节刻画,形成了整体强烈的视觉冲击。他们甚至都没有画出人物完整的脸部。但从整体看一个身穿马褂、皮鞋的肥胖士绅,与身着一条破裤、瘦骨嶙峋的“牺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物的性格特征已跃然纸上,作品的思想主题已在对比中呈现出来(图16)。
除了素描、木炭画,裘沙夫妇还运用油画的方式创作杂文插图,强调色彩的强烈对比、冲突。《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先生悲愤民国的“新星”已经陨落,军阀统治黑暗,国民还是没有跳出“为奴隶”的怪圈。插图中心是象征着“中华民国”的宏大、鲜明的“五色旗”,插图边角是渺小、灰暗的持棍的军警和挑担的劳工,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五色旗上画着的灰色叹号和问号,是对国民精神失落的愤懑追问,是对仁人志士鲜血白流的感叹悲哀(图17);《杂感》中鲁迅再次提出,如果国民的神经衰弱,没有形成拥有独立意志的个人,那么血书,章程,请愿,讲学等救国方式皆无用。插图中描绘了一个扭曲变形的人物,披散着头发,伸着尖利的指甲。裘沙夫妇用多变的色彩、混乱的曲线,营造了荒诞诡异的艺术效果,形成强烈的视觉震撼,以此象征社会和国民精神的混乱(图18)。

图16 《牺牲谟》中的插图

图17 《忽然想到(一至四)》中的插图之三

图18 《杂感》中的插图
裘沙夫妇不仅吸收西方现代派技巧,还从中国民间传统的绘画手法中汲取养分。裘沙在谈到创作杂文插图的初衷时说:“为了帮助年轻人读懂,我想用形象的形式将它变得通俗些,送去的作品不要像我这样大年纪才读懂。让更多的青年人早点懂鲁迅,这实在是一件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和希望的一件大事[2]11”。为了贴近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裘沙夫妇的插画中糅合了民间的图画艺术。《这个与那个》中学步的胖娃娃,色彩鲜艳喜庆的背景可以看出传统年画的影子(图12)。《论辩的魂灵》运用了民间的“鬼画符”,左边写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图8),插图中选取了古代神话的人物,描绘了一个怒目而视的二郎神形象。裘沙夫妇还提取了鲁迅杂文中的语句作为图画的注解,以便阅读者能更清晰明了地理解鲁迅杂文思想。
裘沙说:“插图作者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对文学作品既要钻得进去,深刻理解作家的思想,懂得作家的艺术,同时又要能够跳得出来,不使自己成为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奴隶[5]20”。裘沙、王伟君夫妇的插图是深入鲁迅杂文思想并充分发挥绘画的艺术性能的结果。裘沙夫妇将自己的个性、情思和理解注入鲁迅杂文插图的创作中,用精彩多变的画笔构筑了鲁迅作品的图像世界,复活了鲁迅精神,表现了鲁迅对腐朽落后封建文化的强烈抨击,对孱弱麻木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探索与追求。
注释:
①文中插图均选自鲁迅《华盖集》,由漓江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