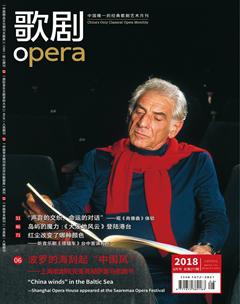“声音的交织,命运的对话”
方博
下笔之初,我长時间反问自己,这个作品究竟要评论它的哪个方面?体裁的创新与实验?艺术表现的多样手法运用?又或是创作理念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观看演出之前,我就曾反复确认,这部作品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作品想要表达什么?真的可以传达出传统艺术生命力的当代声音吗?在拿到节目册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许多顾虑和不解都显得多余了——创作团队并没有打算白纸黑字地解释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体裁/题材,而是用作品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既然评论的对象异于常规,我这次落笔也准备“实验”一回,让阅读者与演出亲临者一样,自己去感受便是。
2018年4月27日晚,香港大会堂剧院的舞台上,一位女演员在布置了大量暗黄色灯柱的舞台上来回走动、蹲下又起身,时不时发出像练声房里“咿咿呀呀”的声音。台下观众仍在陆续进场,夹杂着嘈乱的交流声;台上的女演员继续她的肢体和声音行为,观众也并不安静地等待着“熄灯”“播放剧场观演规则”等演出开场的信号。然而这些信号迟迟未至,女演员便走到一个位置站定,此时管弦乐的伴奏响起,她开始演唱珀塞尔(Henry Purcell)的《孤独颂》(O Solitude)。此刻观众们似乎逐渐意识到,刚刚歌剧女演员奥利维娅·萨尔瓦多莉(Olivia Salvadori)并非是在开演时练习走台和开声,那是她在当晚剧场上演的《肖像曲》作品中的舞台表演,且从她走出侧幕那一刻就开始了。
其后,日本能剧女演员鹈泽光(Hikaru Uzawa)的登场及其表演,与舞台上萨尔瓦多莉的声音重叠、交错,形成了不同体裁艺术形式、声音与肢体行为、语言与表演内容、唱词与精神意识的多维对话。在不同场次中,鹈泽光的个人自白及能剧表演,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自我的寻找。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能剧演员,她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能剧表演领域中的处境颇为坎坷。她口中的自白正是她真实生活的境遇,而她戴上面具后的肢体表演又是舞台化、戏剧化的虚拟。萨尔瓦多莉和鹈泽光在同一个舞台上的各自表演,都是个人身份被赋予戏剧化之后的跳进与跳出。她们二人之间,不同语言、不同戏剧角色、不同个体的真实存在,结合舞台上围绕在鹈泽光脚边的暗黄灯柱和包裹着萨尔瓦多莉脸颊的冰蓝色灯光,随时营造出戏里戏外跨时空的交流。
除她们两位之外,《肖像曲》的唯一男主角,也是唯一未“登上”舞台却时刻主导着戏剧整体走向的人物——昆剧武生演员杨阳,出现在舞台中央悬置的投影屏幕上。杨阳是这部纪录片、歌剧和能剧结合的舞台戏剧作品中的故事主线人物,同时也是导演卓翔数年前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武生》的主角——那个被江苏省昆剧院重点栽培,却因为自己所从事的武生行当在市场化竞争下渐渐衰微而萌生退意的青年昆剧演员:那个因为不愿被动接受戏剧悲剧性程式,而自谋出路创作和编导实验昆剧作品的新生代剧场导演。
《肖像曲》中三位不同国籍的剧场艺术家,三种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舞台艺术,用各自舞台的行为诠释了真真假假的表演实践,以及表演者自身真实的命运。作曲家许敖山说:“虽然所有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可以理解为是假的,只是一场戏,但演出的艺术家们却是活生生的……当我们看见台上的演员抽离自己,进入一个又一个角色,那是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构故事的过程……他们要处理自己和传统的关系、在社会中的包袱和重担、在艺术上的跨越和传承:他们在处理如何演绎故事角色的同时,也在处理如何演绎活在当下的艺术家。”
这些戏里戏外的联结过程,也正如导演卓翔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上所设计的一样——从纪录片延伸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到戏外的真实人生。他还突破了舞台戏剧体裁的界限,把这部剧场作品视作“一部不断即时更新、记载当下的纪录片”。在故事性多重空间同步发展的设定前提下,编剧麦淑贤则是将能剧、昆剧和歌剧三种舞台艺术,从其原先的表演模式中解放出来,选取不同剧种的代表性片段,与纪录片的影像进行拼贴,在艺术家们讲述和表演的内容上进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艺术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命运之间的“遥望”。
就《一个武生》这部关于昆剧武生杨阳艺术道路探寻的纪录片本身而言,卓翔对传统艺术的反思与创新,对职业道路的探索,以及他和他所从事的艺术在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下的时代挑战等方面的镜头语言,都并未对我一此前在中国内地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者——产生特别大的冲击。因为这样话题的探讨和以纪录片形式的呈现方式,我已然看过很多。但是将这样一部纪录片放置在剧场舞台的现场,再结合能剧和歌剧的、带有行为艺术意味的表演,反而将纪录片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无限放大了。
同时,许敖山又是个“玩摇滚”和“玩电子音乐”的新锐作曲家,他的“电子声响世界”的概念,与长期从事传统剧场音乐创作的作曲家有着极大的反差。许敖山在不同章节段落中大量使用夸张的声音效果,将舞台上的表演和纪录片投影画面都衬托得相得益彰。这也体现出他“当代戏剧化声音大于古典艺术审美”的创作意图。可以说,许敖山找到了三种剧场艺术形式中多重音乐语言和文化共通性中的个性,因此他的电子音乐语言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潮流和回响中,实现了平衡。然而,也正由于他的戏剧性声音表达中,运用了大量过于抽象的电子声音,干扰了整体作品中纯粹讲述故事的基本力度,所以他的表达方式会时不时有一种意识流的感觉,而这点又与作品从纪录片向舞台延伸的故事连贯性产生了刻意的反差。这让期待故事性的观众产生“侧幕戏(花活儿)太多了,反而没了故事本身的主戏”的感觉。
剧终幕落,观众的热情仍旧持久。有观众好奇,纪录片男主角在屏幕之后的艺术选择和当下的人生境遇:也有观众不吝表达对穿越历史长河的戏剧/歌剧艺术在当代舞台上另类呈现的欣赏:还有观众感叹,抛开语言和表演形式的障碍,仍然贯穿作品的生命关怀主题。纵观《肖像曲》这部作品的剧场呈现,创作者们就一直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和背离之间,不停地转换。而当代艺术,在形式与内容的彼此位置和具体功能上,本也涵盖着诸多为人们或赞叹、或批判:或期许、或不解的层层“迷之面纱”。
笔者认为,《肖像曲》的mind set(想法)有了,人文意涵也有了,形式内容科技的交织也都清晰了,独缺一点点“眼睛和耳朵的感官体验之外、当代艺术最需要的趣味”。
文末,笔者想以编剧麦淑贤根据此次鹈泽光所表演的能剧《井筒》选段中,日文唱词所翻译的中文诗词,来结束这篇剧场观感:
明月已非去年月,
此春已非往年春。
松风吹响芭蕉叶,
梦中醒觉天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