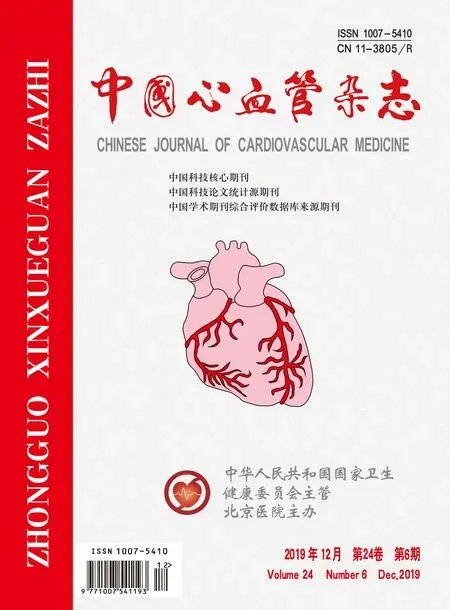“介入无置入”理念的兴起和前景
赵韧 韩雅玲
110016 沈阳,北部战区总医院心内科 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
自介入心脏病学奠基人Gruentzig于1977年完成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例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开辟冠心病非外科手术治疗的新时代起,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技术经历了从PTCA到金属裸支架(bare metal stent,BMS)再到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时代的变迁,特别是2001年问世的DES,使PCI术后靶血管再狭窄率显著下降至5%~10%,DES逐步成为PCI治疗的主流策略。但是,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及病例的长期随访,发现DES远未达到PCI技术的完美境界,如金属框架和载药涂层聚合物的永久存留,会继发一系列血管壁病理生理过程,并影响患者随后的客观评价和治疗选择。在此情形下,“介入无置入”的新理念首先在欧洲应运而生,其中脱颖而出的是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它是目前最成熟的无置入介入技术,这也从此开启了PCI治疗领域的又一次革命。
1 “介入无置入”理念的兴起与应用
DCB是将球囊导管作为把抗增生药物输送至血管病变局部的工具,到达病变部位后,通过球囊扩张与血管内膜的短时间(30~60 s)接触完全释放抗增生药物,由此抑制内膜增生而达到降低再狭窄的目的,同时由于没有异物残留在血管壁,可避免金属异物存留及药物聚合物载体的持续刺激,降低炎症及血栓发生率。DCB结合了单纯球囊扩张术和药物洗脱支架术的双重优势,使这一新技术独树一帜,近年来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开始引领PCI技术朝向最前沿的方向发展。
早在1991年,Harvey Wolinsky就提出使用紫杉醇DCB来预防PTCA后的再狭窄,但在如何增加球囊与血管壁接触瞬间血管壁对药物的摄取率、发挥抗内皮细胞增生的药效上遇到了瓶颈。直到2000—2002年间,有研究者筛选出了一种基于将紫杉醇和造影剂碘普罗胺混合的药物涂层方法,使PCI后新生内膜面积减少63%,从而显著降低了再狭窄发生率,并且血管内皮化良好,未发生术后血栓,从而奠定了DCB技术的核心内容即药物混合基质涂层的坚定基石。
2004年,Bruno Scheller等在Circulation杂志上发表了关于DCB预防PTCA后再狭窄的动物研究数据,验证了DCB输送抗增生药物和抑制增殖的有效性,证明了DES的药物缓释技术对于预防再狭窄并非必需。此项研究结果促使研究者们开始寻求DCB在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ISR)、小血管病变、分叉病变等各类病变治疗中的可行性,不断丰富临床循证证据。
2006年起,陆续发表的PACCOCATH ISRⅠ/Ⅱ、PEPCADⅡ、KurashikiⅠ/Ⅱ、ISAR DESIRE Ⅲ、SEDUCE、PEPCAD DES和PEPCAD China ISR等多个DCB对比传统球囊血管成形术或BMS或一代及二代DES的临床研究,给出了DCB在治疗各类ISR疗效及安全性方面的丰富而确凿的循证数据。
相应地,多个国际指南/共识/文件开始涉及DCB的临床应用推荐。2010年,欧洲心脏病协会联合欧洲心胸外科学会(ESC/EACTS)共同发布的心肌血运重建指南就将DCB推荐用于治疗BMS-ISR。2014年,ESC/EACTS的指南更将DCB的适应证更新为适用于各类ISR(Ⅰ类推荐,A级证据)。同时,DCB也成为了第一个被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评估项目推荐的器械。DCB被正式提升至治疗ISR金标准的地位,“介入无置入”的理念从此得到广泛认可并快速传播。
中国归属于PCI数量大国,2018年全国PCI超过90万例。随着支架使用数量的增加,ISR问题也日益严重,DCB无置入介入治疗技术无疑革新了国内众多介入医生的理念。早在2012年,国内首次发起了在中国人群中评价DCB对比紫杉醇药物洗脱支架(paclitaxel-eluting stent,PES)治疗DES-ISR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即PEPCAD China ISR研究,这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国内17家中心220例DES-ISR)随机对照研究,2年随访结果显示,DCB治疗DES-ISR的疗效及安全性与PE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不仅填补了DCB在中国人群中应用研究的空白,也进一步提高了国内医生进行“介入无置入”实践的信心。2014年,由原沈阳军区总医院韩雅玲院士牵头的中国人群的BEYOND研究是另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国内10家中心入选222例分叉病变)随机对照优效设计的研究,主要探讨国产DCB治疗分叉病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DCB显著降低了靶病变直径狭窄程度。研究中使用的DCB已于2017年12月6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上市,成为第一个国产DCB品牌,也是国际首个获批应用于分叉病变的DCB。
2 “介入无置入”理念的前景
DCB治疗现已是多个指南推荐的ISR标准适应证,并成为中国专家共识中治疗小血管病变、分叉病变的优选方案。此外,DCB技术仍在不断拓展其新的适应证,例如,单纯DCB治疗冠状动脉近端大血管病变的研究结果十分喜人。2018年,EuroPCR大会上公布了首个评估DCB治疗冠状动脉大血管病变效果的随机对照(DCB比BMS)研究的9个月随访结果,显示DCB治疗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BMS(1.9%比12.4%,P=0.00034),且术后仅接受1个月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CB组的靶病变血管重建率为0,提示对于高龄、需要抗凝或存在出血高风险的患者,DCB可以作为冠状动脉原位大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方案之一[1]。目前,国内很多专家也具有应用单纯DCB治疗冠状动脉大血管病变的经验,不少学者认为DCB对部分患者人群的冠状动脉大血管病变疗效甚至有可能赶超小血管,我们期待这个推测能在之后更大规模人群的研究中得到更有力的循证支持。
DCB用于治疗基线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相关临床研究较少,但2019年EuroPCR大会上公布的REVELATION研究结果则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DCB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性不劣于DES[2]。国内也有学者正在及计划在国人中开展DCB治疗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临床研究,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DCB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如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长弥漫、静脉桥血管、周围血管疾病等领域的应用也一直在研究中,虽目前公布的相关研究尚少,但相信随着更多研究者的介入,亦将成为今后的研究热点。
此外,DCB产品本身也在不断升级优化中,如对其核心技术药物涂层的研发。目前,国际及国内大规模使用的DCB产品均采用紫杉醇与药物载体碘普罗胺的混合基质涂层。与此不同,现在临床广泛应用的DES所载药物均为西罗莫司或其衍生物类,研究已证实从疗效和安全性上考虑,西罗莫司或其衍生物类DES要优于第一代PES。因此,新一代DCB的研发中,西罗莫司衍生物将是替代紫杉醇的绝好药物,不过这种设计的DCB是否能带来比紫杉醇更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尚不清楚。Ali等[3]最新发表在JACC: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杂志上的一项随机、多中心临床对照试验显示,一款新型西罗莫司涂层球囊(4 μg/mm2)与临床证实的紫杉醇涂层球囊(3 μg/mm2)相比,在治疗冠状动脉再狭窄病变中有等同的疗效[术后6个月,紫杉醇涂层球囊组节段内晚期管腔丢失为(0.21±0.54)mm,西罗莫司涂层球囊组为(0.17±0.55)mm,两组间12个月的临床事件亦无差异]。虽然该研究样本数量有限(50例),但毫无疑问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信心投入到西罗莫司涂层球囊的深入探索中。由于西罗莫司本身的特性,其较紫杉醇进入血管壁的时间长,而从药物球囊与血管壁需要短时接触快速起效的作用方式上来讲,用何种药物载体或赋形剂对于西罗莫司涂层球囊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在研究中的药物载体或赋形剂有丁基化羟基甲苯、微孔球囊、磷脂赋形剂及细胞吸附技术等,以优化西罗莫司被血管壁吸收后的药代动力学过程。期盼这些新一代DCB在临床试验及循证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
总之,DCB作为“介入无置入”理念的最成熟代表,从出现到被世人所认知、接受与认可,走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道路。随着更多DCB临床数据的验证及临床病例实践和随访的积累,相信“介入无置入”的理念及DCB技术能真正惠及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病患者。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