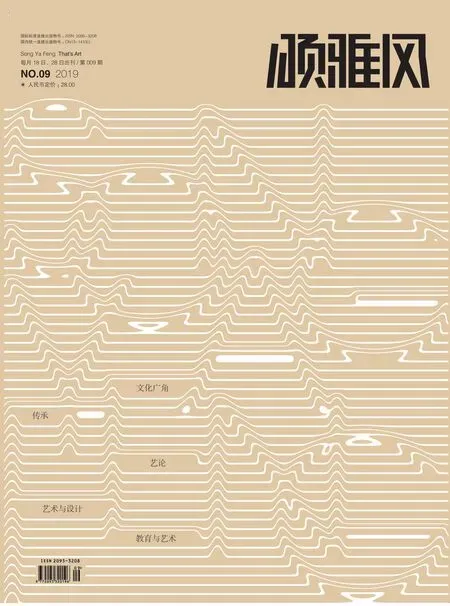笔墨文心下的家族崛起
——读《雅债》有感文氏兴起
◎顾稚冶
作者单位: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当一个外在力量迫使我们每个人画地为牢、安静下来时,我们不由地开始自我对话。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今天,我们通过网络每个人可以是耶鲁的学生、王羲之的弟子。在这个时代,“学习”是如此“平价”,公开的网络课程、高分辨率的书画真迹……甚至花8 块钱可以团购一个在线课程,而这些“课程”如同大众点评上的美食,可以按地域、菜系、口味不同纬度分类,应有尽有。似乎没有你学不到的,只是你不够努力!生在这个时代,原来还要对“学习”这件事情带着“我不够努力”的愧疚感。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也许正是因为纷繁复杂的学习资源,令“时间”成为我们最为可贵的东西,在“学习”之前,恐怕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究竟为什么学习,看看那些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可能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感触吧。
“平行宇宙”中的大师
“我的欢愉就是悲哀。”
——米开朗基罗
十几岁时,最崇拜的艺术家就是米开朗基罗,对于痛苦有着如同飞蛾扑火般的着迷,激动人心的一生似乎就是要自带毁灭属性的。今天,慢慢翻阅《雅债》,品着文徵明淡淡悠长的一生,如同案边的茶,温润而又回味无穷,读着一位明朝才子的经历,就像一位身边的朋友,没有那么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有着似乎跨越时空的契合,也许这就是早已融入骨血之中的炎黄子孙的共鸣。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星米开朗基罗(1475—1564 年)遥遥相对的是东方明朝的文徵明(1470—1559年)。两位大师前后相差5 年出生,都有着89 岁的高龄。在他们传奇的一生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些许相似之处,例如各自都有相依附的权势团体,这种团体与师长的身份不同,更类似于庇主(守护者),社会地位的奠定是离不开这一层关系的;其次,他们都出生在“中产阶级(书香门第)”,米开朗基罗的父亲是地方行政长官,而文徵明的父亲是明朝精英阶层(进士),这也令两人在童年时期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有,他们又同时在各自大环境的“最佳城市”成长成名,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文艺复兴的起源地佛罗伦萨,而文徵明生活在明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
除去一些相似之处,两人又有着天地般的差异:米开朗基罗更像一颗“孤星”,他才华横溢、性情乖张,他和庇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相爱相杀,他对抗达·芬奇,并与拉斐尔为敌,他信奉不婚,脆弱多疑吝啬……文徵明,却像镜子的另一面:当时最有名的画家沈周、最厉害的书法家李应祯都是文徵明的老师,而他娶了自己庇主吴愈的女儿,他岳母的兄弟就是最会画竹子的夏昶,他老师李应祯的女婿就是大名鼎鼎的祝允明……他在长辈的呵护下成长的同时和同辈交好,获得“江南四大才子”等名号。
缔造家族的“人设”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柏拉图
家族的崛起是需要一个精神标杆的,现世的财富、权利还不足以支撑,上辈的武将履历也似乎还不够上档次,于是,文家选择的是“文天祥”,一个人人称道的英雄,一个忠义两全的完美化身,是可以并理应纳入族谱中供奉的!虽然文徵明的太爷爷文惠、爷爷文洪已经构建起一个令人称羡的“书香门第”,然而在苏州的立足仍然离不开“文天祥”这样的祖先。
文氏家族有了精神图腾之后,是开始对“女性家庭成员”的塑造。母亲,是滋养家族的源泉,赞美母亲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及后代的肯定呢?对于家族中的女性成员,文徵明和他的父辈们都是谨慎又不余遗力的去“塑造”人物历史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设”。受儒家思想影响,女性家庭成员都被塑造成守道、勤俭、正直的形象,家族中出嫁的文氏女性与家族的关系也得到了最庄严的确认。例如文徵明姨母祁守清虽因新寡赤贫,但仍然接济照顾好了文氏兄弟,于文徵明有“母道”;文徵明祖父的妹妹文素延加入精英赵家,博览群书且深明大义,在文徵明笔下是儒家正直典范;文徵明姑母嫁给贫困的“吴中名族”俞氏,在文徵明笔下是侍奉公婆、支持丈夫、照顾子女,“虽贫,衣被完洁,器物虽敝不辄弃”;文徵明叔父之妻谈氏与文年龄相仿,文徵明为其书写的墓志铭中非常小心避开了谈氏名字,称颂她的靖恭厚默。
构建互惠的友圈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中国传统人伦关系中,“朋友”排在第五伦,在社会关系中,“朋友”不像前四者有明确的界限,不确定又充满张力。米开朗基罗和庇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签订西斯廷教堂工程的契约,这里既有金钱报酬更有不可违抗的命令。而像文徵明时期的文人,一幅画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吗?有时候可以,但是交换的背后不仅仅是钱,还有“情”,我愿意为你画的“情”和我欠了你为我作画的“情债”。中国人所特有的千丝万缕的“人情网络”,也是文徵明及其家族优雅地经营着互相成就的“朋友圈”。
明朝文人的“朋友圈”不只包含同辈关系,其实师长、庇主、同僚甚至不认识但是通过某种关系羁绊的人都可能纳入到这个圈子里来。文徵明在1511 年(40 岁)左右曾写下一组诗作《先友诗》,八位被提及的“友人”应该说与其父辈的联系更密,虽然其中几位也是文徵明的老师像沈周、吴宽等,但从社会关系上捋的话,缘起父亲文林、叔父文森、岳父吴愈等,可以说文徵明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友”这层关系,而他所作诗集也有意让文家后辈继承这层人际关系网。
再说说“互惠”,这并不是简单的“我给你了什么,你回馈给我什么”礼尚往来思路,可以说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默契感铸就了这种优雅的交互动作。举几个有意思的例子:王鏊,是文徵明的庇主,或者说文依附于王,而这种关系从父辈就开始了,文林(文徵明的父亲)会赋诗去纪念一次宴请王鏊的经历,而文徵明之后也是“持续”赠诗,赞美什么呢?赞美王鏊在苏州的漂亮园子。王虽然是偶尔回复,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建立,1511 年,王鏊为文家的文天祥祠堂做正式的祭文。对于文徵明一家来说,自己修建祠堂认祖是一回事,当代知名人物公开肯定那意义就又不一样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回报并不是明许但是是暗期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存在于彼此的默契之中。
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互惠”事件:1514 年之后文徵明和唐寅的政治观点出现分歧,照理说关于宁王之事是文徵明非常避讳的,但是他和唐寅的互动以题诗形式出现在了一件古迹上——《宋高宗石经残本》。古代学习资源并不丰富,我们现在可以从网络上看到放大数倍的唐寅真迹、文徵明手稿,但是在从前,能够亲眼目睹一份名家真迹是非常难的,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中介绍文徵明“写竹得夏昶之妙,山水出沈周之右,工诗文,精书法,吴越间称之”。从后世的一些记载来看文徵明并没有拜夏昶为师,极有可能是从岳母(与夏昶兄妹关系)处得到夏画,并通过这样珍贵的“学习资源”练习画竹。所以说当唐寅拿出《宋高宗石经残本》长期出借给文徵明时,文不仅在作品上题诗,还旁征博引进行论证。文徵明以自己的名声学识回报唐寅的慷慨相借,使这件作品无论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内涵,都得到了提升。
徐祯卿、钱同爱和唐寅都被文徵明自视为“四人组”(四才子之外一种团体),除了和唐寅的互惠互动外,文凭借自己的人脉,向当时得势的吕㦂推荐徐祯卿的诗,令徐进入更多精英阶层人士的视线之中。而和钱同爱,更是从友情到亲情(钱的女儿嫁给文的儿子文彭),缔结更为长久的“契约”。东方文人的“朋友圈”就是如此妙不可言,同时期在欧洲的米开朗基罗当然不能作为西方的代表,毕竟还有一个同样春风得意、左右逢源、极为会做人的拉斐尔。但从东西方文化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欧洲人的贵族身份基本上是世袭的,每个人很清楚现在的权利对象以及接下来掌管权利的人,奉承结交的对象是比较固定的。明朝就不一样,科举制度意味着人群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掌管话语权的人。进,彼此交好、相互扶持;退,留有余地、后会有期,这似乎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社交哲学。
延伸“死亡”的意义
“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
——费孝通
在科学家眼中,生命是承载基因开往终点的公交车,那么在明朝文人眼中,生命又意味着什么?每个个体承载的又是什么?
米开朗基罗的名句——“睡眠是甜蜜的,成了顽石更是幸福,只要世上还有羞耻与罪恶存在着的时候,不见不闻,无知无觉,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不要来惊醒我!”也有人说这话就是米的墓志铭。相对西方人的墓志铭,中国人对于“死亡”慎重得多,翻开中国艺术史,一大部分可谓是“黄泉之下的艺术”,对于亡者的追思,体现在各种仪式中。文徵明父亲文林去世后,他就先后写书函邀请老师朋友来写行状、祭文、墓志铭。老师沈周和文家一向深交,被邀请写行状;吴宽、徐祯卿被邀写祭文;杨循吉、李应祯被邀写墓志铭。普通人过世没有这般待遇,而文家经过文惠、文洪、文林、文森一代一代的努力,得以在苏州立足扬名,这些身后事是特别讲究的。叠加的赞美、吟颂,锻造着文家特有的家族精神,对于文家的后人,将会秉承这种承前启后的责任,在他们所继承的师友关系中继续互相影响,家族精神(文化)将永远延续下去。在东方哲学中,死亡,从来不是终点……
结语
文徵明无疑是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但他也是文家族谱中的一员,他的璀璨,离不开文家前前后后的每一个人,他自己知道,他的族人也知道,所有的人都努力呵护并不断缔造着这种关系。反观米开朗基罗,他的父亲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他也是欧洲天才而富有的艺术家,当他的继承人终于如他所愿,娶了佛罗伦萨最古老的贵族时,他才觉得圆满了。是的,娶一个贫穷的贵族,一个身份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而文徵明所处的东方,“贵族”是慢慢养成的,可能这也是东西方的差异吧。
——文徵明《致妻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