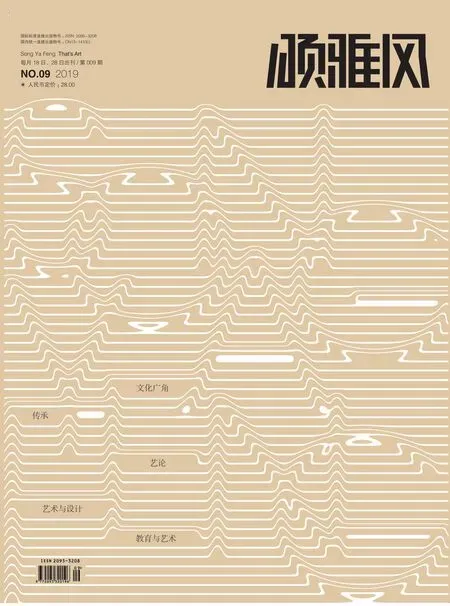羌族傩舞羊皮鼓舞的美学思考
◎刘怡玲
一、羌族释比羊皮鼓舞的概况
羊皮鼓舞在早期现实生活中就是为了驱邪治病、送鬼消灾、安神祈福,所以在这种严肃庄重的场合下进行的羊皮鼓舞带有强烈的祭祀性。在当代,虽然祭祀舞蹈有了不同程度的嬗变,但其祭祀作用依然是基本的功能。尤其在羌族原始文化保存良好的阿尔村,至今仍会有请释比用羊皮鼓舞来驱鬼逐疫的活动。驱鬼逐疫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丧葬仪式,一类是驱邪治病。
在对羌族文化保存最完好的阿尔村,村民们集体论著的《阿尔档案》里记录:若是丧葬,需要由释比老人推算日子,何日何时何地跳丧葬舞,一般人数不限(3、5、7、9、11 人不等,要求必须是单数)。首先由释比老人带头鸣炮,跳羊皮鼓舞,从接货买东西的人和货一起跳到死者家,围着火塘跳一圈,再出来围着棺木边唱边跳一圈结束,随后把买回来的东西交给内管,内管再分别交到执事人员手中。接着在大半夜时,先本寨子的羊皮鼓舞队到位,再去接外寨的羊皮鼓队,然后接舅家人(羌族人以舅家为大,在这种情况下,舅是家族中最有地位和权威的人),接到门外后,开始摆酒设宴,然后释比要开始边唱边跳,丧事唱法中有一种叫na’sua,要将死者的一生经历都唱完,唱出他在世时的艰难苦情。最后送老归山,羊皮鼓队从家里出发,边敲边走到墓地,围着棺材跳一圈停下,释比老人念经请示祖师爷,然后再做完一套仪式后验棺下葬。
而若是某家有人中邪,就医也无法治好时,一般就会邀请释比做法跳鼓来驱邪。在最前面带队的是释比,头戴下坛帽(ba’su’da),用各种野兽的獠牙和牛皮制成,五色的彩纸和五色的布丝带,右手拿法铃,用来指点和指挥鼓队的节奏和队形。左手拿神杖,由天然的木头雕刻,上面刻着祖师爷的神像(象征祖先的保佑),然后是第二位也是右手拿法铃跟着前面做指挥,左手拿五彩旗(ca’qi),最后就是敲羊皮鼓舞的队伍,他们跟着神杖和五彩旗的指挥来跳,按法铃的指挥,羊皮鼓舞的鼓点、脚步和动作就不断地发生变化。
据释比传承人朱金龙说,“羊皮鼓舞的驱鬼逐疫仪式主要还是在解放以前跳得最多,因为那时候条件艰苦,战争动荡,人们的思想也还没有解放,很多不明白的事情,都归咎于神鬼,在恶劣的环境中死去的人有很多,所以曾经人们邀请释比表演都是进行神事和鬼事的祭祀和驱邪仪式。”对比朱金龙先生所说的原始与现在的羊皮鼓舞,可以发现很多跳的场合与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可以说现在的羊皮鼓舞也正在经历一次洗礼,从野蛮走向现代的转变。
虽然现在依然有驱鬼逐疫的祭祀性,但它已然不单单只是单一的实用功能了,还变得更加具有审美性与文化性。因此,这也可谓一场羌族民族文化发展传承的标志。
二、韵律的特征
羌族羊皮鼓舞表演形式古朴,整个流程充满神秘和庄重感。虽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成为全民性的风俗活动,羊皮鼓舞至今仍保留着“万物有灵、以舞示神”的原始自然崇拜的共同特征。例如在羊皮鼓舞中,很多动作都有表示驱赶、恐吓、追逐等意义,如蹉步、大禹步等,还有些动作是模仿山羊的习性动作,如商羊步、按腿划圈等。羊皮鼓舞中一个典型的舞蹈动作就是“商羊跳”,商羊跳是模仿山羊的习性动作,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天降大雨,商羊起舞。”“商羊跳”是以膝盖屈膝然后大腿发力跳为主要特征,常常是在给神的表演中常用的动作,为的是展现出释比的勇猛和坚强。
在舞蹈动作中,主要一直是在俯身屈膝中进行动作的变化,而膝部高低幅度的大小是需随着表演舞者自身基本功能力而定的。老释比朱金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表演时为了偷懒将膝盖只是微屈,其实传统跳羊皮鼓舞膝盖是非常弯的,蹲得很低,释比要在膝盖一直保持深屈的状态下跳十几分钟,其实是非常累的。”
当然羊皮鼓舞也常在丧葬时跳。释比在墓地,随着鼓声的节奏,时而庄重时而明快,念诵死者的一生事迹,边唱边击鼓跳,以此来超度亡灵早日到达彼岸。随着鼓声咚咚,身体保持稳而沉的轴向转动和上身拧倾的韵律。但无论是给神表演还是给鬼超度,都伴随着屈膝颤动,借此带动身体和手部各个动作的延展。羌族阿尔村的村民们还说道:“我们村里跳羊皮鼓舞不会像专业的演出团队那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进行排练,一般就在大家农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练习,但我们表演的羊皮鼓舞非常之默契,也非常之灵活,在演出时可以灵活地根据演出场地和演出性质,由带头的释比与我们一说,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配合表演,我们的动作队形都自觉按照领舞释比的盘铃声和动作来改变。”
三、羌族羊皮鼓舞的美学内涵
德国哲学家卡希尔在《人论》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这样的观点:“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而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的美也隐藏在这种符号形式当中。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有巫术文化的影响。与传统的舞蹈艺术相比,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的内容表现出特有的社会性神学活动(宗教和巫术)以及礼仪的符号意义,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像科林伍德说的:“所有这些巫术仪式都是忠于原型的再现,虽然有所舍取,它们都机械地再现了意图对之有所增进的那些实际运动。”
羊皮鼓舞的每一个动作也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体现着明显的民族肢体符号学的内涵表意。在羌族羊皮鼓舞的表演中有许多手执羊皮鼓的俯身屈膝动作,这类动作一般是在上坛请神所使用,随着俯身到仰身的不同高度的敲击节奏,膝盖也屈伸不同的程度。这类动作由传承人朱金龙解释说:“这是为了表达对上天对神的敬意的作揖,由低到高表示羌族人民的谦卑,由低到高的反复代表对神的崇拜恭敬。人要请神必须表现得非常的恭敬和谦卑,神才会下来帮助羌民。”
释比在请神时鼓点轻捷沉稳,如细语轻言一般,动作主要是轻盈的垫步和碎步。还有在表演中有许多甩鼓的动作,如背身甩鼓、环绕肩甩鼓、左右甩鼓、甩胯下击鼓等。这些击鼓的动作,都是比较快速急促的,要在很短的节奏内完成,所以一般是用于下坛的驱鬼或葬礼仪式,为了震慑住鬼魂,所以较为猛厉。其次在羌族莫恩纳莎中最著名的便是“禹步”,羌族中的许多步伐都是在此基础上变化的。相传“禹步”主要是由于大禹常年治水所以腿有顽疾,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长久以往被人们称作“禹步”。
现在羌族人民都坚信自己是大禹的后人,因此在羌族的传统舞蹈莫恩纳莎中有不少禹步的动作。阿尔村的村民说:“我们跳禹步,是为了纪念祖先,也是为了让祖先赐福避难,保佑我们羌族繁荣。”羊皮鼓舞的肢体动作都不是空穴的想象,而是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积淀中,所有羌族人民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符号,是有意味的形式。羊皮鼓舞不是生活,但却是羌族生活的一部分,它与羌族人民的思想同在且交融在一起。就像著名哲学家西塞罗说:“身体本身只是另一种东西的外壳,要说的内容就像身体里的灵魂,找到和决定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事。”
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并不是为了艺术审美目的而产生,而是为了宗教目的而创作。但是在艺术领域内无论是宗教巫术礼仪活动还是艺术审美活动,在本质上都区别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依靠内在情感驱动进行精神创作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判断,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的艺术不仅仅源自于人们的人性活动,同时还发源于远古氏族时期的宗教礼仪、巫术祭祀等神性活动。只是由于在神性活动的过程中,当时的人民受到生产水平的限制,意识不到艺术美的单独存在,将艺术美与宗教活动相互融合了。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人类审美艺术与自发性艺术行为情感统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艺术审美观念一直依附于神学体系。由此可见,羌族释比的羊皮鼓舞发源于氏族时期,是羌族人民的不自觉行为艺术与神学体系结合的载体,其舞蹈美与宗教情感始终保持同步。
四、羊皮鼓舞的当代舞台化审美发展辨析
对于莫恩纳莎,不止是羌族的人民在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样也受到其他热爱羌民族舞蹈的研究学者与编导的关注,他们对羊皮鼓舞在舞台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羌族的文化和精神风貌。
例如作品《羌魂》反映了羌族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整个节目按照时间顺序将羌族过去朴实的生活与充满现代气息的当代进行连接,既有羌族传统习俗和生活的写照,也有创新的当代羌族舞蹈,让观众了解到羌族的过去和发展。羌族舞台化最为成功的舞蹈,当属《古韵羌山》了,因为在这部舞蹈中采用了实景化的布置,让舞蹈的场景表现得更加具有真实感,营造出了浓烈的羌族人文环境,让观众更加有代入感,更能被吸引和打动。
舞台化的羊皮鼓舞作品在当代出现得越来越多,但要像走舞台民俗风的《云南印象》一样成功,是不容易的。“舞台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产业化和商业化,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满足观众的猎奇和审美心理就会让莫恩纳莎失去原有的质朴味道。如今很多当地旅游演艺中心推出的民俗舞蹈剧,例如广西编排的《印象刘三姐》,其实严格意义来讲是为了经济效益的产业化运营。
但笔者以为较为可喜的是,在四川羌城演艺中心演出的被搬上舞台的羊皮鼓舞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份羌魂,这不只是为了旅游经济的消费,而是这些舞蹈中也渗入了羌民族的自豪感,他们通过跳羊皮鼓舞在告诉观众他们是谁,来自哪里。虽然按观众审美和旅游市场要求,将本土舞蹈进行一些艺术化编排构建是合理的,但舞蹈绝不应该单一模式的发展,而应该多向繁荣发展。不能因为发展舞台化就要摈弃本土的民间舞蹈,没有土壤何来繁荣?羌族本土舞蹈与舞台舞蹈只有合理共存、相互浇灌,才能使羌族舞蹈羊皮鼓舞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