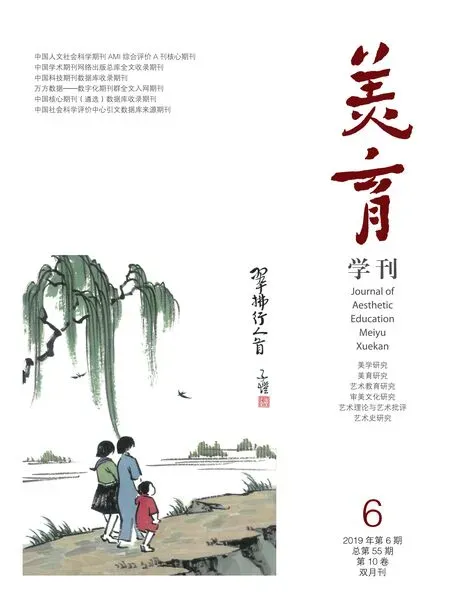儒学修身之艺术特色
白宗让
(1.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 100871;2.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世界各大文明传统无不注重人的全面修养,并且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修身方法,比如古希腊哲学的反思、基督教的忏悔与神启、佛教的戒律,等等。相比之下,儒学提供的修身路径富有艺术性,独树一帜。《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四曰:“儒以道得民”,此“道”就是教育民众之道。《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保氏为教育国子之官,所教之“道”即“六艺”,其中即有礼乐。孔子将儒学的“小六艺”发展为“大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诗》《礼》《乐》三者皆是艺术性科目。
一、道始于情
儒学通过艺术来修身,艺术又诉诸情感,《礼记·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明了儒学修身之路径为顺从人的天性,随后又将此“性”落实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之“情”来讲,不仅完全没有西方哲学中理性与情感之二元对立,而且充分肯定了情感在哲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诗人与哲学家之争,诗人被逐出理想国后,哲学理性就与感性分途。当然,西方哲学家也有重视情感的说法,比如黑格尔曾说:“普遍的和理性的东西必须和一种具体的感性现象融为一体才行。”[1]舍勒(Max Scheler)也说,情感生命不是喑哑盲目的,“个体的情感生命,其实是自然的启示和征兆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个体正是在其中呈露自身”,“情感能够拥有某种寓于情感体验本身之中的意义”。[2]
儒学之核心价值“仁”是一种扎根于情感的德性。《论语·阳货》中宰我质疑三年之丧太久,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通过“将心比心”来理解“仁”,儒学其他一些重要价值如“礼”“忠恕”“直”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阐明,而不是枯燥的教条。儒学不压制人性的欲望,而是要将这种欲望转化到正道上来。《论语·子罕》与《论语·卫灵公》都记录了孔子的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色”是天性,两性之间的互相吸引是人类最为强烈的情感,用“好色”来要求“好德”,才是真正的“孔颜之乐”,此与孟子“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理义之悦我心”(《孟子·告子上》)的说法一样,都体现了儒学“寓教于乐”的本质。《礼记·大学》以“如好好色”来说明“诚意”,《毛诗序》解读《关雎》为“发乎情,止乎礼义”,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好,反纳于礼”。历来的解读都强调了合礼的一面,但对作为前提的“发乎情”与“好”理解得不够,以至于将儒学阐释成了枯燥的教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道始于情”的说法更加证明了儒学立基于情感之特质。
孔子本人情感非常丰富,《论语·述而》曰“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又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每次听闻贤人之死,都要为之哭泣。《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魏晋玄学家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而王弼持不同看法:“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何劭《王弼传》)《论语·宪问》中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从史书记载来看,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情感丰富的、也会犯错误的人,所以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一部通过修身而不断提升自我的记录。
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中,孔子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通过艺术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修身过程。“兴”是儒学诗教最古老、最重要的观念。《说文解字》曰:“兴,起也。从臼,从同。同力也。”朱熹《论语集注》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诗兴激发出来的本真情感是道德力量之源头活水,如舜之“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即“兴、道、讽、诵、言、语”,又记载大师教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毛诗序》之“六义”同此)。“六诗”之“兴”乃是作诗之法,类似“毛诗”标识兴体,被认为是一种用隐曲而巧妙的方式来传达信息的修辞手段。“乐语”之“兴”郑注为“以善物喻善事”,将艺术与道德挂钩,但真正的儒家诗教起源于孔子的“兴于诗”(《论语·泰伯》)与“诗可以兴”(《论语·阳货》)。诗教与诗法是不同层次的观念,但二者内在是相通的。从“兴”而言,儒家诗教有诗志、诗性、诗言、诗政四重维度。
(一)诗志
《礼记·孔子闲居》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博简《孔子诗论》曰“诗无隐志”。“志”是求学的初心、动机、本体。“诗”是“志”最直接、最自然的载体。孔子对“志”极为重视,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志于道”(《论语·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说法。
君子立志之后,通过《诗》中对外物的描述将本体之志感发出来,就是“兴于诗”。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曰:“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诗集传》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马一浮认为“兴”即是“感”:“《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故诗教主仁。”又曰:“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己,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显现。”[3]本体之志与外物感发互动,理性与情感交融。如此看来,儒学诗教本是情志一体,《诗》学史上“诗缘情”与“诗言志”之争可以休矣。
(二)诗性
《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来自《诗·鲁颂·駉》,其中“思”可能是发语词,但孔子的引用必然与道德修养有关系。郭店简《语丛三》曰:“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怠,思无不由义者。”儒家利用《诗》之原文来转喻修身的例子数不胜数,(1)例如《礼记·大学》就将《诗·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之“止”看作了实词。孔颖达《疏》曰:“止,辞也。《诗》之本意,云文王见此光明之人,则恭敬之。此《记》之意,‘于缉熙’,言呜呼文王之德缉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处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思无邪”指诗歌流露出了人之本真情感,人性中潜藏的至善也能通过诗之激发而显现于外。
《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赋予某种美好品质,而是直达人之本性,“温柔敦厚”乃是根本气质之变化。孔子与子夏论《诗》,从“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到“礼后”说明了人性本质的重要性,因为“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礼记·礼器》)。孔子亦以《诗》来判断弟子的人品,《论语·先进》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来自《诗·大雅·抑》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反复朗诵此句,说明已经达到了心性本体之触动。
“兴”还有“兴发”之含义。《毛诗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艺术陶冶性情,只有“发乎情”之“情”是纯真的情感,才可能将此纯正而饱满的情感转化为“止乎礼义”的原动力。《礼记·学记》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禁于未发”只能从本体层面来修养。“发乎情”于不闻不睹之处从根本上防止了恶的产生,这种本体修养是很难达到的,因为算计之心或者“恶”是一种人性的局限,总在修养的破绽处伺机而入。孟子认识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自反而不缩”(《孟子·公孙丑上》)的本体之“畏”。如果真正做到了“发乎情”之纯正饱满,自然就是“止乎礼义”,二者之间没有逻辑跳跃,亦无须外在的道德规约,人性本如此。
(三)诗言
《论语·季氏》中孔子告诉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外交礼仪均用赋诗的形式来表达愿望和态度,《左传》中记载赋诗70余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多用赋诗来委婉地传达想法,《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与其母因争夺皇位而断绝关系,在颖考叔的建议下,母子重逢于地下隧道之中,初次见面即用赋诗来化解尴尬。孔子又告诉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朱熹《集注》曰:“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很多都是启发性的,不同于日常直白式的对话。孔子能够因时因事施教,有时也能从弟子的言语中得到启发。这些就是“诗言”的运用。孟子用“知言”(《孟子·公孙丑上》)来描述一种很高的修身境界。《礼记》《孟子》《荀子》中都大量引《诗》,借诗喻理是儒学的特色。
“诗言”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为了更好地传递那些无法形诸陈述语言的含义,如同《易传》之“立象以尽意”。孔子之后,“诗言”的传统逐渐式微,荀子即认为语言应当完全等同于其含义:“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轴心突破之后,随着理性思维的壮大,艺术思维不可避免地衰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孔子作《春秋》正是因为通过《诗》来实现社会治理已经不可行了。但是,《春秋》依然继承了“诗言”的传统,用笔削来传达“微言大义”,《春秋》之“正名”艺术不同于《荀子》“知通统类”式的“正名”。
(四)诗政
“兴”在培育情感、提高修养、美化言语的基础上,还可以实现政治教化的功能。《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社会风气重在引导,在典范事例或榜样带动的作用下,儒家的礼乐文明以“兴”的方式普及,从而使“仁道”行于天下:“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礼记·大学》)。
《论语·泰伯》之“立于礼”的含义同《论语·季氏》之“不学礼,无以立”。《说文》曰“立,住也”,引申为节制。朱熹《集注》云:“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儒学之“礼”顺从天地与人情之自然:“称情而立文”(《礼记·三年问》),“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但从社会实际来看,“礼”起源于人文与自然的疏离,相对于“诗”,“礼”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约束性社会规范。
孔子早年以知礼而闻名于诸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在周游列国的车马劳顿期间也不忘记与弟子一起修习《仪礼》,《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论语·学而》首章“学而时习之”之“习”就是习礼。“礼”在人格塑成中起重要作用,颜渊问“为仁”之“目”,孔子告之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需要长期的持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曰“待习而后定”,说明修持工夫可以内化为真实可感的性情,使内心的“道德律”更加“深切著明”而“确乎其不可拔”。《荀子》对“礼”之“外入”的塑造作用论述得尤其深刻。
《礼记·乐记》曰“乐统同,礼辨异”,“诗、礼、乐”三者之中,“礼”最容易发生异化,而且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分立也是“礼”之设计的初衷。从“礼主敬”(《礼记·曲礼上》“毋不敬”)观之,疏离感产生庄严感,庄严感产生超越感,从而使“礼”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制度。郭店简《五行》篇“经14”曰:“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一种文明的传承需要虚实结合,“礼”表现于外在的礼制与礼器,让人们通过观赏文物来瞻仰古代礼仪的面貌。“礼”也表现于外在的礼仪与礼容,一个人的内在修为也只能通过“礼”来判断。黑格尔说:“本质和内心只有表现成为现象,才可以证实其为真正的本质和内心。”(2)黑格尔说:“譬如,人们常习惯于这样说,人之所以为人,只取决于他的本质,而不取决于他的行为和他的动作。这话诚然不错,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不可单就其外表的直接性去评论,而必须以他的内心为中介去观察,而且必须把他的行为看成他的内心的表现:但是不可忘记,本质和内心只有表现成为现象,才可以证实其为真正的本质和内心。而那些要想从异于表现在行为上的内容去寻求人的本质的人,其所基以出发的用意,往往不过是想抬高他们单纯的主观性,并想逃避自在自为地有效的东西。”见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篇《本质论》,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2页。因此,“礼”作为一种实物艺术与行为艺术,成为文明的载体和修身的见证。孔子仁礼并重,后世的心性儒学颇有忽视“礼”的倾向,以至于使儒学流向了虚理。我们在注重儒学心性之核心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礼制的重要性,不能将儒学完全还原为“理”。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儒家最为推崇音乐。孔子本人有着深厚的音乐修养,典籍记载他曾有过闻韶、学琴、语乐等经历,在厄于陈蔡之时,依旧“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东汉蔡邕编辑的《琴操》中收录了孔子所作的《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儒学修身之最高境界如“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金声玉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都与“乐”之境界相类似,乐教精神代表了儒学的最高理想。
“乐”能使情感愉悦,“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乐,乐其所自生”(《礼记·乐记》)。乐在修身上有独特的功效,“乐,礼之深泽也”(《性自命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在政治上也能“移风易俗”(《礼记·乐记》)、“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是应用最广泛的艺术。除此之外,“成于乐”的含义主要是指一种更高级的、综合融通的修身成就。乐主同和,是消泯了内外与主客界限的大自由、大解放。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完全超越了道德礼仪的束缚,达到了不思而中的自然境界。郭店《五行》篇中多处提到“不乐则无德”,其“说11”曰:“‘不乐无德’,乐也者流体,机然忘塞,忘塞,德之至也,乐而后有德。”朱熹《集注》解“成于乐”曰:“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
三、诗礼乐之三重和弦
历代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整体阐释主要有三种说法:为学次第说、为政次序说、修身立德说。第一种“为学次第”说来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解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疏曰:“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第二种“为政次序”说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王弼说:“言有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第三种“修身立德”说见于前引朱熹《论语集注》之“诗”本“好善恶恶”,“礼”能“卓然自立”,“乐”使“和顺于道德”。
《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王制》则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二者皆与第一种“为学次第”说相矛盾。此章虽然没有主语,但第二种“为政次序”说也基本可以排除。儒家虽有“乐与政通”的观念,但从《论语》的编排来看,《泰伯》一篇的主旨并非政事,而是德行。如此看来,“修身立德”说是最恰当的解释。孔子此章所言之诗、礼、乐不在具体的技艺层面上,而是上升到了艺术精神的层面,并且着重强调这三类艺术科目对已有的修身成果之进一步提升的作用。古代儒家之“小学”可能有科目次序的规定,“大学”则注重融通与应用,《礼记·学记》云:“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曰:“《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伦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
春秋时期有“诗乐舞”合一的传统,诗、礼、乐的内在精神亦相通,《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孔子闲居》之“五至”也说明乐诗、礼、乐同时并至、一体共进之关系。“诗”兴发志向与本性,结合“礼”之范导,走向“乐”之圆融,三者分别代表修身之本体、工夫、境界。三者从逻辑上可以分开来讲,但本质上是一体的。从辩证法(正反合)的角度来看,诗、礼、乐分别从内、外、合的理路说明了内外交养的方法与最终超越自身局限(分别心)的可能。庞朴的“一分为三论”[4]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辩证关系,“一”是开始,类似本性;“二”是殊异,类似外在约束;“三”是统一于完成,也叫做“参”。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了生活辩证法的三个阶段,即美感、伦理、宗教,大略相当于儒家的诗、礼、乐,但克尔凯郭尔的三段论以否定式前进的方式达到最高,而儒学诗礼乐三者始终是一体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血肉联系不可切断。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章还可以与《论语·述而》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互参。“志”即“兴于诗”之立志,“据”即“立于礼”之自立,“依”即不离弃情感与经验,与本心亲密无间,“游”即是“成于乐”之融通为一,也是伦理道德与主体无限自由之间和谐之见证。“兴—立—成”之“三重和弦”与“志—据—依—游”之“四重进阶”互相发明,共同奏鸣着儒学艺术化修身之交响乐。
四、道艺合一
原始儒学将生命、艺术、伦理、道德熔于一炉,在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中独树一帜。现代学科分类中,哲学、文学、艺术分属不同的专业,学者们自觉守着各自的领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哲学不讲趣味,文学难以载道,艺术不能超升的困境。现代学科中的“艺术”多指独立的、纯粹的艺术,谈到中国的艺术精神时,其源头也多半会追溯到老庄,而不会联系到儒学艺术,更难以和哲学之“道”结合起来。原始儒学中,“艺”即“道”的载体,“道”的灵魂也扎根于艺术土壤之中,形成了以“道艺互生、美善合一”的文化传统。《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无疑是孔子心目中完美的结合。冯友兰说儒学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5]徐复观则说:“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6]3他还通过文字考证了“美”与“善”同义,二字俱从“羊”,在经典中,两义也常能互通互涵。[6]35又说:“由心所发的乐,在其所自发的根源之地,已把道德与情欲融和在一起。情欲因此而得到了安顿,道德也因此而得到了支持;此时情欲与道德圆融不分。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状态而流出……道德成为一种情绪,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道德与生理的抗拒性完全消失了,二者合而为一。”[6]39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一文中说:“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伦理精神,已为世人所广泛了解,且论之者在在皆是,而相比之下,世人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艺术精神的了解,则显得很不够,且论之者亦不多。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而传统艺术的重要功能则是在陶冶性情、潜移默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视作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下的体现。”[7]
艺术在求道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首先,艺术化教学的效果更好,孔子善于用诗歌和音乐的譬喻来晓谕学生。《礼记·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观摩艺术可以兴发学生的本真情感并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使其对“道”的认知更加深切著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之“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使文惠君“得养生焉”。徐复观援引了德国哲学家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前景层”及“后景层”的两个紧密关联着的构造。前景层是物质的、感性的形态,而后景层则是精神的内容。哈特曼特提出“透视”的观念,所谓透视,是知觉把握着对象可以被知觉的东西,更进而指向不能被知觉的东西。前者是可视的、是感性的;后者是不可视的、非感性的,把握这种东西的能力,称为“透视”,此即“洞见”。[6]88-89因此,儒学更注重体味与涵泳,《礼记·学记》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在“藏修息游”中,“道”之丰富的意蕴通过艺术融贯于主体的本真生命之中。
其次,艺术有达致事物本质之优越性。“道”有不可言说的一面,但可以通过超语言的艺术媒介来传达,《易传·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随后又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段话综合了各种艺术手法,如意象、诗言、音乐等。《易传·系辞下》赞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古代哲学经典也多有用诗歌或诗言的形式来写成。《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明确了艺术是达致中道的必要途径。
艺术能够传达语言之外的讯息,《礼记·仲尼燕居》曰:“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己。”《荀子·乐论》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艺术亦有阐微达幽的功能,《礼记·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闻一多在《诗经通义·周南·关雎》中说:“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8]最早的艺术起源于祭祀乐舞,具有“通灵”的功能。舜“以夔为典乐”能使“百兽率舞”(《史记·五帝本纪》)。师旷为晋平公弹奏《清角》,导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韩非子·十过》)。古希腊俄耳甫斯(Orpheus)的歌声能使石块自动砌成祭坛。孔子将艺术的超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已经完全沉浸在形而上的领域中了,是一种超越了善恶的浑圆境界,由知儒学之“天人合一”也是一种音乐的境界,《书·尧典》记载夔之典乐使“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最后,艺术赋予了儒学以“寓教于乐”的特色。乐(yue)与乐(le)相通,“乐”是古代宗教哲学的共同追求,但各家的路径不同。道家有“至乐”“天乐”,佛家有“极乐”,古希腊哲学有“美好生活”,唯有儒家真正将“乐”立足于艺术中来谈,《礼记·学记》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论语·学而》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雍也》孔子赞扬颜渊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颜之乐”也成为历代儒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五、小结
儒学修身的艺术特色不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而是儒学之道本质的必然要求,此“道”并非不变的教条,而是立基于修身主体的情感体验,是时间化、艺术化的“道”。儒学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早树立了艺术的本体论地位。笼统而言,西方思想史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诗与哲学之争,其后艺术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从非实用的、趣味的角度赋予了美学和艺术以独立地位。直到后现代哲学,艺术才取得了某种本体的地位,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说:“我们只应该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故事、神话、类比、寓言、绘画、诗歌来朝向我们和原初世界的前反思的联系。就像塞尚一样,我们必须学习从生活世界出发,在生活世界的画布上描绘我们的意义。”[9]
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传统无不重视艺术,仅从音乐艺术来看,古希腊就有酒神合唱队,基督教有赞美诗,佛教有经咒唱颂。中国的艺术精神最早觉醒,可惜也是最早消亡的。《论语·微子》记录:“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公之礼乐仅存于春秋末期的鲁国,鲁国乐官四散,华夏礼乐文明也就式微了。儒学经典之《乐》早已佚失,这一艺术精神也就失传了。今天,我国和西方在音乐方面的差距尤为显著,这也是颇具反讽意味的。
艺术是前反思的、自发的,能将理想人格建立在本真的生命之上,这正是儒学修身之源头活水。“艺化”能够防止“异化”。多一点艺术修养可以给人生增添乐趣,也可以增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了生存的压力,物质上的算计又使人变得愚昧、功利、幸福感缺失,复兴儒学之艺术精神正是当下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