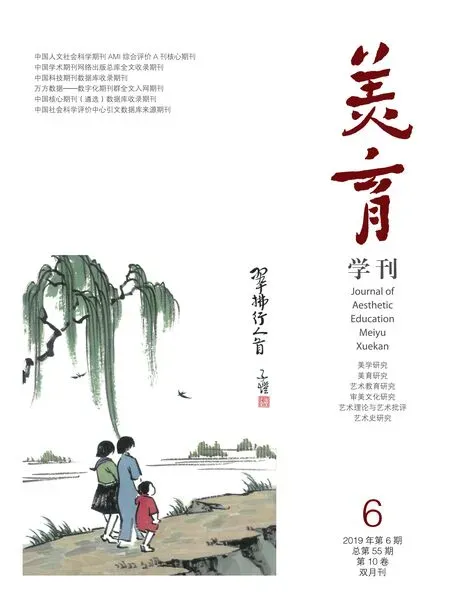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
徐 承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理论奠基人高友工认为,中国艺术及其美学的主流是抒情传统,中国古代不同门类的艺术多以抒情诗的形态为审美理想,而中国抒情诗这一美学典范的最高成就是在圆满的形式结构中蕴蓄(即象征)深厚的伦理价值从而造就抒情境界。(1)参见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尤其是《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试论中国艺术精神》《律诗的美学》等篇。高友工的观点远有儒家“比兴”阐释学的支持,在海内外应和者甚众。然而最近,浙江大学徐岱提出了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与‘抒情传统派’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由‘抒情主义’主导的艺术往往受限于自我利益的得失和功名利禄的计较,在伦理方面完全处于不堪一击的境况。”[1]180徐岱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古典抒情诗。本文无意加入关于中国抒情文艺之伦理价值评判的争论。但高、徐二位针锋相对的论述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对抒情经验加以伦理考量是当代艺术学尤其是伦理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不过,尽管尼采早已指出:“美学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抒情诗人’怎么能够是艺术家?”[2]17但就当今学界的研究热度而言,“抒情伦理”研究相对于“叙事伦理”研究处于绝对的弱势,后者业已成为以小说和电影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抒情艺术往往以个体的情感转圜作为作品的主体结构,格局较小、思想单纯,不似叙事艺术能够通过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多维摹写而展开宏阔的结构、探讨复杂的人伦问题,从而在伦理批评方面具有更大的可被挖掘的空间。恰如卢卡奇所声称:“在小说中,伦理学是一种纯形式上的前提,这种前提由于其深度而有可能进入决定形式的本质,由于其广度而使同样决定形式的总体得以可能形成,并由于其包罗万象而使构成要素的平衡得以实现。”[3]叙事艺术庶几如此。
当然,“抒情伦理”研究并不因此而应当被忽略,毕竟“抒情”是一项重要的人类文化活动,甚至是产生艺术的原初推动力之一。徐岱曾提出大多数中国古典抒情诗“事实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抒情色彩的‘微型小说’”[1]155,以此说明叙事在艺术世界中的普泛性。然而我们在承认抒情对叙事确实具有某种结构上的依赖性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抒情在叙事艺术中正是暂停(或暂缓)故事情节的铺陈而表露人物甚至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部分,因而往往可以被视作作品的“伦理之眼”。就此而言,对叙事艺术展开抒情伦理研究便成为一个别开生面的课题,它似乎属于“叙事伦理”研究的大范畴,但在微观上却借重“抒情伦理”的批评方式。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出一些初步探索,既是对“叙事伦理”研究的充实,也是为“抒情伦理”曲线正名。
二、起源场景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往往把抒情诗、叙事文学(以史诗与小说为代表)、戏剧看成是三种不同的文类,三者间的差异主要通过内容呈现的主客观性或发声的人称来加以厘定,如黑格尔、韦勒克与沃伦、卡勒等都是这么做的。(2)参见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页;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这样的文类区分带有相当程度的理想性和宏观性,我们可以把某部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总体上归为三种文类中的一种,但就这部作品的微观层面而言,则完全有可能同时混融了抒情、叙事和戏剧的成分。本文所论及的叙事艺术,是在比文类更为广泛的艺术体类的意义上,指称一切以故事情节的展开为主体结构的艺术形式。这样的叙事艺术具有广义上的叙事性,无论这种叙事是通过某一人称的独白还是多个角色的对白来实现的;同时因其叙事结构必须在时间中展开而具有了借抒情来调节叙事节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本文所论及的抒情,则是指一种广义的艺术功能,即抒发某一个体(角色、作者、隐含作者等)的内在情感;所谓“抒发”,并非简单的表现,而是指以音乐性来对情感予以赋形(形式化)和延展(风格化)。
就此而言,叙事艺术的鼻祖荷马史诗尽管情节跌宕、气势宏阔,却从来不乏美妙的抒情声音。《伊利亚特》开篇即唱:“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4]这一声朝向第二人称“女神”的吟唱,以雄奇的场景拉开整部战争大戏的帷幕,为全诗定下悲壮、惨烈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里尔琴伴奏下(3)关于荷马史诗的演唱和伴奏方式,参见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的抒情唱词,不仅在情绪营造方面把听众置入心情激荡、悠然神往的境地,还在叙事上打开一扇窗口,把整部《伊利亚特》的情节起点锚定在阿基琉斯因与阿伽门农争执而罢战从而导致特洛伊战局急转而下这一戏剧性的转捩点。抒情的内容旋即使人思绪纷纷,产生伦理方面的疑问:既然战局的逆转、战士的败亡缘于将帅间的私人恩怨,那主人公的行为是否是道德的?作品即将描述双方战士的生命如刍狗般被命运抛弃,那作者的创作动机遵循的是怎样的道德法则?由此反映出史诗时代的古希腊社会具有怎样的道德状况?类似这样的问题,需听取作品的长篇叙事方能寻找答案,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却缘于这段抒情歌词所激起的对战争中蝼蚁般的生命的深深同情。换言之,同情使人发出道德追问,产生穷究叙事情节的兴趣。
相对于通篇保持着紧张与激烈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以主人公战后重返家园的漂泊、怀念、忧思为主题,整体风格更接近于一阕悠远绵长的抒情诗。对于这部与《伊利亚特》风格迥异的《奥德赛》,人文主义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有一段杰出的评论,点出了后者所蕴含的抒情伦理的奥妙:“我猜想,荷马是在他青壮年时期完成了编撰《伊利亚特》的任务。《伊利亚特》有着年轻人的残酷无情。随着经验日丰,感情日沛,他在经历更为丰富、感知力更加细腻时,《伊利亚特》中的人生观可能让荷马感到残缺。……在他人生的后半段,这个游历多方的诗人可能回顾了《伊利亚特》,将其中对于人类行为的态度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荷马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对《伊利亚特》中的人生观既尊重,又批判,结果就诞生了《奥德赛》。荷马用惊人的敏锐感从特洛伊的传奇中选出了一位最接近‘现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做主人公。奥德修斯在《伊利亚特》中就已标志着从单纯的英雄生涯向一种对信念更具怀疑、敏感、谨慎的精神生活的过渡。就像奥德修斯一样,荷马摒弃了阿基琉斯世界中那种直露粗糙的价值观。在创作《奥德赛》时,他穿越灵魂的遥远距离回望《伊利亚特》,既有缅怀之情,又含笑带着怀疑。”[5]这里最后一句话文风隽永、内涵丰赡,道出了《奥德赛》所以能世世代代传唱不息的艺术精髓:对英雄生涯的伴有道德疑虑的怀想与抒情。
从我们对两部荷马史诗的分析来看,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批评大有可为。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风格差异预示着叙事艺术的抒情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保持叙事与抒情各自的界限,令二者各行其是,同时相互映照、相互推动;二是叙事与抒情混融,造就一种高度风格化的抒情性叙事的美学效果。后一种情况的最终发展结果就是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抒情诗剧、诗化电影等在整体风格上接受抒情诗美学影响的叙事艺术。如北京大学吴晓东的《现代“诗化小说”探索》一文即对西方自象征派小说至意识流小说,以及中国从废名、沈从文、何其芳到冯至、汪曾祺的诗化小说传统予以清理,[6]相似主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前一种情况,亦即在典型(叙事情节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叙事艺术中所出现的抒情。关注这类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或许更能体现抒情伦理批评在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典范的树立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经》中的诗作在其原始“表演”场景中是以“诗乐舞”一体的方式呈现的,音乐充当了联结抒情诗与表演艺术的纽带。无独有偶,古希腊戏剧的诞生,也与音乐和抒情诗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美国音乐文化史学家保罗·亨利·朗曾指出:“在感情表现到达极度亢奋时,戏剧会转向音乐。这是最单纯和最古老的戏剧形式的本质要求,因为人的灵魂被深深震撼而只能胡言乱语般呼喊时,只有音乐才能继续表达感情。……埃斯库罗斯,一位音乐家,一位合唱抒情诗人,却创造了因深刻的内心激动而触发的作品。……他所使用的手段具有音乐性—抒情性的特质。在埃斯库罗斯时代,音乐和抒情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言辞与音调、诗歌与旋律同时被创造出来。”[7]13简言之,古希腊戏剧是与抒情诗和音乐同源的,欧洲戏剧的起源须追索至其与诗尤其是音乐性抒情诗之间的密切联系。
当亚里士多德写作文艺理论著作《诗学》的时候,他所谓的“诗”指的是包括史诗、悲剧、喜剧等在内的所有当时以诗格写作的文类。《诗学》首章将该书的写作任务之一描述为对“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8]27予以探讨,这就明示了他重点考察的“诗”乃是“组织情节”的叙事艺术。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些叙事艺术既然通篇以格律诗体写成,那不管是否配以音乐或谱以曲调,都已因为格律的组织而使语言具有了一定的音乐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在整体上带有一定的抒情性。经过对几种不同诗类的比较,《诗学》最终将笔墨集中于悲剧,可见悲剧是亚氏心目中叙事艺术的最高代表。
古希腊悲剧一般都遵循“开场、进场歌、第一场、第一合唱歌、第二场、第二合唱歌、第三场、第三合唱歌、第四场、第四合唱歌……退场”这样的结构,每一场剧情表演中间都插入一段歌队合唱,用以发挥抒情的艺术功能。罗念生认为:“(古希腊)戏剧的合唱歌的风格取自抒情诗。所以,从继承的关系来看,戏剧乃是史诗与抒情诗的结合。”[9]抒情合唱的插入使得戏剧情节的展开具有了规律性的停顿,从而为整体叙事带来了行止交替的节奏感。不过,亚里士多德显然对歌队的抒情合唱不太重视,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在剩下的成分里,唱段是最重要的‘装饰’。”[8]65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只是把抒情唱段视作对叙事的锦上添花,他的关切集中于悲剧“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8]63,亦即纯粹叙事情节的展开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叙事伦理批评也仅仅着眼于叙事情节,依据他的价值评判,优秀的悲剧表现好人(具备智慧与德行的人)遭受不幸命运的情节,从而激起观众怜悯与恐惧的情绪并使之得到净化。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抒情段落的轻忽是令人遗憾的,这导致后世的叙事艺术研究尤其是叙事伦理研究很少关注作品的抒情成分。但所幸,美学史上也有对古希腊悲剧之抒情合唱的美学功能予以高度评价者,尼采和席勒便是个中代表。尼采曾在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用他那种广为人知的极端语调宣称:“悲剧从悲剧歌队中产生,一开始仅仅是歌队,除了歌队什么也不是。……用来衔接悲剧的合唱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孕育全部所谓对白的母腹,也就是孕育全部舞台世界和本来意义上的戏剧的母腹。……悲剧本来只是‘合唱’,而不是‘戏剧’。”[2]25-33这几乎就是在说,是合唱的扩展构成了古希腊悲剧,是抒情歌艺术孕育了戏剧艺术。如果有读者嫌尼采的用语过于夸张的话,那么席勒对古希腊悲剧歌队合唱部分的美学评价似应得到更多的信服:“它摒弃了事件的狭小天地,将自身扩大到超越过去与未来、超越遥远的时代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程度,推断出生命的重大归结,并宣告智慧的教训。除此之外,它还牵扯到想象的威力——牵扯到似乎以天神般的步伐攀登世界万物的顶峰的一种大胆的抒情自由;而且它是同曲调和节奏的所有明显的影响一道在语调和动作中产生了这种自由。”(4)席勒:《论悲剧中歌队的作用》,转引自乔治:《戏剧节奏》,张全全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73页。席勒的意思是,戏剧的剧情作为事件受限于其发生的特定时间与空间,而合唱则有一种特殊的美学功能,能将该事件所包含的生活智慧推广至超越时空的普遍层面,并产生“抒情自由”的审美高峰体验。在笔者看来,“抒情自由”的概念暗示抒情合唱中包含着重要的伦理维度。
通过文本分析不难发现,歌队的抒情合唱段落对于古希腊悲剧伦理内涵的揭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在《普罗米修斯》中,歌队扮演了一组剧中人角色——提坦神俄刻阿诺斯和忒堤斯的十二个女儿。女神的抒情歌声在与普罗米修斯对话的过程中唱出,不仅抒发了对英雄遭遇的深切同情,而且表达了鲜明的道德立场:
除了宙斯,哪一位神不气愤,不对你的苦难表同情?
现在整个世界都为你大声痛哭,那些住在西方的人悲叹你的宗族曾经享受的伟大而又古老的权力;那些住在神圣的亚细亚的人也对你的悲惨的苦难表同情。
那些住在科尔喀斯土地上的勇于作战的女子和那些住在大地边缘,迈俄提斯湖畔的斯库提亚人也为你痛哭。
那驻在高加索附近山城上的敌军,阿拉伯武士之花,在尖锐的戈矛的林中呐喊,也对你表示同情。
海潮下落,发出悲声,海底在呜咽,下界黑暗的地牢在号叫,澄清的河流也为你的不幸的苦难而悲叹。[10]
这些抒情之辞对宙斯予以道德孤立,对普罗米修斯则表达了来自神界、人类各种族,乃至拟人化的山川湖海等自然界万物的道义和情感支持,其内含的伦理评判随着抒情意象的一一展开而仿佛具有了充斥全宇宙的磅礴力量。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须让剧中的好人遭受不幸。然而如何证明并让观众充分感受普罗米修斯的德性之“好”?单纯依靠叙事性的念白恐怕有些苍白无力,此段抒情合唱则以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使观众对普罗米修斯产生强烈的道德情感,有力地保障了悲剧功能——引发怜悯与恐惧——的实现。
《俄狄浦斯王》的歌队扮演的是十五名睿智的忒拜城长老,他们一共出场合唱五次。进场歌被安排在开场俄狄浦斯得报忒拜疫情之后,用以描述男女老少受灾的惨状并向诸神发出祷告。这段抒情歌仿佛在急速推进的剧情中间插入了一幅相对静止的画面,通过对无辜平民受灾之苦的近景呈现来逼问引起灾异的罪魁祸首。之后又有四阙合唱歌,依次安插在剩余五场之间,其内容主要是对道德律令与神的关系、神的权威和公义性,以及俄狄浦斯德行高尚却遭受不幸命运的事实——上述几项内容相互之间显然具有强烈的伦理张力——做出评论和感叹。《俄狄浦斯王》的叙事情节具有步步紧逼、无可逆转的紧张和绝望,抒情唱段的加入,尤其是对神义论和宿命论等人生哲理问题的风格化探讨,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和消解了戏剧化叙事所带来的紧张感和绝望感,有利于观众暂时跳出情节推进的急流作一些感受与反思,从而调整和平衡已被激起的极端情绪。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情节的不断“突转”和“发现”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性,抒情成分则对由此引发的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予以“净化”。
相对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对抒情显然具有了更加自觉的形式安排,同时分派给它更多、更集中的伦理批判的任务。叙事艺术家对抒情的形式上的运用和语义层面的利用已经渐趋成熟。放眼更长的历史,将能看到古希腊悲剧在抒情伦理的表现方面实在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四、隐匿的传统
美国戏剧学者威尔森和戈德法布指出:“歌队是古希腊戏剧中的关键要素,也是最有特色的要素。自古希腊戏剧后,歌队再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出现过。”[11]不过在笔者看来,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仅仅是悲剧歌队的外在演出形式,而其内在精义,亦即抒情段落内嵌于叙事结构中并体现特殊的伦理关怀这一美学特点,则在后世许多叙事艺术中得到了继承和新的发展。
保罗·亨利·朗在谈及古罗马戏剧时指出:“在(古罗马)戏剧领域中,我们重又遇到希腊戏剧,但拉丁变种与其希腊前身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合唱被完全取消;罗马人只有独白或独唱。”[7]41他在谈及中世纪戏剧时又指出:“玛丽亚·玛格德琳(5)玛丽亚·玛格德琳即《圣经·新约》中的圣徒抹大拉的马利亚,为中世纪教会戏剧中的重要角色。的悲歌(‘悲伤咏叹调’)应被认为是(中古教会)音乐戏剧的中心。”[7]104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一种发展趋势: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戏剧逐渐以独白和独唱代替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部分。按照浪漫主义诗论的观点,独白和音乐性是抒情诗的两个核心要义。(6)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98-104页。在这一美学视野下重识古罗马与中世纪戏剧的上述发展趋势,可以认为,在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之间的漫长岁月里,欧洲戏剧逐步凝练和强化了其整体结构中的抒情歌段落。
16世纪晚期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阶段。莎士比亚是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戏剧作品继承了古代诗体戏剧的写作传统,不仅以有格律的韵文写成,(7)莎学专家孙大雨指出:“莎氏的戏剧作品,远绍古希腊、罗马戏剧诗人们的优良传统。莎剧是戏剧,同时又是诗,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韵文所组成,所以古时叫做戏剧诗,近今又叫诗剧,是戏剧和诗浑然一体的文艺作品。”孙大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诗剧》,载《群言》,1986年第10期,第34页。而且大量采用抒情诗和民间歌谣供剧中角色吟诵或演唱。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出现了三首十四行诗,其中两首分别是全剧的开场诗和第二幕的开场诗,以合唱(chorus)的方式提示情节,并对剧中人的悲剧命运及其社会原因予以伦理点评,其作用近于古希腊悲剧的歌队合唱;另一首则是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舞会邂逅时所吟诵的对白十四行诗,它以宗教比喻传达羞涩而热烈的爱情,是全剧最为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哈姆雷特》中出现了多个歌谣片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疯后的奥菲利娅所唱的几段歌谣。且看一例:
姑娘,姑娘,他死了,一去不复来;头上盖着青青草,脚下石生苔。殓衾遮体白如雪,鲜花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12]
这本是民间倩女哭情郎的抒情歌谣,痴情而凄美,在被逼疯的奥菲利娅口中唱来,却带有一种冷峻的隐喻的意味,仿佛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宫廷斗争予以审视和控诉,歌词中的死亡意象则以神秘的气息预示了《哈姆雷特》全剧的惨烈结局。
当莎士比亚在伦敦南郊的环球剧院大显身手的时候,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佛罗伦萨正在兴起一种新的叙事艺术形式——歌剧。歌剧(opera)与一般戏剧(drama)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叙事艺术形式,其戏剧性——此处以亚里士多德所谓叙事情节的“突转”与“发现”来定义这一概念——主要通过歌唱而非说白来呈现。(8)只有极少数歌剧和轻歌剧会用说白来推动情节。诚如美国歌剧学者科尔曼所言:“作为一种戏剧类型,它(歌剧)的本质存在无论在细节上还是在整体上都是由音乐的表达所决定。”[13]正是在这样的美学理念之下,歌剧发展出了主要以宣叙调和咏叹调的交替演唱来完成全剧进程的艺术形式。宣叙调(recitative)的意大利语源意为“朗诵”,是一种接近于日常说话的演唱,其节奏自由而富于变化,不构成有规律的节拍,乐句长短具有很大弹性,音调的旋律性不强,歌词也不押韵。宣叙调多用于角色间的对唱,其实就相当于被谱以音乐的对白,承担着推动叙事情节发展的功能。咏叹调(aria)的意大利语源意为“歌”,是以旋律性见长的抒情歌曲,其节奏往往规律有致,歌词也多采用押韵的诗体。除独唱以外,各种重唱采用的也都是咏叹调的形式,合唱也更接近抒情歌。于是,宣叙调和咏叹调的交替演唱,在美学上就构成了叙事与抒情的轮换。这种内嵌于叙事的抒情方式,隐然呼应了古希腊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抒情段落,无怪乎早期歌剧创作者都认为(实质是想象)他们的工作是在恢复失传已久的古希腊戏剧。事情正如保罗·亨利·朗所言:“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意大利歌剧先驱)至少看出希腊戏剧的抒情性质。他们猜测,不仅有歌队合唱,还有真正的咏叹调穿插在整部戏中,在感情高潮时,剧情变成抒情的夸张,因此需要音乐,犹如教堂的尖顶需要一口钟。希腊戏剧的根本性质的确是抒情艺术,其抒情性只有现代意大利的戏剧堪与之比美。因此,它被视为opera是可以设想的,因为‘opera’就意味着opera in musica,就意味着音乐,而音乐是抒情的同义词。”[7]344
咏叹调之所以成为歌剧中最有代表性的、被传唱最多的唱段,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整部歌剧叙事结构中专门用以抒情的段落,以优美的旋律集中体现角色的情感、性格,并反映创作者(包括作曲家与台本作者)的伦理意图。限于篇幅,本文仅举一例。
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是历史上演出率最高的意大利歌剧之一。它的剧情主要讲述日本少女巧巧桑(昵称“蝴蝶”)抛弃家族信仰嫁给了美国驻日海军上尉平克尔顿,然而平克尔顿抱着玩弄的态度,很快就回国与一美国女子再次缔结婚姻。蝴蝶在孤独中产下平克尔顿的孩子,并终于盼来了平克尔顿返日,孰料平克尔顿只是和他的美国妻子一起来领走蝴蝶的孩子。悲愤的蝴蝶蒙住孩子的双眼执匕首自杀身亡,孩子则留给了被罪恶感包围的平克尔顿。全剧的叙事虽不急迫却充满了戏剧张力,而剧中最享盛誉的一首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就出现在蝴蝶被平克尔顿离弃后在家门前的山坡上期盼和想象丈夫自海外归来的段落:
当晴朗的一天,在那遥远的海面,我们看见了一缕黑烟,有一只军舰出现,一只白色的军舰平稳开进了港湾,轰隆一声礼炮。看吧!他已经来到!我不愿跑去相见,我,不,我一人站在小山坡上边,长久地只向海面张望,期待着和他幸福地相见。看远处有一个人像小黑点,他急急忙忙奔跑,愈走愈近,奔向这边。谁来了?谁来了?铃木啊,你猜一猜,谁在叫,谁在叫?“我亲爱的小蝴蝶,你到哪里去了?”我一句话也不讲,就悄悄躲在一旁,我心在跳跃,满腔热情像火焰般地燃烧。他这样快活不停在喊叫,在喊叫:“我最亲爱的蝴蝶,快来我的怀抱。”这声音还是像从前一样美好,一切痛苦都忘掉。听吧,我的铃木!啊,我相信他一定来到,一定来到。[14]
歌词展开了一幅蝴蝶幻想中的图景,充满与爱人重聚的甜蜜、矜持、激动,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渴盼。然而承载着这些满怀希望的歌词的,却是一支忧伤、痛苦、绝望的旋律,通过戏剧抒情女高音(spinto sopranos)柔肠寸断的嗓音送入观众(听众)心田。歌词与音乐之间的矛盾对比蕴含着巨大的伦理批判力量,歌词内容表明了蝴蝶的善良、忠于爱情和对爱人的无比信任,而沉郁悲怆的音乐却分明在强调残酷现实之不可逆转,并预示着蝴蝶终将为爱情献出生命的悲剧结局。音乐与文学的两相对照,映衬出蝴蝶高洁的人格形象,也间接对平克尔顿的所作所为予以道德谴责。歌剧的叙事内涵也因着这曲咏叹调的独特的对比式抒情而更显丰富、立体。
歌剧咏叹调的抒情作用在现代音乐剧的唱段当中得到了更加通俗化的继承与发扬。兴起于19世纪的音乐剧(musical theatre)从艺术类型学来看与传统欧洲歌剧有很大差异。诚如上述,歌剧一般在音乐范畴中被提及,主要通过歌唱来展开叙事、呈现戏剧性。而流行于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则是从歌舞杂耍表演和滑稽歌舞杂剧中发展而来,同时接受了一部分轻歌剧的影响,最终定型为一种汇集了音乐、对白、表演与舞蹈的综合性剧场艺术,坊间常常称之为秀(show)。简言之,音乐剧往往因其演出形式的综合性而被划归戏剧领域。与歌剧相比,音乐剧采用对白来过渡叙事情节,其唱段则采用节拍相对稳定、乐句相对匀称、歌词押韵的抒情歌曲。这就好比取消了歌剧的宣叙调,而把咏叹调予以保留和转型——转型主要是从古典音乐形式转向更加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形式。通过这些手段,音乐剧极大地强化了在叙事结构中内嵌抒情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并把抒情的比重予以大幅增加。一部音乐剧中最具抒情风格的歌曲,往往也是剧中最能体现主角的人格形象、反映创作者的伦理评价的段落。如《歌剧魅影》中的《夜之乐章》、《猫》中的《回忆》、《艾薇塔》中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悲惨世界》中的《带他回家》等,莫不如此。
艺术史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又在音乐剧身上重现了古希腊悲剧那种对白叙事与歌唱抒情相轮换的基本结构,所不同的是,音乐剧在整体保留了较强叙事性和戏剧性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歌曲唱段的艺术自主性,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多元的抒情风格、展示丰富的伦理内涵,从而获得观众对叙事结构中的抒情段落的空前的审美专注。
五、小结
以上内容尝试对经典叙事艺术中的抒情段落作出伦理批评,并着重展示了一些高度戏剧化的叙事艺术在抒情方式和伦理寄寓方式上的某种历史性联系和呼应,论证了抒情段落往往是叙事艺术的“伦理之眼”这一美学判断。诚然,本文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能涵括历史上各种叙事艺术及其抒情伦理表现的复杂面貌,尤其是本文对整体风格趋于抒情化的那一派叙事艺术的伦理表现状况未予详解,这也更加说明,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批评尚有极大的可挖掘空间。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所倡导的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批评主要采取形式语义学的批评方法。这一批评方法的思想资源来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中欧人文主义批评传统。(9)“中欧人文主义”的提法出自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尤其是《乔治·卢卡奇与他的魔鬼契约》《美学宣言》《走出中欧》等篇。卢卡奇曾在他的一篇谈悲剧的论文中设专章讨论“诗性伦理学”,并指出:“形式是生活的最高审判者。赋形的能力是一种审判性的力量,一种伦理性的东西,而价值判断就包含在每一个有形式的存在中。”[15]根据这一批评原则,伦理内涵的积淀有赖于特定艺术形式的定型与成熟,换言之,艺术形式的变迁为新的伦理价值的探讨提供了可能。因此,叙事艺术的抒情形式每有新的发展,就为新的生活伦理的表达提供了契机,批评若能跟踪叙事艺术的抒情形式发展并充分解析其美学特点,便能够发掘出凝结于特定抒情形式中的特殊的伦理内涵。这就是叙事艺术的抒情伦理批评所采用的形式语义学方法。
当然,对于抒情伦理批评而言,方法论只是其实现手段,价值论评判才是它的根本目的。宋代学者郑樵曾批评汉儒以义论诗之失,指出“诗在于声,不在于义”[16],肯定了音乐亦即抒情审美功能在诗歌艺术中的首要地位。然而郑樵的诗歌美学主张需加上一段音乐美学的补充才能算是意义完整,这就是《礼记·乐记》中著名的对音乐艺术的抒情伦理论断:“乐者,德之华也。……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17]这段话说得再明确不过:音乐艺术是人心内在德性的外在形式显现,只有感情深挚,才能真正生发音乐艺术之华美,所以音乐的创作与表演须正心诚意,不可以为伪。换言之,抒情之所以为抒情,在于艺术家情深意切,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能诚恳而不加矫饰地进行艺术表现,否则,抒情就沦为了“煽情”“矫情”“滥情”——后者正是抒情伦理批评应在价值论层面予以重点批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