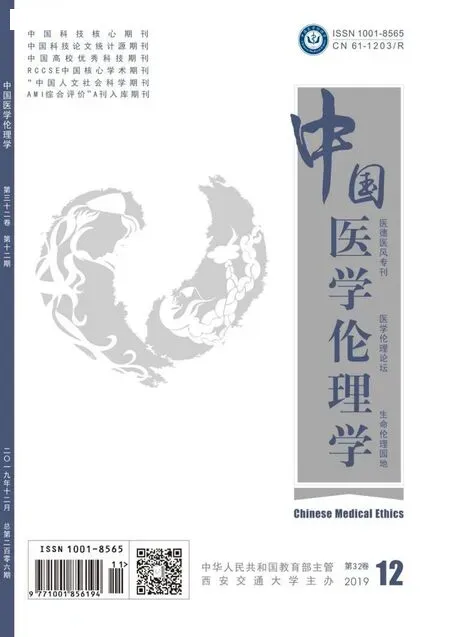尊严死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挑战及应对
黄玉莲,姚中进
(1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广东 广州 510450,779438461@qq.com;2 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尊严死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如果单纯从个人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对尊严死是认可的,许多人认为插管吃药对延长生命于事无补,即便现代医疗科技发达,依然有很多疾病难以有效治愈,最终依赖辅助设备延缓死亡时间,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对患者造成一种极度痛苦的感觉,即使采用先进医疗设备也无法摆脱真正死亡[1]。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亡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充满神圣,对于无法治愈的患者是尊严死还是“活受罪”,这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
传统孝道以生命长度为重。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尊严死,尊严死强调的是生命质量。由此,提倡尊严死势必会与传统孝道相违背,挑战“百善孝为先”的道德理论。这就使尊严死迫切需要法律的支持[2]。目前,我国已经成立生前遗嘱协会,但在提倡尊严死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
尊严死在我国并无明确法规支持,目前还处于建议阶段,这为完善和规范尊严死提供民意支持,通过快速完善相关法律,填补这一空白,才能使选择尊严死的人具备有力法律支持,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3]。
1 尊严死和孝理论分析
尊严作为人类属性,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及心理、情感、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孝道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具有“百善孝为先”的历史根基,“夫孝,德之本也”,这是《论语》中多次提到的孝,“首孝悌”成为衡量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标识。
对于尊严死,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尊严”被贬损,会使其丧失尊严,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方式,那么尊严死应该指的是在没有其他人干扰情况下发生的。换句话说,对于死亡这一问题,应在自然规律允许条件下主宰自己的命运[4]。当一个患者在有意识情况下没有提出合理要求,在生命终结前是否有人挽救,就与尊严无关;当一个患者在无意识情况下想要有尊严的死去,就应尽量按照他本人的意愿,以最大可能估计患者在清醒时可能会作出的选择,以此决定患者以何种方式度过生命最后的阶段[5]。然而,与患者无任何利益关系,以最大诚意帮助患者的人即为决定患者可以接受尊严死的人,想要准确找到这个人,只能靠约定才能达到大致合理性[6]。
目前我国大部分人心中所遵守的孝道就是:在父母健在的时候,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健康快乐;而在父母生命垂危时,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因此,即使子女意识到这将是父母最后的生存时间,即使充满了痛苦,也会尽可能延长父母生命,这就是人们传统意义中的“孝”。这种“孝道”从哲学角度来说,已经毫无尊严可言,无论患者是否被病魔折磨,依然想尽办法延长父母的生命,让最亲近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力,无怨无悔,大大满足了在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心理需求。因此,中国传统意义上对待临终患者大多数是关注患者在世的时间,而忽略了患者死亡的照护,这是导致尊严死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之间矛盾的重要导火索,尊严死的实施受到了阻碍,无法真正实施。
“约定合理”很重要,正是因为这种合理性问题,反映出了“传统孝道文化”与现代观念相违背的现象,对于尊严死问题上,逝者的尊严可能被误认为别人眼中“面子”。这种理解方式恰好与应有之义相反,因为没有考虑逝者的意愿是否在清醒状态决定的,所以具体谁对谁错还无法分辨。其实,将“尊严”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结合起来看,传统的“孝”就是要对父母好,而父母健康、幸福生活就是“孝”最重要的标识,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事,与刚才讨论的“尊严”概念基本吻合。
2 尊严死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与尊严死互不相容,可从患者视角和他人、社会视角两个方面理解。其中,从患者视角理解,当患者身患重病,无法忍受病痛时,患者选择尊严死,这是对自己受到病魔折磨时的宽恕,对患者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结果;从他人、社会视角理解,将健康基于为患者考虑而强行转变为临终者的想法[7]。对于哲学伦理学者来说,不能以“我的传统”思想作为辩证理由。否则,无法与来自不同传统思想人进行讨论,也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想要理解伦理观念是否被大众接受,需先看其背后解释是否存在问题,再对结果进行判断[8]。对于尊严死中伦理道德底线的判断具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确保尊严死是尊重临终者的意愿,防止另有目的的“其他人”以尊严死的名义加速临终者的死亡时间;第二种就是对患者死亡存在不可逆转的判断,在充分科学依据下进行。遵守这两条道德底线,对于尊严死制度的建议具有指导性意义[9]。虽然我们不能忽视传统孝道文化的意义,但却不能给予过多关注,避免发生“价值冲突”,但面对这种冲突问题,需采用实质性方案进行解决,因此,尊严死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2.1 患者视角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乐生恶死”,自然也成为人们的天性,“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指的就是人们对生命的重视,人人都应珍惜生命。无论生活质量高低,都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依据我国传统观念看重生命无可厚非,但忽略生命真正价值却是得不偿失的,这与尊严死倡导的尊重生命本身,又尊重生命价值是相互违背的。因此,“乐生恶死”观念阻碍了尊严死的推广。
2.2 他人、社会视角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健康长寿,然而当人们一旦知道自己亲人患了不治之症,依靠现代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时候,大部分家属都选择对患者隐瞒实情。他们主观上是保护患者,不想给他们造成太大精神压力,可以在生命最后历程中不用遭受精神折磨安然地度过。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实际病情,也就说不上自愿接受尊严死。因此,在选择隐瞒患者病情的家属面前,患者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选择尊严死的机会。
孝文化在当代中国传统上不断弱化,由此带来不可忽视的伦理后果,再加上孝文化观念是一种悠久历史积淀,这种强大的文化惯性,使尊严死在当代中国遭受实质性的挑战。作为患者家属的当事人,在理解尊严死时与其对他人、社会评价的关注是直接相关的。有些人考虑到舆论压力,而不敢提出对长辈实施尊严死或放弃治疗;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长辈的孝心,在长辈死后大办丧事,认为这就是孝,就是使死者死的有尊严等。这其中的某些理解就是对尊严死的误解。只有找到了当前对尊严死误区,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措施。
3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背景下的尊严死
传统孝道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也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当在新时代重新赋予理念。
3.1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
尊重父母长辈的意愿,尽心尽力赡养父母,并尽最大的努力让父母幸福安康,一直以来是备受赞扬的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然而,中国传统孝道中对父母的“尊重”,却是带着主观成分的尊重,当子女认为疾病的真相会对父母带来冲击时,子女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疾病的真相会伤害父母幸福安康的生活,进而对父母隐瞒病情,同时理解为这是对父母真正的“孝”。这种思想的产生,根源于子女对父母自主判断能力的怀疑,是对父母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剥夺,这是对父母自主权利的不尊重。
由于子女对父母这种权利剥夺现象已绵延数千年,早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一代一代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观念里,从而成为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继承于集体潜意识的习惯性行为,让所有中国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是正确的观念,并自觉去践行和传承下去。
3.2 在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践行尊严死
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重点在于尊重父母的基本权利,将主宰生命的权利交回到父母本人手中。当父母能够在自然规律允许条件下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就能回归到真正的“孝”中去,而这一点,就与尊严死的初衷契合了。可见,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尊严死是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的。
那么,如何进一步维护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与尊严死的一致性?
首先,在医疗环境中,需要制定相关的制度措施,保障患者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并确保每位患者的病情知情权,确保患者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主宰自己的生命,有选择尊严死的自由。
其次,目前医疗环境中子女对父母病情的隐瞒及治疗措施的替代决策,大多是因为在清醒状态中,父母没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自己病情的处理意见,从而让子女在面临决断的时候,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无法反映父母的意愿。因此,子女需要在父母清醒状态下,征求父母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及对自己未来生命状态的期待。唯有如此,子女在面临抉择时,才有机会作出最能够反映父母意愿的判断,也才有机会践行真正的中国传统孝道。在此过程中,父母的尊严死,也得以顺利实现。
4 结语
当然,子女与父母共同讨论父母的死亡,这本身又涉及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一大伦理问题,甚至可以归结为子女不孝的表现。这其中涉及中国语言中的隐含意义和惯性推断,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归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真正的“孝”,让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与尊严死握手言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