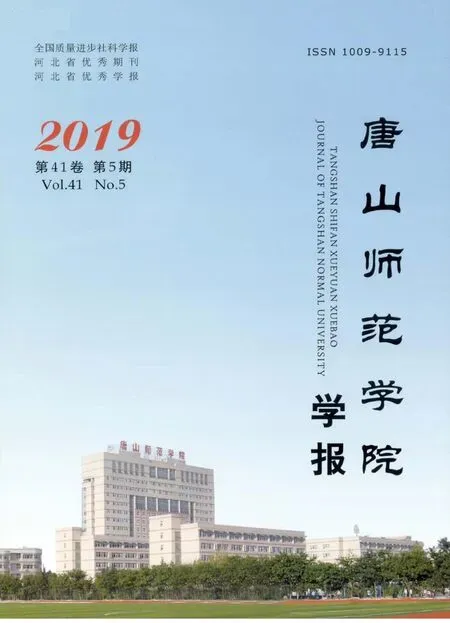生命的律动
——《边城》的音乐性分析
包絮云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声音是具有空间感的能量,而作为声音之一种的音乐以其频率震动的规则性、旋律感获得了更强的空间塑造能力。运用想象,音乐艺术能建构出空间情境。这种空间情境的建构与小说文学艺术有共通之处。作为美的一种形式,音乐不仅能够表达情绪的流变,在套曲、歌剧、以及大型交响乐当中也能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正如阿多诺、维特根斯坦等人既是音乐人,也是哲学家,米兰昆德拉既是音乐鉴赏者,又是小说创作者。对于能随笔进行涂鸦风景创作的沈从文,对音乐艺术的爱好是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沈从文酷爱听西方古典音乐,也在音乐当中寻找精神寄托,寄寓情感。音乐、自然与美陪伴了沈从文的一生。
沈从文对音乐、艺术的喜爱,与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密不可分。他认为真实存在的生命应当符合更高层面的抽象形式,而这种抽象形式属于美。沈从文热爱生命,他认为在时间长河里绵延不断的生命,也将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不断往深刻、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美则存在于生命之中。沈从文尝试用自己对音乐和艺术的感觉进行文学创作,以独立个体诗意栖居的方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画卷当中书写了有情的人生,也正因在“事功”与“有情”当中的人生选择,使得他与同时期的创作者相较,获得了更有韧劲的生命力。
作为其代表作之一,《边城》借鉴和参照了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表达形式。显性的音乐要素大量贯穿其中,充满湘西民族风情的山歌、船歌,男女青年的对唱等,有些部分甚至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隐性音乐要素,作为一种抽象的抒情意识,成为勾连《边城》精神内核的部分。这种抒情意识也是使《边城》富有诗画、诗意特征的原因。这种抒情特征以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为基础,以各种人物、山水、风景的意象构成能指,而能指所对应的所指则面向了无言的、形而上的生命体验。《边城》的音乐性要素不仅体现在语言外壳的音韵之美、叙述方式的“凝滞”与“流动”、故事情节的内容推进、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中,更深层的是体现在了《边城》形而上的精神意旨里,这也正是对生命、艺术与美的深沉礼赞。作为乌托邦与桃花源、供奉人性小庙的《边城》之所以仍旧具有不断被认识的传世价值,正在于其无言的所指具有多角度的阐释空间,音乐性要素的使用正使得沈从文的《边城》创作获得了通透与灵性。
一、沈从文与音乐的缘分
沈从文与音乐有着深厚的缘分。虽然他并不弹奏作曲,但其家人和朋友却有着极高的艺术品味和造诣,无形间为他营造了音乐艺术的生活氛围。旧友王际真学乐,沈从文在给他的复信中提到,“我奇怪得很,顶喜欢提琴,以为非常动听”[1,p39]。1946年在《大公报·文艺》,沈从文也为张兆和三弟音乐家张定和作过《定和是个音乐迷》等有关的散文。
在其侄子黄永玉对沈从文的回忆中,沈从文曾提出过自己对音乐的见解。音乐具有连接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能力。正如张新颖所言:“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2]沈从文对音乐的认识同对人生的理解有共通之处,“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3,p24]沈从文敏锐地抓住了一切艺术本质上的联系,以理性的形式表现人感性体验到的外在世界和社会人生。“一切好音乐都能把我引带走向过去,走向未来,而认识当前,乐意于将全生命为当前平凡人生卑微哀乐而服务”[3,p24]。音乐作为与文学有互文性的要素,对沈从文的影响,本质是以一种生命的节奏与律动形式,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沈从文抓住了所有借符号的形式表达人思想情感的艺术本质,还原真实的生命体验,乃至形而上地抽象出宗教式的恒久魅力。在散文《烛虚》篇中他提到:“我不懂音乐,倒常常想用音乐表现这种境界。正因为这种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4,p24]
音乐所能营造出的境界,对沈从文而言,是一种宇宙人生的感悟与体验,他认为这种体验难以用语言说明,但借用音乐的感觉,却常能表现出“抽象美丽”的印象。在《七色魇集》的《绿魇》当中,沈从文将眼前所见的层次不同的绿色,与乐律联系到一起。沈从文并不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他想表达的是“在这个境界中时,似乎人与自然完全趋于谐和,在谐和中又若还具一纷纷突出自然的明悟”[4,p138]。音乐所煽动的情绪,它的旋律和节奏所营构出来的境界,是能捕捉到沈从文在大自然徜徉中的生命观感的。
沈从文向往和追求形而上的永恒之美。这种永恒之美,沈从文曾尝试在音乐当中寻找。沈从文对古典音乐大师的喜爱,有一种对永恒与抽象、不死之美的追索。他曾在散文中多次提到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在《潜渊》里,他写道:“如由莫扎克用音符排组,自然既然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4,p26]在精神痛苦之际,沈从文也寻求音乐的精神疗救,以洗净极端浮躁不安情绪。在《绿魇》中,他说:“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够了。”[4,p151]莫扎特的音乐,尤其是小奏鸣曲,节奏轻快,旋律干净,在弹奏时需要十足的技术稳定,才能给人以轻盈飞动之感。巴赫则是极端的整饬、平衡和程式的严谨。沈从文在音乐中寻觅精神寄托和信仰,“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5,p56],也在音乐中获得启迪和教育。
沈从文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范围十分宽广,除了西方古典音乐,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的创作之外,沈从文出生成长之地湘西民歌,亦给沈从文带来了巨大影响。沈从文早期为湘西民俗风情的保存和传播做了一些工作,他整理了50首湘西的民歌,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沈从文小说创作也受到了湘西民歌的影响。在《看虹摘星录后记》当中,他提到这几个短篇小说创作所尝试的新方法:“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6,p224]《看虹摘星录》合集并未出版,但沈从文的《摘星录》借用了与音乐创作相似的灵感。“用人心人事作曲”,人心人事是构建小说的材料,正如音符是构建一首曲目的物质材料。串联起音符使其成为旋律的是一种和谐整饬的规律。在叙事学层面上,音乐元素的加入使得故事节奏静止与动感两者相辅相成。如沈从文在《摘星录》中提出的“人心人事”,看似散漫无章,而内部却也有其心理变化和流动的逻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总有诗化、散文化的倾向。其串联起人物事件的内在逻辑,实际突出了感性体验理性显现的音乐化创作取向。除此之外,音乐的元素大量进入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对于像《柏子》《三三》《萧萧》《边城》这些书写湘西风情的题材,小说中总有善于唱歌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而言,唱歌成了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甚至推动了小说叙事情节的演进。
二、《边城》的显性音乐元素
1949年,作者在精神病苦之际,在《从悲多汶乐曲中所得》里说到:“音乐实有他的伟大,即诉之于共通的情感……它使我明朗朗反照过去……《边城》第一行如何起笔,凡事都在眼底鲜明映照。”[6,p216]在《边城》当中的音乐元素,分为显性的与隐性的两种。显性的音乐元素,是指作为书写内容进入小说的音乐要素,这些要素在《边城》当中得到了大量运用。首先是自然的声音。受到湘西自然风土的浸染,沈从文非常善于把握住自然之间的音乐。“大自然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留下的是处处充满天籁般素朴空灵的画面和声音。”[7]在对边城的情境描写之中,自然的声音无处不在,山间黄鸟、竹雀、杜鹃的鸣叫是整部《边城》的交响乐细部。
其次是人为制造的声音,一切自然植物像是皆可奏乐,成为一样专门的演奏乐器,祖父和翠翠闲时就用小竹作竖笛双管唢呐等乐器制造声音,翠翠甚至可以摘一根大葱吹吹唱唱。而在渡江的时候,祖孙两人听歌,而自己也互相唱和的民歌,则以文本凝固的声音形式进入了《边城》。
《边城》中的人物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翠翠不仅爱听歌,自己也爱唱。翠翠所唱的民歌,体现了湘西民歌艺术的风情,也若隐若显现地暗示了翠翠的心声。唱歌的情节多次表达了她朦胧的感情,而这种情感表达不仅只显示在翠翠一人,翠翠曾多次请求祖父为自己唱歌,在祖孙两人的和歌当中,也可以看到祖父的心境变化线索。第一次两人和歌,祖父十分地快乐。慢慢地,翠翠有了心事,祖父也有了心事。翠翠再请祖父唱歌,祖父则再也不说话。二老为翠翠唱歌之后,翠翠听不到那样的歌声,于是祖父为翠翠唱的十首歌,既是爱怜,又是安慰。湘西的民歌对唱是湘西人文风情的重要部分。在《边城》小说中亦反复地出现。翠翠独唱、祖父独唱,祖父两人对唱,沈从文都采用了直接的正面描写。而二老为翠翠所唱的歌声,则采用了翠翠的梦境进行烘托的形式。
歌声是《边城》当中意蕴复杂的意象,也是构成《边城》艺术之美的重要因素。唱歌是边城的风俗,而歌声是情爱的象征。中秋前后,因月色而起,男女整夜地唱歌,如水手和吊脚楼上的妇人,歌声停止,正因为情爱的约定。歌声也是不息生命力的象征。翠翠的母亲极爱唱歌,翠翠父亲则是城里唱歌的好手,在歌声当中唱出的翠翠,则是天真浪漫的艺术之子。歌声也更是某种纯粹永恒神秘境界的象征。在《边城》当中出现过许多的声音,而最为梦幻的歌声,则是唯一一次出现在翠翠梦里的那种声音,沟通了自然与美。沈从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描写了二老的歌声。二老的歌声让翠翠拥有了灵魂轻轻漂浮的甜美梦境,以及在梦中摘了一把虎耳草的故事。但翠翠梦里的声音,却又不完全等同于现实当中二老所唱的歌声。翠翠梦境,应该是说是二老的歌声和翠翠自己的性灵所共同创设而成的结果。在无数山光水色、自然风物和甜美的歌声孕育中,天真而无忧虑的翠翠本身,也成了爱与美的艺术形象。
作为主人翁之一的翠翠,本身就显示出了音乐的特质,音乐赋予了翠翠自然活泼如小兽一般的天性。翠翠最后的一次歌声,十分意味深长。此时的老船夫还未曾预感到自己的死期,然而却因为翠翠的事生了心病。作者没有写翠翠的忧虑、担心,却写到翠翠心中古怪的快乐。翠翠为这份古怪的快乐,唱了许多许多歌。难道翠翠真的是如此的不懂事,不孝顺,没有发现祖父的不同往常?有意味的地方,则在“古怪”二字之上。实际此时的翠翠,自己已经隐隐地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别离。爷爷为翠翠唱歌,象征着爷爷对翠翠的守护和爱,而此刻祖父再不能为翠翠唱歌,翠翠则赌气似地自己唱起来。翠翠不通人事,游离尘世之外,沈从文借翠翠的人物形象,寄托受到伤害却依旧以美、音乐和艺术作为抚慰的心灵。这种“古怪的快乐”只是用快乐的方式去表达情感,本身则是悲伤的一体两面,是一种伤怀之美。沈从文着力刻画翠翠似乎处于蒙昧的、一无所知的状态,而这也是翠翠的灵性所在。正如王德威等学者所言的“无言的世界”,翠翠那性灵的精神世界,是没有清晰所指的,所指在朦胧的爱情上轻轻地划过,又指向一片虚空。只是老船夫的死亡必将结束这样的蒙昧,灵魂在空中可以轻轻漂浮的翠翠也必将真实地走向现世与生活中。在《边城》结尾处,翠翠的哭泣可谓对灵性的告别,亦是承受真实生活所带来的所有幸与不幸的开始。谭文鑫用奏鸣曲式分析翠翠和老船夫,分别是主部与副部的两条线索,独立而又相互交织,最后统一为一体[8]。而翠翠和老船夫这两条故事线索,并不仅只是言说爱情和质疑爱情,在叙述爱情之上,沈从文设置了一个深广的玄思空间。翠翠承担了向完满的精神世界漫溯追求的任务,而老船夫则要为翠翠考虑到世俗和生活本身的法则。于是祖孙两人成了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彼此能交织、融合的叙述走向,也显示出了《边城》的复调创作特色。
《边城》的小说创作,与歌剧《蝴蝶夫人》有着广义的互文联系。克里斯蒂娃曾提到文本空间的对话关系,其中分为横向轴与纵向轴两种,纵向轴直涉内部和外部的跨文本[9]。1949年沈从文谈到:“十分钟前从收音机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悉又陌生过程中。”[5,p42]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讲述的是一位日本女人乔乔桑等待离去的美国海军丈夫克尔顿的故事,而歌剧最后以克尔顿的负心和背弃走向了悲剧结局。在《蝴蝶夫人》当中最著名的唱段是女高音咏叹调《晴朗的一天》,这首曲子展示了女主角对丈夫归来的期待,明亮而又略带温柔与哀愁的声音,与流水般的钢琴伴奏相和而构成感人旋律。女主角面对大海,幻象着丈夫归来的幸福场景。而在《边城》当中,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人,也构筑了翠翠等待的幻梦。如果说等待是《蝴蝶夫人》与《边城》相似的主题,强烈的抒情以迷雾般的特质形成了笼罩文本的幻境和氛围。作为文学文本的《边城》,则展现出了东方古典气质的恬淡优雅。“边城正是沈从文把音乐和自己的文学天赋相结合,打造出来的经典之作。”[10]
三、隐性音乐元素:生命律动与息声寂静
《边城》的隐性音乐元素,指的是小说在叙述方法、叙事结构以及思想内容上运用的音乐要素。音乐对《边城》有更深刻的隐匿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沈从文对人间事物的敏感以及对艺术的造诣。俞人豪提出,在音乐当中,随着音响的变化,听众可以将音乐的律动具体化,甚至构成视觉空间的审美效果,这种处理具备个性的情感特征,结合剧目表演的音乐,也能承担表情叙事的功能[11]。作为沈从文文学最高水准之一的《边城》,是一篇音乐化的小说,而音乐化创作倾向是沈从文有意为之的。《边城》的创作,是沈从文年轻时人生感悟的积淀,他借用文字的形式加以表达,而有意识地使其显示出画面感和音乐性。1949年在其宣告封笔的自传性信件《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沈从文曾提到自己对批评家评论《边城》《三三》的看法:“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3,p25]而《边城》的创作,最后又促成了沈从文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在创作《边城》之后,《边城》的文学文本又成为他欣赏自己家乡音乐的一个互文要素。1956年沈从文重游湘西,曾在吉首苗族自治州听到过这样的苗族歌声:
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的杰作。[12]
一老一少,年纪已过70的歌师傅和17岁的女孩子、深厚的感情和清朗的声音,正像他《边城》里的祖父和翠翠,这种原型形象也许影响到了《边城》的创作。
《边城》叙述的隐性音乐要素之一,是句法上的循环往复之美。曾峰曾详细分析了《柏子》前二段和末尾段句式句法上的音乐性元素,这种分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法结合到一起,显示了艺术之间的互文效果[13]。这种音乐性的句法要素在《边城》中同样随处可见。《边城》的开篇,正如几个极孤单又简洁的音符,而时间又绵延得极长: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狗。[14]
整段没有一个铺张的形容词,而是重复使用了“一”这个数量词。叙述视野由广阔的背景逐渐往内聚焦,最后定格在白塔、老人、女孩子和黄狗身上,而都是独有一份。“一”的世界是孤独的,但也是完整的。《边城》开篇就显示出一种完整简洁的气氛,而量词的反复出现,又形成了句法上一种循环往复的音乐美感。同时,音乐性的构成并非只是简单的字与词运用上的重复。在叙事的文字系统当中,必须掌握重复时间隔的节奏,以及在往复中的变化。
除了句法之外,《边城》的篇章结构,也借鉴了音乐艺术的表达手法。谭文鑫从《边城》的篇章结构入手,分析其与奏鸣曲式结构的相似之处,《边城》以“人事”为旋律,模仿了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结构[8]。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时,是否自觉模仿了西方古典音乐作曲编创的结构范式,有待商刍。但《边城》当中的循环结构是存在的,尤其是小说当中的叙事时间,特别能显示出叙事的循环质感。小说一共写了三次端午节日,而每次端午节日,都对下一次端午节日做了铺垫和渲染,故事也如河流般向前流淌,不断地发生变化。第一个端午是鸟瞰式的边城盛况介绍。紧接着,沈从文以“端午又快来了”,马上开始书写第二个端午。但第二个端午节日发生前夕,沈从文写了翠翠回忆的端午,也就是“两年前”,与二老相见的第三个端午。沈从文借端午这一民间传统节日作为不变的联系点,而故事情节则不断发展,又从新的端午开始。在这两年间,翠翠与二老并未曾见面,而大老则找人送了肥鸭上门求亲。两年之后,在现在的进行时态,所有人物交结于此,沈从文则刻画了一个最为浓墨重彩的端午,所有人的情感、愿望、理想、回忆,都浓缩在了现在进行时态的这个端午节日里。祖父回忆起了自己的女儿,翠翠的母亲与军人之间的事,为翠翠的感情线索埋下了相似的伏笔。而翠翠则在这一天见到了碾坊姑娘,碾坊姑娘带着她的陪嫁,想和二老结亲。在第二个端午节,大老、二老对翠翠的感情都浮出水面,故事逐渐地热闹沸腾。在端午结束之后,则缓慢呈现出平静哀婉的调子。沈从文谈到他的创作:“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乐曲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溶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3,p25]《边城》的人事设计、舒缓而流畅的故事节奏感,正来源于沈从文用音乐的启示在行文当中的运用。沈从文将“叙述”和“发展”两种笔调相互糅合,湍流奔赴处是情节不断发展,人物的情感错综复杂,矛盾集中交汇的地方。而一泓静止处,则是将叙述之笔暂时地缓慢悬空,写出生活的纯真样貌和牧歌般的美好情调。在《边城》里,翠翠看云、看月,听鸟声,等待梦中的歌声都并非闲笔,而老船夫上城里买肉,为渡船的人送药,互相交换礼物也是如此。《边城》的叙事节奏,如云散又聚,也如水流奔腾又止,非常自如和酣畅。
《边城》的最重要隐性音乐元素,是抒情特征,这种特征显示为沈从文“用人心人事作曲”、打通文学与艺术隔阂的尝试。杨义曾说,沈从文组织文字,力图把感情渗透到形象中,柔而不媚,朴雅而不艰涩,体现一种音乐的节奏感和生命的律动[15]。沈从文试图以音乐的方式表达某一种生命体验,也即赋予这一种体验以形式,虽然这种方式有点‘古怪’,但在这种‘古怪’之间,透露出的正是生命的某些不可言说的状态[16]。正如巴赫、车尔尼等人的音乐创作将孤立的音符进行某种结构进行联结一样,沈从文如何讲述“人事”,并使人心人事可以成曲呢?强烈的抒情性是黏合人心人事的重要要素,抒情的特质沟通了沈从文《边城》创作与音乐之间的桥梁。抒情是《边城》无所不在的书写笔触。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城中的风俗、节日,自然风光,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抒情意味。
极度丰富的声音有时会显示出完全的静谧之感。可以说,静谧也是一种声音。在《边城》当中,除了声音,还有没有声音的绝对寂静。这种寂静氛围本身也强调了音乐性的存在。1980年初,《边城》要改拍成电影,在致徐盈的信中,沈从文曾提到对主题曲的理解:“至于主题歌,我怕我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17]《边城》的音乐性则在没有声音的寂静当中得以体现。寂静是作者所要营造的氛围,给美好的边城风光罩上了一层寂寞之冷色,而也正因寂静,显示出静止的时间凝滞之感。时间凝滞之时,又正好突出了空间边界。在这样的处理下,《边城》就构筑了一个封闭、稳固却又辽远美好如诗的“希腊小庙”,时间的凝滞显示也正是沈从文所想追寻的永恒境界。庄子《齐物论》篇当中提到,南郭子綦与子游交谈,曾提到天籁、人籁、地籁之别,而“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各色各样的声音构成无数具有特色的交响之乐,然而最为广袤辽阔之声音,则是“大音息声”[18]。“大音息声”是中国式的美学理想。而在《边城》当中,白塔、竹林、小溪,渡船,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都是中国式的,冷色调的寂静氛围,也是中国传统当中的美学风格。正因其更容易沟通“玄之又玄”的境界。寂静强调了人对自身的关照,从自身出发,又能投射到万事万物之中。然而极度的静中又喧腾着无数声响,在静匿的氛围里蕴藏着无数的动。沈从文在《边城》当中所写的动是与生命力有关的律动。边城的风俗民情,人的思想情感,自然风物和山川,无一不是生命律动的体现。这种生命力的律动离不开作家本人对生命和对生活的热爱。在创作《边城》期间,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并给张兆和写信,最后以《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得以出版。对故土山川风貌的感受,成为沈从文书写《边城》的直观材料:“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1,p188]
在抒情的基础上构成的边城,与现实人生拉开了距离。在其创作的20世纪30年代,这种风格的短篇小说是当时文学板块当中的异类,而与在国外出版和翻译的不断热门和升温相反,之后和其他创作一样《边城》也受到了冷遇。沈从文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而选择走向“瓶瓶罐罐”“花花朵朵”的服饰和文物研究。正如他自己60年代初所写的《抽象的抒情》中,“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起不了什么作用的”[19]。沈从文否定了抒情所能带来介入现实人生的积极可能,而这正实际说明了他在创作之时,借用抒情进行对人生社会的介入和改造的企愿。《边城》所创造的湘西境界越是美如桃花源,就越说明沈从文个人感受到了现实环境的严峻与痛苦。沈从文用抒情的方式,创造了《边城》当中的双层乌托邦,是乌托邦里再套着的乌托邦。《边城》讲述的并非是一个美好的恋爱喜剧,当中有许多悲哀的裂隙。如翠翠的恋爱、大老的死亡和老船夫的死亡等等。《边城》的第一层乌托邦代表了边城实质的人事和生活,而它的纯朴和快乐之中又潜藏着残缺与悲哀。在这样的乌托邦里,沈从文则借翠翠这个角色,用抒情的挽歌笔调埋藏了另一个“无言”的乌托邦,这个“无言”的乌托邦固守了“对内”的法则,它是无言的,也是永恒的,实质显示出了在个人存在和个性意志当中抒情具有的独特价值。而这种抒情性也是音乐性的重要标志。
四、结语
《边城》有这样一段:在一片朦胧的月色之中,祖女二人临江而坐,等候二老的歌声,翠翠问爷爷第一个做小管子这样乐器的人是谁。这个创作《边城》的人,正是以“做小管子”的方式介入了《边城》的世界。《边城》是沈从文在孤独的内心深处塑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边城》作为一个镜面,反照出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沈从文自身所感应到的并不美好的社会现实。尽管《边城》具有封闭的空间感,却在时间上显示出了无限开放的姿态,那个在小说结尾里永远不会,或者明天就回来的人,代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不确定,也显示出沈从文对时间线索的关注。强调空间场域感,却在时间线索上无限绵延,不断变化,这正是音乐所具有的特性。《边城》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独特的异响存在,而如今再三地进行阐释,其价值正在于沈从文用了音乐性、艺术性的方式进行文学表达。表面上看,《边城》的叙述内容有大量的音乐元素,叙述结构也模仿音乐回环往复,静动结合的特质,而就其所要阐释的内核而言,《边城》创作对音乐的模仿,是一种对艺术生命的美的敬礼,整部作品也像绵绵不尽流淌的长河,自然、酣畅,代表着对精神世界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