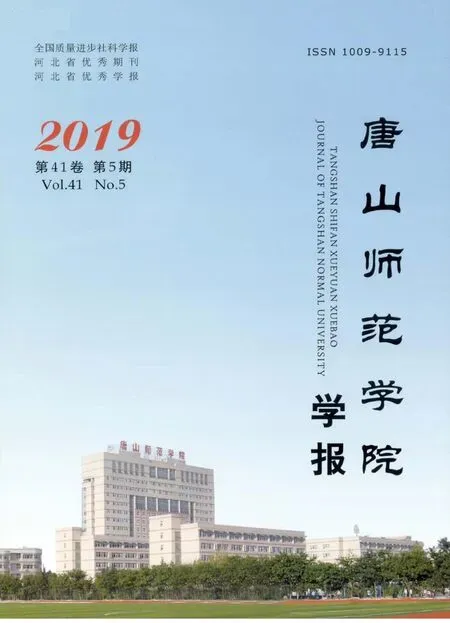性格悲剧理论下的贾宝玉和哈姆雷特
刘利斌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山西 太原 030006)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古希腊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一生著述极丰,以知识的广博著称,以擅长“驾驭”学问闻名,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则称其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他的《诗学》开启了西方悲剧理论的先河。贾宝玉和哈姆雷特这两个中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悲剧人物,虽个性迥异,但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妙笔下,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性格悲剧理论,比较分析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探究悲剧命运之缘。
一、亚里士多德的性格悲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从古希腊高尔吉亚、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前辈手中接过丰厚的诗评遗产,创作出西方悲剧理论的发轫之作《诗学》。“《诗学》立论精辟,内容深刻,虽然篇幅不长,但气度不小,无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大家之作。《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1,p7]在《诗学》第6章到第19章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概念并分析了悲剧的成因和要素。“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p6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通过模仿、表现和旁观等活动,不仅可采用模仿他人来了解对方,也可通过把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来或者旁观,传达给他人并获得对他人的理解,达到交流、沟通并形成共识[2]。他认为“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1,p64],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而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1,p65]。在批判地继承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创新性地提出悲剧理论,对后世悲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悲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作为诗学的一个分支而备受文艺理论家们的关注。”[3]“无怪《诗学》雄霸文艺批评史上二千余年,无怪后世批评家奉《诗学》为金科玉律。”[4]
纵观中外历史,人们对悲剧的成因有多种不同解释。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说”,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戏剧,把悲剧的形成归于命运的主宰和捉弄,因此被称为“命运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过错说”(hamartia),把英雄人物受难归于自己看事不明,由于自身某方面的缺陷而犯的“错”,“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角自身的过失造成的,而不是什么传统的命运观念和因果报应观念”;黑格尔的“伦理观念冲突”,通过分析其推崇索的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指出悲剧是两种伦理观念的体现者对立斗争而形成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则可概为“性格悲剧”,主人公矛盾偏执的性格是悲剧的主要原因,而性格上的缺陷成为他们致命的弱点,莎翁形成自己独特的悲剧观,写下脍炙人口的四大悲剧佳作。在我国浩瀚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同样涌现出震撼人心的伟大的悲剧杰作,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贾宝玉形象。性格冲突是情节性的悲剧作品中悲剧形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在亚里士多德性格悲剧理论视域下,着力比较“衔玉而生”的贾宝玉和“重整乾坤”的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
二、贾宝玉与哈姆雷特性格悲剧之“疯癫”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金玉缘》)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首,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巨著。作者以核心人物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为视角,描写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家族由盛转衰的悲剧过程。《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和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小说中“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5]贾宝玉成为后人争相研究的悲剧人物形象。《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601-1608年是他创作的成熟时期,也被称为“悲剧时期”,莎翁的戏剧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艺术的最辉煌成就,其作品被公认为“受欢迎的圣经”,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人物成为世人耳熟能详、无可复制的悲剧形象。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把貌似平常的丹麦神话故事酿成一出无与伦比的人类精神悲剧,赋予哈姆雷特“橡树栽在花瓶里”的鲜明生动的悲剧艺术形象。“疯”是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同质特点:贾宝玉“头上带着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6,p2],但在世人眼中他往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哈姆雷特则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前装疯卖傻,复仇之路上内心充盈着对人生意义的疑惑与苦闷。
贾宝玉出生于中国封建制度颓废飘摇之际,贾府经历过“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鼎盛繁华,承载着“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6,p2]的辉煌赞誉,在宝玉成长时,“荣宁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6,p17],尽管如此,贾宝玉在贾府罹难沦落骨肉分离之前,一直保持着不谙世事的“孩童”形象,流连在大观园里姐妹们的裙衩粉黛之中,疏于达官贵人间的往来,“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6,p233]。当贾府难挽家道衰落的末世之势时,宝玉作为嫡系子孙成了振兴贾府的希望,背负起生命无法承受的重任。但宝玉离经叛道、厌读四书、鄙视科举、追求爱情、向往自由,其父贾政怒其不争:“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其母王夫人向黛玉介绍他时也说:“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6,p36]贾宝玉被叱为蠢物,笑为痴傻,在世人眼中,他不忠不孝、又疯又癫,实则是自身崇尚“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如果说贾宝玉是封建礼教下的“真疯”,那么哈姆雷特“装疯”,则是在父王神秘暴死、叔父弑君篡位、母亲匆忙改嫁、亡父显灵现身时被迫寻求的自我保护。在危机四伏、邪恶黑暗的环境下,哈姆雷特内心充满了矛盾,只有用“装疯”斡旋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完成保护自己、铲除奸王、替父复仇的神圣使命,即使在心爱的奥菲利娅面前,他也只能忍受着孤独而活在疯癫的面具下,他面容憔悴,身体瘦削,一袭黑衣,衬衫领口敞开,头发“乌黑”“散乱”地贴在前额。哈姆雷特意识到“丹麦是一所监狱”,意识到“时代整个儿脱节了”,而父亲的复仇命令,自然升华为“重整乾坤”的重大历史使命[7],“复仇”注定了哈姆雷特通向毁灭的人生悲剧,“装疯”诠释了哈姆雷特难以救赎的性格悲剧。面对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人生困境,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殊途同归地让他们进入“疯癫”状态,最终突破了敬畏命运的界限,分别在出家循隐、复仇自杀的极悲之中感悟性格悲剧的凄凉与至美。
三、贾宝玉和哈姆雷特性格悲剧之“软弱”
贾宝玉和哈姆雷特都出身显赫,或许也可称为当世的“独醒者”,但他们的反叛行动却都不那么干脆彻底,显现了他们软弱的性格特点,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逃离也无法融合的、或皈依或死亡的悲剧结局。贾宝玉“衔玉而生”,是“姐妹堆里厮混出来”的孩子,从小锦衣玉食,上有老祖宗宠爱,下有丫鬟伺候,无论相貌还是性格都多了些阴柔之美,少了阳刚之气。尽管他并不认同和抵触封建士人的志趣,但他的反叛不自觉也不坚定,仅仅停留在萌芽阶段。他厌烦充彻在荣国府中的世俗与丑恶,却又留恋大观园带来的快乐和逃避。他虽有求真扶善的纯洁天性,却疏离和漠视下层人民的疾苦,无法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这种对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的双重游离,使他的形象不完满却真实,充满了令人惋惜的悲剧色彩。”[7]
悲剧主人公自身性格缺陷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哈姆雷特虽贵为丹麦王子,但骨子里渗透着顾影自怜的软弱。他在著名学府受过人文主义教育,满怀着美好的人生理想,当他学成归来却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惊骇巨变:父亲莫名暴死,母亲乔特鲁德急于嫁给叔父克劳狄斯,昔日朋友罗生克兰和盖登思邓不再亲密无间,心爱的姑娘奥菲利娅似乎貌合神离等等。在悲恸孤独中,当听到亡父之灵的倾诉时,当发现叔父弑兄、篡位、霸嫂的真相时,他虽有匡扶正义的雄心,但软弱的性格让他总是思考、寻找报仇的内在逻辑,屡次错过了动手的最好时机。他无法当机立断地肩负起复仇大任,也成为他不能挣脱痛苦的阶级束缚[8]。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软弱的性格导致了自己的毁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哈姆雷特才拼尽最后的气力将毒剑刺中克劳狄斯,完成了复仇使命。
四、贾宝玉和哈姆雷特性格悲剧之“犹豫”
“在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人生之途中,都有一个洋溢着爱情光辉而又凄惶无助的女性形象,在令人心悸中走向毁灭,这无疑更加深了两位男主人公生活的悲剧意蕴。”[7]在追求爱情的问题上,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犹豫不决。林黛玉是《红楼梦》颇具病态但独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深蕴在内心的性灵光辉。贾宝玉虽自小厮混在众多姊妹之中,却独爱寄人篱下的黛玉,即使在失玉变得呆傻时,他“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6,p387]。黛玉虽因家道中落,寄居在纸醉金迷的富贵人家,却轻怠功名利禄并嗤之以鼻,这恰好与宝玉心灵相通成为知音。她爱宝玉,不惜拖着体弱多病的躯体,在郁郁寡欢的生活中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她似乎看到封建家族对宝黛之恋的不屑与压制,看到封建联姻对宝黛结合的不容与排斥,只能以自己柔弱之躯、泣血之声唤起宝玉的坚定和反抗。宝玉始终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爱恨交织,既充满依赖与畏惧,又不断犹豫与彷徨,最终还是辜负了黛玉至情至爱,黛玉因绝望而死,宝玉失去了唯一的粉黛知己,最终皈依佛门而远离尘世。
哈姆雷特同样忠诚爱情,他曾向奥菲利娅表白:“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言,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9,p141]他深爱奥菲利娅,赞美她“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奥菲利娅也深爱着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他清楚明了自己报仇的责任,但“他所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9,p258],他的犹豫不决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软弱与彷徨。复仇如此,对奥菲利娅的爱也是如此。哈姆雷特在第一幕就说到:“世界是污浊的瘴气的集合,是长满恶毒莠草的荒园,世界就是一座大监狱,而丹麦就是其中最坏的一间。”[9,p1]突如其来的变故更凸显出他灵魂深处的软弱、犹豫等性格特质。哈姆雷特似乎看透到人性的污浊和人在本体意义上的堕落,在情欲逼近时,奥菲莉娅也会“让贞操像蜡烛一样融化”,他的不断犹豫最终酿成了奥菲利娅发疯落水溺亡的悲剧。
性格悲剧的特点是以人的个性力量为主体,突出表现个人情欲冲突,并将悲剧的原因深化为悲剧主人公自身性格内部的矛盾。性格内部包含着软弱、缺陷甚至恶的因素,正是性格中的这些弱点引起错误行动,导致悲剧[10]。布莱德也曾说,“当悲剧发展到它的结局时……这些行为的主要来源就是性格”[11]。
五、结语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曹雪芹一生高傲放达、蔑视流俗、厌恶礼教。这样一个“叛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世俗的理解的,他把自己的人生悲剧中悲惨境遇以及对世俗的鞭挞、嘲讽和谴责都倾注在《红楼梦》上[12],“能解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13],当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6,p3]。在西方文学史上,莎士比亚的悲剧充分体现了性格悲剧而导致主人公悲惨结局。布拉德雷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悲剧中的矛盾冲突并非发生在悲剧主人公和他人之间,也非互为对立的集团之间,而发生于分裂的主人公内在”[14]。莎士比亚悲剧所体现的是“人的弱点与勇气,愚蠢与卓越,脆弱和力量之间永恒的矛盾”,强调了“在悲剧主人公身上崇高与卑鄙的并存”[15]。莎翁的悲剧被公认为性格悲剧的代表,西方理论界甚至将“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作为性格悲剧的代名词。“洁来还洁去”,贾宝玉和哈姆雷特承载着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两位中西文学巨匠剖析人性的使命,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性格悲剧理论比较贾宝玉和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可以发现他们均因无法超越自身的疯癫、软弱和犹豫等性格悲剧,最终也无法逃脱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