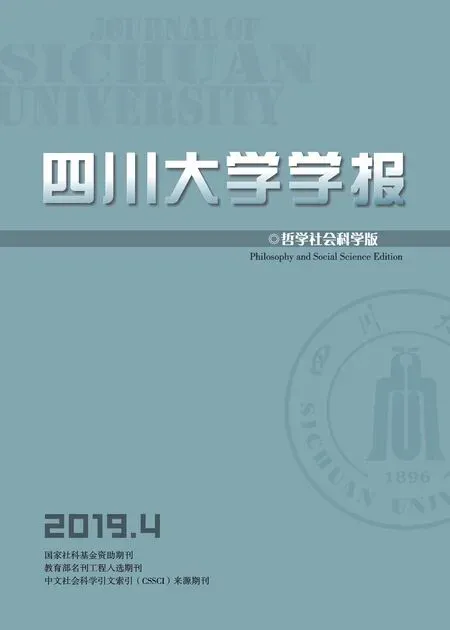晚明戏曲集《乐府红珊》的编纂体例与选本个性
——兼及戏曲文本研究的多向度问题
晚明时期戏曲刊刻活动繁盛,南京、杭州、苏州、建阳、成都等书坊集中地皆曾有为数不少的戏曲剧本和选本面世。就刊印曲籍的数量和影响而言,金陵唐氏书坊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颇为突出,它们的主人都来自江西,彼此倚重,互通有无,甚至借板翻刻,成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书籍出版团体。《乐府红珊》就是万历年间金陵广庆堂刊刻的一部具有独特编纂体例和文本个性的戏曲选本。编纂者一改以“曲”或“剧”为中心的戏曲选本编纂体例,树立以“出”为中心的编选理念,赋予折子戏独立的身份;同时,还按照日常生活场景,将所选一百出折子戏分为十六种类型,使《乐府红珊》具有鲜明的仪式性演剧特征,在明刊众多的戏曲选本中独树一帜。
对于这样一部颇具特色的戏曲选本,最早的介绍者是民间文艺学家李家瑞。1937年他谈及曾偶遇《乐府红珊》明刊本,并将之判定为说唱艺术陶真的底本。[注]李家瑞:《陶真选粹乐府红珊》,《中央日报·图书评论周刊》第5期,1937年6月17日。然其所见稍纵即逝,直到1963年,哈佛大学汉学家韩南在大英图书馆发现嘉庆五年(1800)积秀堂覆刻明广庆堂本《乐府红珊》,并撰文向学界澄清此书不是陶真而是一部戏曲选集,[注]韩南:《〈乐府红珊〉考》,《中外文学》(台北)第4卷第7期,1976年。此文后收入《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才再次引起学界对这部戏曲集的关注。韩南的介绍首先受到台湾王秋桂先生的重视,他不仅翻译了韩南的《〈乐府红珊〉考》,还在上世纪80年代将英国藏《乐府红珊》影印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以方便更多学者利用。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者田仲一成、吴新雷、赵山林以及朱崇志、蒋山都对《乐府红珊》有所探讨。[注]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第八章“宗族演剧的戏曲世界”,云贵彬、王文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吴新雷:《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44页;赵山林:《中国戏剧传播接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0-326页。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91页;蒋山:《〈乐府红珊〉叙考》,《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尤值提及的是,赵继红博士对这部选本的发现过程、编选观念、选本性质、分类思想、文献价值作了系统研究。[注]赵继红:《明万历〈乐府红珊〉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6月。以上所及皆为重要研究成果,然在《乐府红珊》的编纂目标、成书形态尚有歧见,尤其是对其仪式性演出特征存在继续研究的空间,故撰小文就相关问题再做些讨论,以丰富、深化对这部晚明戏曲选集的认识。
一、编纂目标:兼顾文人清唱与戏班演出
在选本成书的过程中,书籍的风格很大程度取决于出版人,如书坊主的经营理念、编纂者的身份和好恶都会影响到戏曲选本的编纂原则和体例。故而,探讨《乐府红珊》的选本个性,势必要对其编辑者、书坊主以及成书时间等信息做基本的了解。
今存大英图书馆的《乐府红珊》保存完整,[注]因《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多有漫漶,请英国留学的徐巧越博士代为复制此藏本,特致谢忱。卷首《校正乐府红珊序》的“万历壬寅岁孟夏月吉旦秦淮墨客撰”落款透露原版为万历三十年(1602)序刻本,而扉页的“积秀堂藏版”“嘉庆庚申新镌”题款,显示其为清嘉庆五年积秀堂的覆刻本。正文卷首题署“秦淮墨客”选校,“唐氏振吾”刊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秦淮墨客则是该堂延聘的书客。广庆堂是晚明金陵绣谷的书坊,和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集贤堂、兴贤堂同来自江西金溪县。[注]苏子裕:《明代戏曲出版物之最——江西人编选、出版的剧本》,《戏曲声腔剧种丛考》,台北:“国家”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根据晚明金陵书坊存世文献的版本信息,除广庆堂唐振吾、唐国达,富春堂唐富春,世德堂唐晟,文林阁唐锦池、唐惠畴,兴贤堂唐少林,集贤堂唐鲤跃之外,还有唐鲤飞、唐文鉴、唐龙泉、唐廷瑞、唐建元、唐际云、唐谦等唐氏书客在南京从事刻书、售书的经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晚明金陵的唐氏书坊有15家之多,[注]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6-247页。坊主之间关系密切,互通有无,彼此转移或租赁版片。[注]如《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版心镌“富春堂”,可扉页却署“金陵唐锦池梓行”,“从富春堂与文林阁两者刊书的年代来看,此版本《白蛇记》最初应由富春堂所镌,然后转版到了文林阁,由其添换扉页重印”(参见赵林平、许建中:《明末清初书坊戏曲版片的转移与变更》,《文献》2014年第3期,第143-146页)。此外,富春德寿堂梓行的《重校拜月亭记》借版于文林阁,世德堂重刻的《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借版于富春德寿堂,世德堂也曾将《新刻出像音注宋江水浒青楼记》版片租赁转借给富春德寿堂刷印。最能体现其合作关系的是别本《绣刻演剧》的出版,唐氏各家书坊对六十种戏曲的底板皆有贡献。[注]这套戏曲全本的选集共六集,每集十种凡六十种,其中富春堂刊本传奇三十种,文林阁本二十种,世德堂本七种,另配入文秀堂和继志斋刻本各一种。详参程有庆:《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辩》,《国家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Z2期,第140-145页。互借版片、互相校订的密切合作关系,使金陵的唐氏书坊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出版团体。
关于“秦淮墨客”的身份,孙楷第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根据万历三十四年刊本《杨家将通俗演义》“秦淮墨客校阅”的题署、卷首《自序》的“秦淮墨客”落款,以及“纪氏振伦”“春华”二方私印,判断秦淮墨客为纪振伦,字春华。[注]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90页。这一结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又据秦淮墨客所撰《续英烈传叙》中“当今不幸而伏处山林,沉观事故”诸语判断,他当是一位科举不第的读书人。除纪振伦外,时受聘于唐氏书坊者还有谢天佑、吴修德、朱少斋、绿筠轩、罗懋登等数位,他们基本来自江西南昌、抚州等地,因科场不振而成为同乡书坊的书客,通过编辑或创作小说戏曲及日用俗书来糊口养家。书客们在曲籍编纂、刻印各环节中审定音律、校正异文、订释词义、注明字音、描绘图像、旁注点板,期以竭尽所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多元需求,从富春堂本《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世德堂本《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赵氏孤儿记》、文林阁本《新刻全像点板高文举珍珠记》、广庆堂本《镌玉茗堂新编全相南柯梦记》等曲本的全名,即可看到他们对曲籍出版所作的贡献。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世德堂本《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发现天头留下不少“评注”文字,是编校环节留下的痕迹,如第七折《诸友赴场》【浣溪沙】处,注曰:“吴本有浣溪沙词而无后白,徽本、浙本、闽本虽有之,俱驳杂,今从古本。”第十二出落唱诗处,注曰:“诸本落场诗丑句在前,外句在后,失序无味,今从古本更定。”[注]陈志勇:《孤本明传奇〈剑丹记〉〈玉钗记〉的作者问题——兼论古代剧本著作权与署名不对称现象》,《戏曲艺术》2016年第4期,第31页。可知校刊者是以古本《琵琶记》为底本,参校徽本、吴本、闽本、浙本,在异文校勘、声律核订、曲白删润上付出颇多辛劳,很大程度提升了书籍的品质。《乐府红珊》的编纂者纪振伦即是晚明书客群体中的一员,尽管未知其更多的行实事迹,然据《乐府红珊》与《杨家将通俗演义》刊行时间万历三十年和三十四年,至少其在此四年间为广庆堂校订书籍。经纪振伦之手的曲籍除《乐府红珊》之外,还有八种传奇剧本[注]即《剑丹记》《双杯记》《七胜记》《折桂记》《霞笺记》《宵光记》《西湖记》《三桂记》。另外,《葵花记》《题塔记》《南柯记》《全德记》《红梅记》《偷桃记》也为广庆堂所刊行,只未知是否经纪振伦校订。和一些通俗小说、日用杂书。
唐氏书坊所刊行的剧本现存81种,[注]苏子裕:《明代戏曲出版物之最——江西人编选、出版的剧本》,第553页。其中有25种成为《乐府红珊》遴选折子戏的底本,[注]富春堂本15种,分别是《联芳记》《白兔记》《三元记》《千金记》《玉环记》《紫箫记》《和戎记》《荆钗记》《浣纱记》《玉玦记》《草庐记》《玉合记》《丝鞭记》《还带记》《十义记》;文林阁本5种,分别为《投笔记》《绣襦记》《玉簪记》《红拂记》《四美记》;世德堂本5种,分别是《琵琶记》《断发记》《拜月亭》《玉合记》《还带记》;广庆堂本2种,分别是《萃盘记》《拜月亭》。去除重复者,合计25种。基本涵盖了《乐府红珊》选录折子戏较多的那些戏曲。这也就意味着,《乐府红珊》很有可能是依托唐氏书坊刊印或庋藏的曲本来完成的。广庆堂书坊的商业性质决定了《乐府红珊》的编纂首先会考虑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而达成这一目标,不仅取决于选本内容是否充实、体例是否完备、特色是否鲜明等基本条件,如何设定阅读人群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乐府红珊》重点编选流行昆剧的名段,同时也模仿一些昆腔选本设置唱曲通则。卷首《凡例二十条》实际上是魏良辅《曲律》早期的改本。[注]吴新雷:《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0-132页。魏氏《曲律》被昆腔清唱家视为圭臬,不单是《乐府红珊》,晚明其他选本也存在改窜移用《南词引正》的情况。[注]如《乐府名词》“曲条”、《吴歈萃雅》“魏良辅曲律”、《词林逸响》“昆腔原始”、《吴骚合编》“魏良辅曲律”和《度曲须知》“律曲前言”。秦淮墨客在《校正乐府红珊序》中言:“况乎辞人骚客之谭,有足以供清玩者,何取于连篇累牍为哉?”从中透露出《乐府红珊》就是为文人雅士的宴集娱曲演剧提供参考,满足他们唱曲自娱的需要。
除此之外,《乐府红珊》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目标消费人群呢?日本学者田仲一成主张《乐府红珊》是以宗祠为中心宗族演剧的蓝本,并以宗族演剧的视角对选本中的一百出折子戏作了理论阐发,揭示它们所蕴含的特殊场景意义。例如,《乐府红珊》卷三所选《断机记·商三元汤饼佳会》,为《商辂三元记》第二十二出,演商府小妾爱玉生子辂,举行“汤饼会”,正妻秦雪梅主持庆贺宴会。对于这样一个生活场景,田仲解释道:“在庆祝的宴席上,商府的正室雪梅占据主角,……唱道‘望你传家读经史’,表达了把孩子培养成读书人的决心。宗族那种以通过仕途功名来延续男系血统的繁荣为至上的理念被显示出来。”[注]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第240、229-267页。尽管《乐府红珊》很多折子戏可以配合宗族仪式进行搬演,就如“商三元汤饼佳会”在宗族演剧过程中被赋予“通过仕途功名来延续男系血统的繁荣为至上”的象征意义,然为特殊场景所赐,并不具有普遍性,故田仲将此一百折戏全部阐释为“宗族演剧蓝本”颇为牵强。此外,《乐府红珊》没有出现宗族演剧最常见的祭祀演剧、节令演剧、习俗演剧等类型的折子戏。总之,无证据表明《乐府红珊》是专为宗族演剧而选备。
韩南指出《乐府红珊》所选剧目是“为演出而用的”,其“可贵之处在于显示了当时民间戏台上实际演出时的曲文”。[注]韩南:《〈乐府红珊〉考》,《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71、278页。吴新雷也认为《乐府红珊》是舞台演出本。[注]吴新雷:《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0页。翻看《乐府红珊》,确实可以发现剧目来源并非全部是昆腔散出,例如卷五“激励类”所选《五桂记·万俟传祭衣巾》的【剔银灯慢】中就加入了五处滚唱。《万俟传祭衣巾》是流行于晚明剧坛的名段,[注]该戏搬演张榜之前,诸生听响卜以占上榜与否。其中,万俟传因榜中错写成万侯传而误以为落榜,故悲痛地撰写祭文以辞书笔纸砚。后来,随从察觉高中会元的是自己东家,万俟传由悲转喜。其他明代戏曲选本亦有辑录。[注]如《八能奏锦》卷四和《乐府玉树英》卷五有选录,但目存而文佚;《大明天下春》卷四、《乐府万象新》前集卷三、《群音类选》“诸腔”卷三皆存曲文;《群音类选》本有曲无白,没有滚调;《乐府红珊》本与《大明天下春》《乐府万象新》曲白全同。此外,卷八“报捷类”选录的《丝鞭记·吕状元宫花报捷》、卷十“游赏类”辑选的《红叶记·韩夫人四喜四爱》、卷十五“阴德类”收录的《四美记·蔡兴宗伞盖玄天》也出现了滚唱。这四出插入滚唱的折子戏很可能是弋阳腔或受弋阳腔影响的青阳腔剧本,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就将《乐府红珊》所选的《三元记》《十义记》《和戎记》《草庐记》列入“杂调”,而“杂调”戏文的选录表明编纂者有为民间戏班提供底本的考虑。不仅如此,《乐府红珊》按生活类型分为十六卷,涵盖了日常戏班所能见到的各种演出场景,艺人只要能将《乐府红珊》中的散出烂熟于胸,就可以应付东家点戏,或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择戏搬演。类似于粤剧“排场戏”的示范功能,即艺人将某些折子戏经典化——故事的典型性和艺术的精致化,使之成为同题材戏曲可资模仿的“母本”,[注]王馗:《解行集:戏曲、民俗论文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222页。《乐府红珊》的百出折子戏就是在实际演出中可以套用的100个生活场景。这种设计显然是对晚明流行曲文演出情况予以充分考量的结果,蕴含为民间戏班演出提供文本参考的编选意图。
由上可见,《乐府红珊》的目标人群既不完全锁定为纯粹的文人雅士,也不仅仅为戏班艺人演出所设,而是二者兼顾,体现出编纂者对晚明时期折子戏演出潮流和戏曲书籍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
二、体例特色:“出”为中心与场景分类法
《乐府红珊》付梓的万历三十年,正处于折子戏独立登上戏曲舞台、演出极为盛行的时代。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将构筑园林、置办家乐、宴游雅集的闲适生活方式视为时尚潮流,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和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都真实反映出这种流风时俗。在他们的日记里,折子戏频频登上文人堂会的红氍毹,宴集演戏几无日有歇。风气所向,大量散出选本应运而生,而《乐府红珊》在众多选本中因体例鲜明而独树一帜。
《乐府红珊》对于选本的体量设计和框架搭建有着精细地考量。编纂者从62种戏曲中选录100出折子戏,分门别类归入16卷。“百出”是个吉利圆满的数字,表明编者对《乐府红珊》的总体规模有通盘的设计;16卷按门类分配折子戏,从3至10出不等,不追求每卷体量的均衡,但分册大致匀称,体现出编者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而在编排方式上,《乐府红珊》的第一个特色是以出为中心,其总目录以折子戏出目为序编排,剧目从属于出目,而且在正文中不再标注剧目,淡化每出折子戏与母本的归属关系,凸显了折子戏的主体性,让折子戏成为选本的主角。
明代戏曲散出选本,就选录对象的存在形态而言,大致形成了三种编纂模式,除《乐府红珊》采取的“出中心”体例外,还有“曲中心”和“剧中心”两种情况。“曲中心”选本传统是由正德十二年(1517)《盛世新声》开创的,《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月露音》《南音三籁》《吴歈萃雅》踵华增光。它们受曲谱体例的影响,多以宫调、南北曲、小令散套等为序次编目,不但散曲、剧曲混排,而且不注明剧名、出目,有意淡化剧曲的来源,大多弃宾白而仅录曲辞,致使剧曲与散套难以判别,诚如梯月主人所言:“余论时曲,而惟取其情真境真,则凡真者尽可采,不问戏曲、时曲也。”[注]周之标:《吴歈萃雅·题辞》,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2辑,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9页。此类选本以满足文人士夫雅集娱曲、清唱吹奏的需要为目标,甚或完全是为曲家填词斟律作参考。
然而,晚明文人士大夫并非都精通声律,故以剧目为纲来编排全书的“剧中心”选本,也有相当大的市场。较早的此类选本如嘉靖年间所刊《风月锦囊》,就是从流行的名剧中摘选若干“锦出”组成新的演出文本,其中《全家锦囊伯皆》从《琵琶记》42出中遴选35出,《全家锦囊荆钗》选取《荆钗记》48出中的23出。《风月锦囊》从同一剧目中挑选如此多的散出,而且副末开场和大团圆结局齐备,只是减省了一些枝蔓或过渡的场子,在某种程度上其所谓“摘锦”就是全本的舞台演出缩节版。明末金陵奎璧斋刊《歌林拾翠》是此类缩节版戏曲选本的殿军,《西厢记》《琵琶记》《金印记》《红拂记》《百花记》《连环记》《玉簪记》等名剧皆选摘10出以上,将情节精彩、戏点突出的戏出贯串来演,既节省时间也保留了原剧的精华。这种编纂方式处于全本演出向折子戏演出过渡的阶段,以简便易于操作而渐渐成为晚明时期戏曲折子戏选本的主流。民间书坊就常从时兴的名剧中挑拣若干折加以编排,然后按照相对均衡的原则分卷成书以牟利。需指出的是,同为以“剧”为中心的选本,分卷模式也会有所不同,如《群音类选》是以声腔为主,兼及官腔与诸腔、北剧与南剧、剧曲与清曲;《怡春锦》则兼顾剧曲与清曲、弦索与南音、昆腔与弋腔等多个方面。但无论以何种标准分卷都始终秉持以名剧为中心的理念,散出从属于全本的思想没有改变,即便是搬演折子戏,但仍是著录全剧的题名。
“曲中心”选本所呈现的是只曲或套曲的优美婉转,重在清唱,而“剧中心”和“出中心”选本都重在演绎。就编纂方式而言,戏曲选本的重心由“剧”转向“出”,意味着选本辑校与刊刻者的编纂观念发生了转变,也表明晚明折子戏以独立姿态登上戏曲舞台,成为全新的观演方式。以“出”为单元的折子戏可以在各类型演剧场合演出,其情感蕴涵和艺术魅力被最大限度激活,并最终在社会上形成“止索杂单,不用全本”[注]李渔:《闲情偶寄》卷四《演习部·变调·缩长为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78页。的时代潮流。需指出的是,晚明时期以“出”为中心的选本,在编排散出时,分集分卷的编纂理念存在差异,如《乐府珊珊集》以文行忠信分集,《月露音》以庄骚愤乐分卷,《吴歈萃雅》以元亨利贞分集,《缠头百练二集》以礼乐射御书数分集,更多的则以风花雪月命名。这些选本以品行、情感、易卦、六艺或自然风物来分集别卷,兼顾各集(卷)体量匀称和以散出分类的成书目标,符合书坊“快而省”的经营策略,晚明时期建阳书商所刻曲选多是如此。但与绝大多数曲选有分卷而无明晰的分卷标准、散出完全可以在卷间互换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乐府红珊》对分卷内容有通盘考量,以场景归类分卷,卷内每折戏的先后次序也有大致的排列。而这正是《乐府红珊》的第二个特色,即以生活场景类型作为分卷标准,跳出基于折子戏艺术水平的单向评价体系,探索折子戏与演出环境配适的新的可能。其全名《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首先强调的是对所选折子戏的“分类”特色,亦说明编者具有折子戏类型化的自觉意识。
《乐府红珊》从卷一至卷八为庆寿类、伉俪类、诞育类、训诲类、激励类、分别类、思忆类、捷报类,卷九至卷十六为询访类、游赏类、宴会类、邂逅类、风情类、忠孝节义类、阴德类、荣会类。若将这十六类生活场景想象为一位古代书生的人生历程,前八卷可说是其入仕前立身成家、苦读奋取人生的上半场;而后八卷则在演绎其入仕后宦海交游、仕途邂逅的人生下半场。当书生的人生大幕徐徐降下,其子其孙又在循环往复中开启同一个“故事”。十六类生活场景清晰描绘出读书人的生命轨迹,每一卷里的生活场景都是人生的横断面,连缀起来就是一副徐徐延展开来的人生画卷。戏剧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不但是惟一的能够进行自我实验的类,而且是唯一能够在假定性的时空中进行自我实验的类,这个假定性的时空就是剧场”,也就是说,“戏剧是人的自我实验”。[注]陈世雄:《戏剧人类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页。通过舞台演出,观众可以了解生存的要义,洞察社会,探求人性,拷问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戏剧演出就是人类审视自身的“一种工具,一种自我研究、自我考察的手段,一种救世可能性”。[注]布鲁克:《空的空间》,邢历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64页。《乐府红珊》将读书人的生活场景依照人生的流程进行编排,可视为一种审视自身的自我实验。
然而,人生阶段的场景无法平均分派,《乐府红珊》的编撰者又是如何编排人生各类场景的轻重繁简呢?细按这百出折子戏,在十六类生活场景中分布最多的是分别,选有10出;次之是思忆、游赏、宴会,皆9出;再次是庆寿,有8出;而训诲、报捷、忠孝节义,也各有7出之多。依照戏剧是对人自身行为的观照这一逻辑,能给人带来最大触感的正是分别类生活场景,因为分别预示一个生活空间和生存体验的结束,同时开启新的生活模式,是人生的转折,但所带来的并不是圆满幸福的情绪。就明传奇的体制而言,离合之象不仅是“传奇之法”而且是情感转捩之关窍,全本戏曲很注重对分别戏出的营构,它在《乐府红珊》之类的戏曲选本中数量较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分别之后是思忆,贯穿于分别与团圆之间,思忆与分别两类折子戏紧密相连,共同构筑“离象”。分别思聚,报捷类散出能消解观众因分别、思忆积聚起的负面情绪,寄予着富贵团圆的人生理想。而游赏、宴会、庆寿、训诲则是人生旅程中的常态场景,文人风雅与夫孝妻贤皆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相应地,询访和阴德类所选较少,这是因为询访类关目在明传奇中就比较少见,即便有也多为书生询访妓女之类,并不适合于堂会或家宅环境演出;而阴德类表达的是积德行善而获好报的故事,为礼佛茹斋的信士所欢迎,受众面相对较小。由此亦可见,对于场景轻重繁简的选取,《乐府红珊》具有更为严整细致的设计考量,使之在成书观念和编纂体例上显现出与其他戏曲选本完全不同的个性色彩。
《乐府红珊》的第三个特色是在每卷之首精选“头戏”,并精配插图,以此强化十六类生活场景的艺术性内涵,达成图文互参、文成图显的效果。“头戏”首先是选择具有突显本卷场景性功能指向的独特戏出,在本卷的所有戏出中最具典型性。如首卷第一帧插图描绘《升仙记·八仙赴蟠桃盛会》,演绎汉钟离、吕洞宾等八仙前赴西王母蟠桃盛会,奏请将功德圆满的王寿真列入仙班。题材喜庆、寓意吉祥,极适合寿庆场合演出,如朱有燉所言:“庆寿之词,于酒席中,伶人多以神仙传奇为寿。”[注]朱有燉:《瑶池会八仙庆寿引》,赵晓红整理:《朱有燉集》,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14页。明末小说《梼杌闲评》第三回讲述王尚书家老太太上寿,点的就是裴航蓝桥遇仙故事的《玉杵记》。旦角扮云英唱道:“飘飘丰致,真有神仙八极之态;竟是仙女天姬,无复有人间气味。”[注]《梼杌闲评》第三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羽化登仙、长生不老是人类永恒的愿景,《乐府红珊》以凡人升仙来开启寿庆的大幕,编纂者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又如卷十二邂逅类的“头戏”《拜月亭·蒋世隆旷野奇逢》演绎旷野中书生呼喊失散的妹妹,却因名字类似而误答,佳人邂逅才子,两人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这份“巧合”较之张生在佛殿与崔莺莺、伍经在贞女祠与二兰、韩翊在章台与柳氏之类的相遇,更得男女“邂逅”之要义。其次,“头戏”要寓意富贵吉祥、和美圆满。如卷二《琵琶记·蔡议郎牛府成亲》演蔡伯喈状元及第、入赘相府,这可谓封建时代书生的人生巅峰状态,将之列为伉俪类的“头戏”极为适宜。卷三“诞育类”首出《断机记·商三元汤饼佳会》、卷八“捷报类”的首出《丝鞭记·吕状元宫花报捷》无不具有美好祝福、吉祥喜庆的文化品格。[注]《商三元汤饼佳会》演魁星下凡的商辂刚满三朝,商府举行汤饼宴会并定下娃娃亲,阖家“喜之重重,欢声迭迭”;《丝鞭记·吕状元宫花报捷》通过搬演吕蒙正寒窑苦读得中状元的故事传达书生可登临的人生境界。更为显者莫如卷十六“荣会类”的“头戏”《金印记·苏秦衣锦还乡》,苏秦六国封相的荣耀远较状元及第荣归故里要强烈,对观众会产生深远的心理暗示作用,以它来绾结《乐府红珊》全篇,收煞有力,寄寓深远。再次,“头戏”要有相当的知名度,当为流行的名段。《陈妙常秋江送别》《吕状元宫花报捷》《楚霸王军中夜宴》《卓文君月下听琴》《萧何月夜追韩信》等都是明代戏曲选本最常选的散出,在剧坛上经演不衰,像《苏秦衣锦还乡》(《六国封相》)更成为很多地方戏开场必演的例戏,延续至今。可见,“头戏”的设置不仅显现出编纂者对于题材的倾向性,也让每卷内部戏出产生良好的凝聚效应,实现了选本整体外部框架的稳定和匀称。
综上,《乐府红珊》的编者既重视选本整体框架的搭建和分卷标准的设计,也不忽视卷内戏出之间的融合协调和满足目标人群的演剧需求。周全诸多因素,注重细节打造,使得《乐府红珊》个性鲜明。
三、功能延展:从阅读性文本到仪式性文本
《乐府红珊》选录的百出折子戏极适合家乐戏班或民间戏班在特定场合演出,当它们进入不同的演出场域,其仪式性功能就进一步获得释放。具体而言,百折散出的独特仪式性功能在《乐府红珊》成书与演出两个环节逐次被激发和扬显。
首先,当《乐府红珊》编纂者从62种全本戏中抽选折子戏,并予以场景化分类编排,其仪式性就已获得初步显现。作为全本戏的有机组成部分,单折戏此时不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即便再精彩,仍被淹没在全本的情节和情绪之中。例如当“崔莺莺长亭送别”处于《西厢记》全本中时,受众主要关注“花间美人”[注]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17页。般的曲辞、崔张爱情的关目流转、崔莺莺蔑视富贵与珍视爱情的可贵品格等等,很少会去考虑它应该在什么场合演出。可是,一旦“长亭送别”被抽调出来并将之分配至“分别类”场景中,其仪式性特质就会被放大。同样,丧期演剧也不会演出过于喜乐的散出。邹迪光《石语斋集》卷十记载,万历四十年其妻病故,友人来吊,演出的是汤显祖的《紫钗记》。《紫钗记》搬演的是李益和霍小玉之间才子佳人的缠绵爱情故事,由邹迪光的诗句“急管烦弦声正哀,翩翩有客夜深来”“分燕此时怜玉镜,调鸾何处望琼台”[注]邹迪光:《石语斋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58页。可知,伶人当是选取了《紫钗记》中《折柳阳关》《边愁写意》《怨撒金钱》等谱写离愁别绪的散出。尤其是《怨撒金钱》,霍小玉边唱【小桃红】【哭相思】等如泣如诉的哀鸣曲,边在舞台上抛撒纸钱,这与民间哭丧、送葬的习俗和场景完全协调合拍。于此可见,散出浓郁的场景性意蕴及其体格小而意境集中的特点极适合仪式性演出。
《乐府红珊》折子戏仪式性功能的初步显现,一定程度取决于编纂者对晚明剧坛剧目和散出流行情况的把握,如何从流行名剧中择选出具有典型仪式性特点的名段,以迎合读者的需求,使《乐府红珊》获得更高的认同度,是对编纂者的识见和智慧的考验。百折散出若平均分布于62个剧目,每个剧目不足两出,但《琵琶记》《西厢记》《千金记》《投笔记》等9个剧目却共选入36出,占据百出折子戏的三成多。像《琵琶记》“蔡伯喈庆亲寿”“蔡议郎牛府成亲”,《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君瑞泥金报捷”,《香囊记》“张状元琼林春宴”都是剧坛名折,其适合哪种场合演出,民众熟稔于心,故而《乐府红珊》的遴选表明编纂者充分考虑到戏曲消费市场的实际。另如《四节记》中的“杜工部游曲江”(春景)、“苏子瞻游赤壁”(秋景)、“党太尉赏雪”(冬景)被选入游赏类,也是充分考察到每一出戏独特的场景演出特质。
其次,当具有独特场景意义的折子戏进入特定的演出环境时,其所蕴含的仪式性内质会与演剧场合中的事件和人群构成情景相融的在场关系。尽管目前没有传世文献记载《乐府红珊》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编选的折子戏如何在搬演环节显现仪式性功能,但通过晚明文人对折子戏演出仪式感的重视,可以从侧面加以印证。明末陶奭龄就特别强调剧目整体风格、情感类型与演出场合的契合度,云:
余尝欲第院本作四等,如《四喜》《百顺》之类,颂也,有庆喜之事则演之;《五伦》《四德》《香囊》《还带》等,大雅也;《八义》《葛衣》等,小雅也,寻常家庭宴会则演之;《拜月》《绣襦》等,风也,闲庭别馆,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于《昙花》《长生》《邯郸》《南柯》之类,谓之逸品,在四品之外,禅林道院皆可搬演,以代道场斋醮之事。[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明崇祯八年(1635)李为芝刻本,第65-66页。
陶奭龄以《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原则来权衡明代戏曲适宜何种场合演出,显现出明确的仪式性演剧意识。事实上,通过李日华、潘允端、冯梦祯、祁彪佳等人的日记以及当时小说对演剧场景的描写,可以体味到晚明时期文人对折子戏场合性的特别关注,以及民间演剧在传统礼乐文化下行过程中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层次影响。
寿戏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演剧形态,为父母长辈庆寿的剧目最多,《乐府红珊》庆寿类亦是如此。除首出《八仙赴蟠桃盛会》外,《班仲升庆母寿》《张九成兄弟庆寿》《裴晋公绿野堂祝寿》《关云长公祝寿》《老莱子戏彩悦亲》等戏出也属于这一范畴。晚明文人士大夫追求上演剧目既要应景又具可观赏性,不同场合的演剧有别,中年人的生辰往往会另选剧目搬演,《快雪堂日记》记载万历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冯梦祯参加沈二官为其夫人的生日设宴,伶人搬演的是《麒麟记》。[注]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丁小明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麒麟记》演梁红玉辅助丈夫韩世忠抗击金军的故事,有红玉在战场上诞下麒麟儿,仍亲执桴鼓、激励将士击溃金兀术的关目。这出戏场面闹热喜庆,能表达对夫人的敬意,且合时境。
在人生状态转换的节点上,人们乐于举办各种礼仪加以标识,也往往会通过演戏来增添气氛和强化对事件的记忆。晚明华亭人宋懋澄在《顺天府宴状元记》中记述万历三十五年春,顺天府公宴新科三鼎甲,仪式隆重而喜庆,“献酬之仪”共分七节,第二节献上弦索调,摘唱《破窑记》末出吕蒙正苦尽甘来,“喜得功名遂”。[注]宋懋澄:《九籥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03页。这出折子戏不仅应合公宴表彰场景的氛围和仪式意义的需要,更与宴会程序的进度、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新婚大喜同样是人生进程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乐府红珊》卷二伉俪类为这种特殊的礼仪选入《琵琶记·蔡议郎牛府成亲》《联芳记·王三元相府联姻》《玉环记·韦南康夙世姻缘》《紫箫记·李十郎霍府成亲》《双烈记·韩世忠元旦成婚》五出折子戏。婚庆场合的演剧需传达良辰美景、瓜瓞绵延的美好寄寓,所以对仪式感的要求显然更甚于艺术性的追求。沈自晋《望湖亭记》第二十三出“迎婚”敷衍了一段戏中戏的场景,婚宴开锣演剧,新郎官只要点新戏,搬演的是柳下惠的故事。副末上场讥嘲新郎“微伤大雅”。[注]《沈自晋集》,张树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页。新婚之喜,长辈盼望早诞子嗣,新郎却点不近女色的柳下惠的戏出,自然是有伤大雅。
明末清初词人陈维崧曾和朋友杜于皇谈论过关于点戏的经历,杜说他曾经坐寿筵首席,“见新戏有《寿春图》,名甚吉利,亟点之,不知其斩杀到底,终坐不安”;陈维崧也表示曾参加寿筵,不明就里点了新戏《寿荣华》,“以为吉利,亟点之,不知其哭泣到底,满堂不乐”。[注]陈维崧:《贺新郎·自嘲用赠苏昆生韵同杜于皇赋序》,《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364页。戏点错会破坏喜庆欢快的场景,导致“满堂不乐”。更极端的后果甚至会让人为此丢掉身家性命,《梼杌闲评》第四十三回讲述武进士顾同寅到城外为同年饯行,席间不听劝阻而点了戏单上的《弓记》中的一出《李巡打扇》,旋即被辑事报入东厂,魏忠贤党羽认为顾同寅以刘瑾映射阉党谋逆而将之判斩。[注]《梼杌闲评》,第480页。《弓记》全本已佚,《词林一枝》卷四与《八能奏锦》卷五所选《李巡打扇》在明末颇为流行。剧演明武宗初年太监刘瑾图谋篡位,家奴李巡在给刘打扇时欲以扇击之,几被发觉而巧言蒙混过关。可见,当进入某种情景氛围中,戏出原有的题外之意会被放大,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联想牵延效应。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亡后,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驾临张家,伶人搬演“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以南宋康王得以神助、化险为夷的典故,巧妙契合鲁王面临清军追迫、国事多艰的况景,寓意吉祥。故戏筵结束,张岱送王闾外,书堂官两次传旨曰:“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注]张岱:《陶庵梦忆》附录佚文“鲁王”条,弥松颐校注,杭州:西湖书社,1982年,第111-112页。这与顾同寅点戏被杀的结果恰恰相反,点戏因应景且契合主宾内心的诉求,给宾主带来的则是另一番美好的观剧体验。
剧目“意义”的生成,与人的感受和体悟有关,伶人的表演行为与观众的接受心理都会对戏出搬演效果有着实际影响。陈悰《天启宫词》记载,天启五年(1625)、六年的重阳节,钟鼓司都给皇帝演唱《洛阳桥》“攒眉黛,锁不开”一阕,“宫人相顾以为不祥”,不久天启驾崩。“攒眉黛”曲选自《四美记》第十一出《邀回》,演蔡兴宗的妻子身怀六甲,丈夫赴京赶考杳无消息,只得返回母家待产。【孝顺歌】“攒眉黛”表达的是蔡妻对儿夫的无限牵挂、思念以及自己处境的艰难,归于《乐府红珊》思忆类,奏之文人堂会颇为合适,然单出置于内廷演出,其苦情悲境就被“放大”;将之与天启皇帝不久驾崩事件相联系,被宫人视为“不祥之兆”就不足为奇。当宦官刘若愚获知钟鼓司在重阳节为天启皇帝演唱“攒眉黛”曲,也“哂其不合景,失大体矣”。[注]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合景”与“得体”四字为点戏者和伶人划出一条标准线,然而有时候“合景”的戏并不能保证每句唱词都是“得体”,例如,有贵官为母庆寿称觞演出《太君辞朝》,出目合景,“曲文完美”,然其中有一句“母死王陵归汉朝”就不得体,伶人“怵然”间改为“母在华堂儿在朝”,避开生死而论富贵,引得“主人大悦”,此伶也因急智化解危机而“一时名重”。[注]焦循:《剧说》卷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198页。可见,戏与境的融合状态会因场合和对象的不同而生出无数种可能,“合景”与“得体”是折子戏脱离全本进入演出环节面临的新要求和新境界。
同一部剧可以析出多折戏,能否在特定场合挑选出恰当的散出来搬演,对于点戏人和伶人都是考验。《白兔记》是一部夫妻别离、妻子历尽辛苦盼来全家团圆的生旦剧,情绪有喜有悲,情节则始困终亨。若搬演《磨房》《撇池》中李三娘在丈夫刘智远从军后在家受尽兄嫂折磨,身怀六甲磨面担水,咬脐产子,新生儿被恶嫂撇池加害的苦境,可能就会产生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四所载的情景:万历三十一年夏,一中贵造国花堂既成,设宴演剧,“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注]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四,《雪珂斋集》,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 1180页。不过,同样是《白兔记》这几出戏,张岱《陶庵梦忆》所记天启三年上元节绍兴严助庙串客的表演则给人完全不同的情感反应,“科诨曲白,妙入精髓,又复叫绝”,[注]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严助庙”条,第47页。引来八方观众的一阵阵喝彩声。固然,折子戏的场景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认知,但独特的演剧场合所赋予剧目的新内涵亦不容忽视。祁彪佳《林居适笔》记载崇祯九年十月初三,其外家族众举酌,庆贺“式弓舅”的遗孤过继给“九舅”为嗣,演出的剧目正是《白兔记》。[注]《祁彪佳日记》,张天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234页。《产子》《送子》《追兔》演绎的是咬脐郎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文武全才的英俊少年的人生历程,这样的折子戏意境既寄寓了族人对遗孤成人成才的美好期盼,同时也极契合“嗣子承祧”的仪式性场景。
实际上,从阅读性文本到仪式性文本,因文本消费人群和场景功能的改变,《乐府红珊》的百出折子戏会以何种方式被搬演和接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百折散出在成书环节所蕴蓄的仪式性特征,势必成为东家点戏或伶人挑选戏出的重要参考。就此角度而言,《乐府红珊》的选本价值和编纂目标得以实现。
四、研究向度:从文献、文学到文化的考察
《乐府红珊》提供了62种剧、100出折子戏的大容量文本,其中有10个剧目为以往文献中所未曾著录的孤本戏曲,18个剧目31折散出为明传奇之佚曲,[注]十种孤本戏曲是:《(王寿真)升仙记》《单刀记》《斑衣记》《联芳记》《单骑记》《(丁士才)玉钗记》《丝鞭记》《茶船记》《玉环记》《偷香记》。详参赵继红:《明万历〈乐府红珊〉研究》,第121-134页。余下的34种剧目亦可资版本校勘。韩南《〈乐府红珊〉考》一文对每折散出的本事、曲文来源作了详尽考索,藉此揭示出《乐府红珊》的文献学价值。而赵继红《明万历〈乐府红珊〉研究》对《乐府红珊》作了曲律和评点意义方面的揭发,则属于曲学和文学层面的研究。无论是版本校勘、佚曲辑录、曲文整理还是折子戏的定量统计分析,以及曲学、文学的研究,《乐府红珊》都值得深入发掘,其价值和意义是多维的,需要我们以多重眼光审视它,以多向度方法去研究它,才能尽量还原它的本相,更加接近明代戏曲的原生态。
当晚明其他戏曲选本编纂者还在强调插图与点板(如《新刻出像点板增订乐府珊珊集》)、标榜时尚新调(如《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凸显评点特色(如《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的时候,《乐府红珊》则以其生活场景的“分类”特色脱颖而出,其独特的文本形态和选本个性给我们描绘出晚明时期折子戏仪式性演出的生动图景。折子戏演出的仪式性功能,离不开观众和演出场合重新赋予戏曲内容(故事)新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在考察折子戏演出时“不能抽离表演场合来判断一个剧本及其演出的实际意义”,“研究中国戏曲不能只满足于剧本的文本分析,更必须结合它的表演场合来理解、掌握它的功能意义”。[注]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自序”,第4页。亦即要注意演出场地、仪式目的、剧目意义及演出方式的交互关系。由《乐府红珊》独特的分类意识和原则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不能套用传统范式,不能以纯文学观念去看待,因为它还牵涉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诚如韩国学者吴秀卿教授所言,对戏剧文本(text)的把握,应该由过去传统的文人文本(literary),向演出文本(performing)、演出语境(context)范畴扩展,因为后者才是戏剧的本质,这种转向和扩展本身正是戏剧研究的本质回归。[注]吴秀卿:《从“文本”问题看中国戏剧研究的本质回归——兼谈韩国的中国戏剧研究》,《戏剧艺术》2003年第1期,第75页。
事实上,中外不少戏曲史学者已经自觉地以立体多维的视野来审视中国古代的戏曲文本,例如元明杂剧中的几部“关公戏”,由于其强烈的祭祀仪式性,一些学者主张它们其实就是祭祀仪式场景下演出的脚本。黄天骥先生认为关汉卿的《单刀会》“则近于是平面式的颂文”,其最初的演出“应与金元之际民间酬神赛社的活动有关”;[注]黄天骥:《〈单刀会〉的创作与素材的提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九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容世诚认为《关云长大战蚩尤》“实际上是在戏台上重演一次古代傩祭中方相氏驱鬼逐疫的仪式”。[注]容世诚:《关公戏的驱邪意义》,《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田仲一成认为元杂剧《西蜀梦》“更近于平面式的咒文或祭文”;并且将与鬼神有关的戏剧如《霍光鬼谏》《东窗事犯》《孟良盗骨》解读为英灵镇魂戏,将《窦娥冤》阐释为幽鬼超度剧;甚至在他看来,“历史剧基本上都是祭祀戏剧”。[注]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戏剧研究》第五章“镇魂戏剧的产生”,布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230页;康楽整理:《金元杂剧与祭祀仪式——田仲一成教授与康保成教授对谈录》,《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第50页。尽管有研究者对田仲先生的研究范式提出异议,但“田仲教授将各种地方剧本放置于乡村祭祀、宗族、市场的演出语境之下,借以勾勒明清时期戏剧变迁背后的社会变革,将那些孤立的、静止的故纸文献,还原成了具体丰富的、动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会’行为,体现了融合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和西方‘文本性’(Textuality)研究的深厚功力”。[注]吴真:《田仲一成〈古典南戏研究〉的中国学特点》,施爱东、巴莫曲布嫫主编:《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58页。在笔者看来,田仲教授重视祭祀、宗族、市场的演出语境对戏曲文本产生深层次影响的研究理路,与晚明戏曲集《乐府红珊》跨越历史的空间,传递给当下研究者的启示和新命题完全是相通的。
《乐府红珊》独特编排方式,显露出编纂者对折子戏“演出”核心要素的独到理解,即把戏曲视为“活”的艺术,重视演剧的“场所”要素。这既与晚明社会越来越重视戏曲文本“场上”演出有关,更折射出编纂者目光向下、关注折子戏演出市场和功能的立场,其以生活场景和仪式功能的分类编排方式,客观上强调了在场的人(伶人、点戏者、观众)对演剧的感受。由演剧场所的观演活动汇聚起来的万千精神场域,就是那个时代的戏剧文化。在此意义上,《乐府红珊》契合的正是吴秀卿教授所说的戏剧的本质,作为一种戏曲文本,其编纂者能将视野由案头文本转向演出文本,高度重视仪式性演出场合与演出文本之间内在的融洽度。这无疑为我们审视明代戏曲创作、传播和接受的生态链条提供了另一视角,指出了一条从文献到文学再至文化研究的新路向。
结 语
晚明时期,各地书坊制作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戏曲选集,[注]李平教授指出:仅万历年间,“福建建阳麻沙书坊,就曾辑刻过三百多种戏剧的选集”。参见李平:《流落欧洲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页。然而《乐府红珊》的编纂者并没有蹈袭大部分选本粗制滥造以求速成射利的老路,而是另辟融合案头、场上与仪式演出的新径,为书坊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透过精良的戏曲选本,不仅可“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的作品”,[注]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更重要的是从编纂原则和选录内容探悉当时社会的戏曲消费文化。《乐府红珊》建立以散出为中心的选剧总原则,与万历中后期以江浙地区崇尚散出搬演的社会风气鼓桴相应,高度契合了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戏曲市场的实际。尽管选本所收录的昆曲折子戏占据绝大比例,从表面看似乎是为士大夫清唱而编选,但精明的编纂者通过生活场景分类法强化了其仪式性文本功能,使之兼顾了民间戏班仪式性演出和文人雅集的双重需求。在一定意义上,《乐府红珊》呈现的是一部复合文本,它兼具“阅读”为中心的案头文本、“演出”为中心的场上文本和“联想”(意义)为中心的仪式文本的多重特质,成就了其既能兼顾不同人群需求又能保持独特选本个性的目标追求。由于比一般提供案头阅读的戏曲选本多出了场上之需、仪式之备两个层面的设计,《乐府红珊》在晚明众多戏曲选本中更加引人注目。同时,因为《乐府红珊》体例的“另类”,也让研究者看到了晚明戏曲更为丰富多彩的面相,促使大家反思和拓求戏曲文本研究方式和路径的多种可能。
——现代新诗选本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