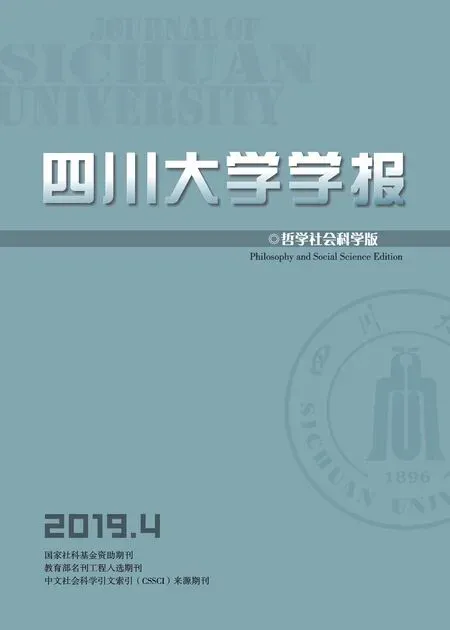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对靖国信仰的创造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日本战败40周年之际,以首相身份参拜了已将二战甲级战犯合祀其中的靖国神社,从而引发周边国家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疑虑。尽管中曾根康弘本人了解到国际社会的立场后,于任内再未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开创的先例却将“靖国神社问题”与战后日本的政治话语联结在一起。其后的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必以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彰显民族主义的标志,日本国会内还出现了名为“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议员团体。安倍晋三作为该团体的一员,直到2012年再度执政后还念念不忘:“至今仍为没能在第一个首相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而懊恼。”[注]「安倍首相が初の靖国参拝、中国は即座に反発」,https:∥jp.reuters.com/article/t9n0ji02f-yasukuni-abe-idJPTYE9BP02G20131226。实际上日方并非不知道周边国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中曾根首相参拜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就日本内阁成员在抗日战争40周年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表示遗憾,指出这一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注]《1985年:中曾根首相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932/8933/20020909/818217.html。中方的立场早已非常清楚地传递给了日本,这才会有中曾根首相停止参拜的自省举动。
但时至今日,日本政界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却有所倒退。日本政坛甚至还为这种违反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治行动披上了“传统文化”的外衣。日本国内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每每以“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传统的一环”为由,要求世界各国尊重日本的文化传统,最终接受日方的参拜行为。[注]《小泉为参拜靖国神社作辩解 声称邻国会渐渐理解》,http:∥www.chinanews.com/n/2004-01-01/26/387227.html。这种诡辩将作为政治问题的“靖国神社问题”包装成了“文化冲突”的牺牲品,从而把一切“反对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都置于日本文化反对者的境地,而且这种诡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部分日本民众所接受。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初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事后,日本共同通信社进行的紧急舆论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有43.2%的人对于首相的参拜行为表示认同,甚至有25.3%的受访者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传统,“在此问题上无需顾忌外国的感受”。[注]「首相の靖国参拝 朝日の世論調査でも6割賛成」,https:∥news.yahoo.co.jp/byline/kimuramasato/20131230-00031149。
保守派政治势力在看似严密的逻辑链条环绕下,俨然成为了日本传统价值观的守护者。然而,如果从学理上探讨作为靖国神社存在理论根基的“靖国信仰”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来,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政府为巩固自身统治,借用甚至曲解了本国的神道教传统,才创造出以效忠皇国为最显著特征的“靖国信仰”。“靖国信仰”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其实质却是明治政府通过“祭政一致”来巩固政权的工具。本文关注的核心正是“靖国信仰”在近代创生的过程。
一、从日本文化的“原型”到国家神道
“日本的神道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吸收外来思想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宗教”。[注]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从国内学界对神道教的定义上即可看出,神道教的发展固然是以日本文化的“原型”[注]这里的“原型”借鉴了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社会形态时的认识方法,即神话、古代传说中所表现出的思考样式和价值意识。参见『丸山眞男講義録』第四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41页。即万物有灵论的自然崇拜为基础,但在神道教理论的完成过程中,外来思想文化的作用绝不可忽视。神道教在走向理论化之初就十分注意吸收周围文明的精华为己所用,它绝不是一个只承认自身优越性的封闭的体系。记录日本诸神创世神话的典籍《日本书纪》就是用汉文书写的,日本的中世和近世时期,神道教理论又吸收、融合了由中国传来的佛教和朱子学因素。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假借伊势神道的宗教元素所创造的“靖国信仰”却显示出极端的封闭性和绝对主义倾向,在这种“信仰”中,日本人成为在神国中生活的“选民”,天皇是奉天照大神之名神授的“万国之总帝”,[注]如竹尾正胤在「大帝国論」中提出的“我君天皇乃地球之总帝”。参见芳賀登、松本三之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51卷,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491页。在为天皇而战的“圣战”中死亡是日本人的最高荣誉,死者会被奉为“英灵”。在靖国信仰的名义下,日本对作为传统神道教文化来源之一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神道教由此背负起“弑父”的命运,这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神道教从根源上讲是日本的本土之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长期面临一个外来的论敌,那就是佛教。虽然二者在神佛习合[注]简而言之就是为处理神佛关系而出现的一种“神佛共同体”观。的名义下似乎取得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但是采取神佛习合形态的时候,一定是佛教为主神道为从。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寺院充分利用寺请制度,确立了檀家制度,[注]寺请制度与檀家制度肇始于德川幕府对基督教的禁令,即民众需要皈依寺院,并由寺院来证明该人是本庙檀越,以排除其基督教信徒的嫌疑。强化了和庶民的联系,通过将葬礼仪式化实现了经济繁荣,凌驾于神社之上。实际情况是,虽然不是其本意,但是神社不得不遵从寺院”。[注]今井淳、小泽富夫编:《日本思想论争史》,王新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6页。
伊势神道独尊日本而排斥外国,显示出封闭性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应激反应。从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日本以来,日本宗教界一直存在“神佛之争”,且神道教在与饱经印度、中国等多种文化淬炼的佛教对峙的过程中逐渐趋于下风。对于希望挽回劣势的神道教来说,其内部诸教派进行过多种理论尝试,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诉诸民族情感。经历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忽必烈的两次征讨,与外部势力的对立在相当程度上催生了日本的民族意识。因此,日本学者广神清把国际环境的冲击称为“当时由神道自己确立神道理论的重要机遇”。[注]今井淳、小泽富夫编:《日本思想论争史》,第35页。以此为背景,日后成为神道教重要派别的伊势神道横空出世。伊势神道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以击退蒙古的入侵为背景,用过去在日本文化中零散的民族意识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神国”光环,并把这种光环奉为神道教的第一要义。[注]将“蒙古袭来”作为日本国家自觉与神道自主立场确立契机的代表性学者是久保田收,其观点参见久保田収:『中世神道の研究』,伊势:神道史学会,1959年。
“伊势神道尊崇象征天皇至高无上地位的三种神器,还着重宣扬神是君皇的‘内证’,君皇是神的‘外用’”,[注]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其根本经典被称作“神道五部书”,即《天照坐伊势二所皇太深宫御镇座次第记》《伊势二所皇太神御镇座传记》《丰受皇太神御镇座本纪》《造伊势二所太神宫宝基本记》和《倭姬命世记》。一种宗教理论的创立必须回应一个难以规避的难关——本体论问题,也就是世界的起源。由于宗教理论创设者所处的时代与混沌之初有着难以逾越的时间区隔,这就使得其必然要运用想象来补足资料上的欠缺。此类现象在伊势神道理论的创建中非常明显,即便是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神道自己确立的神道学说的特点是,首先确定了经典,旨在树立一种应该说是神道神学的教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假托历史上有权威的先哲作为作者的经书,或者一些伪装成很久以前所作的书籍。”[注]今井淳、小泽富夫编:《日本思想论争史》,第35页。换言之,伊势神道是在对抗佛教的急迫需求下创造出的“人工合成结晶”,而非亘古不变的日本文化传统。“托古之作”一直是伊势神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后以伊势神道为蓝本,奉复古之名创造出的“靖国信仰”所复之“古”,本身也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已。
事实上直到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居于中心的位置。因此,把天皇一脉视为信仰核心的伊势神道也仅仅是诸多神道流派之一,且不是主流,而是地方性的边缘教派,不受当时政权的重视或扶持。江户时期真正掌握日本实权的德川幕府亦有尊其初祖德川家康为“东照大权现”的独有家庙系统,更遑论比起神道教,佛教才是民间的主流宗教。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扶持伊势神道进行了一系列教义和仪式上的改变,终于将其打造成为君临于日本一切宗教之上的“国家神道”。而本文所讨论的靖国信仰即是国家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解决了如何在国家宗教中安放“为国捐躯的英灵”的问题。
所谓“国家神道”是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通过1868年颁布的《神佛分离令》、1870年颁布的《大教宣布之诏》等法令及宗教政策,逐步建立起来的“祭政一致”(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宗教体系的建立不能仅仅作为宗教改革来加以认识,如果横向对比“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明治政府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就会发现包括创立“国家神道”在内的所有明治新政,其施政目标无不指向强化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正是出于上述强烈的政治需求,尽管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明文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下,有信教之自由。[注]「大日本帝国憲法」,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但实际上由于政府的操纵,国家神道已经渗透到日本国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日本政府在宗教领域驾驭民众的皮鞭是“不敬罪”与《治安维持法》,比如1941年改订过的《治安维持法》第7条就将“否定国体、亵渎神宫或者皇室”入罪。[注]「治安維持法」,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A03022545700。以佛教日莲正宗面目出现的创价学会就因坚持信仰,不愿屈从于国家神道而遭到内务省迫害,其创始人牧口常三郎更遭到特高警察逮捕并被关押至死。[注]相关内容可参见小高良友:「内務省による宗教弾圧 : 創価学会の場合を事例として」,『東海女子大学紀要』2006年总第26期,第85-93页。从涉及牧口常三郎被捕的特高秘密档案可以得知,宗教界人士一直是特高警察重点关注的对象,特高秘密档案中甚至还有名为“宗教运动状况”的专门条目。档案显示牧口常三郎被捕的理由是:散布不必参拜伊势神宫(的言论),被检举宣扬其所信的日莲宗曼陀罗是至高无上的礼拜对象,因而无需再礼敬包括神道教在内的其他一切宗教的神佛,乃至有毁坏神符、神札的行为,以此推定其有冒犯皇大神宫的不敬嫌疑。[注]日本情报机构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每月将全国情报系统报送上来的信息汇总,发行一期《特高月报》。本条见『特高月報』昭和18年7月号,第127-128页。由此可见,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民众在相当程度上很难行使宪法所赋予的信仰自由权利而对国家神道加以拒绝。归根结底,国家神道在诞生伊始就并非纯粹的宗教,而是明治政府用以麻痹、控制民众的“精神鸦片”。
早在1665年,德川幕府发布了《神社条目》,从此“唯一神道”[注]室町末期经吉田兼俱之手而最终完成的一种神道教形式,因此又称“吉田神道”。其特点是在强调“神主佛从”的“反本地垂迹说”的同时兼收并蓄,将佛、儒甚至阴阳道等其他宗教都融汇其中。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明治维新前神道教中信徒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教派。但明治维新以后,唯一神道与德川幕府的紧密关系使得其同佛教一样,必须从统治日本的意识形态核心中被驱离,而填补这一信仰空白的就是国家神道。不过在多神教体系中,神的职责往往较为琐碎,即便是作为最高神的天照大神也只是国家以及天皇一脉的守护神。如此,那些效忠天皇者的信仰又如何在国家神道中得到安置呢?靖国信仰在明治时期的创生正是为了摆脱这一理论上的困境。
二、明治政权与靖国信仰创生之关联
“自明治二年(1869)6月29日感明治天皇之御思而建东京招魂社伊始,经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之名一直延续至今”。[注]参见靖国神社网站对自身由来的介绍,http:∥www.yasukuni.or.jp/history/index.html。与一般神社多以日本神话传说中的某一具体人物为主祭神不同(如伊势神宫内宫以天照大神为主祭神),靖国神社的主祭神却是特定的复数——“英灵之忠魂”。既然涉及“特定”,那么就必然有一预设的选择标准,即能成为“英灵”必须要忠于明治政府并经过明治政府认定。“英灵之忠魂”的标准充分体现了招魂社设立之初衷,也就是明治政府通过行使“英灵之忠魂”的解释权和选择权,诱导民众向以天皇为政治象征的自身效忠。所以在靖国信仰确立过程的背后,天皇、明治政府及明治元老的影子总是若隐若现。
建立招魂社的原始文件是1868年5月10日发布的题为《关于在东山祭祀癸丑以来殉难者事宜》和《关于在东山祭祀伏见战争以来战死者事宜》的两份太政官布告。[注]「太政官布告第385号」「太政官布告第386号」,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第一卷,东京:原书房,1974年,第159-160页。当时日本内战的局势尚未明朗,由维新派政府官方举行祭奠本方死难者活动的设想,无疑有助于在内战中划清敌我界线、占领道义高点以增强本方的凝聚力。但随着战局的推进,战线逐渐从天皇所在的京都转移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真正的政治中心——幕府将军所在的江户(后来的东京)。所以明治政府初次大型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是1868年6月2日在江户举行的,这时距离5月3日新政府军接管江户仅有一个月的时间。这场空前祭祀活动的执行者是皇族出身的东征大都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公卿出身的天皇近臣三条实美。明治政府由此开创了通过慰灵以向其效死者提供灵魂归宿,并为生者提供精神慰藉,激励其奋勇效忠的政治操控式信仰,因而意义重大。靖国神社宫司贺茂百树在其主持编纂的《靖国神社志》中提出“这场祭祀可称东京招魂社的源头之一”。[注]賀茂百樹編:「靖国神社誌」2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16146。
政局初定,从京都转移到东京的明治政府便开始花费大量心思筹建东京招魂社。被后世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便提出过“在经过战斗洗礼的上野建设东京招魂社的方案”。[注]妻木忠太編:「木戸孝允日記」明治二年正月十五日条,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075389。虽然木户在明治政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最后被采用的却是在陆军任职的大村益次郎[注]大村益次郎是日本陆军军人,被尊为“日本近代军制之父”。明治二十六年靖国神社专门在社内修造了大村益次郎的铜像。所建议的“九段坂上三番町幕府陆军屯所旧地方案”。一方面,正如木户所指出的“上野处清净之地”,但清净也意味着僻远,与此相对“九段坂上”却毗邻天皇的皇居。到底选择适宜宗教活动的清净之地,还是选择具有更强政治意义的天皇脚下,从明治政府创设靖国信仰的目的推演,其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日本军方对靖国信仰的影响力不可忽视。1869年6月28日,东京招魂社落成并将鸟羽伏见之战以来新政府军的3588名战死者合祀其中。次日,军务官知官事小松宫嘉彰亲王以祭主的身份举行了第一次合祀祭,而副祭主同样是作为军方代表的军务官副知官事大村益次郎,之后东京招魂社也被纳入由军务官改制而成的兵部省管辖。
日本军方对靖国信仰影响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在认定“英灵之忠魂”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发言权。1881年内阁书记官就补充“英灵之忠魂”问题向宫内省提出照会:
嘉永癸丑以来殉难死节者之履历书,……由各府县发出者,内务省次第将先般诸书类送达我官。然事迹查核,若由贵省着手,则可望尽速达成是也。……附别纸为武市半平以下八十人之履历呈报贵省,以供判断。[注]「公文録」,编号029711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从照会的内容可以看出,按照表面的程序,“英灵之忠魂”的认定应该是由内务省、内阁书记官和宫内省协商决定的。但实际上内务省、内阁书记官和宫内省三者的决定并非最终的结果,“最终必须经过与陆军省、海军省的协商才能进行合祀”。[注]高田祐介:「明治維新志士像の形成と歴史意識」,『佛教大学歴史学部論集』第2号,2012年,第43-70页。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军方在政府中话语权的急速膨胀,军方甚至取得了单独拟定合祀者名单的权限。1898年9月30日举行的第25次合祀把“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战役中,在战地因疾病、灾害或其他有关出征事务的死难者”都列入了合祀范围,而这样做的依据则是陆军大臣桂太郎发布的一份“陆军大臣告示”。[注]賀茂百樹編:「靖国神社誌」98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16146。到后来,合祀者的选定程序变为“由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选定后上奏天皇,获得天皇核准即可进行合祀”。[注]春山明哲:「靖国神社とはなにか―資料研究の視座からの序論」,『レファレンス』2006年7月号,第49-75页。此时,在靖国信仰背后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唯一拥有超乎军部之上影响力的就只有天皇一人。
其实,天皇本身在靖国信仰中占有最为关键的地位。靖国信仰与靖国神社(含其前身东京招魂社)同步产生,如过说靖国神社提供的是祭祀的空间,靖国信仰提供了崇拜的对象,那完成这个祭祀活动的主体则是被奉为“现人神”的天皇。
靖国神社在其网站上充满自豪地提道:明治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明治天皇首次参拜招魂社,并作御歌“为我国尽忠之人,武藏野的玉垣,至今仍悼念其名”。这是天皇对创建靖国神社初衷的训示,即“为了祭奠为国家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的御灵,并将其事迹永传后世”。甚至连靖国神社社号中的“靖国”二字,也是明治天皇御赐的,其中包含了天皇对“祖国平安”和“建设和平国家”的祈愿。[注]「靖国神社の由緒」,http:∥www.yasukuni.or.jp/history/index.html。《靖国神社志》中更是直白地宣称“与天皇的特殊关系”正是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的最大区别,这集中体现在“例祭的日期由敕定决定、实施祭典时会获得敕旨认可,以及天皇会在例祭时派遣敕使作为自身的代表”。[注]賀茂百樹編:「靖国神社誌」1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16146。
在明治天皇主导下,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其意义并不简单,背后隐含着靖国信仰的内核由传统的“镇魂”向“祭祀”与“彰显”并重的转变,这也是靖国信仰在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下最终得以完成的标志。“对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独立或统一、为获得领土而进行的对外战争、帝国主义活动等)战死者的追悼和纪念,是与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伴生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本也不例外,选拔英雄再将其赋予特殊意义,并构筑记忆装置将之转化为国家记忆,这是明治时期新生的民族国家日本所要面临的课题”。[注]Fabio Rambelli:「靖国神社と近代日本の歴史記憶の問題」,『札幌大学総合論叢』第26号,2008年,第119-124页。传统以面向彼岸世界为主旨的“镇魂”已经不能满足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由具有现人神地位的天皇彰显死者对国家之功绩、给予死者无上之哀荣,将信仰赋予面向现世的价值取向,才是当时日本“祭政一致”官方宗教体系的发展方向。毕竟,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一系列措施,明治政府在国内建立中央集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尤其是1879年3月,日本通过彻底吞并琉球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东京招魂社在同年更名靖国神社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偶然。因为接下来的日本所需要的恰恰是一种能蛊惑民众投身对外扩张战争的精神麻醉品,即使这种“信仰”的内容其实完全背离了日本文化传统。
三、靖国信仰与神道传统的乖离及其背后的逻辑
建立在“万物有灵论”的文化原型之上的神道教原本并不对“灵”加以甄别,不但神灵没有绝对的善恶,人死后的亡灵也不再区分敌我。在日本的传统信仰中,“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祭祀”。[注]刘江永:《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5-61页。甚至连平安时代“大逆不道的叛臣”、企图自立为天皇的平将门,在死后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其“怨灵”的恐惧,也得以享受祭祀。[注]包括平将门在内,日本历史上有所谓三大怨灵,即菅原道真(太宰府天满宫)、平将门(御首神社)、崇德天皇(白峰神宫)。三者死后都受到很好的祭祀,香火绵延至今。这一点即便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也不例外,“当年丰臣秀吉发动战争,出兵侵略朝鲜,在战后,日本人也是将双方战死者的‘亡灵’共同祭祀的”。[注]孟威:《一个日本学者眼中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第78-85页。然而在靖国信仰中,不但只有在为天皇进行的“圣战”中战死的人才能得到祭祀,而且所有的死者还都成为了不可分割且具有神性的“一柱”。从神道教的历史看,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关于靖国信仰中选择特定的“英灵”单独祭祀的现象,日本学者梅原猛直言不讳道:“靖国信仰完全脱离了传统的神道。如果以《古事记》中的神话系统作为神道教的传统,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事记》中涉及的神社有两个对立的系统。一是天皇祭祀自己先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被天照大神一系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二者相比,反倒是出云大社修建得更加宏伟。出于镇魂的目的,将权力斗争中被消灭的一方的神社修建得比祖庙更宏伟,这才是神道的传统。”[注]梅原猛:「靖国は日本の伝統から逸脱している」,『世界』2004年第9期特集「靖国問題とは何か」,第1页。
更何况,神道教(包括唯一神道、伊势神道等诸教派)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民众信仰中并不居于垄断地位。在江户时代,神道教的灵魂观还要面临其他宗教的挑战。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时的明治政府不仅要在政治上完成统一,还希望在精神上垄断民众的信仰。有学者将明治政府“独尊神道”形容为:“以近代日本为现场,国家、民众以及宗教人士关于灵魂安置之所的争夺战。”[注]永岡崇:「霊魂をとらえ損ねる——神の声から考える民衆宗教大本——」,『人文學報』总第108号,2015年,第143-158页。笔者则认为,明治政府推动的信仰垄断之实质,就是靖国信仰所推崇的“一元灵魂观”这一想象中的“复古”传统,对民众所信“多元灵魂观”的覆盖。由于日本民众的“多元灵魂观”根深蒂固,所以笔者更愿意用“覆盖”这一动词来描述明治政府主导的宗教改造。这意味着“多元灵魂观”并未被彻底抹消,明治政府用“一元灵魂观”来替代“多元灵魂观”,只是用修正纸遮蔽了日本文化真正的传统,却不能改变其存在。既然民间的信仰难以彻底根除,那明治政府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创造一种所谓的“传统”呢?这大概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阶级状况,便会发觉“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领主制国家,资本主义还较弱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当然,他不可能去领导明治维新”。[注]吴廷璆、武安隆:《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在明治维新这场被吴廷璆先生称作“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尽管新上台的“藩阀”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又几乎都出身旧封建武士阶级。加之当时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相对而言旧武士阶级的力量仍不容小觑。既要推动日本尽早加入西洋列强的队伍,又要适当地考虑旧武士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为了兼顾二者,明治政府的诸多政治活动都需要披上旧的外衣后再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尽管明治政权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却需要用“王政复古”的旗帜、“太政官”这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封建色彩的粉饰。靖国信仰也是如此,它只是借用伊势神道的形式,性质却是为资本主义侵略战争进行精神动员。
如果说明治天皇参拜伊势神宫是利用“万世一系”神话,以“孝”道控制日本人的话,明治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则通过“为天皇殉难者”的神圣化,用祭祀“英灵”的仪式,把所有赞同者团结在一个以“忠”命名的、封建色彩浓厚的道德集团之内。虽然这个道德集团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但是集团一旦形成,就有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基于它在物质上的无上地位,而是由于它被赋予了道德的权威。凭借其道德权威优势,靖国信仰集团得以对其成员发号施令,号令成员按照规则(义无反顾为天皇牺牲)行事。面对集团的强大力量,个体不仅会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威慑,还会因为内心引发的尊崇感情而自愿遵守集团所制订的规则。这样,集团对成员的道德作用不是外在的规定,而是内化于心灵的文化;成员服从于集团的指令,也不是因为强大的集团足以战胜个体的反抗,而是因为集团是受到尊崇的对象。
靖国神社自称基于国家神道的靖国信仰是“天地悠久之大道”,是日本文化传统之一。显然这种说法是非历史性的。参照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靖国信仰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明治维新后创造出来的,它与伊势神道中“万世一系”的神话相辅相成。“天皇的‘神圣性’是日本政府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依据,天皇的‘御稜威’是战争胜利以及与其关联的世俗幸福生活的保证”。[注]张博:《近代天皇信仰的制造与侵略战争》,《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32-38页。因而,在“万世一系”神话中得到统治正当性和神圣性保证的天皇,又成为了靖国信仰之神圣性的理论依据。靖国信仰正是通过将“为天皇殉难者”神圣化,把所有的赞同者团结在一个道德集团之内。集团的道德权威令其内部的个体淡忘了个人的牺牲,把感情投射到想象的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耀。经过这一类似炼金术的过程,一种“天选之民”的自我定位披上宗教的外衣,将“本国中心主义”内化入日本国民的心中,化为强大而自觉行动的力量,而宣泄这种不断膨胀力量的出口则是对外侵略。这也就是明治以来的日本政府鼓吹靖国信仰背后隐含的逻辑。
四、结 语
通过分析,本文将靖国信仰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靖国信仰尽管假借了神道教的一些宗教仪式,但其内涵悖于神道教乃至日本文化传统。真正的神道教虽然是日本的本土宗教,但在发展过程中,其主流一直是开放和相对主义的,它从诸多外来文化中汲取过养分。而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神话在明治以前的神道教中从未居于完全主导的地位。为天皇而死的人会化为带有神性的“英灵”,这个信念是明治维新以后才被发明的。
其次,靖国信仰之所以会与神道教的传统有如此大的乖离,根源就在于它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是明治政府为巩固政权和发动侵略战争人为创造出来的。靖国信仰在明治政府主导下被创造的过程恰恰暴露出其本质属性。
最后,战后日本围绕靖国神社衍生出各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方不愿正视靖国信仰的实质乃是维护“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明治政治体制的精神工具。在靖国信仰中,只有那些被政府认定为殒身于奉“万国之总帝”的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者,才会得到祭祀,而对死者的祭祀又变相成为了对他们所献身的“圣战”之肯定。战前,“英灵”在庆祝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登基的“建国纪念日”获得祭祀;战后,政治人物在“终战纪念日”慰问“英灵”。这两个值得玩味的日期把“英灵”与“天皇”永久地捆绑在一起,哪怕这种捆绑早已非天皇所愿。[注]普遍认为昭和天皇对于在靖国神社祭祀甲级战犯持保留态度,因此在1978年合祀完成后,日本天皇再未踏足靖国神社。
事实上执掌靖国神社的宫司对天皇之态度也并非表面上那般谦卑恭顺。靖国神社宫司小堀邦夫在2018年6月20日举办的内部学习会上抛出“(明仁)天皇似乎想要摧毁靖国神社”这样妄揣上意的大不敬发言,[注]「陛下は靖国を潰そうとしてる」靖国神社トップが「皇室批判」,https:∥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378852。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靖国神社内部围绕皇室问题一直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另一种声音。对天皇表面上的尊崇并非基于神道的教义,而是为了借助天皇的威信来巩固自身。在这一点上,今日靖国神社的神官与当年出身藩阀势力的明治重臣倒是不谋而合。
2019年是靖国神社建社150周年。从2018年开始,靖国神社就围绕“明治维新与靖国神社建社”的主题在游就馆举办特展,大肆宣传明治精神与靖国信仰血脉相连。由此可见,明治时代遗留的靖国信仰幽灵仍然游走在现代日本政界与普通国民的生活之中,这也就是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