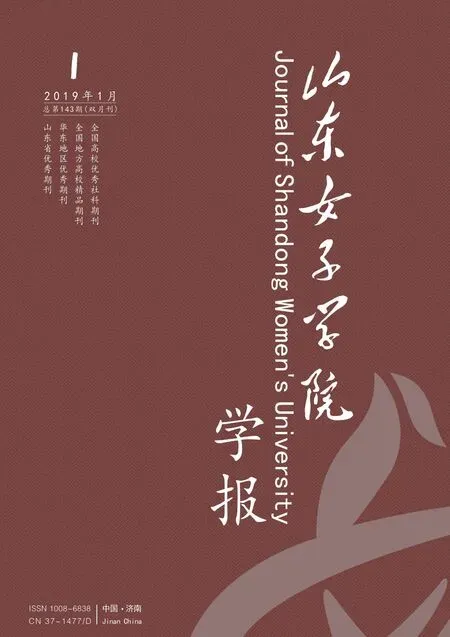试论1990年代后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漂泊意识
翟瑞青, 耿聪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3)
1990年代以后,王安忆作品中对“漂泊意识”的书写,从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与逃避的繁琐生活入手,真实而又清醒地描绘了广大女性群体因漂泊而经历的离合悲欢,以及漂泊过程中细微的感受和体验,从更纯粹、自然的角度展现了人物的生存状态,以追寻生命的真谛。
一、女性漂泊意识在王安忆文学书写中的具体呈现
王安忆对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在其文本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具体表现为因求生漂泊、寻爱漂泊以及寻根漂泊这三种具体方式。
(一)因求生而漂泊
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最低层次也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指的是对食物、水、空气、睡眠等的需要。笔者要讨论的王安忆作品中的为“求生”而漂泊中的“求生”即是如此。
为“求生”而漂泊,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漂泊。在当代社会,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务工,因为生存搬迁到异地,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不少因求生而漂泊的人。
王安忆写过不少关于保姆题材的小说,《富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富萍》中以主人公“奶奶”和吕凤仙为代表的扬州女人们从年轻时就到上海当保姆,这类女人多无依无靠,无夫无子,为了生存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连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特殊文化符号。
《富萍》中的“奶奶”到上海几十年,一直在被上海市民定义为真正上海的淮海路做工,侍奉过无数个东家。以“奶奶”为代表的保姆们一直生活在上海,比年轻一代的人更懂上海。她们熟知上海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能对发生的上海故事追根溯源。可是,尽管如此,“奶奶”们依然融不进上海这座城市,“奶奶”一但有了“那岔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1]。她们走在大街上,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乡下人,容易让人一看就知道其身份是保姆。
为了生存,“奶奶”们离开家园,作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联结者,她们因为漂泊者的身份而失去了一种纯粹的归属。她们努力融入城市,却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城市文化。她们若回归乡村,也因为长期的疏离,而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根系而被乡村文化环境残忍拒绝。正因如此,“奶奶”才过继了孙子“李天华”,随时做好“告老还乡”,回乡下“颐养天年”的准备。也正因如此,在上海棚户区艰辛生活的舅舅、舅妈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上海的外省人,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上海居民的身份。
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也写了不少外来务工者。主人公秧宝宝迫不得已去温州做生意的父母、神秘的“打工妹”黄久香、每到夜晚就聚集在镇碑路大树下的“江西人”“河南人”……作家写他们的生存遭遇,写他们的“惺惺相惜”,以及他们不被城市接纳的孤独和无奈。这些为了生存而奔波漂泊的底层劳动者们好似在城市中游荡漂离的“鬼魂们”,无着无落,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安放之处。
《富萍》中始终以外人身份寄存在他人家的“保姆们”、居住在上海边缘地带的棚户区的居民们……这些为了生活而不得已奔波漂流在外的人,即便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遭到排挤,但仍不卑不亢地面对苦难努力经营好生活的热切,使得她们勤劳、质朴的特点得以放大。原本已被命运定义了归宿的富萍,不服从命运的安排,义无反顾地选择“出走”,哪怕前方是更加艰辛的漂泊旅程。
王安忆写这些外来的女性底层漂泊者们,一方面倾注了自己对她们的同情和关注;另一方面,也欣赏着她们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精神,努力发现她们生命中的闪光点。
(二)因寻爱而漂泊
因寻爱而漂泊,这里的爱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和情感上的寄托。与男性相比,女性因为自身性别的特点,更注重生命中细微的情感体验,对爱情、婚姻的期许和体会要比男性的感受更加复杂和丰富。故而才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2]的警训。可即便如此,无数女性在寻爱的过程中依然可能迷失自我,她们会困于现在,惶惑于未来。王安忆遵从现实来写女性的“寻爱”遭遇,以及女性因“寻爱”而开始的无所归依的精神漂泊史。
王安忆在《我看〈情人〉》中曾说,爱情其实是我们在漂泊无定的生涯中攀附的立足之地,为我们疲惫紧张无根无望的灵魂寻找归宿,它带有岸的面目。王安忆笔下的不少女性因为爱情而漂泊,在她们看来,爱代表了安全、保障和归宿。可在王安忆看来,爱情并不是女性真正的彼岸,它不过有恰似岸的面目,带有迷惑的性质。短暂的温暖体验过后,女性仍然改变不了要继续漂泊、继续寻觅的命运。
女性寻爱的过程是艰难的,寻爱的过程就是精神漂泊的过程。甚至在拥有了爱情之后,她们也经常因为自己的患得患失,而体会不到爱情带来的温存与美好,从而陷入更加孤独寂寞的处境。《长恨歌》是一部寻爱史,“通读《长恨歌》,每个人的爱情都是那么孤独,而每个人都在以爱情拯救人性的孤独和漂流”[3]。《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身边周旋了无数的男人。从最初的程先生,到连真名都不肯透漏的李主任,再到懦弱无责的康明逊、极度自恋的老克腊,兜兜转转,浮浮沉沉,王琦瑶周旋其中,也深陷其中。
程先生的懦弱与多虑使他对王琦瑶只有爱的想法却没有爱的能力。康明逊虽是绅士,体贴又懂情调,但危难来临时也是只求自保,给予不了王琦瑶应得的名分。极度自恋的老克腊只因为留恋王琦瑶身上的那点旧风情而与之产生“畸形恋”,与其说是爱王琦瑶倒不如说是更爱自己。王琦瑶最终选择了李主任,是因为李主任可以给予她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和需要。后来李主任飞机失事,王琦瑶失去物质保障,不得已再次踏上寻爱之路。她希望用寻爱来结束自己精神上漂泊无依的处境,但最终却无奈飘浮一生,一直寻爱未果。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在拥有了比尔的爱情之后,一直妄图抓住爱情,可比尔一句“不能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谈恋爱”把阿三与他的界线划分得一清二楚。比尔喜欢的是阿三中国女子的身份,于是,阿三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比尔心中中国女人的样子。阿三努力地迎合比尔,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不断改变自己。这表面上看似是回归中国文化,实则是努力地向西方文化靠拢,她愈是靠拢,比尔便愈是后退。阿三在失去比尔后,偏执地与外国人交往,在寻爱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堕落、毁灭。
《富萍》中的富萍也是如此,她最终没有选择寡淡的李天华,而是决定与残疾的年轻人结合。富萍原以为找到了自己爱情的归宿,拥有了稳定安宁的生活。但小说的最后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写富萍怀孕,这也恰恰暗示了富萍为寻爱而付出的代价,富萍与其下一代漂泊的命运不过才刚刚开始。
王安忆试图通过自己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来说明爱情不是女性的归宿,它不过是命运漂流过程中的一条船,带有岸的性质;可事实是女性在停靠后仍要继续漂流,继续寻找,继续无所归依。
(三)因“独立”而漂泊
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男性主导一切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不像男性一样独立自由,凡事都要听命、依从于男性,更没有机会外出漂泊。
王安忆所处的时代,女性开始进入社会,不再遵从传统意义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指令。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女性在进入社会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急需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由此就有了因“独立”而漂泊的现实。
但几千年来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人们对以男权为主的父系社会文化不自觉的认同,外界种种因素对女性群体的约束与改造……这些现实遭遇使得广大女性在进入社会后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刀霜剑严相逼”。女性进入社会虽然实现了表面上暂时的“独立”,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使得女性仍然作为弱势群体而漂泊在社会中。
富萍来到上海后见识了崭新的世界,尤其在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后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富萍看到奶奶、吕凤仙等人尽管看起来风光体面,但实际上依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默默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富萍看到了自己与女学生们生活的根本差异,当她看到爱撒谎的“跟屁虫”拖着一大堆弟弟妹妹时就好像预见到了自己以后的人生。富萍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选择离开自己的未婚夫李天华,和一位残疾青年生活在了一起……富萍的这一重要抉择遵从了她自己的意愿,她要自己选择生活方式。富萍有觉醒的意识,希望过上自由独立的生活,改变被别人操纵的人生。
与富萍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以及《我爱比尔》中的阿三。王琦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食其力,取得了护士资格,并以此谋生。阿三虽然依赖比尔,但她在物质上始终是靠自己的能力,靠卖画为生。尽管如此,生活并没有因为她们的独立觉醒而给予其优渥的待遇。王琦瑶在独立与依赖之间自我挣扎,阿三则在尝试了短暂的独立后选择自暴自弃而走向堕落。
王安忆身为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对整个变革的社会环境的感悟要比普通女性更多。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希望女性在生活中同男性一样能找到归属,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她在思索、追问,拷问进入到社会中力求解放的女性是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女性追寻独立的过程实则就是离开原生家庭在外漂泊的过程,这一选择使得女性又陷入了新的生存困境,愈是寻求独立,就愈要学会独自面临生存压力,独自面对漂泊在外的境遇。
现实中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不存在,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时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并不能让她们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不少女性选择看似如娜拉般壮烈地出走,实则多是自身无法控制客观环境和改变自身境遇的无奈之举。她们只能在追求独立中继续漂泊,在漂泊中不断追求独立。
二、王安忆文学书写中女性漂泊意识的共性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其漂泊境遇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伴随漂泊过程始终的孤独寂寥、个人无法逃离漂泊的宿命、在漂泊过程中对自己的家族文化根系的追根溯源。
(一)漂泊与孤独
王安忆写漂泊带给人的“孤独”,通过人物生命的遭遇写孤独带给人的生命体验。“她的孤独,是她对普遍生态的感悟、发现与描述,其中饱含着理解与悲悯,由此,她比先锋派充满形而上意味的孤独更平易、更实体化,在对隔离处境的表达中奇异地实现了与民间的无限切近与融合。”[4]其小说《纪实与虚构》是作者写自己的一部“孤独史”,孤独体验的最大来源是我“外来者”的身份以及“我”本身脆弱敏感的心灵。
《纪实与虚构》中,作者写未满周岁的“我”随着打着腰鼓扭着秧歌的同志们,坐在火车的痰盂上,跟着母亲一起漂进了上海。来到上海后,母亲“同志”身份的特殊,要求我们不准与弄堂里的世俗市民来往,环境交流的阻隔使我觉得孤独,感觉被周围所抛弃。
母亲明明会上海话,却要求我们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语言上的隔阂使“我”感到难堪不已。“外来户”身份的自我暗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阴影。童年的“我”对上海没有任何的归属感,尽管我渴望进入上海,但是“我”并没有把上海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孤独感一直伴随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从始至终,“我”都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人而存在。此外,母亲、小五、张先生这些人也是孤独的,他们的孤独是由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造成的,缺乏沟通、彼此隔离,于是人们便陷入自我臆想、自我封闭的状态中,精神上也始终处于放任漂泊的状态。
《长恨歌》中作者写王琦瑶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寂寞与孤独处境,写上海这座城,写它的世俗与灯红酒绿,及其战争动荡背景下的觥筹交错、兴衰荣辱。王琦瑶的孤独是自己选择的孤独,这孤独是小众的,虽是平常,但却最显示悲剧性。她的无所寄托、无依无靠,从踏进“爱丽丝”公寓的那刻起就已命中注定。愈是繁华的外境,也就愈彰显出个人精神的无所归依,漂泊孤独。
《我爱比尔》中的女主人公阿三同样是孤独的,只不过她的孤独带着太多自我和极端。阿三是一名画家,她热爱艺术,性格孤僻,后来认识了年轻帅气的美国外交官比尔。阿三是真心爱比尔的,比尔离开后,阿三承受不住失恋的打击,陷入更加孤独的处境。她开始自我否定,开始为恋爱而恋爱,出卖自己的身体,无可救药地堕落下去,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抛弃了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失落感、寂寥感、沧桑感、萧瑟感,这些都是个人漂泊过程中产生的孤独体验,带有一定的悲剧意蕴。王安忆擅长写孤独,漂泊与孤独是王安忆对于女性漂泊意识书写的一个典型特点。
(二)漂泊与宿命
命运,是一个带有玄学色彩而又很难阐释清楚的现象,它裹挟着看似永远无法预测但似乎又一切都早已命中注定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对之既恐惧又敬畏,既畏缩又反抗。古代儒家学说宣讲的“天命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体现的“宿命观”,似乎都在告诉世人愈是妄图摆脱命运的摆布便愈是深陷其中而遭到命运的戏弄。
正是由于命运的不可预知性和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在命运之中始终处于被动无奈的位置,默默承受着命运带给人的苦难。在王安忆看来,人类没有归宿,漂泊是永恒的,个人逃脱不了命运的戏谑安排。故而对于漂泊的书写,特别是女性漂泊的书写,王安忆往往把其与宿命联系起来。在《伤心太平洋》中,作者指出,漂泊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将永远处于不断的漂泊之中。
《长恨歌》中最能体现宿命漂泊的就是主人公王琦瑶这一悲剧人物。综观小说,王琦瑶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被预设好了,她的命运从接触“片厂”开始,从看到“片厂”拍戏的那幕场景落幕。
王安忆以“戏”作比喻,颇有象征韵味,暗喻着人生的虚无和不真实。王琦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般的命运,一切不过皆是虚妄的存在,如泡影、浮云般到头来竟是一场空。这无疑给人一种苍白和凄凉的感觉,加强了宿命感和悲剧的意味,让人为之叹惋、感伤。
小说以《长恨歌》作为题目也颇有暗示之意,“那一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却是《长恨歌》中,杨贵妃玉殒香消,魂魄在了仙山的情景。阿二不由生出悲戚来,他想起的美人图,全是不幸的美人图,正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5]自古“红颜薄命”,萦绕在王琦瑶身上的也是美人薄命的不幸气息。
上海在改变,王琦瑶也在改变,但这改变是被动的,入不了时代变迁的法眼。王琦瑶似乎难逃宿命,历经沉浮、几经辗转,一颗漂泊无依的心始终没有归处,开始如此,结局仍是如此。
王安忆在作品中描述的保姆们也是如此。保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连接着上海与其他地方的文化。她们自出生时起,就逃离不了命运的预设,世世代代的传统延续下来,就好像有了一个生来就要做保姆的使命,也似乎注定了个体势必漂泊在外的命运。
宿命般的人生使个体生命均无法逃离命运早已织好的天网,这些意识都彰显在王安忆对女性漂泊意识书写的作品中。
(三)漂泊与寻根
以往的中国文化不论是历史的纪实还是文学的虚构,都以男性为中心。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中,女性很难找到自己的精神归栖之地。即使是在养育自己的故乡,哺育自己的家庭,女性始终要嫁作他人妇的命运也让她们很难找到系根之地。
女性漂泊不同于男性漂泊,男性漂泊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而女性在古代史上没有外出漂泊的机会,这使得她们始终作为“深闺者”的形象而存在。历史留给她们的标签只是等待和守望,女性寻根却无根,这就决定了女性在精神上得不到如男性一样以故土文化为自己血脉根源的安全感。
在《纪实与虚构》中,幼年的“我”随母亲从江浙移居上海,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深切感到自己与上海本地人的差异。王安忆及其家庭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使得她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恰当的归宿,让自己能在上海这座城市落地生根。“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6]仿似“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6]王安忆描写“我”的邻居小男孩家隆重繁琐的祭祖仪式,祭祖寻根这一古老的文化仪式看似与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极不协调,但从王安忆字里行间的描写中依然可以感到她对小男孩家庭这种传统仪式的羡慕。作者在文本中自我探求、追本溯源,回归到家族历史,去努力追寻自己家族文化血脉的根系。
作者想从追寻自我家族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系,结束这种精神上的漂泊无依状态,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祖先不论是母系家族还是父系家族在历史中也是处于长期漂泊的状态。
王安忆通过无根、寻根、寻根未果、依然寻根等一系列的书写创作,把漂泊与寻根相连接,不论是对家族文化的追根还是对民族文化的溯源,她一直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
三、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漂泊意识形成的缘由
(一)作家主体因素
上海对王安忆来说,无论怎样都不是其灵魂与心灵可以驻足的地方。王安忆对于上海而言,也仅仅是一个“寄宿者”的身份。1954年出生的王安忆,在不满周岁时便随母亲迁至上海。作为一个孩子,幼小的王安忆所表现出来的与这个城市想要热切融为一体的愿望被一次又一次打击,所居弄堂里发生的所有或新奇或平淡的事都与她没有关系,她根本无法真正参与其中。
这种童年时期形成的性格让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始终持着疑惧的态度与观望的距离,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始终抱着“不确定性”的认知态度。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来户,似乎没有一种确切的身份来证明王安忆的存在。王安忆所感受到的人情与世态都让她有一种深刻的疑惧,自身外来者的身份,使她没有办法真正接近上海这所现代化都市的灵魂。
所谓上海的真正灵魂正是植根于弄堂、石库门里,植根于真真正正的小市民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当中。尽管生活在上海,因为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差异,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灵魂的这些精髓并未真正熟知与了解。
此外,王安忆的作品之所以有浓重的漂泊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作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投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根”意识。在王安忆的观念中,城市人是没有根的,她据此创作了《纪实与虚构》,在现实和历史的接轨之处以一种虚构的方式重塑了现代城市人的历史。
王安忆写漂泊、写寻根,这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还是她通过虚构和想象来满足对现实的弥补所获得的精神上的自我慰藉。王安忆重视家族文化的血脉渊源,但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漂泊感使她对家族文化根系的追寻达到了热切甚至偏执的程度。
正是因为创作主体具有强烈又清醒的文化观,才会在自己缺失这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强烈的诉求来实现,由此可见,王安忆作品中的漂泊意识不仅有现实的因素,也带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具有独特的意义。
除了创作主体强烈的无根意识之外,这种诉求还表现在作者选择了漂泊的另一种隐性形式——写作。
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提及成年后的“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认为写作的过程实则就是在自我反思、自我对话、营造自我空间体验的过程。王安忆热爱写作,对她来说,“书写真是一件快事,它使一张白纸改变了虚空的面貌,同时也充实了我们空洞的心灵”[7]。王安忆自小敏感细腻,对生活的体验关照更是感触深刻。她多思善感的性格加上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历使得孤独感和宿命感时常萦绕其身。王安忆意图通过写作这种形式把现实中无法纾解与排遣的矛盾心理转移,甚至通过写作来弥补现实的缺憾。但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持续漂泊的过程,写作过程中精神漂泊所获得的体验与感受甚至比现实生活中的无所依靠还要壮烈与彻底。
1990年代的都市充斥着光怪陆离与人情冷暖,“漂泊”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名词。王安忆1990年代曾旅美游学,异国漂泊的体验,使她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以一个作家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来俯视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的漂泊命运。她通过写作来关照时代巨变下的个人,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来展现漂泊,王安忆选择了写作也就选择了漂泊,写作的过程也是她精神上虚拟漂泊的过程。
(二)客观外界因素
王安忆描写漂泊意识的作品中,给人漂泊体验最明显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顽固的排外性。上海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具兼容并包性。但直至今天,上海的排外性,仍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文化标识而存在。
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与其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有关,儒家文化讲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故而成就了“好客山东”。上海独特的文化精髓使得大部分本地上海人对外来人口持有巨大的排斥性,不管是居于经济优势的上层还是处于底层的小市民阶层。
作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高级人才的引入和外来务工者的加入,势必要与居于上海的本地人争夺宝贵的发展资源和机会。上海人对于这些人的蜂拥而入既惶恐又憎恶,倘若与迁入的人相比,自身没有可与其竞争的优势,那么,上海人居于劣势的处境势必会让他们以宝贵的上海居民户籍身份来压制与反抗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来讲,这应当属于一种对自我及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导致其要摧毁别人的自信,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心理。传统意义上的上海文化,是由小市民阶层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构成的。即便是上海的作家,譬如张爱玲,她写上海,也对上海狭隘的小市民观和精明的市井文化持或隐或显的讽刺态度。上海顽固的排外性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地域文化心理,这种心理表现愈明显也就愈使漂泊在上海的外地人感受愈深刻,漂泊在上海的情感体验也就愈复杂。
20世纪90年代,产业社会化和消费社会化使得宗法制社会迅速解体,传统文化中建构的信念、坚守、理想、道义等文化风尚逐渐被急功近利、欲望膨胀、物质享受所取代,血缘、亲情、文化根系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淡漠。
这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时代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从讲究人情世态的乡村漂泊到追逐经济利润的大都市。农民工离开乡村涌向发达城市所遭遇的现代化冲击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的是人情世态的炎凉与淡漠、自身与家族文化血脉根系的脱离、异地漂泊的无归属感、孤独感……
1990年代的时代巨变,使得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上了商业元素,“文人下海”“文人经商”等一系列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地位从正统与中心滑到了边缘位置,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对正统的精英文学的嘲弄足以看出经典文学正遭受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中的人总是被不断发展的文明所异化,这也使作家产生了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考。时代是反映作家创作的一面镜子,同样,作家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者存在着相互渗透的意义,王安忆具有“漂泊”意识的作品,便具有这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总之,随着创作水平的提升和思想意识的深化,王安忆在1990年代的创作不仅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有所改变,而且也开始进入到对女性自我进行深入认识和剖析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的精神和灵魂领域。1990年代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潜藏其中,这对王安忆来说是个突破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