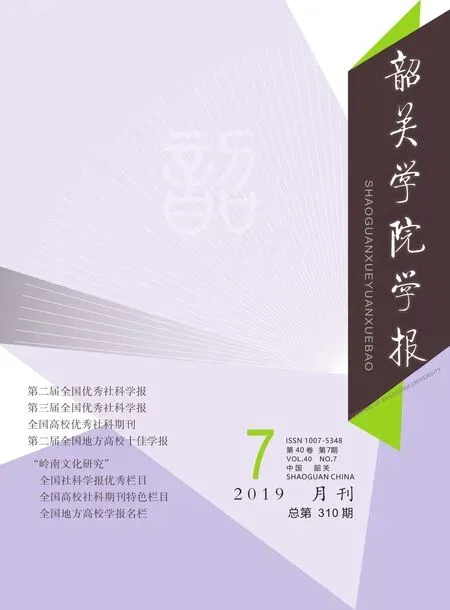论《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的石刻文学景观价值
江朝辉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 来宾545004)
《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以下简称《纪铭》)是广东目前发现石刻中年代最久远的汉碑,其作者学界虽尚有争议①,但该碑的年代及其在广东石刻中的史学、文学、书学价值却受到方家一致肯定。桂阳郡又因跨越湘粤,据《汉书·地理志》载:“桂阳郡,高帝置。县十一: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浛洭、浈阳、阴山”[1]。大致包括今郴州的各个县区,衡阳、永州部分地区,广东北部,如阳山、浛洭、曲江、浈阳等部分地区。碑载于乐昌县西武溪,武溪,又称武江,古称溱水、泷水,发源于湖南临武,在韶关市区沙洲尾与浈水合流,称北江。从秦汉开始乐昌峡就是广东四大关隘之一,而乐昌因南越王赵佗驻守的缘故又名赵佗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岭南交通要道。碑文记载了汉桂阳太守周憬开凿粤北泷水河道便利交通的功绩,宋人洪适《隶释》收录全文,欧阳修《集古录》、曾巩《南丰类稿》、赵明诚《金石录》、刘昌诗《芦浦笔记》、赵一清《水经注释》等二十余种著作对此碑皆有考证。今人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辑校和研究》对碑文进行了很细致的辑对[2]。但除传统金石学、文献学考证与辑校外,对该碑的文学研究成果却鲜见,后代学人多次题咏,形成广东一处重要石刻文学景观。文学景观“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在于除了它的人文属性,还有文学属性。”[3]《纪铭》以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及历代文人的应和题咏,形成具有独特人文价值与岭南文化意蕴的石刻文学景观。本文将该碑置于广东石刻文学景观的宏观地图中,探究《纪铭》的文学价值,彰显此碑作为石刻文学景观的影响和价值。
一、《纪铭》的文学价值
屈大均将该碑视为广东一地的文化标杆,比之扬雄。《广东新语·文语卷十一》专列“郭从事碑”,认为“碑文甚奇古,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云”。“东汉郭从事苍,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学能文,举茂才,为荆州从事。灵帝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某,开导昌乐泷,治崄为夷,以便舟楫,郡民颂之。从事为撰《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纪铭》,曲江长区祉勒石泷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4]碑文内容共五段,第一段简述周憬其人及施政措施,“宣鲁卫之政,敷二南之泽”;第二段介绍桂阳郡的地理环境,重点是武溪之险阻,“蛇龙诘屈,沣隆郁浥。千渠万浍,合聚溪涧。”第三段描述周憬开凿之功,“弼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断硠礚之灵波,弱阳侯之汹涌。”[5]36-37第四段记载立碑时间和立碑人,最后一段是铭文,颂扬其功德。
《纪铭》出自东汉熹平三年,它虽偏处岭南,却反映了东汉碑铭的典型性。《纪铭》以立碑故吏所在之郡题碑,是汉碑风尚。又碑主既为官吏,则碑首多有题名,表明碑主身份,与之相似者如《博陵太守孔彪碑》《荆州刺史度尚碑》等。《纪铭》分为两个部分,前为碑序,叙述碑主周府君生平功德,散、韵兼行;后为碑铭,总括碑序事实,犹如史传后之论赞,整齐有韵,以七言兮字句式为主,是汉碑典型的前序后铭的文体结构。东汉时期,“碑文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写作对象的应用文体,有着其特定的语言形式和规范。但是作为东汉文学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同时受到时代审美观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汉碑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的总体特征是与同期的文学变化一致的。”[6]162作为广东石刻萌芽期的扛鼎之作,其碑文语言雅正,体用骈文,可见东汉文学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本文拟从隶事用典和崇尚骈偶两个方面稍作探讨。
“汉碑雅训,词句皆有所本,不可目以剽窃。经子成语,触目皆是。”[7]汉碑多引《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尊经重典。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映了当时社会强烈崇敬儒家经典的心理,以致“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行文亦彪炳六经,稠叠纬侯,构成了两汉文化对经典的特殊依赖。如言功德,以禹、汤作比,《泰山都尉孔宙碑》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罪已。”[8]对《诗经》的引用,如以《诗经·召南·羔羊》喻正直,《卫尉衡方碑》:“兢兢业业,素丝羔羊。”[9]90《淳于长夏承碑》:“羔羊在公,四府归高。”[9]94以《凯风》《蓼莪》吊母氏,如《梁相孔耽神祠碑》:“竭凯风以惆怅,惟蓼仪以怆悢。”[10]《司隶校尉鲁峻碑》:“息睿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构,析薪弗何,悲蓼莪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11]从以上诸例可见汉碑隶事用典的大致情形。碑文以传播美德、铭记功勋为旨,以流传久远为要,具有公共属性,于措辞间更注重雅正之风。在“行文时或化用经书文句以助文笔,或引用经史典故以形容表象,形成语言典奥、风格凝重的特色。”[6]163《纪铭》描写曲江水势之凶险:“泉肇沸踊,发射其颠。分流离散,为十二川。弥陵□阻,丘阜错连。隅陬壅蔼,末鹞骋焉。尔乃贯山钻石,经□□□。□扬争怒,浮沉潜伏。蛇龙诘屈,沣隆郁浥。千渠万浍,合聚溪涧。下迄安聂,六泷作难。湍濑□□,泫□潺湲。”[5]36随即直接引用《诗经》在行文中描写与泷水险状进行对比:“‘百川沸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盖莫若斯。”引用经书文句与描写对象比照,典雅庄重。周府君思夏后之遗训,命良吏、将帅与壮夫凿通水利,“繇是小蹊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5]37此处述写周府君功绩,化用《诗经·卫风·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之句,完全去除原诗讲述一位女子失婚成为弃妇的悲愤,只取其形容商贸繁盛之意。“汉碑中引典,主要用典来形容,以典故比附事实,因此往往可以不分地位,使用随意。”[6]163这种多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将原典熔铸为新的词语的用典,使典故的运用符合碑文表达的要求,意蕴浑厚又颇具新意。该碑虽偏处岭南,但是它的创作特征同样反映出东汉碑文中用典情形的普遍,用典技巧的日趋成熟,显示出碑文用典已经成为东汉文人创作的一种文学自觉,是汉代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骈文在六朝成熟定型,但东汉时期文章整体上开始有了骈化的趋势。“从文章体制上看,东汉中期以后,骈俪之体已渐渐脱胎,成为文坛上的主潮,影响及于各种文学体裁,开始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12]因受时代文风的浸染,碑文的创作也毫无例外地受其影响,具有骈文的一些特点,句式以对仗为主,注重用典隶事。尤其是汉魏“门阀士族文化上追求审美,在诗赋文上就体现为骈化。这是文学形态上的审美追求的结果。”[13]如蔡邕存世四十余篇碑文,虽然其文不尽是骈俪,但传世佳篇,皆以骈俪著称。如《郭泰碑》:“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采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危言之未绝,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14]其中的骈句已较为成熟,文采富丽,音节雅和。而《纪铭》骈散兼行,以骈句为主。其文多为四字句,杂以三、五、六、七等字句,符合骈文尚未完全定型前的文体形态。全文多对仗句,杂是文言虚词承接婉转,如美周府君之德则言:“乃宣鲁卫之政,敷二南之泽。政以德绥,化犹风腾。抚集烝细,□绥有方。进则贞直,退则错枉。”[5]37“乃”字引起,对仗更为工整,亦基本不影响句意。此乃汉魏之风,后唐宋四六文中虚词比例极少。其叙周府君之功句:“断浪漾之电波,弱阳侯之汹涌。繇是小蹊乃平直,大道允通利。”“虽非龙门之鸿绩,亦人君之德宗”[5]37,“繇是”“虽”一词亦类似,而又变动不拘,韵律感强,语言气势充沛,使庄重典雅的碑文平添华美流畅的韵味,气脉通顺,酣畅淋漓,拓展了碑文的文学表现力与感染力。骈文中是否使用虚词,在骈文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取舍过程,在东汉文章逐渐骈化的时代,此文残留虚字是骈文从先秦古文中脱胎而出的演化印迹,而后六朝骈文虚字渐少,至宋四六基本绝迹,到晚清骈文合一,虚词又开始大量出现。文章体现的这个趋势与东汉文学的演进是一致的,是作家审美意识与文学观念觉醒的标志。文章有意识的运用事对、反对等表现力极强的对仗方式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如“鲁卫之政,二南之泽”一句,形象地表达了周君施政岭南时,以平等、宽厚的心态传播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当时民族融合和团结的景象跃然纸上。而文中“君子道长,小人道消”“非龙门之鸿绩,亦人君之德宗”等句,从正反角度展开阐述,已得“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15]之三味。
作为一篇石刻作品,《纪铭》一旦入石,其文字内容与其石质载体,地理环境甚至整个岭南文化背景即融为一体,与虚构性文学景观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抒写景观纪事铭功的抽象文学,而且成为景观的实体部分,在后世的追仰和应和中成为意蕴丰富的石刻文学景观。
二、作为石刻文学景观的《纪铭》
“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6]对于各个地理坐标的石刻作品而言,并不仅仅是记载古人行程,客观描写地貌,抒发一己之思,一旦刻石,它就同原来的地理景物一起,为后人提供了重新认识的可能,折射出不同的情趣、阅历和知识。对于《纪铭》来说,刻石之文乃欲托金石以不朽,目的在于纪念周憬之功德,但此事具有强烈的地理依附性。石刻依景而立,景物因石刻而生发出新的内涵,赋予了景观再创造的空间,后世必多趋附,题咏日多,最终形成石刻文学景观,因此又反过来赋予了景观更多的意义,《纪铭》碑亦如是。要想成为一个石刻文学景观,需要有如下条件:第一,由名家书写成文刻石。第二,作品文学价值高,流传久远。第三,具有一定的审美观赏性的艺术价值。第四,内蕴一定的文化思想或普遍意义。第五,在后代读者中产生共鸣和影响。第六,在遭到自然或人为损毁后,是否重建。当然,并非要全部满足如上条件,如果有几项特别突出即可。而《纪铭》基本符合全部条件,是当之无愧的广东著名石刻文学景观。此碑当时勒立于乐昌县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成为后代尤其是唐宋以后文人迁客拜访题咏的石刻文学景观胜地,尤其是宋代,蒋之奇、陈尧佐、苏轼、陆游、方信孺等名家均在此地刻石,其中蒋之奇《续武溪深》最直接体现了《纪铭》对后世的文学影响,苏轼“九成台”等题刻成为后人如清代翁方纲等追仰、摹刻的丰碑。徐师曾还论及文体学研究中极少有人关注到的碑阴文,将其单列一则,与其他诸文体并列:“凡碑面曰阳,背曰阴,碑阴文者,为文而刻之碑背面也,亦谓之纪。古无此体,至唐始有之或他人为碑文而题其后,或自为碑文而发其未尽之意,皆是也。”[17]不管是他人“为碑文而题其后”,还是“自为碑文而发其未尽”之意,都说明碑阳之文与碑阴之文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因位置的特殊关系而产生意义上的相关性,使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体裁的石刻交相融合,成为意蕴复杂的、具有整体性的景观文本。如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碑阴共有祖无择、向宗道、程师孟、黄佐、阮福、何元锡等撰文、题名十余则;蒋之奇《武溪深诗》题于《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阴,可与之参读;苏轼又于重刻蒋之奇《武溪深诗》碑阴题“思古堂”“九成台”“九成台铭”,方信孺跋刻陆游“诗境”二字于《武溪深》碑阴。
一个景观之所以能成为文学景观,在于其自然、人文属性外,还有文学属性。石刻文学因景而立,相较于纸本文学作品阅读的私密性而言,“石刻这种矗立通衢,或摩崖名山,多在公众易到易聚之处,受众范围大,传播人群无拣择,时间持久,在诸多传播方式中,成为传播文学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人们不经意间最易接受的一种方式。”[18]读者身临其境,既览石刻文中所述之景,又读景中石刻之文,景观既是文本,文本亦是景观,这种景文合一的阅读方式,与披荆除藓、摩挲碑刻的独特阅读体验相结合,使石刻文学景观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鲜明、立体地呈现出来,产生与纸本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文学意蕴。
据《粤东金石略》载:“蒋颖叔续武溪深诗碑,在韶州西武溪亭上,亭今为九城台。碑高六尺,阔三尺五寸。其额正书:‘宝文蒋公武溪深诗’八字。下前刻马援辞,后刻颖叔和续。”[19]180其文曰: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淫!
飞湍瀑流泻云岑,砰激百两雷车音。吾闻神汉之初始开斸,史君姓周其名煜。至今庙在乐昌西,苔藓残碑仅填读。武水之源自何出,郴州武县鸬鹚石。南入桂阳三百里,峻濑洪涛互淙射。其谁写此入新声,一曲马援门人笛。南方耆旧传此水,乐昌之泷兹乃是。退之昔日泛潮阳,曾到泷头问泷吏。我今以选来番禺,事与昌黎殊不类。未尝神色辄惝慌,何至形容遽憔悴。但怜岁晚毛鬓侵,故园一别至于今。溪光罨画清且浅,朱藤覆水成春阴。何为在此婴朝簪,翩然走马驰骎骎。南踰瘴岭穷崎崟,梅花初开雪成林。韶石仿佛闻舜琴,曹源一滴清人心。远民安堵年谷稔,百蛮航海来献琛。嗟余才薄力不任,报君夙夜输诚忱。布宣条教勤官箴,有佳山水亦出寻。乐乎吾乐何有极,不信愁歌武溪深。”[19]180
此诗以七言歌行体的形式,通过追源溯流,从武溪之险状追述东汉周府君治水之功,追古抚今,以古自喻,抒发作者教化百姓之志向,安贫乐道之逸情,与《纪铭》的题材与立意形成呼应。据考,九成台已于1928年韶关市城建中被拆,石亦湮灭。诗中所谓“马援辞”,意指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其门人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寄生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淫!”[20]蒋之奇开篇以引用马援诗句,暗示作者“布宣条教”的雄心,又化用李白《蜀道难》诗句,以穷山恶水的自然和舜琴曹溪之清心形成鲜明对比,而同样是地处荒蛮,“蚕丛”“鱼凫”开国茫然,周府君却有“苔藓残碑”,胜之一筹。作者明写自然中的“武水之源”,实则暗喻周府君的宣教、引导是粤北思想文化之源,因此粤北成为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思想洗礼的地区,故诗中云:“我今以选来番禺,事与昌黎殊不类。”随后,作者刻画自己年老力衰,“岁晚毛鬓侵”又久别故乡,但此地有梅花成林之自然美景,舜琴曹溪之人文遗声,有百蛮航海之交通便利,故应当老骥伏枥,报君夙夜,方不负如来不负周君。
“碑文化是中国人‘立象以尽意’思维方式的体现:‘其称名也小,其联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其事肆而不隐。’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21]一个著名的石刻文学景观,其价值是极其丰富的,有地理的价值,有文学的价值,也有历史、哲学、宗教、民俗、书法的价值,而正是文学的形象性、多义性、感染性和想像性,使石刻和文学、景观结合,人们在游览景观时从中得到人生感悟和启示,比仅仅阅读文学作品或是观看景物要来得更生动、形象、立体,使其从单纯的自然物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特的人文地理坐标。此地重要的石刻还有苏轼《九成台铭》。据翁方纲考,韶州九成台旧名闻韶台,在北城上。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获赦自海南北归经韶州,正月一日郡守狄咸邀之新台之上,同行苏伯固谓舜南巡,曾奏乐于此台,宜名之“九成”,苏轼“即席为铭,自书刻石台上”,惜后元祐党争,碑毁台废。铭曰:
“韶州太守狄咸新作九成台,玉局散吏苏轼为之铭。曰:‘自秦并天下,灭礼乐,《韶》之不作,盖千三百一十有三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则《韶》既已隐矣,而况于人器两亡而不传?
虽然《韶》则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盖常与日月寒暑晦明风雨并行乎天地之间。世无南郭子綦,则耳未尝闻地籁也,而况得闻其天籁?使耳得闻天籁,则凡有形有声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瓠弦。
尝试与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苍梧之渺莽,九嶷之连绵。览观山川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鸟兽之鸣号,众族之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数而均节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利极以安天下,人和而气应,气应而乐作,则大成所谓箫韶九成,来凤凰而舞百兽者。既已粲然,毕陈于前矣。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吉日,眉山苏轼记。’”[19]187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自昌化贬所移廉州安置,六月二十日渡海,七月初至廉,八月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苏轼行至英州,闻玉局之命,故此铭称“玉局散吏”也。是年苏轼在韶州度岁,次年辛巳正月五日过岭至南安军。这篇铭文是为九成台的重新建成而作。在这篇铭文中,苏轼思绪飞扬于辽阔的时空,思考了人为灭绝韶乐与韶乐永存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认为存在于自然之间的韶乐永远无法泯灭。在苏轼看来,《韶》乐是天籁之作。《韶》乐之不作已有一千三百二十三年了,但是消亡的不过是人籁而已,还有远胜于人籁的如《韶》乐的天籁,是“江山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鸟兽之鸣号,众窍之呼吸,往来唱和”的天籁,这才是音律音节自成的《韶》乐之大成。苏轼认为,如果天下安定,人和则气应,气应而乐作,那么这种音乐就会与自然之间的音乐协调,成为天地间的极品,有如传说中的九曲萧韶,能引来凤凰,令百兽起舞。《九成台铭》体现了苏文一贯的潇洒与灵动,将身世沧桑化于造化大象无形的体悟之中。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录《九成台铭》全文,并记:“宋碑不知毁于何时,至我明嘉靖改元壬午,有识之士周叙刻石,丁亥太守唐升又刻之,通判符锡书。”[19]187“九成台上又有明万历十八年知韶州府檇李陈奇谋重修记。又有万历九年广州司理陈绍功省月台记,省月台即九成台也。”[19]190从这段考证可知,元祐间石刻被毁之后,鉴于苏轼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与文学影响,他所书“九成台”额与《九成台铭》被毁之后,明代多次复刻。后人摹其所书“九成台”三字,一勒于符书碑首,一勒于蒋之奇《武溪深诗》碑阴。
此外,《武溪深诗》碑阴还摹有宋陈尧佐“燕誉亭”字,点画浓重,世谓之“堆墨书”;方信孺刻陆游“诗境”题字,每字长八寸,左“陆游书”三字。右跋云:“开禧丁卯正月书。时信孺丞萧山而放翁退居镜□,年八十三矣。后一年嘉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谨模刻于武溪深碑阴。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识。”
武溪本是一处穷滩恶水,经周府君及后代治理,成为交通和商贸的要道,功泽千秋。此地作为自然景观,景致奇险,又毗邻州城,为从北入粤的必经之水道。从周府君、马援、韩愈、蒋之奇、苏轼、陈尧佐、陆游、方信孺等前贤的石刻中,可见由自然开出人文,“扩而充之为文明,承而传之为教化”[22]。此仿同元结开朝阳岩,化自然景观而为人文景观。武溪自此有一主题 ,此主题不在山水,而在人文。显而易见,从东汉《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到宋代蒋之奇《武溪深诗》、苏轼《九成台铭》,虽然石已无存,但因刻石留文,后世得以踪迹古史。这些石刻文学作品不仅在传统的传抄、刊刻纸本文献之外为文明的积累作出贡献,而且体现了人物与景观的交融,表达着天人合一的美好情境。